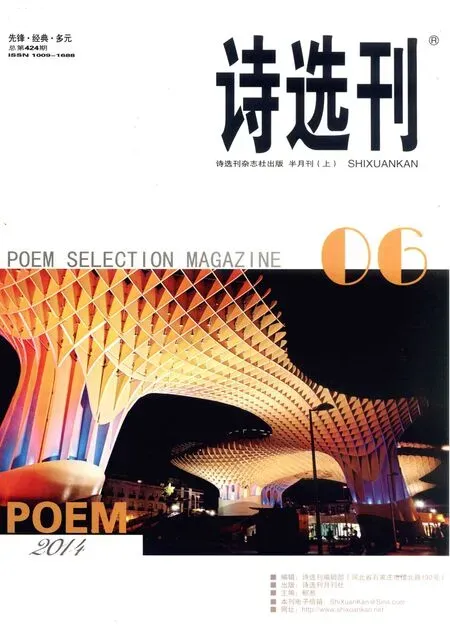被画上记号的人
2014-11-15胡茗茗
■胡茗茗
一
现在的我,一根刺都没了
疾病不会说谎,身体空空荡荡
头顶的白炽灯被旧报纸遮挡
它侧目这个三十四病床上的人
在我之前,我之后
到底谁是被上帝之手
画上黑色记号的人
钟表滴答,流水汤汤
属于我的黑夜来临
就这样卸下全部装备
只身横在隧道口前
二
跳下去吧,一个人
只能一个人,没有另外的手
没有药物和手术
没有救赎和胜之不武
只有无法放松的肌肉
不能解释的牙关紧咬绷
这半生犯下的错
被一一缝合,又见日出
我双手接引爬出洞口的我
像沙滩捧住被大海送回的漂流瓶
三
这瓶体光滑,外湿内千,声音微颤
它经由海浪、鲸鱼、虎穴龙潭的吞吐
肚子里的纸条没有人捡到
它只是被爱与不爱画上一道道记号
我捡到了我,以及岁月的印痕
就这样建立起的三角形
旋转而稳定
四
我在地上行走,神在天上行走
死亡在地下跟着
凭什么我们就能与战争、疾病
擦身而过?除了侥幸
唯有终点的不确定
一定是内心的球茎扎根太深
它向下生长诗歌,向上生长健康
我不知该取舍哪一样?
抑或是我想要的太多?
我已经准备好与生活
交换最致命的东西
曾经到达的山顶,远看依旧葱郁
我一万次地搬动脚底碎石
将一座大山,画上和身体
一样的记号
毕力斯台风
一
像迁徙的鸟儿承诺着归来
我们承诺着相互寻找
月白昼之外的语言,不可诉说的诉说
分离人群、山水和时间
可以坐下来,左手优雅,右手冰凉
可以相拥,隔衣、隔墙、隔来去无端的魅影
雷声就在三米之外,更重的乌云压下来
水流于沙硕中嘶喊,狂风抖动枯枝
我们已经身体焦煳,门扇唏嘘不止
手持钥匙之人,反复徘徊,越走越远
是什么让我们同时垂下眼帘?
天,完全地黑了下来
它完全地裹住两个发光的人
二
我看到一只白鸟,雨夜中神秘一闪
不惊慌,不空茫,而风声来了,风声再响……
现在,你醒来,我只要你醒来
鸟儿的羽毛脱落,我的白发生出
捆绑自由的铁链都不再能发出声响
我一再把你从水中捞出,一再淹没自己
一分钟可以心跳八十次,呼吸十八次,吻我八次
如果上苍给我的时间只有这些,我情愿
只用来看你
看你从前世醒来,看你复杂的眼神直至忧伤
只字不提我的湿淋淋
其实你没有地址
其实你藏于别人
三
我怀疑此刻的暴雨是否真切
怀疑双脚不在水中,而在砂石中
一直等待双手空空的一天,我要看到自己
看到燃烧
看到粉碎或者抽干,之后我将大声告诉你
还有你们:交通断绝!
交通断绝,谁想找到我都会很难,
而我轻易就能敲开任意一扇门,而哪扇门后都没有你。
所以走,只能走,不停地走,在没膝的水里走
在黑暗里走,在走里走,不停……
上帝啊,你拿走的潮湿,必以更多的温润馈我
拿走的干涸,必以更重的坚硬载我
就是把你从天上拉下,你也要答应
把我丢失的还给我
四
上帝以分离的方式制造差别,制造寻找
我们以寻找的方式保持骨骼端正,步履大方
像一张虫蛀的旧椅子,吱吱作响也要支撑
这是一匹什么样的马?什么样的芒鞋?
诅咒上帝的人——不听话的孩子,骨肉注定缺失
告诉我,当目睹了生活是如何沿着树干缓慢抵达树根
抖掉绿叶与花、遮掩与谎言
而真相要从根部走到枝头凝为露水
这一切,又该经历多少个时辰?
二十世纪的仲夏,模棱两可的黄昏
百年不遇的台风,冲刷一座陷落之城。
我们把城市命名为噩梦,把暴雨命名为晴朗
把柔软盛开的凹凸之花叫做地狱里的天堂鸟。
现在,拉紧我的手,回身后顾,你看你看——
水漫旧道,放眼一望,全是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