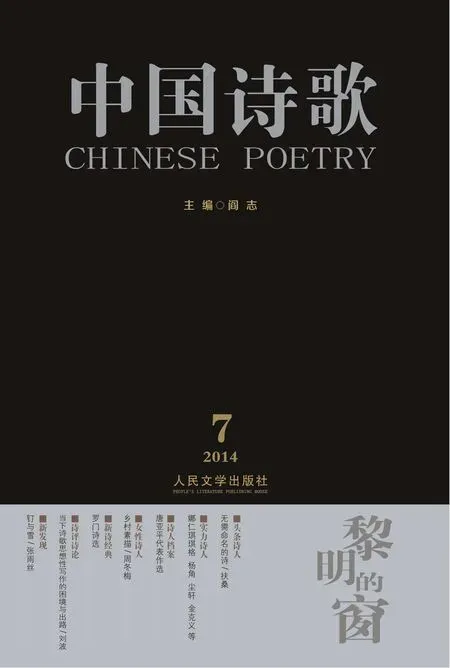诗学观点
2014-11-15韩玉
中国诗歌 2014年7期
□ 韩玉/ 辑
诗学观点
□ 韩玉/ 辑
●沈奇
认为若还认同诗歌确有其作为“文体”存在的“元质”前提的话,那么汉语新诗至今为止只能算是一种“弱诗歌”。这个“弱”的根由,在于新诗一直是喝“翻译诗歌的奶”长大的,且单一凭靠现代汉语的“规矩”所长成,故无论比之西方现代诗还是比之中国古典诗,打根上就难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且总难以摆脱“洋门出洋腔”的被动与尴尬。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性,来自这个民族最初的语言;他们是怎样“命名”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便怎样“命名”他们。而诗的存在,就是不断重返并再度重铸这最初的语言、命名性的语言。今天的汉语诗人们,要想真正有所作为,首先应考虑一下,如何在现代汉语的明晰性、确定性、可量化性之理性运思,与古典汉语的歧义性、隐喻性、不可量化性之诗意运思之间,亦即“翻译体”与“汉语味”之间,寻求“同源基因”的存在可能,以此另创一条生存之道,拓展新的格局和生长点。总结说来就是:内化现代,外师古典,融会中西,再造传统。(《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对新诗及当代诗歌的几点反思》,《诗潮》,2014年第1期)
●林宗龙
认为海荣的诗具有多维度空间,像一个多面体。他在历史、时间、自然之间穿梭,运用各种现代表现元素,将音乐、舞蹈、神话融入到诗歌的内核之中。他试着用最朴素的抒情,去挖掘生命存在的秘密,用其已知的部分与自然和世界进行一次次精神对话。这种精神对话包括三个角度。一是与自然的对话。在海荣的精神世界里,他试图在天狼星的影子中,去寻找某种与心灵相契合的自由和永恒;在宇宙这个大命题里,他用朴素的语言赞美地球母亲与人类所经历的苦难,试图去揭示宇宙在演变过程中的自然规律。二是与世界的对话。海荣的诗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他来自茫茫雪原的北方,身上散发着狼的狂野和粗犷,他站在世界的屋檐,抒情,赞美爱情,歌颂原生态的牧民生活。三是与上帝的对话。海荣曾旅居国外,在他的诗中,散发着强烈的西方的哲学意味和宗教情结。他穿梭于中西方文化之间,带着双重视角去发现存在的真正本质,探讨生与死、肉体与灵魂、时间与空间、人与神等问题。这每一次的对话过程,其实也是海荣对自我的发现和认识的过程。(《对话——评海荣的诗》,《诗林》,2014年第1期)
●叶延滨
认为当下的中国诗坛正处于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交流的激流中,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处于全球化的开放时代,呈现出空前的丰富多样的状态。在这个多样芜杂的舞台上,认真梳理一下,大致有三种主要的流向,扮演着三种主要的文化角色(这里主要就大陆地区的诗歌进行分析):第一,面对世界的外向姿态。这是中国大陆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育了三十年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之一。第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即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现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这种潮流近三十年经过多次流变而成为中国诗坛上最主要的文化角色之一。第三,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这也是中国诗坛重要的角色。这三种主要的姿态,形成了中国诗坛的三股主流,互相角力,互相影响,互相映衬,完成中国诗坛的生态平衡:只讲现代就会忽略现实,只讲当下就没有了根源,只讲坚守就不可能发展,正是这三股力量的平衡,才使中国诗坛发展成为现代的、现实的和具有传统之根的。(《叶延滨:时代永远的歌者》,《诗选刊》,2014年第1期)
●燎原
认为本时代是一个常规化的时代,当下诗歌已在潜滋暗长中形成了自身新的格局。其基本特征是:以往诗歌写作所依赖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化、潮流化的模式已经风光不再,多元化写作中的诗人们依据各自的时代感受和艺术趣味,历史性地进入到了伏藏着深层艺术景观和精神景观的文本建设之中。当下诗歌在似是波澜不惊的表象之下,实现了文本内质海底大陆架般的整体隆升。经过时代之手的深度洗牌,原先那种广场幻影式的庞大诗歌人群,早已各归其流地抽身撤离,随着诗歌核心人群的水落石出,及其艺术更新中诗歌魅力的纵深拓展与昭示,更具文化感受力的一代,又不断地汇入其中。也就是说,历经价值取向切换的震荡,当下诗坛的人群结构,已经实现了一次首先是“去伪存真”,继而是“去粗取精”的吐故纳新。具体地说,在诗歌的虚幻社会光环消失之后而选择诗歌者,必然缘之于其真实的内心需求和相应的文化自觉。他们需要通过阅读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与读者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当下诗歌现场,很少再有单纯的读者、传统意义上的读者;绝大部分的读者,都是具有相应能力的书写者。因此,事情的本质,并不是当下的诗歌失去了读者,而是广大具有表达渴求和表达能力的读者,变身成了写作者,并与既有的诗人一起,构成了诗歌共同体。(《多元化建造中的纵深景观——本时代若干诗歌问题的描述与回应》,《诗刊》,2014年1月上半月刊)
●戴潍娜
认为南歌的诗是在处处留白的古中国背景下的有历史意识的写作。西湖、嫦娥、麓山、楚国等等,都是经典的古中国想象。南歌正是在这惊人的历史感和空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他的现代诗创作。这种轻与重、漫长与空白、广阔的历史背景与尖锐的时代精神,两相对比,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充满回声的复调空间。古中国以转喻的、微妙的或是意外的方式影响着现代性的书写。一方面,中国有着最长的无中断的史学传统,另一方面,诗人可以选择栖身其中的历史造物又是如此有限。古中国回避了物质上的见证,只存在于精神意识中。当南歌恳求一朵花“在心底代替我芬芳和凋落”时,永不凋落的正是历朝文人在空旷无垠的古中国背景下所感受到的可延续的瞬间。这些瞬间被植入到了南歌现代诗歌的最中心。在她看来,深刻的历史观是一个好诗人的必备品质,而南歌对历史与时间、语境以及想象的吊诡关系都有自己清醒而明亮的认识。(《同期声:南歌、谢晓婷诗歌品评会》,《诗刊》,2014年1月下半月刊)
●刘波
认为大解作为一个默默写诗的弃工从文者,从分行文字里获得了另一条精神的通道,他写纵横的人生,也作个体的遐想,大都带有自传性质。他的最新的长诗《史记》撷取了记忆中相对熟悉的人生,以词典的形式完成了对家乡的诗性重构。在字里行间,大解以他惯常的寓言形式书写了一个地域的历史和神话,既有细节的生动绵密,又不乏整体的意味深长。我们跟随诗人走进了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村庄,它或许很平凡,很普通,但在诗人笔下,它获得了世俗之外的另一种记忆的诗学魅力。大解与村庄的对话,不是以跌宕起伏的叙事情节来制造喧嚣,他还是渴望宁静平和的表达,以求故乡自然伦理的显现。《史记》中,诗人没有以纵向的时间顺序来书写一部乡村史,而是以横向的罗列构筑出一部空间性的地域传记。虽然大解这种虚实相间的写作,在一些人看来有刻意之嫌,但这种灵魂的独语,就是在为一个村庄立传。然而诗人没有限定于面面俱到的罗列,也没有要求承载多么厚重的历史感,他的书写只求在个性的范畴里呈现微妙的诗意,让人想象,促人反思,这其实也就够了。(《诗如何为一座村庄立传——关于大解的长诗〈史记〉》,《星星》,2014年1月上旬刊)
●臧棣
认为诗歌是语言,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抵制语言。他很尊重语言的游戏性,在诗歌中,他关注的核心目标始终是语言与审美的关系。对于他来说,语言是一种感官。也就是说,他希望在自己发挥得比较好的时候,语言会成为他感知世界的一种内在能力。在他的心里,会特别警惕像“语言的惯性”这样的东西,因为它会导致一种表面的流畅。他认为现代诗歌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抵制这样的流畅,或顺畅,一种肤浅的结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诗歌写得皱皱巴巴的。现代诗歌完全可以写得充满光泽和温润,最理想的状态是达到罗兰巴特所论及的一个类似的情形:在语言中自如地滑翔。(《臧棣:诗歌就是不怯魅》,《诗歌月刊》,2014年第1期)
●霍俊明
认为雷平阳是一个真诚而朴拙的写作者,他的诗歌性格冷静而克制,孤苦而决绝。其诗像是黄昏中顽健老牛的尖角,在安静的背景之下向下向内挖掘的同时不断给人以持续性的颤动与撞击。他的诗中有很多被历史、时间、权力、政治等力量所闲置和荒废的物象、器物和空间。这些物象、器物和空间代表了一段历史性的社会和文化构造,代表了更具精神启示性和命运性的事物关联。无论是对于一条消失的小路,一座颓圮的寺庙,还是对于一条流到中途就消失的河流,诗人都在承受虚无和迷幻的过程中呈现出对于“时代废弃物”的孤独的追挽。雷平阳的真诚和朴拙使得他将诗歌视野一贯地停留在“云南”空间,但在他那里,“云南”已不再是地理学上的空间概念而是广义的城市化时代履带重重碾压下“人类童年期”剩余一角的隐喻。这一特殊的文字化、精神性空间因为带有了超越性而具有了普遍人性、现场感和生命诗学的意义。可以说,他的诗歌来自于乡土却又超越了乡土。(《用“祷辞”重建空间与秩序——读雷平阳长诗〈春风祷〉》,《扬子江》,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