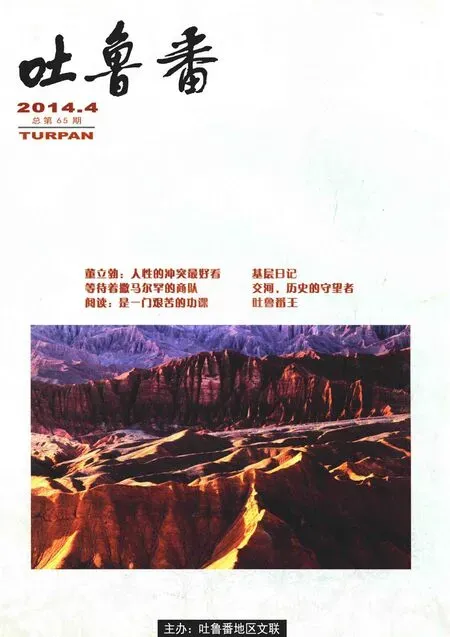董立勃人性的冲突最好看
2014-11-15董艳
董 艳
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白豆》发表在《当代》今年第1期上,并荣获《当代》文学拉力赛2003年首站赛“最佳”称号,编者的话是这样说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刊登之前,全编辑部的男女老少都传看且都叫好,已很难得;而这部把编辑部男女老少感动得刻骨铭心的西部经典,竟出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之手,就更其难得了”。4月,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紧接着的两个月内,漓江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他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烈日》和《清白》。
董立勃并不是完全不见经传,他写作多年,上世纪80年代初就因写作风格特异引起新疆本土文学界的注意,但在国内文坛寂寂无名,直到今年初“一飞冲天”,一下子成了中国小说界的一匹黑马,引起极大反响,得到了普通大众和评论界的双重认可。日前,他从北京参加完《白豆》的研讨会回到乌鲁木齐家中,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他。
努力写“好看”的小说
记者:您好!《白豆》出版后获得很多好评,在此之前,您的名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比较陌生。
董立勃:非常陌生。我80年代初读大学时开始发表作品,后来也写过一些中短篇,影响不大。最近10年几乎没怎么动笔,一直在想。
记者:想什么呢?
董立勃:我很困惑,有很多素材可以写,但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表达。小说一定要吸引人,不能吸引读者的目光,这样的小说不如不说。现在出版的很多小说,让人看不下去。我不想写这样的小说。
记者:后来怎么又拿起了笔?
董立勃:想法变得简单了,一句话,怎么好看怎么写。别的东西,不管那么多了。也就是说,写好看的小说。
记者:仅仅是“好看”?
董立勃:往“好看”方向去写,其他都不重要。这么多年没有写,写不出来东西,我反省了一下。就是把小说想得太复杂了,就像搞一个大工程,在各个方面都要达到一个高度。例如,要写得思想深刻一点,在结构上独特一点,赋予它社会学、历史学等等意义等等,其实你没有那么大本事,你做不到,也就无法完成了。不要让小说变成教科书,要去教育人,启蒙人。太多说教,已让人烦,打拼生活,也很累,这个时候,让读者拿起你的书,能轻松一点,愉快一点,就很好了,很了不起了。
记者:有评论说,《白豆》在结构上像一个拉长的中篇,是不是您把它“简化”了?
董立勃:对。长篇小说给人的印象是,一定要有复杂的情节和线索,我尽量让线索简单,人物关系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深刻的东西,在形式上往往很简单。我没有刻意地引导读者对那个时代的体制、思想发生什么思考。我捧给读者的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好看的故事,故事里到底藏着什么,让读者自己去想。
人性美最为动人
记者:《白豆》这个故事有原型吗?
董立勃:完全一样的原型是没有的。我在新疆的军垦农场出生、长大,对军垦生活非常熟悉。农场上有这样一批女性,她们有很多故事,“白豆”只是其中一个。我的母亲,我的姨姨,都有过和“白豆”类似的经历。
记者:白豆经历了苦难,但仍然美丽地活着,在她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质朴、坚强,洋溢着人性的美。您怎么看待她?
董立勃:在白豆的身上体现了我对女性的理想,甚至是对整个人类的理想。这些女性很单纯,对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提防,她们用善良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她们承受了很多伤害,几乎都是默默地忍受,但她们性格中有很固执的方面,比如对理想对爱情的追求。白豆的故事能引起那么多人共鸣,我想,很重要一个原因,她身上洋溢的人性美,是人们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它和时代,和政治,和时尚,和贫富都没有关系,只有是人,都会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记者:《清白》说的是关于“贞洁”的故事。搁在任何一个年代、换成任何一个环境,“贞洁”的散失都会带来冲突,您把这个冲突放在军垦农场里,有什么特点吗?
董立勃:“贞洁”问题带来人性的冲突、男人和女人的战争。这个冲突放在西部的荒野上,在军垦农场这么一群人当中,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本质上,没什么不同。《清白》里面有两个男人,一个有文化,一个没有文化,当他们面临贞洁问题时,处理的方式虽然不同,但对两个女人的伤害都很大。我想说的是,不管你是个什么人,不管识字不识字,都有着相似的人性的缺陷。
记者:小说里的女性不那么脆弱,而男人似乎是弱者。
董立勃:我同意你这个说法。在《清白》里头,后来穗子带着孩子回来,刘付全跪在她的面前,李南忏悔,男人全失败了。男性看起来很强大,那只是外表上的,在贞洁问题上,看起来是对女人的摧残,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最后李南被砍死在玉米地里,刘付全的腿被雷劈,都是对他们的惩罚。最后女性胜利了,是柔弱力量的胜利,是善良的胜利。世界上,好多很大的悲剧,其实不是社会造成的,而是我们人性中的弱点所致。
创作受沈从文影响
记者:您的小说语言特别漂亮,比如写白豆的美丽,“白豆从水中站起来,身上滚落无数颗水珠。大太阳把每一颗水珠变成了小太阳,无数颗小太阳,像无数颗明亮的眼睛,恋恋不舍地盯着刚用泉水洗过的白豆”。您说过您的写作受沈从文影响非常大。
董立勃:对。从80年代接触沈从文的作品到现在,在我心目中他是排在中国作家第一位的。是我的偶像。现在国内很多小说家受翻译文学的影响,用的都是欧化的语言,其实中国的语言有它独特的魅力,已经足以表达思想、情感。沈从文在30年代就已经熟练运用纯中国化的语言,有音乐上的节奏,同时画面感很强,语言干净、准确。有大师做样子,我只是跟着学,尽量让语言透明,生僻的字眼,不用,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
记者:你是不是想从文字开始,就让小说好看起来?
董立勃:是的。读者拿到一本小说,先看到的是语言,语言好不好,直接影响到读的兴趣。如果语言很败胃口的话,再好的故事也没有人去读。一部好看的小说,文字一定要好。这是起码的,基本的。
记者:有评论将您的作品归入“西部小说”,也有单列为“垦荒小说”,您对这种归类怎么看?
董立勃:从地域上讲,我生活在西部,写的也是发生在西部的事儿,大部分是垦荒题材,所以把我归为西部作家或垦荒作家都是可以的。西部垦荒,是一件伟大而悲壮的事,还表现得很不够。成功的垦荒小说比较少,我还要努力,希望能有更多作家,把目光投向西部。这里的文学矿藏,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记者:能透露一下您目前的创作情况吗?是否继续写垦荒题材?
董立勃:手边有五部已经写好了,都是垦荒题材。写的够多了,想暂时放一放。不过,以后还会再写。下野地那个地方,还有很东西可以写。这是我一辈子的事。目前打算写一部都市情感题材的小说,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影视机构跟我谈这件事,不知能不能写成。我不会勉强自己。我想,写什么题材并不重要,重要是写出好看的小说,别让读者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