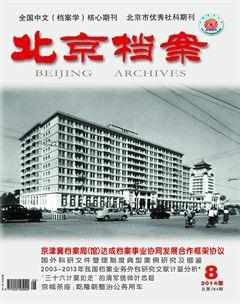沈志华 用档治史的方法与态度
2014-10-29刘晓菲
刘晓菲
摘要:现代史著名研究专家沈志华通过不断发现利用新档案,适当借鉴口述档案,巧妙利用回忆录等方法进行史学研究,揭开历史事实真相,其实事求是的原则、独立求索的精神、注重细节的态度和精密求证的学风值得我们档案人学习,其用档治史的经验也引发我们对档案利用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沈志华史学研究档案利用
一、沈志华其人其作
沈志华,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学者,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兼任社科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北大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曾是大陆史学界惟一经济完全独立的自由学者,无官方专职头衔,但就是这样一个“无名小卒”搅动了波澜不惊的史学界。其研究领域在苏联史、冷战史以及中苏关系,并花费大量精力搜集解密档案,专著、编著、参与合著十余本,拥有三百余万字著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苏联历史档案选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等;发表论文近百篇;承担近10项国家重要课题。[1]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展开的理论思路重新阐释了当代中国历史起点的一系列事件,具有巨大的首创价值。沈志华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一脚踏入档案领域,其传奇的档案人生和宝贵的经验和做法为我们档案工作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借鉴。
二、沈志华用档治史的方法
(一)不断发现利用新档案
傅斯年说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正所谓追本溯源。沈志华在其现代史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依靠不断发现新的档案。他认为利用档案,探寻历史真实,要“竭泽而渔”,全面收集资料并进行对比研究;避免“选我所用”。对比其他当代史研究者,沈志华以新挖掘的档案史料为基础,其所用原始档案,并非传统档案史料,而是未公布的一手资料。
以《朝鲜战争揭秘》[2]一书为例,沈志华利用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包括斯大林给苏联驻朝大使、私人军事代表和毛泽东的密电,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录、访谈记录、电报以及信函。此外,沈志华所用档案数量巨大,选材广泛在学术界也是少见的。单就其出版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系列,共三卷,参考档案总计700多件,其数量之多,选材之广,是该题目国内外之首。
(二)尽信档不如无档
档案文件中的白纸黑字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档案作者本身都是基于自己的理念思想来记录或“制作”档案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主观色彩。甚至处于某种需要而留下言不由衷、文过饰非、掩人耳目的历史记录。也许历史研究要求的真相是不可达到的高贵梦想。
沈志华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不是从既定和先验的结论以及概念出发,而是从档案史料入手,重建历史事实,然后得出自己的分析,这从方法论上对那些传统的党史研究套路造成了冲击。在瀚如烟海的档案史料中,充斥着大量的历史真实、内容本身失真的档案,有的是为了宣传而造出来的,并非原有档案。沈志华基于史料而又不迷信史料,能够从档案和资料中出来,尊重事实,让事实说话,避免陷入档案主义。
(三)适当借鉴口述档案
进行历史研究,不能简单孤立地使用口述史料,因为人的记忆难免会出现偏差。尽管口述史料真实性和准确性受到质疑,但是并不能就此否认其重要性。档案不是万能的,需要其他档案形式做补充。档案文献往往需要以口述史料作为补充。
沈志华并不否认口述史料的重要功能:其一,当事人的描述能够起到帮助研究者解读文件的作用;其二,没有口述档案而仅靠纸质档案,历史的链条是连不起来的,当事人口述档案可以在档案文献缺乏的情况下,填补历史链条的空白;第三,口述史料可以弥补档案文献的缺乏。[4]
除以上三点,当事人对当时的场景、语境和情况的描述,可以使枯燥呆板的档案文字所记录的历史场景更加生动活泼起来。沈志华曾用一个小故事加以说明:美国研究人员凯佩尔就将专家本人的叙述和档案文件有机结合。凯佩尔利用在莫斯科报纸上刊登广告的办法,招募30几名曾经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根据专家们的回忆,使凯佩尔加深了对俄国档案文件的理解,使得后来的描写显得鲜活生动。[5]
(四)巧妙利用回忆录
沈志华的大量论著中多次利用当事人回忆录和采访录,这是沈志华收集研究冷战国际史史料的又一个重要方法。首先,仅查阅白纸黑字的档案文献会给人不知所云的感觉。例如,俄国公布的档案,其中一份关于1956年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其内容非常简单,只有看似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如“有时强加于人”、“应该纠正缺点”、“形式匆忙作出决议”等等。[6]26日会议的记录也是让人读起来摸不着头脑,如“哥穆卡尔实在太过分了”“关于罗索夫的一点很关键”。解读这些原始档案就需要当事人的回忆来帮助更好地理解档案的内容。曾经两次担任刘少奇会议秘书的师哲,据他的回忆录记载,刘少奇在会议上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错误,并表示中国将在任何情况下努力维护中苏友好团结关系。而26日的会议记录实际上是记录了刘少奇与赫鲁晓夫的一致意见:哥穆卡尔把国防部长罗索夫从波兰政党的领导人中排挤出来是中俄两国都不能接受的。[7]由此可见,当事人的描述能帮助研究者解读文件。其次,回忆录也可以作为历史考证的途径之一。但要求研究者对回忆录和当事人的记述进行核查和鉴别,避免造成重大的历史误会。
总之,历史研究要学会把原始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以及回忆录等结合起来,二者相互考辨、相互印证、相映生辉。
(五)结合不同材料得出结论
在沈志华的著作中利用的档案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十分广泛,从国外公布的档案看,包括电报、报告、会议纪要、速记记录、工作记录、信函、文本条约、决议草案等等。“从重要性上看,这些文件是同等的;但是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要区别对待,对不同形式的档案按层级进行划分。”[8]有一些非历史专业人员写的文章或者是图书,有的称纪实、文学,不能作为史料看待,但是有些也夹杂着对当事人的采访,只是更需要研究者敏锐的眼光和考察力。“在引用重要的文献时,需要对比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因为其中的注释和正文都有可能存在着差别。”[9]
例如,我国传统观点认为,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由中国起草,苏方同意后形成最终文本,依据的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分别发给刘少奇的电报。电报作为一种原始档案,具有较大的真实性。但这两份电报只有中方当事人的说法,其说服力就没有那么强了。沈志华在俄国的档案馆中查找了大量的条约文本,其中包括1950年1月6日至22日共7次起草和修改的关于该条约的俄文文本、23日苏方交中方的俄文文本、24日中方经修改后退还苏方的译本以及31日周恩来与高扬商议条约的报告。这些文本都证明了条约最初应该是由苏方起草的,中方只是做了简单的文字性修改。[10]二者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俄国所公布的文本档案更具说服力和权威性。
此外,沈志华还大量转引国家公开和内部的报刊资料,如《内部资料》、《人民日报》等,这两大刊物不仅信息量大而且内容真实,为其研究大跃进时期的各地民情提供了史料来源。[11]
三、沈志华用档治史的态度
(一)实事求是的原则
党史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会踏入禁区或“雷区”,这就要求他们独立思考所谓的“敏感”问题,进行创造性探索。历史研究者都是历代记录者主观选择的结果。我们发现在国家利益面前,其真实性有时不得不让位于国家利益,所以有些历史事实并非档案记载的那样,特别要注意政治家、官方的结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层面的,即档案本身就是伪造的,本没有档案,后来被塞进去的;二是政治层面的,档案形成时,出于某种需要被制作和修改。所以我们常说,档案也有陷阱,档案里说的事不一定是真的,我们所说的档案真伪的判断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所以,研究者要避免掉入档案为我们设置的陷阱(形式真但内容假的档案)。
沈志华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该向古代史官一样,敢于秉笔直书、实事求是、讲老实话、讲真话。”[12]关于朝鲜战争的宣传,我国党史的阐述是南朝鲜打响战争第一枪,而沈志华根据大量国外公布的档案看,其结论正好相反。随着事实的不断揭露,沈志华推翻了以前一个个根深蒂固在我们大脑中已经形成的认识,但其底线是不触犯有可能越过的红线。所以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档案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的不断权衡。一方面历史研究不能单纯是为了政治宣传、服务于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另一方面,档案工作者要肩负起历史的责任,还公众一个个真实的历史,做到既尊重官方机构著作的话语权,又要揭开历史事实。
(二)独立求索的精神
沈志华获得史料的过程就如同他的历史和人生一样充满了传奇。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商界小有成就,凭着对学术的热爱,毅然重返学术圈,可谓是“弃商从文”。他数次前往俄罗斯收集档案史料,十几年来,奔波于美国、俄罗斯和韩国之间,来往于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仅路费和资料费的开支就高达150万。[13] 1996年至2002年期间,个人出资140万,不远万里从美国和俄罗斯收集10000多件解密档案,并把全部资料自费复印一套赠送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些档案还制作成光盘,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提条件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
沈志华远赴国外将历史档案的复印件买回进行深入研究的行为,看似是一桩具有想象力和个性的个人行为,但这是一代中国历史学家立足民间、独立求索的见证,是一种自我生成的能量,是中国学术界的活力所在。此外,沈志华通过不断学习,能够将中、英、俄三种语言运用自如,这也是他得以深入理解国外档案的基本能力。《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14]是其亲身前往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将一手的俄文文献翻译成中文编写而成,为后来我国研究者站在苏联角度研究相关史实带来了巨大的方便。
(三)注重细节的态度
沈志华进行现代史研究不是紧盯关键事件研究,而是通过国外档案馆的文件和档案反过来印证我国当代史的记录,检验二者是否吻合,利用史料资源,发掘分析出隐藏在史料背后的东西,注意细节的呈现和串联。在他的著作中,甚至有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动员问题的描述。沈志华将目光下沉,而不仅仅将关注点聚焦领导人和高层,传统的党史研究多半会将大量笔墨放在会议史上,或是着眼于政策的制定、理论的提出。而在沈志华的现代史中看到了具体的人和社会具体的变化,使得政治不是悬而又空的东西,使得读者看待历史的视角、关怀和过去有所不同。他认为:“注重档案的利用......可以从社会基层对国家政策的反应以及不同群体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来考察中央与地方、高层与基层的互动,对于决策的结果和执行具有重要意义。”[15]
历史研究要将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与沈志华所强调的“小历史”观相结合,注重宏观架构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需要以微观研究为前提,要想成功构造整体,就必须先有碎片化的研究作为基础。利用档案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就要一点点地从微观做起,由点到面,然后整合这些碎片化的点,进而把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得出较为宏观的历史判断。
(四)精密求证的学风
解决争辩和疑问的最好办法就是小心求证,而非急于斗嘴。其基础就是大量一手资料和权威的档案史料。与学术界目前所盛行的粗犷笼统的学风不同,沈志华的学术观点一直坚持建立在精密的实证基础上,他认为一份档案的公布,需要数份档案的互证。即使真正找到了几件核心的档案史料,也仍需要研究者对比参照其他现有的史料,经过认真考证和缜密的梳理之后,才能保证还原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如,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紧张。对于这段历史,国内研究者大多认为事前中方已向苏联通报了即将炮击金门的消息。一是刘晓198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最早提出这种说法;二是随后公布的1956年吕晓芙访华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记录中,也记载刘晓的观点是源于10月2日毛泽东在会谈记录中的讲话。有了这两件档案的依据与印证,人们似乎可以得出此前结论的正确性。但沈志华在后续的研究考察中发现了持更多相反观点的史料。首先是在吴冷西回忆录中所引证的1958年11月毛泽中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所印证的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二者都记载了关于炮击金门军事行动毛泽东只字未提。并且,在行动前的20多天,尽管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两位领导人进行四次会话,但也没有提及该行动。根据这些档案史料的记载,得出的结论就与传统的定论大相径庭。[16]
该案例说明了研究者在史学研究中要克服急躁的心态,在发现一件长期寻找的档案后,切记保持谨慎的态度,避免因过度兴奋、急于得出结论而草率公布结论。学习沈志华在即使利用原始档案也要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学习其仔细对比、反复考证的治史精神。
沈志华在利用档案史料进行历史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大多并不是他本人创立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是历史的传承,既有继承也有创新。沈志华的主要贡献是在还原重大历史政治事件时,做了原来主流研究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澄清了重要历史史实,更披露了一般人看不到的史料。
四、沈志华带给我们的思考
(一)学者与商人之视角
沈志华是一个从商界杀回到学界,甚至取得了比纯学界人士更大的成就,笔者认为与其所处环境和个人经历有关。他曾经在学校接受过基本的学术研究,在经过人生的磨炼后,更加懂得如何看待人生的价值和追求,因此会选择自己真正比较喜欢和更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体会探索的无限乐趣。目前,跨界和混搭这种所谓的“软连接”是文化融合与创新的一种途径,对于如何实现不同领域间的跨越也是沈志华现象带给我们的思考之一。沈志华多次往来于官、学、商多个领域的经历,有利于构建多元价值观,可使人生不囿于局限。他将商场上的效率观带入学术研究中,打破传统的研究方式。而官场也需要学术研究上的求真观,让政治更加道德透明;将官场上的务实观引入学术界,让学术界更准确地把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分寸和尺度。
(二)档案与史学之关系
档案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史料,而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档案无疑是最重要的史料,所以档案的开放和利用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原始档案资料对历史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点:一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是档案的开发和利用,历史研究的进展离不开档案的开放;二是档案依靠研究者对其内容的解读和分析来破解历史之谜。沈志华在档案开放的问题上首推俄国档案的大量解密。在20世纪末,俄国大量公布和解密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随着这些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公布,人们对冷战历史中的诸多问题有了重新和更加全面的认识,且近几年东欧地区的档案馆也为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打开大门。[17]视角回到国内,2000年以后,地方档案馆陆续开放1949年以后的档案;2003年上海档案馆首次开放50年代中后期的案卷;2004年,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社会开放。随着档案史料的不断开放和公布,极大地增加了研究者还原历史真相的信心。
(三)史学研究之方向
沈志华的成功,某种意义上将历史研究的门槛降低了,代表了一种当代历史研究的民间趋势。一是党史的研究开始渗入民间的立场;二是治史研究开始重新着重史实的梳理,让位于基础性的复原历史的工作。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就会得出与过去的历史和根深蒂固的认识不一样的结论。近年来,网络上对中国近代史或朝鲜战争全盘否定的声音甚嚣尘上,而立论者所依据的基础事实只是表面化、似是而非的。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学术界自由的争鸣,但是结论的得出必须基于确凿的事实。处在快节奏、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当代史的研究风气面临巨大的挑战,作为一名历史研究人员要转变浮躁的风气和“高端”的视角,将目光下沉,从史料着手,严格规范研究方法,重建历史事实,挖掘全面的资讯,接受严谨的学术熏陶,因此笔者认为将沈志华的思想经验总结出来,对当代史学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资队伍[EB/OL][2014-06- 18]http://history.ecnu.edu.cn/products_view.asp?id= 2179
[2]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M].香港:利通圆书有限公司,1995.
[3]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92.
[4]沈志华.历史研究与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的案例种种[J].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 01:155-174.
[5]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J].历史研究,1998,05:136-149.
[6]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2一53,54
[7]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百年潮》1997(2):13一16
[8]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J].历史研究,2003,01:156-174.
[9]沈志华: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料[EB/OL][2014- 04- 03]http://www.hprc.org.cn/gsyj/xkjs/gsyjff/ 201305/t20130515_219448.html
[10]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J].历史研究,2003,01:156-174.
[11]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02.
[12]沈志华.提高党史研究水平的关键在于实话实说[J].中共党史研究,2000,01:6-7.
[13]学术传奇人物沈志华[EB/OL][2014-04-03]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71.html
[14]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92.
[15]沈志华.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01.
[16]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J]中共党史研究,2004(3)
[17]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J].历史研究,2003,01:156-174.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