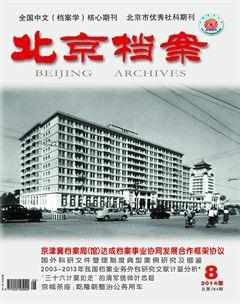实说老天桥
2014-10-29王兰顺
王兰顺
一提到天桥,老北京人总有说不完的话。自打2004年重新修建了永定门之后,仅过了九年,而今又使天桥这座历史建筑实现了“新生”。看来人们正在以复建历史文化载体的方式,搭建着发展与记忆的桥梁。
一、天桥的桥
天桥始建于何年,史无详载。早在元朝,这里是大都的南郊,为一片水域沼泽地带。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修建了天坛后,在元大都中轴线的延长线与城外河流的交汇处建起了一座单孔拱桥,以通“御路”。桥用汉白玉石料砌成,桥面用石板铺就,桥长约8米,宽约5米,桥基呈八字形,桥身东西两侧各5根栏柱,桥孔券洞上雕有螭头以镇水。在石桥两边各搭一座木板平桥,中间的石桥平时用木栅栏封挡,专供皇帝祭天时坐轿通行。可见这座石桥当时纯属礼仪用桥,而不是交通桥,除了皇帝其他人只能走木桥。
明嘉靖年间,为防御北方蒙古族的侵扰,将北京城“南扩北缩”,加筑外城至永定门一线,过去的南郊地区被圈在了外城里。为建造外城的城墙,明朝的统治者命人将那里大片的水泽填平,但因地势低洼,那里仍是一片易于积水的地带。而一遇到旱季,这里地面的浮土遇风则起,严重袭扰环境。
到了清雍正年间,天桥正式得名。而这里的环境并未得到改观。据《清会典事例》记载:“雍正七年谕,正阳门外天桥至永定门一路,甚是低洼,此乃人马往来通衢,若不修理,一遇大雨,必难行走。……天桥起至永定门外吊桥一带道路,应改建石路,以期经久。”
直到乾隆五十六年,在这里修渠以后,使这里的环境大为改观。乾隆皇帝也对他晚年的这一力作倍感欣慰,亲自题写了《正阳桥疏渠记》,刻在方碑上立于天桥桥头的东侧。碑文中说的都是天桥以南的事情,可题目却是“正阳桥”,可见乾隆把天桥看做了“第二正阳桥”。
《正阳桥疏渠记》大意是说,天桥至永定门间为一条石板路,石路两侧地势东高西低,以致路西常年积水,而路东积沙又常因西北风刮到路西,堆壅了先农坛的一半坛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天桥以南平行石路两边各开挖了三条水渠,又在石路两侧各修筑一条土路专供行车。挖渠的土,一部分筑路使用,其余在渠边堆成土山,上面种植树木。渠中的清水改善了城南的饮水质量。在碑文中赞美道:“……于是渠有水而山有林,且以御风沙,弗致堙坛垣,一举而无不便……胥得饮渠之清水,为利而溥。而都人士之游涉者,咸谓京城南惬观瞻,增佳景……”又说,修渠筑路以后,可以“洁坛垣而钦毖祀,培九轨而萃万方,协坎离以亨既济,奠经涂以巩皇图”,更赋予了强化皇权形象的意义。可以说,这是一次集疏导交通、防治风沙、改善饮水、美化环境、彰显礼制的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乾隆皇帝又把乾隆十八年立在永定门外燕墩上《帝京篇》的方碑再刻了一座,立于天桥桥头的西侧。这样,天桥桥头的东、西两侧就有了两座尺寸、形式完全一致的石碑,形成了一河、一桥、双碑组合的格局,而这种格局恰好符合古代都门制度的形制。
而到了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在刚刚平息了以林清为首的天理教事变之后,有人说天理教“作乱”与乾隆时疏浚天桥河渠,破坏了清廷的风水有关。又因为当时天桥地区多酒肆、茶馆、戏园,是商贾外来人员聚集之地,难于管理。天桥至永定门的河渠直接连至外城护城河,二十余丈宽的河渠加上沿岸的树荫及城门水洞等,都容易出现防控的漏洞。于是清王朝下令“湮河流,填土入之”。
道光十二年(1832年)北京遭遇特大旱灾,天桥下面的河水几近枯竭。同治十三年(1874年)北京再遭旱灾,河床干涸。光绪二年(1876年)由于干旱,天桥下面的河床被摊商利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整修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将路上原来铺的石条一律拆除,改成碎石子的马路,天桥高大的桥身拆掉后,改建成矮矮的石桥。重建后的天桥开始了人车混行。1927年,由于铺设有轨电车轨道,将天桥的桥身修平,两旁仍保留石栏杆。1934年拓宽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将天桥两旁的石栏杆全部拆除。”桥基被埋入地下,天桥从此匿迹。
关于《正阳桥疏渠记》与《帝京篇》那两块方碑的下落,著名史地民俗学者张次溪在其《天桥一览》序言中记载:“闻父老言,桥之两侧,旧各一亭,内有方石幢一。咸丰年犹在,至同治,其一移桥东某寺。又一置桥西斗姥宫,至今尚存。迄光绪间,仅余二亭之三合土基址而已,今则并基址亦渺不可寻矣。”
在张次溪先生所指的桥东某寺就是红庙街老门牌14号的弘济院中保存的一幢石碑——正阳桥疏渠记碑。又据北京市档案馆藏《外五区弘济院僧智峰关于登记庙产请发寺庙凭照的呈文》中,寺庙法物登记条款上明确记载有“汉白玉石幢一座,高约二丈方约四尺,系清朝乾隆五十六年所建。”与正阳桥疏渠记碑的形制、纪年相吻合。
张次溪所提到的天桥以西之斗姥宫现已不存在,据民国《晨报》记载:“先农坛石幢,旧在前门外天桥西路北之斗姥宫内,因便于保存,乃移至于先农坛外坛之坛墙下。后外坛拆除,古柏地亩皆标卖,乃又将幢石迁移于内坛。”斗姥宫的石幢移至先农坛内坛东北角保存后,幢顶、幢身、幢座,被分别拆卸,散倒于地。新中国成立后因久历风尘,被深埋地下40余年。2005年初,该幢在先农坛北坛门附近的京青食品厂院内重见天日,现置于首都博物馆东北侧广场上。
由此可见,现首都博物馆前的乾隆御制碑与天桥东侧红庙街老门牌14号弘济院的正阳桥疏渠记碑,确是原立于天桥南端两侧碑亭之内无疑。这对石碑是清代中后期,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建筑景观。
二、天桥的水
天桥下面原是一条沟通北京内、外城的古河道。它源自双塔庆寿寺东面的水涡,向南流经双道栅栏流向北新华街尽头的内城城墙水闸,与内城护城河相连后继续向南,经南新华街流经虎坊桥,向南不久折东,流经永安桥,屯于苇坑(南纬路以北、永安路与曙光路西端以南,在元、明、清时为一片水乡沼泽);而继续东流,沿先农坛北墙流经天桥,屯于金鱼池,再沿天坛北墙东流,经红桥转向东南方向,经过四块玉东侧的龙须沟,流向左安门附近;在位于康家园位置的外城墙闸口出水,与外城护城河链接。
而天桥以南过去也有水域。那就是乾隆五十六年,在明朝建外城城墙时被填平的那片水域上重新开挖的河渠,这道河渠进一步沟通了天桥地区南北方向的水流。在此工程中,以疏渠之土作为渠岸之山,并在渠旁植树,形成树林,以御风沙,且在河渠里栽种荷花,因而将这一地区改造得渠清柳绿,景色盛极一时。
嘉庆五年(1800),有诗《天桥春望》曰:“种柳开渠已十年,旧闻应补帝京篇。天桥南望风埃小,春水溶溶到酒边。明波夹道且停车,人为临渊总羡鱼。尘外千树柳,随风绿到第三渠。城南车马太匆匆,坛树云返照红。几个闲人临水立,任他疑作信天翁。”还有诗云:“桥头新水活粼粼,桥外高楼聚酒人。酒人漫说登楼好,春衣且步沿溪草。碧瓦朱棂护泾云,千重坛树波光绕。……清漪夹道苍烟暮,指点游人垂钓处。……桥下水为当日无。”从其诗词中可见天桥地区的动人景色。
而到了嘉庆十八年,为了肃清天理教的残余势力,又有碍于风水一说,使得靠近永定门的河道被填埋,因而天桥地区的水不能直接向南流至永定门导入外城护城河,使附近的自然风貌又开始改变,碧波荡漾、红莲映日、杨柳依依的景色不复存在。由于这里的地势低洼,一到雨季便容易积水成灾;入夜后,蛙鸣不已;明沟秽水,臭气熏蒸。
民国六年(1917年),人们削平了这里的土地,修筑了南、北土路。在先农坛的东坛根下凿池引水,种植稻米并栽种莲花,开辟了水心亭商场;到这里开办茶社的有环翠轩、绿乡园,开办杂耍馆的有天外天藕香榭,开办饭馆的有厚得福。同时,人们拓宽河道并修筑长堤,在岸边种植杨柳,使这里又有了红莲碧稻,波光粼粼的景象。可尽管如此也无法与乾嘉之际宽阔浩淼的河渠相比。而在民国九年和十年,天桥接连三次遭遇大火,水心亭市场一带火势尤为猛烈,以至于不能复修。
到了1920年至1924年北京进入大旱期,天桥一带的水域大幅度缩减,再次露出大片空地。到了1928年至1930年北平再次遭遇大旱期,使天桥一带的河面基本干涸。尽管如此,为了防御天桥地区的旱涝起伏不定,1931年7月,北平市工务局还是启动了“修永定门至天桥土明沟及砌涵洞工程”。
1934年,为展宽马路,天桥的形态彻底消失。1935年至1936年又是北平的旱期。失去了水的天桥,少了几分雅致,也没有了灵气,却增加了许多平民,多了一些嘈杂,多了几分民俗。而失去了桥的天桥,后来仅作为地名被保留下来。
三、天桥的路
由皇帝祭天出入的天桥,到成为平民百姓的聚集地,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水退却了,陆地大了,人聚集多了,这时就会感到交通的不畅。
清末民初,为了溥仪祭天的需要,市政当局修建了天桥南大街,将马路附近的空地进行了平整,驱散了天桥的自发市场,结果造成了天桥地区的萧条,后经过商户与市政当局的协商,天桥地区重新招商。
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十五日,天桥至永定门的马路开工建设。据档案记载,这次展修马路“共计长四十三丈九尺、宽三丈”。拆去了古时候的石板路,填平了旧路的坡度,用汽碾走轧,在路两旁栽立石牙,在路上铺上四寸九分厚的石渣,并做到十分坚实。
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七日,北京电车公司致函京师警察厅步军统领衙门,由本年十一月起开始建筑天安门至天桥的电车线杆,请求京师警察厅步军统领衙门转告各区队,使所栽立的电车线杆得到保护。此次栽立的电车线杆长约二千五百公尺,实行双轨制。
1929年,因有轨电车行驶不便,就将天桥的桥身修平,但两旁仍有石栏杆。1934年,为展宽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就将天桥两旁的石栏杆全部拆除,天桥的建筑形态不复存在。
1946年5月,北平市工务局清除了天桥南大街两旁的秽土,并在道路两侧修筑了花池。
1954年,天桥东一巷北坛根至法华寺街道路施工图纸上交,由此拉开了将天桥向东的河道改造为道路的施工工程。
通往天桥的路畅通了,却颠覆了天桥一带样貌独特的泥土气息。后来,天桥修建了汽车总站;再后来,由交通带来了人口聚集、环境混乱、令人堪忧的治安状况,直到市政府下决心对天桥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拓宽后的天桥至永定门大道,就像张开的双臂,不断延展着流动的旋律。
四、天桥的乱
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开始,天坛的西坛根和北坛根,先农坛的东坛根和北坛根就有一批社会底层的流动摊贩聚集于天桥一带,形成了贩卖日用百货和食品的自发市场。由于市场是自发形成的,政府不向这些市场的摊贩征税,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市场的迅速扩张,使得一些茶馆酒楼相继在此开业,不久在天桥东侧又形成了一个贩卖鸟类的鸟市,天桥西侧则形成了一个金鱼市场。
除了自发的市场,天桥地区的十余所庙宇内定期的庙会也对整个天桥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每逢庙会,舞狮、中幡、秧歌、摔跤等民间技艺竞相上演。
民国以来,由于水系逐渐枯竭,腾出了大片无主空地,天桥开始建戏园和平民市场,使这里成为“五方杂处,百商集”的环境。贫民窟、自由市场、茶园、戏棚、摊商、卖艺的、嫖娼的、赌博的、贩卖毒品的随处可见,所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和百样吃食”就是对天桥地区的形象描写。
由于天桥市场出售的日用百货和小食品价格非常便宜,受到社会底层市民的欢迎。还有一些江湖郎中,在天桥出售自制药品,兼提供拔牙、修脚等简单的医疗服务,由于价格远比正规医院和私人诊所便宜,因而也形成了天桥市场聚集人气的一大特色。
可是由于管理混乱,导致天桥地区的刑事案件频发,从1920年起,京师警察厅不断接到在吉祥茶园打架、天桥市场中有恐怖表演、摊贩之间互不相让摊位而造成的扭打事件。
又由于天桥游人众多,影响范围大,北洋军阀政权、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政权将天桥设立为刑场,地点在天坛二道坛门的空地上。从1926年至1936年,镇威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司令部军法处、军事部军政署军法司、京师警察厅大兴县、陆军军法裁判处等机关都在天桥枪决过所谓匪犯、案犯,遂有了“上天桥——挨刀去”的歇后语。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也是在这里被杀害的。
从1931年至解放前夕,外五区警察局不断贴出因穷困潦倒,饥饿而死的倒毙无名尸首请领验的告示;又不断接到流氓聚赌、暗娼甚多、售卖毒品情形的报告,甚至还有巡警警官、警长受贿的检举信函。
1946年,北平市政府有碍于天桥一带混乱的市容环境及社会治安状况,决定对天桥一带的棚户区进行迁移改造。1948年,又对天桥以南的空地进行了造林美化。
尽管如此,天桥地区搅在一起的乱局,仍成为落在这片城市上的一块顽疾。解放后,天桥地区仍然是治安状况最复杂的区域。
五、天桥的艺
民国年间天桥地区曾经是北京最大的市井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天桥撂地表演,流行于中国北方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在这里都能找到。
1924年,由于修建和平门外大街,原本在海王村举办的厂甸庙会曾经与天桥市场合并,由此在天桥地区逐渐形成了以百样杂耍、小食、低档日用消费品为主的综合市场。这个时期,出现了所谓“天桥八怪”,成为天桥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们的表演成功及绰号的获得,标示着观众的认可,也标志着这些艺人融入了由街头艺人群体所构成的一类社会。天桥的百样杂耍表演已成为该地区文化及北京社会底层市井文化的一个标志。
旧时的天桥,沿袭了平民市场、贫民区以及逐渐形成的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每天都有武术、硬气功、摔跤、杂技、盘杠子等“撂地”表演的摊子,这些“把势”大多先是嘴上滔滔不绝,等到把观众吸引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时候,才肯表演真功夫。所以就有了“天桥的把势——光说不练”这句歇后语。
当时在天桥的各种表演非常迎合底层市民的欣赏口味,其中有评书、相声、评剧、梆子、大鼓书等曲艺节目,也有洋片、魔术戏法、训蛤蟆等表演。
从北洋政府时期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天桥民间艺人表演日趋成熟的黄金时代,大金牙、云里飞等人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同时新世界游艺园等现代游艺设施的兴建,不仅提高了天桥地区的整体品味,同时也使天桥进一步成为了北京城的娱乐中心。
在天桥文化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戏棚。当天桥撂地卖艺的艺人积攒一定收入后,便会组成自己的戏班并兴建戏棚,在固定场所演出。天桥的戏棚最多时达到了三十余家,这些戏棚大多以芦席、铁皮板等为主要建筑材料,堆土为台,戏棚规模有的可容纳七百到八百人左右。京剧名角荀慧生、评剧名角新凤霞都是从天桥戏棚中走出去的艺人。他们为了生存各施绝技、互相竞争,使许多民间特艺得以保存和发展。
而在天桥谋生的多数艺人并非出自艺人世家,他们是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流动的结果。不过,聚集在天桥的艺人无论在外表上或在骨子里都沿袭了民间艺人、江湖艺人的讲义气、敬拜祖师爷、豪侠放任、遵守行规及禁忌的习性,而他们为维持生计的凄苦以及对于身心的折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1937年3月,北平市警察局曾发布关于取缔天桥卖艺男女、常作惨苦身体工夫、戏棚演戏语多猥亵、小疯子演唱过于浪漫及禁演“赛金花”戏剧的训令。
到了日伪时期,市井萧条,百姓生活水平下降,以杂耍和娱乐业为主的天桥也受到了冲击。这时候惨淡经营的尚有天桥贫民窟的爱邻馆、天桥影院、吉祥影院、天桥茶社、天桥德盛轩、新民茶社以及天桥市场内开设的临时小电影席棚。
日本投降时天气较热,人们在天桥南侧搭席棚卖瓜品,为游逛天桥的人提供纳凉之处,同乐马戏团也在这里表演马戏,一时间较为热闹。天桥这边的曲艺场所虽有起色,但常有国军在茶园里听戏不购票,更有一些地痞流氓,为敲诈、勒索而踢场子的现象。可以想象那些艺人为了生存而承受的生活压力。当时天桥电影场所的秩序较为混乱,先后有天桥、中乐、新民等影院开张或歇业。而不久受到国共内战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天桥再次遭到打击。
1949年后,新的北京市政府对天桥进行了整治,清理了市场中的黑社会组织,同时对撂地艺人的演出内容提出了管理规范,禁止了一些内容的表演。1954年至1959年,天桥剧场进行了改扩建,使这里成为演出电影、戏剧、戏曲的场所。
1957年,天桥市场虽然修建了铁罩棚,而天桥的艺人们已大多不在这里聚集,他们有的改行,有的成为文艺骨干或运动员。后来又由于反右运动的爆发和三年自然灾害等原因,天桥市场在多方压力的共同作用下自动解散了,从此代表天桥地区市井文化的载体消失了。
六、天桥的魂
解放后,天桥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6年自然博物馆开始筹建,占用了这里的大块土地,使北京增加了一块科普园地。
公私合营后,天桥传统民俗娱乐业已渐渐远去,余下的工、商业氛围成为这里的主力军。当时尚存的有天桥木材市场、天桥菜市场,后来又有了以天桥为品牌的企业,如皮鞋厂、胶印厂、帽厂等。其中,一直存活下来的天桥商场(后称天桥百货商场),在1958年大跃进时尤为活跃,先是市委领导彭真召集商场的职工进行座谈,不久,天桥百货商场被树为“商业战线红旗”的称号。改革开放后,天桥地区统一建设了商业服务中心,天桥百货商场成为了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又成立了天桥投资开发公司,继而天桥股票获得上市。在这种商业氛围的带动下,天桥地区的宾馆、旅店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而天桥的传统民间娱乐业,仍在人们的魂牵梦绕之中。可此时的生态环境早已是换了人间天地,人们尝试着成立天桥魔术小组,但技不如人,最后不得不撤销。后来成立的天桥民间艺术小组,虽然也曾到日本进行演出,但最终没有得到发展。1992年,合资经营的“天桥乐茶园”获得立项,又在2000年后被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收购,现为德云社的大本营。
据说,1992年,曾有建天桥演艺区的计划,“但因人口密度大及经济原因的限制搁浅了”。直到天桥地区启动了拆迁改造工程,一时间天桥搬家公司的生意火爆。
此时,人们带着能否恢复老天桥味道的复杂心情,对此有所期盼。可经过改造后,基本摧毁了人们心中的那份记忆,保留下来的仅仅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地名,人们感叹道:过去的天桥真的翻篇儿了……
而接下来的是复建永定门,直到新复建的天桥亮相在世人面前,似乎又让人看到了展现天桥历史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的希望。可随着时代的变迁,想要复兴天桥的文化就不像修建剧场那么简单了,在环境改变和观众欣赏品味的变化中,想要结合时代来传承民俗艺术,确实是要面临较大的考验和挑战。
几十年的时光流逝,天桥一带的景象已与过去迥然有异,对前人留下来的历史形态,如何才能懂得善加利用,而不走弯路,少一些失望和遗憾呢?天桥样貌独一无二的土地,又是城市个性文化发展的源动力。怎样才能保持并传承它的历史形态与文化形态,成为人们共同思考的课题,而这个课题更需要这座城市的管理者和专家学者们注入更多的智慧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