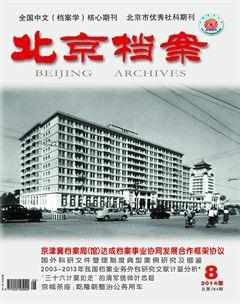从贝满女中看近代北京的女子体育
2014-10-29童萌陈希
童萌陈希
体育是整个近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子体育更是此中的关键。随之而来的身体观、性别观等思想意识的变化与卫生健康、社会结构等其他领域发生联动效应,推动整个近代化车轮的前行。
近代中国的女子体育发端于学校,而近代学校又肇始于基督教。办学是基督新教在华传播的重要方式,传教士试图通过教育事业融入中国社会,并期望藉此在华广传福音。女子学校是基督教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不仅在于促进了中国女子体育的近代化转型,更在于对近代中国女性解放的积极推动。北京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而成为近代中国的焦点地区,贝满女中是脱胎于公理会在京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在多所近代女校中最为典型。
本文将以贝满女中和公理会档案为基础,通过分析贝满的案例一窥北京女子体育的近代化进程。由于贝满的校名在各方档案中有多种记载,本文采用约定俗成的“贝满女中”进行讨论。
一、贝满女中及其体育
1.学校的建立与发展
1864年春天,美国公理会第一位赴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遗孀贝满夫人(Eliza J. Gillett Bridgman)在北京灯市口创设蒙学性质的“贝满女塾”(Bridgman School),开启了百年贝满的历史。[1]作为近代北京的第一所女子学校,贝满女塾在初创时期并不顺利,只有通过免除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来吸引无力抚养女儿的人家把孩子送到这里,直到1869年时的入学人数也只有16人[1]。继公理会之后各差会陆续在京开办学校,规模和影响力也不断扩大。1892年,走上正轨的贝满开设四年制中学班,正式开始了“贝满女中”的历史。1905年,贝满增设大学课程,成立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由于学生人数增加,协和女大于1916年从本部移至临近的佟府,贝满成为专门的四年制中学。
1922年,美国公理会成立在华董事会并交付学校行政权,聘协和女大教授管叶羽为贝满的首位华人校长。管叶羽出任贝满女中校长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他将原来的二二学制改为三三制并取消了宗教课,还提出“敬业乐群”作为学校的校训。1927年经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贝满女中正式纳入全市教育体系之中。至 1936年,贝满女中已有初中十班,高中六班,教员32人,职员11人,学生626名。抗战期间,贝满女中被日伪政府接管并更名为市立第四女子中学,战争结束以后恢复原名。1948年,贝满已发展至高初中共18个班,学生达到史上最多的964名,教职工69人。[2]北京和平解放时,贝满女中校友、我国首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王琇瑛出任学校董事长,语文教师陈哲文任校长。
1951年5月1日,学校改名“五一女中”。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市教育局、卫生局和民政局分别接办了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滞留的外国传教士陆续撤离。1952年9月,五一女中更名为市立第12女子中学,正式结束了教会办学的历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此后,女12中于1968年改为男女生合校的“红卫中学”,1971年定名为北京市第166中学,至今仍然是北京市著名的示范性中学。
2.体育锻炼和教师队伍
贝满女中的体育锻炼大约发端于19世纪90年代。在1892至1893学年,“体育锻炼成为必修项目。尽管遇到了部分学生的抵制,但学校安排了多种形式的锻炼,教师们希望这可以成为学校的特色。”自此以后,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逐渐成为专门的课程,并由外籍教师指导。美国女传教士欣曼(Hinman)来到贝满后,每天为学生上一次体操课,即使在冬天也不例外。李教士(Bertha P. Reed)和范教士(Mary E. Vanderslice)也曾为贝满女中及协和女大上过体操课。在贝满建校50周年的纪念典礼上,学生们还为来宾和校友展示她们的体操练习成果。[3]除体操外,其他锻炼形式也逐渐常规化。1913年起,明教士(Louise H. Miske)开始训练学生打篮球和网球。当年冬天,老师们即组织了贝满女中与协和女大的篮球比赛,协和女大最终获胜。此后,学校各班篮球队经常进行比赛,还组建校队与外校切磋。冰心就读贝满女中时即入选了校篮球队,除平日练球外,“还组织篮球队到通县同美国的女生篮球队进行比赛。”[4]学校的运动场所也日渐专业化,从最早的操场,到专门的运动室,甚至还曾计划建立室内体育馆。
在政府立案以后,贝满女中的体育锻炼成为定制。到1935年时,学校常设两名专任体育教师,其中一人从大学毕业,一人从体育专科毕业,每周保证15课时的体育课。[5]除体育正课外,每周还安排两次必须参加的课外体育锻炼。各年级学生按兴趣和特长分若干队,每队设队长一名,在其带领下练习篮球、排球等项目。[6]到抗战结束后,课外锻炼时间已扩展到每天下午,内容也增加了射箭、武术、田径等。[7]为了使体育锻炼在学生中普及,学校尽量添置各种运动器材,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为更好地管理学校体育事务,贝满女中还组织教师成立体育委员会,安排专人指导初、高中各个校队,并为球类及田径赛等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学生也在自治组织“学校市”中附设体育股,在体育委员会的指导下参与管理学生的一切体育事宜。[8]
3.体育成就
1916年,汇文、清华、协和三校发起体育对抗赛,开创了北京校际比赛的先河。1917、1918年高师取代协和加入三校对抗,1919年在此基础上成立北平市中等以上学校体育联合会,邀请各校参加,即北京市运动会及市际球类、游泳、滑冰赛的开端。[9]几乎与此同时,贝满女中开始在每年春、秋两季举办为期三天的全校运动会,初、高中分别进行田径赛和球类比赛,还有以年级为单位的团体操表演穿插其中。在平日间,还时常举办班级间的排球、篮球、垒球和拔河比赛等。
由于多年的体育锻炼和比赛积累,贝满女中的体育水平在北京市、华北地区、甚至全国都处于前列,篮球、排球、田径等项目的实力在女子中学中一度居于首位。在北京市运动会上,贝满女中是团体和个人冠、亚军的常客,还时常以优异成绩刷新各项纪录。1928年,在首次增设女子组比赛的第十三届华北运动会中,由于贝满女中的刘文汉等优秀运动员没有参加,使得比赛成绩甚至不如前一年春季进行的北京市运动会。[10]1933年的北京市春季运动会,贝满包揽了初、高中总分第一名。
贝满女中的体育健将都能够体、智均衡发展,她们毕业后大部分都考入燕京大学等名校,当时较著名的有肖美贞、方纪、方絪、寇叔勤、沈崇寄、李保贞等。代表中国的国家队中也不乏贝满学生的身影,曾为新中国第一批女篮国家队队长的著名篮球教练周懿娴就出自贝满。而早在1923年日本召开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贝满女中就有两人代表中国参加了女子排球比赛。
二、近代北京的女子体育
1.学校女子体育的发展
整体而言,近代北京女子体育的领军者是基督教女子学校。除创建贝满女中的公理会外,其他差会也先后设立女学,并在其中开设各种体育课程。如美以美会的慕贞女中,始建于1872年,田径、篮球、排球的整体实力均十分出色;长老会于1970年建立的崇慈女中,曾涌现出名噪一时的篮球健将魏莉。
在女子体育发展的大趋势下,清政府于1907年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将体操列为各级女校的必修课程。民国政府对女子体育更为重视,于1929年颁布的《国民体育法》第一条即说明,“中华民国青年男女有受体育之义务,父母或监护人应负责督促之。”又在第六条规定,“高中或与高中相当以上之学校,均须以体育为必修科。”与之相呼应,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于1917年设立体育专修科,为包括女校在内的所有初等、中等学校培养教师,并于1921年开始招收女生。
到抗日战争前,北京的学校女子体育已日趋成熟,不仅在基础教育中成为各级女学的必修课,更成为女子高等教育的重要专业。其时著名的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即设置体育专修科,至抗战开始前共办五届,培养出百余名女体育工作者。其中彭静波在1928、1929年两届华北运动会上获得个人总分第一名,毕业后被校友、市立女一中校长朱启明聘请为体育主任。1930年前,女子文理学院体专学生曾多次在各级运动会上获得佳绩,北京市参加华北、全国运动会时,一些项目的代表队基本以该学院为中心。
2.公共女子体育的发展
在学校女子体育事业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北京的公共女子体育也悄然兴起。1923年,北京女青年会举办第一次北京女子联合运动会,地点在北京第四中学。运动会的内容较简单,以集体操、集体舞等表演性集体项目为主,优胜者奖一支银盾。两年后,召开了北京第二次女子联合运动会,情况与第一次大体相同。北京市运动会也逐渐将女性纳入进来,除鼓励男女运动员同场竞技外,还将女子体操列为赛前表演项目,以展现她们的风貌。
抗战胜利后,以北京市运动会为代表的公共体育事业继续发展,形成以田径赛为主体,各种球类比赛相辅的赛事制度。每次比赛女运动员都分为高级组(大学、社会团体、成年个人)、中级组(高中)、初级组(初中)和小学组。但有时因报名人数少,高中生成绩又常比大学为好,所以将高、中两级合并为公开组。此时的女子运动会不再是贝满女中或女子文理学院一枝独秀,慕贞女中等学校逐渐赶超了传统强校。如1946年的春季运动会,慕贞女中以总分53分力压第二名贝满女中。当年的秋季运动会,慕贞女中又在女子公开组获得49分,以超过国立北平体专8分而险胜。
尽管直至解放前,北京的女子体育事业始终围绕着学校进行,但声势日大的地区和全国性运动会已然对社会各阶层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近代女性的身体观,从思想层面上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
综上可知,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近代北京的女子体育事业蓬勃开展,在战火和动荡中步入正轨。其迅速的发展得益于基督教、政府和知识分子等几方力量达成的共识,即女子体育的发展绝非为了竞技,而是帮助中国女性从身体和心理两个层面成为健康的人,最终达到全面解放。贝满女中创立体育课时就认为,这“不仅是完成了规定的锻炼,更对女孩们的健康有确实益处。”[30]除引入西式体育锻炼外,贝满等基督教女学还大力推行放足,并努力增设体育场所,将女孩从闺房中带到户外,使她们拥有更为健康的体魄。“曾经迟缓木讷的女孩们被户外运动注入了热情,她们的身体变得优雅而充满活力。”
当然,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近代女性需要克服积累已久的传统观念。冰心在代表贝满女中与美国女学生比赛时就发现,贝满的“篮球队员们都穿着竹布上衣,青色的裙子,到球场上一看,比赛的对方,队员们全都穿着紧身的上衣和短裤,无疑比穿长裙的中国队员灵活多了。”但是积极的进步亦不能忽视,正确的身体观逐渐形成,与此相伴的还有人际交往和竞争等健康的心理意识。在1947年北京的秋季运动会上,慕贞女中派出了以西洋乐队为主体的拉拉队,用悠扬小调为本校健儿加油。她们甚至与育英等男校拉歌:“上山流水希里里里里里里,下山流水哗啦啦啦啦啦啦。”这动听的歌声传达出的正是她们健康向上的心理,女性解放的大门已经随着近代化的进程慢慢打开。
参考文献:
[1]左芙蓉.基督教与近代北京社会[M].成都:巴蜀书社, 2009: 55.
[2]李铁虎.民国北京大中学校沿革[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7: 200.
[3]冰心.我入了贝满中斋[M]//卓如.冰心全集:第七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5:518.
[4]卓如.冰心全传: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58.
[5]私立中学体育教员统计表[M]//韩朴,田红.北京近代中学教育史料:上册.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 1995.
[6]吴廷燮.北京市志稿:文教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1:73.
[7]黄亦平,李爽麟.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家——缅怀贝满女中管叶羽校长[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
[8]李爽麟,蒋雯.贝满女中[C]//北京文史资料精华:杏坛忆旧.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文员会.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306-328.
[9]吴逸民.漫话旧京东城的现代体育运动[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四十四辑.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9:145-146.
[10]刘然.第十三届华北运动会[C]//北京市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北京体育文史:四.内部发行, 1989:121.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