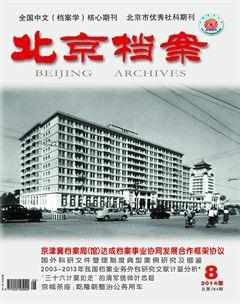“三十六计莫如走”的清军统帅叶志超
2014-10-29哈恩忠
哈恩忠
1894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打响,战场上清军接连失利,消息传回,国人一片哗然和震动。诗人、外交家黄遵宪悲愤交加,提笔写下《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降将军歌》等诗文。在《悲平壤》诗中痛言:“三十六计莫如走,人马奔腾相践蹂。……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诗中勾勒战场情状,以讽刺清军统帅叶志超。
叶志超是何许人?相较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叶志超或可说流于无名,而实际上,丁汝昌执掌北洋海军,叶志超则是入朝清军的陆军统帅。叶志超是淮军将领,字冠群,号曙青,安徽合肥人,早年曾随刘铭传镇压捻军,赐号额图浑巴图鲁,深得李鸿章赏识。1889年(光绪十五年),升任直隶提督。1894年6月3日,清政府应朝鲜国王之请,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部2400余人前往朝鲜,协助镇压朝鲜东学党起义,从而使叶志超与甲午战争“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
心无斗志,成欢首战失利
叶志超率部进入朝鲜后,觊觎朝鲜已久的日本终于找到了借口,先后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任和保护侨民为名,派出400余人的海军陆战队和8000余人的混成旅团,占据汉城至仁川一带的战略要地。日本海军则派出8艘军舰,控制了釜山和仁川港。一时间,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笼罩着厚厚的战争云霾。7月14日,鉴于形势日趋紧张,清廷令“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驻,以期迅赴戎机”,叶志超率部驻扎牙山。25日,日军在丰岛偷袭清军,运输船“高升”号沉没,导致清军的援军和火炮迟迟没有到位。27日,鉴于牙山与天津的海道联系中断,加之牙山滨海地形开阔不利防守,叶志超遂决定留一营驻守牙山,聂士成率部移驻牙山东北五十里的成欢驿,叶志超则驻扎成欢南面的公州,同时等待援兵。29日凌晨,聂士成所部在安城渡与日军前卫部队发生激战,这是中日两国陆军的初次接仗。随后日军的增援部队到达,以炮兵向清军阵地猛烈射击,清军虽然英勇奋战,却伤亡惨重,而清军各部的炮兵却由于距离阵地较远,超出火炮射程,且“叶志超因战事无多,仅带小炮八尊”,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经过激烈交战,日军渐呈包围之势,叶志超见此心生胆怯,没有派出增援部队,却决定放弃成欢,聂士成部奋勇抵抗不支,亦一同退往平壤,此举瞬间打乱了清政府夹击汉城日军的作战计划。聂士成在《东征日记》中回忆这一幕:“师行至公州江浒,遇官军反斾渡江,讶之。有顷,叶军门策马至,相见,言‘公州不可守,不如绕道至平壤,会和大军,再图进取。遂率所部驰去。”
指挥无方,平壤再战溃败
7月21日以后,清军援军陆续通过水、陆两路,向平壤集结。援军共四路,第一路卫汝贵的盛字军12营、第二路马玉昆的毅字军5营走水路,第三路左宝贵的奉军马步各3营和第四路丰升阿的马队、盛字练军2营走陆路。8月4日至9日,四路大军日夜兼程陆续抵达平壤,并与叶志超的残部汇合。而出现在援军眼前的叶志超残部,为躲避日军追击,穿林越峪,缺粮少药,衣衫褴褛,给初到朝鲜的援军士气以极大打击。集结后的各路人马共15000余人,李鸿章坚持由叶志超统率,各路援军颇为不满。然而,尽管有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叶志超却并未积极战备,甚至主张“俟兵齐秋收后合力前进”。9月13日,日军分四路逼近平壤,切断了清军退往义州的后路。14日晨,日军攻占城北山顶清军营垒。左宝贵亲自督队争夺,未能成功,只得率部退入城内。当晚,叶志超见城北形势危急,主张弃城逃跑,遭到左宝贵等将领的反对,左宝贵还派令亲军监视叶志超,防止其再次逃跑。9月15日凌晨,日军发起攻击,中日双方猛烈厮杀,形成对峙局面。战斗中左宝贵等官兵相继阵亡。见此情况,叶志超战斗信心又发生动摇,连忙召集各路将领商议撤兵之策,除马玉昆主战外,其余各将均同意弃城。于是平壤各清军防地挂起了白旗,并乘当日夜深雨狂弃城逃跑。不料日军早已做好准备,在城北山隘堵截,打死打伤清军2000余人,俘虏数百人。清军退至顺安时,又遭日军拦击,损失惨重。16日,叶志超等率余部逃至安州,然后马不停蹄又逃往义州。至24日,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撤回国境内。
逃避责任,谎报两次战果
对于战场溃逃的玩火行为,叶志超当然自知是无法向清廷交代的,为逃避责任和惩罚,叶志超早已作打算,玩起了“游戏”。成欢之战后,叶志超向李鸿章发出了“报功”电报,进而又接连得到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嘉奖:“叶志超廿五、六两日,又连获胜仗,毙倭贼二千余人。该提督偏师深入,以少击众,克挫凶锋,深甚嘉悦。”“著赏给该军将士银二万两”。甚至在各路援军集结到平壤后,清廷对叶志超依然深信不疑,发出电旨:“现在驻扎平壤各军为数较多,亟须派员总统,以一事权。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夙著,坚忍耐劳,即著派为总统,督率诸军,相机进剿。”并一再告诫叶志超“力矢公忠,破除情面”,“将一切战守事宜认真经理,严驭诸将,咸遵约束”。9月21日李鸿章的奏折中,依然向清廷报告来自叶志超的“战况”:“当派卫汝贵、马玉昆两军将江东之贼击退七八里,枪毙不计其数。”“各军奋力齐上,追至四里外,生擒及割取首级二百余名,枪毙不计其数,我军共伤亡三百余名。”而这一切或是叶志超始料未及的,接踵而来需要面对的是如何“收场”的问题,叶志超身心俱受煎熬,其“倏得头眩心跳之症”,提出开缺养病的要求,却只被命令在军营休养。
后人评说,作战失利原因
关于叶志超,今人对其多有定论。其大端者无非有二:一是在成欢之战和平壤之战中顾自退却,导致清军在朝鲜境内连连失利,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动摇军心;二是隐瞒战况,虚报战果,导致清廷误判战场形势,使在与日本交涉中每每陷于被动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叶志超战场退却、虚报战绩的种种劣迹,多为人所诟病和不齿,即如前述黄遵宪诗文。但如果考察甲午时期的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环境和状况,对叶志超的评价或许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清廷对于日本的战争挑衅,和战不定,特别是李鸿章主张的“避战求和”方针。李鸿章言“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甚至叶志超请示李鸿章“倭日益猖獗,韩急望救援,各国调处卒无成议。此时速派水陆大军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前进,择要扼扎……”,也被否决。没有做好充分战争准备,丧失战机。第二,清军部署不及时,指挥失策,缺乏战略眼光。7月19日,眼见日本步步紧逼,持续增兵朝鲜,和谈几成泡影,李鸿章才开始向朝鲜增兵,但日军丰岛偷袭运兵船队,运输船“高升”号被击沉,结果到达朝鲜的清军援兵仅1300人。关于这一点,日军也说,“驻守天安的叶志超军未及时增援聂军加剧了清军败势,叶军如果共防成欢,清军就会占有更多优势。假如我联合舰队7月25日丰岛海战没有击沉“高升”号运兵船,成欢清军的总数量就会超过5000人,大炮增至21门,成欢战斗的胜负就很难定论”。第三,北洋水师海战失利,清军后路有可能被切断。7月的一份上谕就提到:“此时平壤后路,必须陆续添兵援应……大同江口,为平壤运路,关系紧要,应令海军各艘,梭巡固守。”而事实上,清军后路一直是叶志超的心头所系,也是日军攻击清军的重要计划。但无论怎样评说,作为主帅的叶志超庸懦怯敌,指挥无方,既未主动歼敌,也没有血战到底的决心,一经接仗,率先逃跑,甚至打出白旗投降,致使军心大乱,而且谎报战绩,加重了清廷对形势的误判,对此叶志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平壤之战后,叶志超即屡被御史参劾,如10月5日御史高燮曾言:“至叶志超统率无方,孤负圣恩,亦请交部议处。”10月13日,清廷命令撤去叶志超统领职务,“听候查办”。后依律判其“斩监候”,“于光绪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等年,朝审情实,均蒙恩免勾”。1899年1月刑部奏报,叶志超“十二月十六日(1月27日)患病,医治未痊,于十七日病故”,结束了饱含争议的一生。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史料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