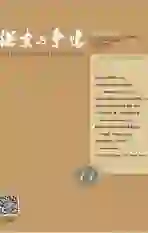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命运①
2014-10-21俞兆平
内容摘要 科学主义的问题,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日益显现出来,因为它是“现代性”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科学自身具有一种实践性的品格,人类在掌握自然规律之后,势必推动自我去改造外界客观事物,以使得自身本质力量得以确证。“科学是生产力”,科学促进了物质生产,创造了财富,改善了人这一族类的生存状况。但正如卢梭所指责的,科学与文化进步的同时,也带来其负值效应,因为它刺激了人的贪婪、虚荣、野心等欲念,进而引发掠夺与战争等暴行。这是科学异化无法卸脱的“原罪”。
关 键 词 科学主义 工程—技术取向 精神—道德取向 百年命运
作 者 俞兆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 361005)
一
科学主义一词为科学概念之衍生。人们崇奉、信仰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在趋于极致之际,多会产生科学万能的信念,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均在科学的掌控范围。不仅外在自然界能以科学方法来认识,而且内在精神界,如价值判断、情感好恶等,也可以用科学法则来衡量。也就是说,科学主义一词的概念内涵,并不只是指数理化一类学科对自然规律的探寻、把握及技术操作方式等,它更注重的是科学的“精神”,即科学上升为一种价值信念与原则导向,它从“物界”泛化至“心界”,有着从认识论向价值论转化的意义,已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性质。“要而言之,科学主义可以看作是哲学观念、价值原则、文化立场的统一。在哲学的层面,科学主义以形上化的世界图景和实证论为其核心,二者似相反而又相成;在价值观的层面,科学主义由强调科学的内在价值而导向人类中心论(天人关系)与技治主义(社会领域);在文化立场上,科学主义以科学化为知识领域的理想目标,并多少表现出以科学知识消解叙事知识与人文知识的趋向,与之相联系的是以科学为解决世间一切问题的万能力量。在科学主义的形式下,科学成为信仰的对象。”[1]这是对科学主义内涵更为全面的概述。
科学主义的问题,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日益显现出来,因为它是“现代性”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科学自身具有一种实践性的品格,人类在掌握自然规律之后,势必推动自我去改造外界客观事物,以使得自身本质力量得以确证。“科学是生产力”,科学促进了物质生产,创造了财富,改善了人这一族类的生存状况。但正如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一书中所指责的,科学与文化进步的同时,也带来其负值效应,因为它刺激了人的贪婪、虚荣、野心等欲念,进而引发掠夺与战争等暴行。这是科学异化无法卸脱的“原罪”。
近代以来,科学以工业为媒介,在实践上全面进入人类的生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促进了社会文明的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激发人的贪欲、恶念等,造成人的物化、工具化,以及人的社会关系商品化的现象,即马克思所说的“非人化”的状况。因此,在当代社会中,对物质主义及“人的物化”、“非人化”的批判,往往追溯到对科学主义的质疑与反思。物质与精神的矛盾深层隐藏着更尖锐的科学与人文的对峙。这也是“现代性”所欲探索及力求化解的核心命题之一。
二
“现代性”的内涵,是人们对近二、三百年以来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诸种现象的认识、审视与反思,是对现代化的正值成效与负值后果的理论概括与价值判断。因此,与其相关的科学主义问题,也是在近代方才凸显出来。
远在古希腊时期,科学是作为实现希腊人的人文理想,即达到自由的一种学问。当时,希腊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要实现这种自由,只有“理性”才能保证,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2]古希腊科学理性的伟大传统在“科学—理性—自由—人文理想”这一流程中得以呈现,这是科学与人文血脉相融的源点。
对于科学的这一古老的人文内质,百年中国学界也有所呈示,像鲁迅即称之为“神圣之光”。在《科学史教篇》中,他写道:“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破仑之战将云。”[3]在鲁迅心目中,真正的科学,有着神圣的光芒,照耀着世界,它阻遏邪恶末流,孕育美之情感。在这一向度上,科学不仅是“器”,而是上升为“道”,即科学不只是科技原理及具体的操作方法,而且还放射出人文的“神圣之光”、“人性之光”。鲁迅还精辟地指出:“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也就是说,像科學发明此类“灵感”,甚至受启于“非科学的理想”,孕育于深厚的人文内涵之中。因此,鲁迅还向科学家提出这样的人生准则:“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其中,“恬淡、逊让”,强调的是生存伦理;“理想、圣觉”,则是指科学家在日常的生存与工作中决不能忘却科学的人文内质。鲁迅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他深得古希腊科学中人文传统的奥秘,在1907年就向国人强调了科学的人文精神、人文理想,纠正了“以器代道”、以工具理性淹没科学中的人文精神的偏误。
和鲁迅的主张类似,徐志摩亦把科学分为两类:“纯粹的科学”与“科学的运用”。现今学界多把徐志摩当成一位浪漫诗人,殊不知他在科学方面也有一定造诣,1920年,他就翻译发表《安斯坦相对主义》长文,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中国最早译者之一。对于“纯粹的科学”,徐志摩指出:“真纯的科学家,只有纯粹的知识是他的对象,他绝对不是功利主义的,绝对不向他寻求与人生有何实际的关系。孟代尔(Mendel)当初在他清静的寺院培养他的豆苗,何尝想到今日农畜资本家利用他的发明?法蓝岱(Faraday)与麦克惠尔(Maxwell)亦何尝想到现代的电气事业?”[4]也就是说,纯粹的科学研究是完完全全的求“真”过程,它的目的是探索自然物的内部奥秘,揭示其构成及运动的规律。在这一进程中,它不会去考虑“善”的功用价值,不沾染任何实用功利意欲,有着一种形而上的纯净的意味。这种超然与纯粹,才是真正的科学大师的精神品格与生存方式。这一分法,亦是古希腊的传统精神的延续,因为当时的科学,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概念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离实用目的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科学作为一种无功利性的知识,是不自觉的,所以是“自由”的学问。
随着人类历史的行进,科学日渐发展、成熟。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开始有了分野,科学主义苗头亦即萌生。近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笛卡尔和培根所开启的两大传统:数理传统和实验传统。笛卡尔将主体与客体彻底分开来,为现代意义上的认识论扫清了障碍;而培根的实验哲学,则为人类知识的确定性追求,提供了直观实证的可能性。尤其是笛卡尔的人与物的主客二元论哲学,突破了神学的藩篱,从根本上解决了束缚科学发展的哲学问题。人的理性得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肯定,物质世界不再是一个神性的感知对象,而是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
事物是辩证的,科学的快速发展亦潜存着负面隐患。因其专注于现实物质世界的确定性知识的掌握,就逐步淡化、疏离了对人的生存价值及终极性意义的追问,最终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分离。美国当代哲学家史华慈将笛卡尔哲学断定为西方哲学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即“笛卡尔的断裂”:“这套二元论,一方面是整套的科学,对物质的机械论看法;另一方面就是物质的对立面,它不是上帝而是人这个主体心灵。两个世界:主体(心灵)和物质彻底完全地分开了。”[5]这种分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的断裂,物质与精神的断裂,也是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人文精神不再是科学的“神圣之光”,科学也不再是对人的自由精神的追寻。
从欧洲启蒙主义时期到当代,科学创造出无与伦比的辉煌的业绩,科学以其神话一般的魔力给予人类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物质享受。人们对其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妨借用胡适的一段话,来看看20世纪初科学思潮进入中国时的状况:“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6]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科学有着至高无上的威权,有着无所不能的功效。由此,“科学万能”成了一种新的宗教,科学理性成了新的上帝。当科学僭越了人文的席位,当科学把人的灵魂物化时,科学主义思潮便泛滥开来。
三
西方的科学及科学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何以能风靡中国呢?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一个缺席者;而积弱处贫、内忧外患的社会现状,更激起国人以科學救国的思潮。
若就文化内质来说,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从理解方法看,中国传统文化缺少西方文化将事物或者问题化约为某一核心点的方法,故缺少科学元素的理论构成。当然,中国也讲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但相对于西方的“原子论”的化约境界,相去甚远,甚至流于巫术的预测。至于“道生万物”的抽象与庞杂,则永远令人捉摸不透,缺乏万物本原的追寻,而后者正是支持科学发展的动力。
其二,从认知模式上讲,中国传统文化主客不分,缺少“笛卡尔的断裂”,产生不出现代意义的认识论。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一直是从大我出发,来透视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不是天人感应,就是日常伦理,强调的是集体理性。而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是认识主体的独立性,只有在自由地思考中科学思维才可能诞生。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均以圣人之言为准,禁锢了个体主体性与自由的思想。
其三,从传统氛围上讲,中国文化重修身而轻技艺,更多的是关心人格的修养,而忽视了对外在世界的规律把握与实践改造。典型的范例莫过于《庄子》“外篇·天地” 中有关子贡与“为圃者”的对话。子贡路过汉阴,见一种菜长者,“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十分吃力而收效不大,就问他,为何有桔槔这一汲水器械(利用杠杆原理制作的)却弃之不用?答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7]庄子借此说明:使用机械者便是投机取巧,顺之他就不具备纯洁清白的品质,进而他就会心神不定,如此当然无法容道于心了。“机心”与载道之“纯白”心胸是对立的,因此机械也就成了邪恶的。显然,这种传统文化氛围扼杀了科学之苗在中国的正常成长。
至19世纪末,甲午战争之惨败,马关条约之辱国,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未有的劫难之中。当一个阶段的历史走到了终点,也就预兆着它的新生。寻变革图强之法,思谋国救世之道,成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活动的中心。中国积弱难治的原因何在,西方世界强大的秘密又是什么?他们在苦苦思索与寻求。这样,中国以往儒教精神规范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原有经学价值体系的可行性也受到了质疑。随之而来,是对构成近代世界“现代性”最根本的要质——西方的民主、科学的推崇和高扬,并迅猛地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形成壮观的大潮。
西方的科学在中国扩展的进程大致经历这三个阶段:一是坚持固有的传统,以守旧的封闭心态排斥之。当时的清政府仍然做着他的天朝上国梦,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人就站在天地之间,对西方的日心说等所知甚少,对西方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革命毫不知情,对全球的海洋地理也了解甚少。因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一开始就予以拒绝。二是面对西方“船坚炮利”的残酷现实,不得不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器”,即物质机械的实用性技术角度接纳之。像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代表了这一阶段的典型观点。但他们将西方文化仅限定在实用性方面,科学在中国难于正常发展,洋务运动雷声大,雨点小,成效甚微,即是明证。三是洋务运动失败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才进而认识、理解到科学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开始从思维方法、价值体系上推崇科学,从而对科学的理解由“器” 演进、提升到“道”的境界。但也内蕴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激化,客观上促进了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泛滥。
这一从“器”到“道”、从技术操作到价值信念、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演进、转化的过程,主要源自严复。19世纪90年代,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系列文章,揭示中西事理、学理之不同。其著名的《论世变之亟》一文明晰地抉出了西方国家与中国相异之命脉,严复的目光锐利,比前人看见了更为深层的东西。西方国家之优异,不在于“善会计”、“擅机巧”、制“汽机兵械”之类,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其“命脉”关键之所在,为此二者:即学术上求“真”——科学之真,政治上求“公”——公正与民主。[8]此二者方为形而上的“理”、“道”。他把科学的内涵和意义,从“器”推进到“道”,使国人从价值论的形而上的高度来重新审视“科学”。
严复还向传统的经学体系发起了攻势。他翻译了《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两部西方逻辑学专著,并以此科学的方法论与传统的经学方法对比,揭示了后者的弊端。他指出,西方的学运昌明,得益于逻辑上的归纳法,逻辑学“如培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严复称逻辑学中归纳法为“内籀”,演绎法为“外籀”,两者中他更为推崇归纳法,认为归纳法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而中国传统经学的方法则属于演绎法,往往以“子曰”、“诗云”作为大前提来演绎推导,它虽然符合三段论,但由于大前提是先验的,“大抵是心成之说”,是旧有的“已得之理”,因而不可能从中获得新的知识。他打个比方:“夫外籀之术,自是思辨范围。但若纯向思辨中讨生活,便是将古人所已得之理,如一桶水倾向这桶,倾来倾去,总是这水,何外有新智识来?”[9]经学之“外籀”——演绎法所衍生的知识,仅如一桶倒来倒去的水而已,无创新之义。其弊病与陈腐,呈露无遗。因此,以科学体系代替经学体系也就势在必行了。
在当时,促使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科学语境形成的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等。康有为所著的《实理公法全书》就是国内首部运用科学方法从各个领域推导变革理论的著作。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亦致力于对西方科学的学习,他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中,高度推崇培根与笛卡尔,认为其两人“为数百年来学术界开一新国土”,并使人摆脱了“心奴隶”——精神上奴隶之状态。他概括了培根为代表“格物派”的英国经验主义和笛卡尔为代表“穷理派”的欧洲理性主义的要义,提出“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的原则,并认为循此原则即可对古今中外的学术作出评判:“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10]传统经学研究方法那种诚惶诚恐的“子曰”、“诗云”的前提规范全被抛舍了,国人可以在科学理性的导引下,自由地巡视、评判、取舍、扬弃古今中外的学术。这种境界与气度,正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所梦寐以求的。康、梁时为学界之泰斗,经其两人登高一呼,国人自然齐声相应,趋之若鹜。科学、科学方法,及科学的价值观念,经时日之集聚、累积,初步演化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特有的倡导科学的文化语境。科学地位的上升,“科学万能”的崇奉,便促使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思想界弥散开来。
四
对一种思潮的竭力强化,也就隐伏着对它的不足之处的疏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之际,往往遮蔽了它的负面后果。科学方法变成了无所不能的万应灵药,成了新的“上帝”,科学偶象化、神圣化了。
如前所述,在人类思想史上,对科学负面后果的质疑始自卢梭,但引起这一怀疑的全面爆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中,由先进的科学技术所发明创造的武器,屠杀了大量参战的士兵和无辜的平民。科学的“成果”毁灭了一座座城市和乡村,毁灭了人类予以自豪的人性与文明,于是人们在对科学的盲目信仰与顶礼膜拜中惊醒,开始对“科学万能”之价值,即科学主义思潮,有了另一向度的判断目光。
在中国现代思想界,梁启超是最典型的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1918年底,梁啟超、张君劢等作为中国赴欧观察组成员参加巴黎和会。在欧洲,他们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生灵涂炭,民生凋敝,思想混乱,精神失落。这一切都使梁启超震惊不已,但他更关心的是战祸及危机的根源,他也像卢梭一样把它归罪于“科学万能”论。[11]人所共知,梁启超乃清末以来鼓吹西方文化、倡导科学思潮着力最甚的代表人物。今天,他居然一反前说,对科学的地位,对科学主义思潮的偏颇,提出质疑,这就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成为其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前奏。
这场论战的导火线,是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所作的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其演讲的要义是:人生观问题的解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它只能依赖于人类之自身。原因是: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由于科学诸特点恰与人生观相对立,故科学不能提供人生观。[12]他悖逆“五四”时期崇奉科学之时代大潮,系统而全面地对“科学万能”说发难,要求重新审视、确立人文精神的价值。
此前,丁文江曾私下和张君劢就这一问题作过多次争论,此时按捺不住了,同年4 月发表了《玄学与科学》一文,予以反诘。他称张君劢等为“玄学鬼”,意即沉溺于虚幻之境中。丁文江等认为,传统精神、直觉、美学、道德、宗教感情等,实则为虚幻的玄学,只有科学精神才能对人生观的树立起积极作用。因科学能使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科学的分析研究,能够深入到宇宙人生的所有方面,对各种问题都能作出解答,包括精神意念、生命意义等。
这场论战迅疾地在中国思想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的第三次大论战。胡适、吴稚晖、陈独秀、瞿秋白、梁启超、张东荪、王星拱、范寿康等众多知识界的精英人物都卷入了论争。在当时崇奉“德先生”、“赛先生”的历史语境中,表面上是以张君劢、张东荪等为代表的“玄学派”败下阵来,而以丁文江、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科学派”获得胜利。
但得胜的“科学派”一方内部并不统一,反而在原则立场上产生了分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派的“物质一元论”与自由主义派的“心物二元论”冲突的开始。陈独秀认为,胡适与张君劢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他指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13]而胡适则不赞同陈独秀把“物质的”一个字仅解释成“经济的”,他说:“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14]
茅盾曾在《语体文欧化问题和文学主义问题的讨论》中指出:“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浪漫主义文学里的别的原素,绝对不适宜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来了。”[19]这里,不适宜于今日的“浪漫主义文学里的别的原素”,显然是指其反科学主义的本质。在其后的接受进程中,浪漫主义的反科学主义内质逐渐被扬弃,它变异了,“中国化”了。它的反科学主义本质,它对“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的要义,它回归自然的本真性等,均被扬弃、排斥了,余下的只是与中国古典美学“诗缘情”接轨的主情主义和文学创作的一般心理能力——想象这两大成分,即浪漫主义变异了,“中国化”了。
由此,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的所谓浪漫主义的定性,可以推导出新的看法。一项确凿的证据是,1930年之前,我们在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肯定浪漫主义之处。显然,这和科学主义有关,因为郭沫若等是崇尚科学主义的。郭沫若在《论中德文化书》 中把大战的起因与罪责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归结于政治上的动因。他还在此段文字下特地加上附注:“此处有意反对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该书正尽力鼓吹科学文明破产。”[20]他和胡适的观点一样,认为梁启超错了,科学文明更应大力提倡,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一科学落后的国家,更要高扬科学及科学精神。在本质定性的基点上,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有了如此之大的距离,你说郭沫若等能原原本本地首肯、奉从来自西方的浪漫主义吗?由此,崇尚科学主义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不能冠之以浪漫主义社团的称号;而真正趋近于浪漫主义精神旨向的,应是以宗白华、沈从文、冯至等为代表的美学追求与实践作品。
其三, 科学主义与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国内学界诸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论及20世纪20-30年代文坛时,对古典主义思潮采取回避的态度。其原因就在于学界未能从科学主义的视点上,未能从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矛盾对峙这一世界范围的现代性语境中,来考察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科学主义强调科学之无所不能,科学至高无上,人的自由意志便无足轻重,人生存意义可忽略不计。这样,人文精神便渐渐地萎缩、削弱,有一类国人敏锐地感应到这一危机。1919年底,留美的陈寅恪与吴宓有一番深谈:“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21]这是陈、吴二人对中国当时重理轻文,重科学轻人文偏向的批评及欲采取的对策。他们认为,科学的机械论不能决定人生的自由意志,物界的事实判断不能涵盖心界的价值判断,若一味地唯科学、机械“马首是瞻”,必将陷入人欲横流、道义沦丧的境地。
其后,吴宓回国,创办《学衡》,成学衡派中坚,其“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在以革命、革新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思潮中显得格格不入,其“守旧”和“复古”的倾向,在当时思想解放的历史大潮中,显然是逆流而动的。但学衡派及其后的新月派在精神内质上,则与前述“科玄论争”中玄学派一脉相承,由他们学说与作品构成了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激进对于保守的批判是合理的,但保守对于激进的质疑也是必要的。在学术史的建构上,我们不能仅以政治趋向而否认其学术地位,甚至取消其作为一种思潮的客观存在。就历史现代性来说,以学衡派、新月派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对科学主义的抗衡,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但他们的价值选择却趋向审美现代性。他们对现代化进程中物欲私利的膨胀、机械理性的扩展、道德伦理的沦丧等事关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持警觉、反思、抗衡的态度;他们偏重于人文精神的传承,偏重于艺术的自主性与审美自律性的设立,亦制衡、削减了历史现代性的负值后果,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均衡,构成推进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合力。它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形成另一种逻辑关联,一样属于新的时代。
六
“科学主义”这一概念由人类现代化进程而诞生,也因纳入现代性语境而遭质疑。对它的反思与拷问,从18世纪延续至21世纪。
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位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而出向科学发难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1750年,卢梭写出了《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人类文明建构的乐观性、进取性的信念,遭遇到第一次强有力的阻击:“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说是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22]以科学、艺术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一向是人类的骄傲,人类理性的标志,在卢梭这里成为新的“原罪”,成为被否定的异化现象,遭到了激烈的指控。文明的正值增长中所内含的负值效应,被卢梭以一种矫枉过正的语言公开地暴露出来,人类第一次看清了自身两难的境地。
18世纪以来,由科学所推进的工业文明在经济领域创造了奇迹。当时虽然还没有“科学主义”的概念设立,但是科学所导致的异化现象,人类文明的正值增长所内含的自否定因素,即馬克思所说的“非人化”状态,日益呈现出来:物欲无限度地急剧膨胀,技术思维的单向、片面的隘化,人与自然的日渐疏离,商品交换逻辑渗透至生活及人的意识的深层,意识形态所涵盖的话语权力严密的控制,人类精神的“神性”和生存的“诗性”沦落、丧失……这些异化的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忧虑及抗衡。以卢梭为源端的这一浪漫哲学、美学思潮,历经康德、谢林、诺瓦利斯、叔本华、尼采,到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直至当代的罗素、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诺、史华兹等,“他们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人的本真情感的纯化,力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惨境中吟痛的人灵。”[23]
在中国,科学主义一词的使用,按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像是起自徐志摩。1923年初,徐志摩翻译、发表了罗素《教育里的自由——反抗机械主义》一文,在译者序中,他写道:罗素“所主张的简单一句话,是心灵的自由,他所最恨最厌恶的是思想之奴缚。他所以无条件的反对机械主义,反对科学主义之流弊。”[24]这里,正式出现了“科学主义”一词,研究界应予重视。但是否最早,仍需考证。
在此概念出现之前,对科学主义一类的流弊的质疑与批判早已展开,其中最为激烈、最为深刻的,当数鲁迅。1907年,他所写的《文化偏至论》,揭示的两大“偏至”之一,就是深层为科学主义所引发的“物质主义”弊端:“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荫,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25]鲁迅揭示,由于19世纪“知识”、“科学”高速发展,单向地助长了“惟物质主义”,其失衡的偏误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恶果:“物欲”遮蔽了“灵明”,外“质”取代了内“神”,物质文明的高涨,精神文明的低落,人的旨趣平庸,罪恶滋生,社会憔悴,进步停滞。“物化”、“非人化”,这是科学主义引发的19世纪的社会弊病,难道不也是今日生存于21世纪工业化社会中人类的困境吗?因此,你若不以科学主义、人文精神等为理论参照系的话,则永远无法领会鲁迅思想的超前性与深刻性。
在中国百年思想史上,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力度能与鲁迅比肩并立的是林语堂,遗憾的是学界对此至今未能引起关注。他的批判文字主要集中在《啼笑皆非》这部著作中。该书出版于1943年2月,是对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世界局势,二战的动因、趋势,以及人类的精神拯救等作出评述。
林语堂尖锐地批判道:“科学的催命手抓住了西方,科学或客观的研究方法,已染化了人的思想,引进自然主义,定数论和物质主义。所以说,科学已毁灭了人道。自然主义[信仰竞争]已毁灭了行善与合作的信仰。物质主义已毁灭了玄通知远的见识及超物境的认识信仰。定数论已毁灭了一切希望。”[26]由于科学的纯客观认知的原则,使自然主义、定数论和物质主义盛行其道。自然主义把自然界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法则用于人类社会,人类潜在的不可遏制的贪欲,引起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斗,爆发了今日的世界大战。而物理世界的公式、定理被移用于人事,人变成事实与公例的现象,变成数学上可计算的物质定数的范型,这一“科学定数论”(亦即“科学主义”),窒息了人的灵性,造成宿命的悲观主义。至于物质主义由于披上科学的外衣,有了尊严,使强权政治可托庇于其门下。这种由“科学主义”所引发的物质主义、自然主义等错误的观念,使整个人类变成一座争斗不息、弱肉强食,毫无人道、理想、温情的荒林。
林语堂还在该书《中译本序言》,陈述了自己思维逻辑的推演流程:若世界大战为“果”,强权政治为第一层之“因”;若强权政治为“果”,那么物质主义就为第二层之“因”;若物质主义为“果”,那么科学定数论和自然主义就为最根本的“因”。林语堂就是这样地揭示出了:世界大战—强权政治—物质主义—科学定数论(科学主义)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还比史华慈更早地论及“笛卡尔的断裂”问题:“欧洲知识界的毛病是当笛卡儿把宇宙切分为心与物两个方便的部分开始时,……这种趋势达到了上帝的‘灵及人类的‘灵必须服从笛卡儿方法的程度。”[27]由此,亦可看出林语堂思考的学理深度。
1949年政权的更迭,使国人关注的思想热点转换,“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把“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关系”这类形而上的“玄学”命题,挤压得影迹无存。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展开,这一问题才渐渐进入学界关注的范围。但在百废待兴之际,科学自然以其实践性、现实性的力量,首先为国人所重视,“科学的春天”的到来,让神州大地为之欢欣鼓舞;科学的先期复兴,拯救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但新一轮的对科学崇拜、神化的氛围,也渐之弥散开来。甚至连以精神追索为终极的文学界,也兴起以科学为核心要义的“文艺批评方法论”热潮。原属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新三论”,被引进至国内文艺理论批评体系之中。
时代在前进,人文精神却相对萎缩,这一社会状况引发一批有识之士的焦虑。1993年,上海学界以王晓明为主发起一场“人文精神讨论”,在《上海文学》、《读书》等报刊上发表100多篇相关论文,其热烈的程度出乎时人所料,显示出这一论题对中国当代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历史仿佛在重演,70年前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像是在中国思想界再一次展开,但与“科玄论战”有所不同的是,反方没有出现,讨论成了一边倒,几乎全是肯定人文精神的正方,以理直气壮的姿态展开对潜在反方的声讨。
1993年这场讨论,比起1923年那场论战,论辩的焦点不够明晰,未能透过事象直逼科学主义这一根柢。虽然也有几位学者接触到这一问题,像李天纲指出:“理性原来包含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现在工具理性急剧膨胀;与此相关,追求效益、崇拜乃至迷信科技等等,都压抑着人性的全面发展。我想,这是现代人性迷惘、委琐的重要原因。”高瑞泉进而论及:“对科学主义的弊病,王国维在本世纪初就意识到了,他的名言‘哲学上之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就表达了对科学主义的忧虑与对人文精神的追求。”[28]但若与林语堂《啼笑皆非》一书相比,批判的功力与深度都显得稍逊一筹。
因此,1993年的上海这一战,远没有完成历史交给它的任务。而其后出现的清华大学一位大四学生为了测试熊的嗅觉与灵敏度这一科学认知目的,用硫酸去泼北京动物园黑熊的令人痛心的事件;以及至今仍在各高校盛行的用计量数学方式来评估人文学科教授学术水平的荒唐做法;近时崔永元与方舟子关于“转基因”如此分明的问题的论争,仍无法判断的迷离现象……这一切说明,在今天深入探析科学主义,依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还是以史华慈之论为结语吧。史华慈把人类思想史上的科学主义倾向称之为“工程—技术取向”,把对人文精神的执守称之为卢梭式的“精神—道德取向”。他认为:“马克思的魅力就在于其晚年的著作对这两股潮流进行了出色的综合。……马克思既像卢梭那样对工业化的发展表示愤慨和哀叹,又像那些工程-技术论者一样对人类的技术天赋表示惊叹,并毫不掩饰自己的自鸣得意之情。……当然,马克思所谓的美好社会并不是卢梭的斯巴达式的乌托邦,在这一社会中,个体不仅享受着艺术与科学带来的丰硕成果,而且在他们的身上还体现着盧梭梦寐以求的社会美德”。[29]虽然这一结合是不稳定的,而且将永远在行进中,但看清这一前景,远比陷落在迷惘中要好。
注释:
①关键词的撰写,和辞典词条相似,它不仅是个人的写作行为,更多的是历史文化的累积,是集体劳动的汇总,科学主义一词亦是如此。新时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其重新关注,起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9年,李泽厚、庞朴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了美籍华人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书,引发了这一课题的探索;其中,成果最为显著的是杨国荣1999年出版的《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一书。本人此后所做的工作只是把这一哲学问题引向文学研究领域,发表相关系列论文和出版《中国现代作家论科学与人文》一书,本文的写作亦受启于郭、杨二位学者。
参考文献:
[1]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7.
[2]吴国盛.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2001(4).
[3]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5.
[4]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4卷).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196.
[5][29]史华慈,许纪霖、宋宏译.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17、105.
[6]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0.
[7]曹礎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175.
[8]严复.严复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4.
[9]严复.名学浅说.严复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11]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83、198.
[12][13][14][15]张君劢、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35-38、7、27、32.
[16]张利民.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
[17]陈独秀.陈独秀文选——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15.
[18]茅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1920(9).
[19]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87.
[20]郭沫若.文艺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9-17.
[21]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101.
[22]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6.
[23]刘小枫.诗化哲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11.
[24]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3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321.
[25]鲁迅.文化偏至.论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2.
[26][27]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3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59、161,202.
[28]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41.
编辑 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