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春暖花开
2014-10-11戴建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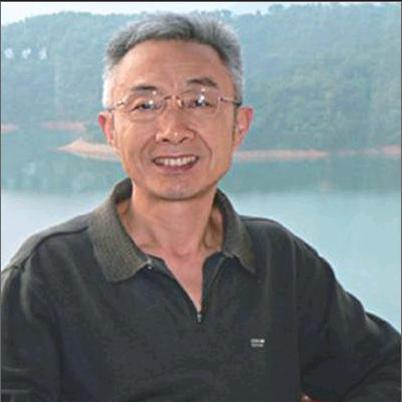
戴建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华中师范大学首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评选中,他位居榜首。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自己的学生,除了教书,他更注意育人——主张研读经典、注重师生交流……学生这样评价戴建业:“他的课堂总是爆满,甚至有不少外校学生慕名前来听他讲课。他讲得忘记了时间,学生也听得忘记了时间。”“新学期,一定要去蹭戴建业的课!”
1977年,接到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的手颤抖得很厉害。
录取通知书写明第一年在华师京山分校就读,报到后才发现这所分校建在离县城还有几十里的乡下,京山这个丘陵地区与我们麻城老家十分相像——转来转去还是没有离开乡村。农村孩子更向往大城市,我高中录取的同学都在武汉,京山校区和周边环境让我失落感很强。高中毕业后,我是家中挣钱糊口的顶梁柱,我到京山上学,家中只有多病的老母和念中学的弟弟,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我自己在班级和年级中也不合群,主要是我的方音大家听不懂,交流起来十分困难。到京山头一个星期,与喻志丹等同学一起爬山,我说这个地方“最美丽”,居然没有一个人听明白。起初我以为是大家嘲笑我,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发音与普通话相差太大。种种因素凑在一起加重了我的困扰,外人看来我是七七级天之骄子,我自己却整天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更要命的是,我几个月连续严重失眠,看书和写作也无兴趣,读什么作品都觉得没有味道,写任何体裁的东西都不满意,甚至觉得大学生活也非常无聊。大学一年级上学期上当代文学课,老师在课堂上差不多讲了一个学期的毛泽东诗词。可能是自己情绪太不好,而不是老师讲得太糟糕,连自己喜欢的文学课我也厌倦了。小说诗歌实在读不下去,我后悔原先没报考理科,于是给本部教务处写信,要求转到数学系或物理系,校方回信称没有这样的先例,并要求我培养专业兴趣。我们六班班主任是刘兴策老师,我到刘老师住的平房里倾诉自己的苦闷,最后我向他提出退学申请。我想回家复习下届重考理科,但这话没有对刘兴策老师挑明,我怕引起刘老师的误解。刘老师听说我要退学十分吃惊,刚刚期中考试成绩我门门优秀,可我的退学理由是自己读不好中文。刘老师说考上大学很不容易,七七级又是令人羡慕的年级,你目前的成绩还不错,辅导员对你也没有任何负面评价,你这样主动要求退学实在太轻率了。没有多久我又向刘老师第二次申请退学,刘老师两次拒绝了我的请求。刘老师待人热情、细心、和蔼,我每次和他谈话都感到温暖,是他的鼓励和温暖避免了我荒唐的退学悲剧。在京山的半年真是度日如年,夜晚难以入睡,白天昏昏沉沉,医生说我是神经衰弱,现在才知道那是严重的抑郁症,甚至已经严重到有了想自杀的极端倾向。
京山半年是我一生最灰暗的日子。这次毕业三十周年聚会,同学们都到京山重温旧梦,我一个人没有随大家同去,那段日子不堪回首,我再也不想见到京山!
原先说要在京山呆上一年,多亏同学们齐声反对,在京山呆半年就回到武汉华师本部。暑假过后来到桂子山报到,我到校的时候是夜晚八点多钟,第二天一起床我就去找高中班主任曾说过的那栋“圆顶教学大楼”,连问几个同学都说不知道,有的还说华师没有圆顶大楼,几经打听才知道就是物理系原先的教学大楼,现在改成了学校的行政楼,看到楼上那个小圆顶,我真是哭笑不得。
学习和生活环境变了,我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一些,但仍然事事都提不起精神。没有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来桂子山本部后我们年级开始上英语,我在中小学从没学过汉语拼音,更没有正儿八经学过英语。别的同学是怕记英语单词,我的麻烦是元音和辅音发不准,每一个英语单词的发音我都拼不出来。最怕老师点我拼单词和读课文,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是宋淑蕙,她每次要点人用英语对话,对我就像是大难临头。刚开始用的是一种油印教材,我一看到它便心里发怵。分班时我被分到了年级英语慢班,慢班里大多是年龄较长的同学,我可能是这个班里年龄最小的弟弟,这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侮辱。我特地请室友李建国兄帮我补习英语,我们一人搬个小板凳,在西区五学生宿舍的树下对口型,念元音,发辅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学会发音。学了几个月才能念出单词拼音,在课堂上还头一次得到了宋老师表扬。事实上,李建国要算我半个英语启蒙老师,毕业时他还把自己的英语小辞典送我作纪念。
由于把精力转移到了专业和英语学习,加之我坚持天天跑步,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我逐渐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二年级以后我就觉得春暖花开,阳光明媚。
现在想来,三十多年前要是糊里糊涂地退学了,以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很难再考上大学。要不是碰巧遇上刘兴策这么耐心的老师,我今天的人生肯定潦倒凄凉。患了抑郁症和要求退学这件事,只有我和刘兴策老师知道,今天在这里我向刘老师鞠躬谢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