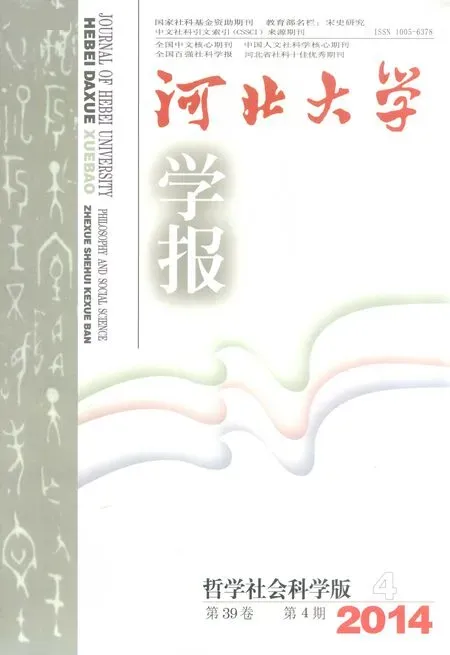维特根斯坦论自我
2014-10-08姚东旭
姚东旭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
近代认识论转向以来,关于自我的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维特根斯坦对自我的考察大体继承了近代以来自我理论的问题意识和思路。但是又由于其处于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语言分析的方法取代了传统的概念分析,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维特根斯坦的自我思想大体按照他个人思想的分期,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维特根斯坦以“界限主体”或“形而上学主体”来阐释自我,并指出唯我论与实在论的一致性;而在中后期思想中,维特根斯坦区分了“我”在不同语言游戏中的差异,并指出,哲学家们在“我”的问题上犯的错误是由于表达形式相似性造成的联想所造成的。本文将分别讨论维特根斯坦前期与中后期自我思想,并简要对维特根斯坦的自我思想作出评论。
一、前期维特根斯坦:唯我论与实在论的一致
(一)自我不是表象主体
简单的回顾一下近代哲学中对于自我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自我思想的思想背景。笛卡尔肯定“我思”,即肯定一个意识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前提地位。但是,由这个意识活动出发,是如何认识到更复杂的知识的?它是如何表象更复杂的实在的?如果从“我思”出发,我们除了它自身以外,似乎再也无法更进一步。
洛克接过了这一问题,在洛克那里,自我首先是一个由诸多外感官集合而成的生命体,对外在刺激的接受形成的知觉活动是首先发生的,而对心理活动的反省则在知觉活动发生之后,这一反省意识可以通过回忆,当下认知和预期的方式与这一生命体的过去、现在、未来发生联系。无论这一生命体如何改变,这一意识都可以保持同一,因此,这一同一的反省意识即是自我[1]。
洛克的思路大体是笛卡尔的一个逆转,由一个能够表象诸种复杂材料的反省意识取代贫乏的“我思”,形成了一个复杂表象主体的构建。但是,这一表象主体依然不是自我。休谟和罗素的思路中,洛克的反省意识没有超出感觉经验的范畴,而在经验中人类形成的自我只是由习惯形成的知觉集合体。罗素认为对自我不能形成“亲知的知识”,而只能形成对于个别思想和感觉意识的认识,是一种“描述的知识”,达不到前者的确实性[2]。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两点:
(1)表象主体不能是简单的,不然它将难以表象和认识复杂对象。
(2)如果自我是经验的一部分,那么将不可能形成对它的确定的经验知识。
维特根斯坦作为经验主义思路的后承,面对着以上讨论所带来的问题:
(1)自我与表象主体的关系是怎样的?自我是否是表象主体?(自我的本体论问题)
(2)自我与经验的关系是怎样的?自我是否是经验对象?(自我的认识论问题)
维特根斯坦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首先否认了自我是一个表象主体。在命题意义的逻辑图像论中,“每个命题都是对基本命题作真值运算的结果”(TLP 5.3)[3]69。但是,维特根斯坦对此提出了质疑:“初看起来,一个命题也可能以别种方式在另一个命题中出现。”(TLP 5.541)这类命题包括“某些心理学的命题形式”,如“A相信p是真的”,“A思考p”等。在这种形式中,命题的真值取决于主体A的命题态度。这就使得外延论点(Extensionality thesis)遇到了困境。表面上看,A是不同于命题p的主体,这也是心理学所设想的具备命题态度的主体概念。那么,心理学的主体是自我吗?维特根斯坦对此批评说:“但是很清楚,‘A 相信p’,‘A 思考p’,‘A说p’都是‘p说p’的形式:这里涉及到的不是一个事实和一个对象的相关,而是借助于其对象相关的诸事实的相关。”(TLP 5.542)也就是说,表象主体与事实(事态)之间的关系即是借助共同关涉的对象A建立起的一个命题符号系统对另一个命题符号系统的具有同样逻辑多样性的描画关系。即“‘p’说p”。命题态度“相信”“不相信”“思考”“怀疑”等都只是作为判断要素而出现。这样一来,心理学的主体—心灵就成为了具备复杂性的表象主体,而非一个不能被进一步分析的对象。但是,维特根斯坦评论道:“一个组合的心灵就已经不再是心灵了。”[3]81-82一个复合的自我不是自我。因此,自我不能是表象主体。
(二)由表象主体到界限主体
维特根斯坦对自我问题的回答是:“主体不属于世界,然而它是世界的一个界限。”(TLP 5.632)罗素对自我的处理方式是将自我看做是对我当下意识到的东西的意识,牺牲了自我的跨时间与空间的同一性,而使得自我有可能成为经验知识。维特根斯坦则坚持了更彻底的经验论:“如果我写一本书叫做《我发现的世界》,我也应该在其中报道我的身体,并且说明哪些部分服从我的意志,哪些部分不服从我的意志,等等。这是一种孤立主体的方法,或者不如说,是在一种重要意义上表明没有主体的方法;因为在这本书里唯独不能谈到的就是主体。”(TLP 5.631)也就是说,在经验的成分中我们无法发现自我,自我不能被经验或对象领域中的成分同一化。在接下来的一部分中,维特根斯坦更加形象的用眼睛与视域的关系来表达这一点:“你会说这就正好像眼睛和视域的情形一样。但是事实上你看不见眼睛。”(TLP 5.633)“视域肯定不具有如图这样的形式”[3]85-86。

图1 维特根斯坦的“眼睛”比喻的示意图
这样一个比喻可以类推到认识主体的任何一个领域。“如下之点是真的:认识主体不在世界之内,不存在任何认识主体”(NB 20.10.16)[4]244。
维特根斯坦这一思路受到了叔本华和康德思想的影响。康德将自我看做是属于不在经验之中的“物自体”的范畴,作用在于将经验统摄起来,使其成为一个统一体。叔本华同意康德主体属于物自体范畴的结论,并认为意志是世界的主体,世界只是同一意志在不同层面上客体化的产物,自我不是世界中的任何对象,而是意志主体。
维特根斯坦对康德和叔本华的思路有所继承和综合。他认为:“哲学的我不是人,不是人的身体,或者具有心理性质的人的灵魂,而是形而上学主体,是世界的界限(而非其一个部分)。”(NB 2.9.16)[4]237即以界限主体取代一切经验的及对象化的成分,撇清了主体与表象主体的关联。同时,维特根斯坦肯定了意志主体,“意志是主体对世界的一种态度。主体是意志主体”(NB 4.11.16)[4]245。但是,“作为伦理主体的意志是不可说的”。也就是说,叔本华肯定自我属于物自体领域,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他同时对只能“显示”的自我有所言说了,即说了主体的本质是意志,这样就使自我的本性归之于意志,而“主体的本质 被 完 全 的 掩 盖 起 来 了”(NB 2.8.16)[4]232。“意志是主体对世界的一种态度”(NB 4.11.16)[4]245。康德的“物自体”自我学说正确的把握了自我的“说出”与“显示”之间的关系,但是康德的思路在于解释自我是如何起作用的,即自我统摄经验的知识论功能意义,而没有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本质进行说明。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上的我是界限主体。用两点来说明:“如果意志的善的行使或恶的行使影响到了世界,那么它们只能影响到世界的界限,而不能影响到事实,只能影响到不能借助于语言加以描画而只能被显示在语言之中的东西……可以说,它(世界)必定作为一个整体而增长或缩小。正如经由一个意义的添加或略去一样。”(NB 5.7.16)[4]220自我是不能对世界中发生的事实产生影响的,它是属于意义价值层面的范畴,而这些是不可说的,只能诉诸于神秘体验。它改变的不是世界的内容。我们举起手臂,发生的是手臂举起来这一物理事实,而我的意志并没有发生在经验之中,也没有对这一物理事实发生影响。自我改变的不是事实,而是事实的意义与价值。
另外一点,维特根斯坦强调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世界和人生是一回事”(TLP 5.621)。 “我 是 我 的 世 界 (小 宇 宙 )”(TLP 5.63)[3]85。“生命就是世界,我的意志弥漫于世界”(NB 11.6.16)[4]219。也就是说,虽然我从我的世界中消失,不在我的世界中出现,但是世界仍然是我的世界。因为自我是不可言说的,自我唯有作为形而上学主体在不同的事实配置境况中才能够显示自己,即作为事实意义上“无”的“我”通过世界之中作为事实的不同的“有”而生成。
(三)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以上两部分分别讨论了自我是否表象主体与自我的界限主体的内涵。这一部分讨论的内容是唯我论与实在论的关系。在以上讨论中,并未涉及世界和事实的表征问题。维特根斯坦是否在构架某种缺乏公共性的“私人世界”?从而造成了唯我论与实在论之间的不相容?如同经验主义传统中经常出现的“自我中心困境”?
维特根斯坦在这里采取的方式是揭示出唯我论的自我中心困境的内在矛盾:“我们不能思考我们所不能思考的东西;因此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所不能思考的东西。”(TLP 5.61)“自我中心困境”的根源在于没有将唯我论坚持到底,“唯我论意味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它不能说,而只能自己显示出来”(TLP 5.62)[3]85。自我中心作为只能“显示”的内容,虽然不能出现在经验世界之中,但是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的逻辑图像论,由于描画世界所使用的语言是“我所唯一理解的语言”,因此,这种语言的界限即意味着世界的界限,从而保证了“世界是我的世界”。
维特根斯坦用一段话来表明唯我论与实在论的这种一致:“我所走过的路是这样的:唯心论将人作为唯一者从世界中挑选出来,而唯我论则只将我挑选出来,最后我看到,即使我也是属于其余的世界的。因此,在一边没有任何东西存留下来,在另一边所存留下来的东西是作为唯一者的世界。因此,唯心论,当其被彻底思考之后,导致了实在论。”(NB 15.10.16)[4]243
二、中后期维特根斯坦自我思想的推进
中后期维特根斯坦自我思想由理想或本质语言的建构转变到日常语言分析的思路。维特根斯坦试图强调在使用之中的日常表达式的相对于各种理想语言或本质语言建构的优先地位。在唯我论与实在论的争执中,维特根斯坦并不如前期一样试图建立一种自我理论,或试图为两者之间的融贯提供一种新颖的理想语言或理论构建。而是试图指出唯我论、唯心论与实在论都是对日常语言表达的背离,是由于“表达方式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联想”[5]77的产物,是需要治疗的哲学疾病。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主要工作就在于通过指出哲学对于日常语言表达式的诸种误用(如对“我”的不同用法的混淆)来进行“哲学治疗”。“你在哲学中的目标是什么?给苍蝇指明从捕蝇杯中出来的出路”(PI 309)[6]177。
(一)“我”的两种不同的用法的混淆
我们有两种命题描述,一种用来描述外在世界中的事实,另一种描述感官体验。在日常情况下,我们并不混淆两种描述,令我们发生混淆的是我们就这两种描述的表达方式的相似产生的联想。比如,我设想一间“视觉屋”,这间房间是由我的个人经验作为材料构成的,我们可以在描述它的时候使用习以为常的认识论术语,如感知到什么,看到什么等,但是维特根斯坦问:我们是否能拥有(have)这间“视觉屋”?我们能否看到一间房间而不能拥有它?我能否拥有一间房屋而不能在其中走来走去察看它?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形:在一幅画上画着一所房屋和一个农民,如果我们说“这所房屋属于这个农民”,那么,这种“属于”是哪种意思呢?这个农民不可能走进这所房屋,我们也不可能拥有一间由感觉材料构成的房间,在其中走来走去,买卖它,装饰它等,因为“视觉屋的所有者必定是与它本质相同的;但是,他既不在它之内,也没有一个外部”。这就是唯我论所导致的荒谬的结果。对于“有”来说,一个具有现实实在的“我”不可能有一间“视觉屋”。一个“内部”的东西如何走到“外部”?这条横沟似乎永远无法消除。除非我们承认,“有”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它的“外部”含义[6]204-206。这里维特根斯坦反思的是以康德为代表的先验自我对一切表象的统摄和伴随理论,因为,我们不能事先决定一切都事先被自我“拥有”,只有一种“拥有”可被怀疑,可能是错误的,谈及“拥有”才有意义。而唯我论的支持者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因此才会谈及到一种私人的“拥有”。即将“精神世界”看做是一个如物理世界一般的有广延、可观察、可所有的空间。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奇怪的假象。
维特根斯坦通过一系列的例子来指出关于“我”的诸种命题之间的差别。他区分我的“主体的用法”和“客体的用法”。我的主体用法中包括“我疼”,“我听见如此这般”,“我看见如此这般”,“我牙疼”,“我感到你的牙的疼”,幻肢的感觉,感到别人身体的疼痛等,而客体的用法则包括“我的手臂断裂了”,“我长了10厘米”等。前者与后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不可怀疑的,不存在识别错误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总是有识别错误的可能性[5]87。例如关于“我”的哲学困惑的根源就在于这两种用法之间由于它们使用同一个词“我”却含有不同的含义而产生的混淆。他用“几何学的眼睛”和“物理学的眼睛”来比喻这两种用法,我们在谈论“几何学的眼睛”时,如我们谈到在几何空间中如何看待某个图形,不同于我们用“物理学的眼睛”对事实进行观察。这两者之间的混淆让我们误认为自我是一个如“物理学的眼睛”一样的对象,而去寻找它的经验世界中的对应物,从而走上了将自我对象化的道路。或者以为“物理学的眼睛”实际上是“几何学的眼睛”,即可以用主体用法取代客体的用法,那么将会导致唯我论的思路。
(二)“我”的主体用法
那么,“我”的主体用法与客体用法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哪里呢?这里的回答是:我的主体用法中,“我”不是代表一个对象的名称,但是却与名称有关联。“我”的作用就像是“这儿”一样,通过指示共同空间中的一个位置来标明自己。维特根斯坦举了一系列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当我呻吟着说“我疼”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要让别人去注意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想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我”并非用于区分两个特定的人,而在于无条件的将别人的目光引向我,提醒别人注意自己,这就是“我”的作用。他设想了一个思想实验:一群人围成一圈,每个人都接上一个电极,电极会不确定的给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人释放电流。如果我们假定每次只有一个人会被释放电流,那么感知到电流的人就可以通过说“我”把电流释放的位置标记出来,而如果我们假定每次电极都无差别的释放电流给每个人,那么说“我”则变的没有意义。也就是说,“我”在这里不再起到标识或提醒的作用。“我”的主体的用法与客体的用法的关联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名称,但是它可以用来解释名称(PI 409-410)[6]208-209。
三、关于前期与中后期维特根斯坦自我思想的评论
从维特根斯坦前期与后期自我思想的关系来看。相同之处在于无论在理想语言层面还是在日常语言层面,都强调自我的非客体性,即自我不是一个经验对象(可被考察的心理状态、中立感觉材料、身体、物理对象等),自我不是经验中出现的任何东西。前期维特根斯坦强调主体是世界的界限而非世界的一部分,主体是形而上学主体或界限主体。中后期维特根斯坦区分我的两种用法“主体的用法”和“客体的用法”,并指出“主体的用法”的“我”在句子中的作用在于提醒或标识一个公共空间中自我的位置(这儿),同样是来论证自我的非客体性。区别在于前期维特根斯坦立足于使得这一点与本质和理想语言的阐明相兼容,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转为对日常语言实际用法的描述之中来。但是其前后期自我思想的整体倾向是一致的,就在于“反客体主义”(anti-objectivism)[7]。
维特根斯坦的这条思路被用于作为反对将自我作为某种经验对象进行研究的各种进向。在当代,寻找古典哲学式的精神实体或某种直接经验成分的自我的进向逐渐衰微,但是在神经科学和心灵哲学的讨论当中,关于自我的讨论采取了一些新的形式。例如认知科学家通过对人类大脑的考察,推断出某些与人类“自我”相对应的大脑机能,以内格尔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二元论者,将自我等同于成为“像是”(What it is like to be)某个特定的有机体所是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些讨论虽然采取了新的形式,但是依然没有摆脱客体主义的巢臼。Jesse Prinz将维特根斯坦的思路与当代神经科学中的各门进向进行对比后,发现,当代神经科学的思路大体还是其背后的传统哲学前提的翻版,例如,Goldberg的“失去自我”的认知实验是笛卡尔式二元论的一个翻版,Blakemore与Frith的断定感觉内容与身体行为相互对应的实验是梅洛·庞蒂的的现象学自我的一个证据,而Manos Tsakivis的更加新近的关于人能否“具有”一只假手的实验是康德的“知觉意识集合体”的自我概念的一个证实[8]。而这些实验所代表的思想范型都无法摆脱“客体主义”的巢臼。
值得注意的是由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想法。内格尔在他的《成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样子》[9]中,认为意识的主体性是实在的不可推断的特征。虽然我们不可能感知到主体,但是我们会有一种无法脱离它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观点”(point of view),即“像是”(What it is like to be)某个特定的有机体所是的东西。我们无法想象自己成为一只蝙蝠是怎样的,是因为我们不具备蝙蝠的“观点”。内格尔的看法似乎是在凝合维特根斯坦的“我”的两种用法之间的沟壑,即为“主体的用法”的我赋予某种有机体的对象特征,但是这种凝合是不成功的。我们在日常使用“我”(Ⅰ)的时候,并没有意味着有个有机体作为被指称对象,相反,我们在说“我”的时候,并不考虑我是否是一个生物体或有机体。
当代另外一些学者并非如神经科学家一样提出一种客体主义的自我解释,而是另辟蹊径,例如,丹尼特(Daniel Dennet)认为自我是人进化的产物,人形成自我是盲目的和缺乏思想及理解的,是大脑的一种本能和幻象,是由于人类叙述方式发展而产生的叙事重心(narrative gravity),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fit)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比如我们将大脑两个半球在保留神经联系的同时放入两个不同的身体,那么每个身体都可以说它是原始的那个自我。因此,他认为自我和同一性问题无关,而只是与人类的生存问题有关[10]50-64。这些讨论为我们讨论自我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和深邃的思路。但是它们依然只是一种解释,类似于叔本华的意志主体的解释,而我们理解日常语言的用法之所以具有意义,不依赖于任何解释,而仅仅在于我们能够正确的在一定的情境下使用它。
汉斯·斯鲁格(Hans Sluga)对维特根斯坦的反客体主义提出了一个质疑。他认为维特根斯坦只指出了自我并非一个对象,这是一个否定或消极性的表达,这里没有正面的论证,即没有对“真实的自我”,即历史、道德、社会中的自我进行讨论,从而混淆了“自我概念”与“真实自我”[10]349-350。在笔者看来,这一点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有关,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的功用在于澄清人们由于语言误用而导致的理智疑惑,就如同医生治疗疾病一般。医生无法对健康的人提出任何建议,就好像哲学家无法对不患理智疾病的人提出任何建议一样。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如果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目标是给予苍蝇以飞出捕蝇瓶的道路的指导的话,那么苍蝇飞出瓶子后该往何处去,那不再是哲学家的工作。哲学家的工作只在于指出如“我”这类哲学问题中,人们犯下的各种思路上或语言使用中的错误,并帮助人们回归到正常的语言用法中来,而并直接不对真正的人生、道德、历史问题提供答案。这是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界限所持有的看法,这也使得他遭到了诸如以上提出的责难。
综上,本文探讨了前期和中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自我问题的不同处理。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自我是界限主体或形而上学主体,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同时,“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中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在自我问题上受到表面形式的相似性的诱惑而导致各种哲学疑惑,需要通过对语言日常用法的分析来得到澄清。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前期和中后期自我思想所持有的是一种相通的反客体主义的思路,即指出自我不是经验对象,这正是哲学家们讨论自我问题时容易犯下的错误。总之,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站在语言哲学的出发点,对自我问题这一传统哲学问题作出推进。
[1]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6-83.
[2]罗素.逻辑与知识(1901-1950年论文集)[C].苑莉均,译.张家龙,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96-200.
[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维特根斯坦.战时笔记1914-1917年[M].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维特根斯坦.蓝皮书和褐皮书[M].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7]HANS SLUGA.Whose house is that?[M]// Wittgenstein on the Self/剑桥哲学研究指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45.
[8]JESSE PRINZ.Wittgenstein and the Neuroscience of the Self[J].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011(2):147-160.
[9]内格尔.成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样子[M]//心灵哲学.高新民,储昭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5-119.
[10]ROBERT ALLAN.Wittgenstein on Sensation and Self[M]//Master of Art Thesis.University of Calgary,Alberta,Canada,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