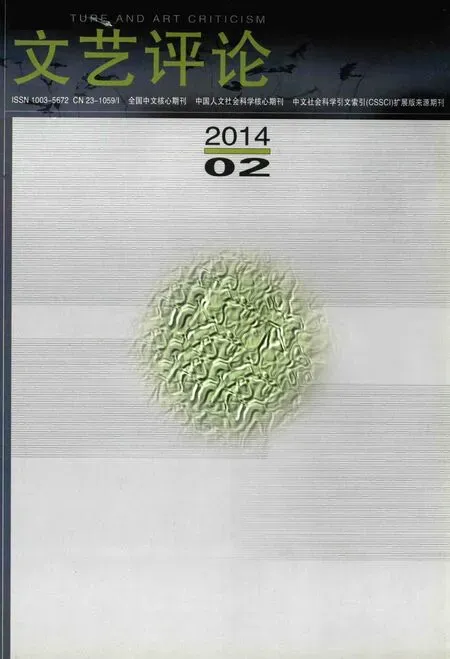论董仲舒与汉代以《诗》决狱
2014-09-29张华林宦书亮
张华林 宦书亮
董仲舒首次运用的“以《诗》决狱”是对其“以《诗》为法”《诗》学观的落实,而其“以《诗》为法”的《诗》学观则是在其《春秋》学基础上提出来的。在董仲舒的影响下,“以《诗》决狱”被汉代学者反复使用,从而成为汉代极具特色的用《诗》方式之一。
但学界对“以《诗》决狱”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成果,只有刘立志的《汉人引诗决狱刍议》①一文,该文主要从秦汉时期儒法合流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而对于董仲舒之“以《诗》决狱”观生成的内在经学因素与流布情况却未作全面论述。
本文主要从经学角度讨论董仲舒“以《诗》决狱”这一用《诗》方式的生成原因和汉人对此用《诗》方式的延续情况。
一、以《春秋》为法
董仲舒是《春秋》学大师。他认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为后王确立王道大法。其言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前者言孔子以《春秋》来体现其“素王”之文法;后者言《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中布满了孔子的王法。
《春秋》既是孔子受命所作的王道大法,故董仲舒提出以《春秋》为法的观点:“孔子……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前一条材料说孔子著《春秋》“以为天下仪表”,也即是以《春秋》为天下法;后一条材料则是对此观点的细化:他认为《春秋》乃以伯姬和齐桓公的行为为天下之法则,以为天下人所取法。两条材料所表达的皆是以《春秋》为法则的观点。
不但如此,董仲舒还将“以《春秋》为法”的精神贯彻于现实生活中,其具有代表性的行为便是他对各种案件的审理也依据《春秋》“大义”来作出判决,此即“《春秋》决狱”。据《汉书·艺文志》,董仲舒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列传》则言:“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这《春秋决狱》可能就是《汉志》所说的《公羊董仲舒治狱》,惜其多已亡佚,今仅存数条佚文。兹列一条以见其例。据《太平御览》卷六载董仲舒《春秋决狱》佚文曰: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议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也,不当坐。
在此案中,董仲舒以为父子至亲,子甲执杖救父乙而导致误伤乙,但其动机非伤父,乃救父。故据“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春秋》“大义”和《春秋》赦免许世子止因进药其父而误致“弑君”的行为,认为也应赦免甲之罪。可见董仲舒“以《春秋》决狱”即是依据《春秋》或“大义”来对相关案件作出断决,也即“以《春秋》为法”。
董仲舒不仅要求以《春秋》为法,他还进而要求以六艺为法。他在元光元年的对策中还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认为六艺之科即是孔子之术,而“六艺”独尊,即可实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此即认为“六艺”与“统纪”、“法度”有关,乃民之所宜效法者。这便是认为六艺皆可为天下法。而《诗》是“六艺”之一,故亦可法。
正是在这种经学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以《诗》为天下法”的观点,并有了“以《诗》决狱”的具体实践。
二、“以《诗》为法”与以《诗》决狱
(一)董仲舒“以《诗》为法”的提出
董仲舒在其《春秋》学的影响下,在《春秋繁露·祭义篇》中首次提出了“以《诗》为法”的观点。其文云:
《诗》曰:“嗟尔君子,毋恒安息。静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诗》为天下法矣,何谓不法哉?其辞直而重,有再叹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谓也。
董仲舒首先认为君子应该以真诚而恭敬的态度去对待祭祀;然后引用孔子之言进一步说明孔圣人也是如此;而鬼神是公正无私的,那些公而无私的人是会受到鬼神的福佑。他认为《小雅·小明》之“嗟尔君子,毋恒安息。静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就体现了这点。此言君子不应长久的贪图安逸,当恭谨地对待自己的职事,好与正直者交往,这样就会得到神灵的福佑。然后董仲舒进一步阐述道:“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这就将诗义由君子交往的具体的某个“正直”之人延伸为更具普遍意义的“正直”的处世态度,而且说这就是人们应该遵守的法则。在此基础上,董仲舒进而提出了“以《诗》为天下法”《诗》学观。这里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就其所引诗句而言,认为此诗所体现的正直的处世态度,不仅应该是君子的法则,而且应该是天下人的法则。另一层面则是说,不仅当以此诗为天下之法则,而且应该是以《诗三百》为天下之法则。
同时他也表达了对人们不以《诗》为法的疑惑与不满。从这种疑惑与不满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以《诗》为天下法”是董仲舒的创见。然后董仲舒从《诗》的语言特征和表达形式方面肯定了《诗》中必有大义存焉,是值得天下效法的。
另,“以《诗》为天下法”之“下”字,据有些版本作“子”。②由于此字直接关系着对董仲舒《诗经》学的理解,所以不可不辨。本文认为当作“下”,而不是“子”。考辩如下:
该段文字主要讨论的是君子的言行,而《春秋繁露》中的“君子”一词,主要指那些乐于“循理”而行的有德之士③,它与“贤”近,又曰“贤人君子”,其为政,则可“三卿之位”;它是一个集合名词,具有涵涉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的可能性,但《春秋繁露》中绝无以“君子”指“天子”者。而《小明》一诗,《毛诗序》说它讲的是“大夫悔仕于乱世也”,三家《诗》无异议。其中“嗟尔君子”一句,郑玄《毛诗笺》云:“谓其友未仕者也。”即此“君子”为“未仕者”,乃大夫之友,皆与“天子”无涉。且“天子”二字也无法涵涉前面君子、孔子、圣人等内容,这在行文上无法与前面的内容形成逻辑关系。在接下来对“以《诗》为天下法”的重要性的阐述里,董仲舒云:“有再叹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如果是就“天子”言,这里恐怕不当称“人”。
此外,《春秋繁露》中还有与“为天下法”相同或类似句子。如《楚庄王》篇之“宋伯姬恐不礼而死於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又“孔子……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为天下仪表”即是为“天下法”。此外,《尚书纬》也有类似说法。如“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④,“可以为世法”即“为天下法”。而遍检董仲舒以及《史记》、《汉书》等汉人著作,无“为天子法”句式。所以此句当作“以《诗》为天下法”,而不当作“以《诗》为天子法”;“子”乃“下”之讹。故有的学者将此说成是“以《诗》为天子法”是不准确的。
由此可知,董仲舒在中国《诗》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以《诗》为天下法”的观点(本文简称为“以《诗》为法”),要求将《诗经》作为天下人言行的法则、典范。此一《诗》学观点的提出,将《诗》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天下法”。
(二)董仲舒以《诗》决狱
董仲舒不仅提出了“以《诗》为法”这一观点,还有进一步的具体运用,如“以《诗》决狱”。这见载于董仲舒的《春秋决事》,其文曰: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⑤
在此案件中,甲乙关系是关键点。乙乃弃儿,非甲亲子,于是甲乙两者间的父子关系在法理上便有可商酌之处。对此问题的处理,董仲舒依据《诗经·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一句,认为螟蛉之子为蜾蠃所养而为蜾蠃之子;然后据此断定作为他人弃子的乙为甲所养大成人,则自然为甲之子。如此,甲乙父子关系因《诗》而得以明确。甲之隐匿义子的行为动机便有了经典的依据,从而具有了合法性。再依据《春秋》“父为子隐”的原则,董仲舒肯定了甲隐匿乙的行为之合法性。
从这一处理案件的过程可以看出,董仲舒是以《诗经》作为认定甲乙父子关系的依据与法则,这便是“以《诗》为法”,即将《诗》作为处理现实事务的法则与典范。这与后面紧接着以《春秋》为法,作出断案是同样用法。而“诏:不当坐”一句,表明汉武帝对董仲舒这种以《诗》为法、用《诗经》来作为处理现实政治事务的法则的肯定。于此可以看到,这种以《诗经》为法则,甚至将其当作法律来处理现实政治事务的情况,与此前的用《诗》方式有明显的不同,其意义不可忽视。而且如前所言,《春秋决狱》载有二百三十二事,可以想见董仲舒以《诗》决狱或许不止一次。而且这些内容受到了汉武帝等朝野的肯定而被作为治狱之典范来对待的。这必将对“以《诗》决狱”的用《诗》方式之传播产生影响,此后陆续出现的以《诗》决狱现象应该就是源于此。
三、汉人对董仲舒以《诗》决狱的延续
(一)汉代学者对“以《诗》为法”的接受
董仲舒提出的以《诗》为法的观点得到了司马迁等两汉学者的认可。
如董仲舒弟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司马迁认为六艺皆是孔子为后世所制作的“仪法”、“统纪”,也即王道大法,所以可以六艺为天下法。此即董仲舒所谓的以六艺为法。
具体就《诗》之可“法”性而言,司马迁有更明晰的论述。其文曰: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以备王道,成六艺。
此“王道”,即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说的“《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中的“王法”,也即前面所说的“仪法”、王道大法。此言孔子之时诗有三千多篇,孔子选取相关的作品,去除其重复,按“礼义”标准选择相关作品,然后依据历史先后顺序进行排列,从而使《诗》具有了王道大法的功能。此即以《诗》为法。
对于汉成帝常常召见言祭祀与方术者,延续了董仲舒灾异之学的谷永上疏成帝说这些人是“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此即以“五经”为“法”;《汉书》扬雄说《诗》乃“法度所存”,并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诗人之赋”即《诗》中作品,“则”,法也,此言《诗》可法则,与其所说的《诗》乃“法度所存”同义。
受董仲舒思想影响的谶纬,也延续了他“以《诗》为法”、以六艺为法的观点。如《春秋演孔图》说孔子“作法五经,运之天地,稽之图像,质于三王,施之四海”,此言包括《诗》在内的“五经”乃孔子为天下所作之“法”。还有郑玄亦反复强调“以《诗》为法”。他在《诗谱序》中言及诗的功能时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剌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於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即言《诗》具有“法”“戒”之功效。郑玄释“雅”曰:“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此言诗人作《雅》诗的目的在于为后世法。等等。
由上论述可见,自董仲舒“以《诗》为法”的《诗》学观提出后,在其“儒宗”地位的影响下,不论是《鲁诗》学者(司马迁、刘向)、《齐诗》学者(班彪)、《毛诗》兼《韩诗》学者(郑玄),以及无法确知《诗》派对扬雄、谶纬《诗》学等等皆认可并积极提倡董仲舒的“以《诗》为法”。因此可以说“以《诗》为法”已成为汉人在《诗经》学上的一种共识。
(二)汉人对“以《诗》决狱”的运用
随着董仲舒“以《诗》为法”的被广泛接受,他提出的“以《诗》决狱”也被汉人广泛的接受与运用。
如刘向称《诗》以断陈汤、甘延寿之狱。据《汉书》卷七十《陈汤传》载,陈汤、甘延寿矫制发兵斩单于,而中书令石显、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等人对陈汤、甘延寿立大功不赏而反欲因其矫制而治罪,元帝无主见,故久议不决。对此,刘向上疏称《小雅·采芑》诗文,说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而今陈汤、甘延寿之功,虽周宣之方叔、吉甫也无法与之相比;又称《小雅·六月》诗文说吉甫之归,周厚赐之;而今陈汤、甘延寿之功远超方叔、吉甫,不但不如吉甫受祉之报,反而久挫于刀笔之前。因此应立即解除其罪,赦免其过。结果是元帝纳刘向之议,赦免了陈、甘二人,并议封赏之事。
由上述可见,刘向在议陈、甘二人功过之时,主要依据《采芑》、《六月》二诗中关于方叔、吉甫的功劳与周宣王对二人的奖励行为,提出陈、甘二人也应受到方叔、吉甫的待遇,元帝则接受了刘向的论断。这便是“以《诗》为法”之据《诗》断狱。
据《汉书·文三王传》载:
永始中,相禹奏立对外家怨望,有恶言。有司案验,因发淫乱事,奏立禽兽行,请诛。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春秋》为亲者讳。诗云‘戚戚兄弟,莫远具尔’。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傅致难明之事……污蔑宗室,以内乱之恶披布宣扬于天下,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增朝廷之荣华,昭圣德之风化也。臣愚以为……既已案验举宪,宜及王辞不服,诏廷尉选上德通理之吏,更审考清问,著不然之效,定失误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广公族附疏之德,为宗室刷污乱之耻,甚得治亲之谊。”
有司奏请诛梁王立,其罪在于梁王与其姑园子有奸情。对此,谷永称《大雅·行苇》之诗文以辩之。而《毛诗序》曰:“《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即此诗乃言和睦宗族之事。对于所引诗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毛传》曰:“戚戚,内相亲也。肆,陈也。”郑《笺》云:“莫,无也。具犹俱也。尔谓进之也。王与族人燕,兄弟之亲,无远无近,俱揖而进之。”
《毛传》《郑笺》所言与《序》一致,即此诗乃言王与族人相亲相爱、和睦共处之情形。而谷永称此诗句,也在于明确并强调成帝与梁王间乃族亲、公族关系。将梁王之事与同宗的天子关联起来,然后在“为公族隐讳,增朝廷之荣华,昭圣德之风化”的基础上,论定梁王立之无罪。从而达到为梁王开脱罪责,免于治罪的目的。这种先称《诗》文以明确梁王与天子的宗族关系,再以《春秋》为亲者隐讳的经义断之无罪。其方式与董仲舒以《诗》治狱如出一辙。
此外,《汉书》卷八十三《朱博传》载谏大夫龚胜等十四人认为傅晏“干乱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计谋,职为乱阶,宜与博、玄同罪,罪皆不道”。其“职为乱阶”出于《小雅·巧言》,郑玄《笺》云:“此人主为乱作阶,言乱由之来也。”龚胜等当取其“为乱作阶”义,言傅晏乃乱之所由,属汉律之“造意”、“首恶”之罪,于法当诛,故言“罪皆不道”。此乃直接称《诗》定其罪。
由以上对汉代以《诗》断狱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从《诗经》所起作用的方式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诗》文为标准来判定某种定罪是否成立,如刘向、昌邑王条等;二是依据《诗经》来为罪行的判决建立某种条件,使这种条件成为断罪之依据,如董仲舒和谷永条。
第二,所涉案件,包括天子之废立事件(昌邑王),涉及王公大臣之生死事件(梁王、匡衡、傅晏等等),以及一般平民之案件等,皆与以《诗》决狱有关。由此可见出其在汉代的使用层面极为广泛。
第三,汉代以《诗》决狱现存材料,主要集中在西汉武、宣、元、成、哀时期,东汉此类用《诗》方式较少。
第四,“以《诗》决狱”一方面促进《诗经》在整个社会阶层中传播,另一方面则促进《诗经》的法典化,使《诗》由经典向法典的转化,进而使《诗》兼具经典与法典的特性与功能。这极大地提高了《诗经》在汉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