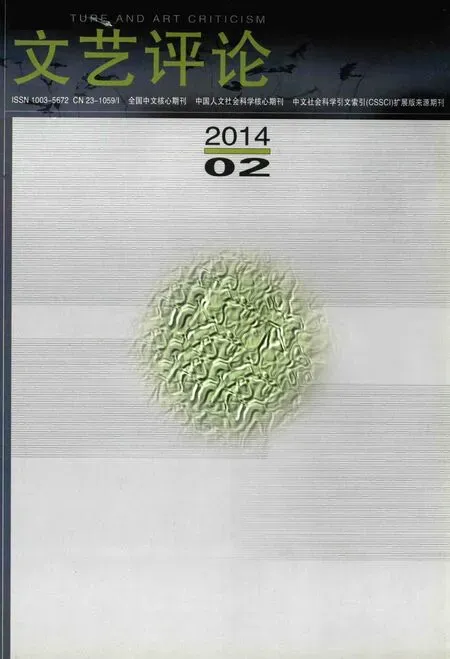曾燠扬州题襟馆考述
2014-09-29高政锐
高政锐
曾燠(1759—1831),字庶藩,号宾谷,江西南城人,清中叶著名诗人、学者。他初任两淮盐运使期间,标举风雅,奖掖后进,广交天下诗客。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建立了题襟馆。这是此前扬州盐官,如曹寅及卢见曾等,都未做到的。题襟馆是为往来杨州文士提供了生活和居住场所,也是曾燠公务之余与宾客诗酒唱和之地。自曾燠到达扬州后,扬州的文人雅集变成了常态,这种雅集主要是在题襟馆中进行的。可以说,题襟馆是乾隆五十八年后扬州文学发展的载体,题襟馆内任何一种生活状态,如观花、饮酒、品味美食等,都会催生诗人的创作。题襟馆优美的环境和充裕的物质条件,使宦游扬州的文人处于较佳的生存状态中。由此,也迎来了他们创作的旺期。
一、“题襟”源流考略
“题襟”一词,不见先秦典籍,亦不见汉魏六朝诸贤文集。《新唐书·艺文志》载有段成式、温庭筠等人的《汉上题襟集》十卷,即是以“题襟”命名一部文集,这是较早出现“题襟”语词之处。题者,书写也,襟者,襟怀也。“题襟”即抒写襟怀、表达情志之意,是文人意绪的诗意表达。晚清文人姚华在《论文后编·目录下》对“题襟”有清楚的剖析,“既而用宏于题襟,途广于赠答,语妙书工,旁开藻饰,镌崖锓木,涣衍寰区,巨可及于江山,琐亦周於厕溷。”可见,抒写襟怀、表达情志是建立在文人唱和基础上的。《汉上题襟集》属于文人唱和总集,《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八《经籍考七十五·总集》云:“《汉上题襟集》三卷,陈氏曰:‘唐段成式、温庭筠、崔皎、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唱和诗什,往来简牍。盖在襄阳时也。’”①由此可知,“题襟”是指在多人唱和中,文人对襟怀、理想的描摹和表现。清人汪师韩《诗学纂闻》亦云:“诗有数人唱和因继而汇为一集者,白香山与元稹、刘梦得有《还往集》、《因继集》……段成式、温庭筠、逢皎、余知古、韦瞻、徐商诸人之《汉上题襟集》是也。”②可以说,“题襟”一词是为多人唱和结集并命名而出现的。曾燠在扬州主编的《邗上题襟集》即属此例。
至清代,文人诗歌中的“题襟”,在诗酒之交的过程中有所升华,多指友朋之间的深情厚谊。清初著名诗人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之二有云:“肝肠迸裂题襟友,血泪模糊织锦妻。”《和东坡西台诗韵》共六首,为钱谦益在狱中所作,“题襟友”与“织锦妻”相对,且以“肝肠迸裂”为修饰,“题襟”已超越了文人间诗酒唱和的普通关系,上升为一种友朋之间的生死之交。曾为两淮盐官的曹寅有《程霱堂至诗以慰之》一诗,亦云:“暂止题襟泪,江乡近若何。”表达了友朋之间的离别之情,“题襟”蕴含着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
翻检曾燠幕府中诸多幕宾的诗作,多有言及“题襟”者,这自然与题襟馆中的文事活动息息相关,有的诗人在此基础上,将“题襟”代指为“朋友”,表达了对题襟馆生活的诚挚怀念。王芑孙有《真州院斋坐雨有怀题襟》一诗,云:
雨雨风风到此时,堕阶红惜海棠枝。遥闻旌斾方行部,好为江山与赋诗。官局恼人如恶酒,私衙留客似残棋。飘然一钵空云水,挂塔随缘我自嗤。
王芑孙在乾嘉诗坛颇有诗名,与曾燠交往甚密。他任真州书院教习期间,于嘉庆元年曾抵扬州小住,“两淮盐运使南城曾燠邀芑孙饮于题襟馆,并出示袁枚所赠宋文天祥绿端石蝉腹砚,嘱为赋诗。”③曾往来于题襟馆中的其他诗人,如吴嵩梁、吴锡祺等,亦与王芑孙过往甚密。《真州院斋坐雨有怀题襟》一诗即是对题襟馆短暂生活的感怀之作。“题襟”固然有指“题襟馆”之意,但其诗作中所流露出的人生失意、自怨自叹的情怀,分明是对朋友的一种倾诉,“遥闻旌斾方行部,好为江山与赋诗”是对题襟馆诗酒生活的追忆,“题襟”与其说是指建筑方位上的扬州题襟馆,不如说是指题襟馆中往来唱和的文人友朋,他们观花饮酒,赋诗赏石,谈笑风生的快意生活实是难得的友朋聚会。所以,王芑孙的“有怀题襟”,更多的是在怀念以曾燠为中心的题襟馆友朋。
二、《邗上题襟集》的刊刻与题襟馆的建立
《邗上题襟集》刊刻于乾隆五十八年十月,收录了曾燠与其幕宾的诗酒唱和之作。它的刊刻与题襟馆的建立,有着重要关系。曾燠幕府的幕宾王文治有《宾谷来扬州,一时名士唱和成帙,择其优者锓版以行,题曰〈邗上题襟集〉,兹复于衙斋西北隅筑题襟馆以实之,为赋两首》诗,从诗题上看,《邗上题襟集》刊刻在前,题襟馆修筑在后,而且,题襟馆的建立是受到了《邗上题襟集》的影响,它使文人雅集不仅有题襟之名,而且有题襟之实。王文治诗共两首,其一云:“汉上题襟事,骚坛喜再闻。古今虽异地,贤哲自为群。邗水秋风渡,平山日暮云。长空飞雁影,聊复点斜曛。”④该诗清雅而有韵味,把曾燠的扬州文事活动与温庭筠、段成式等的汉上题襟相对比,彰显了《邗上题襟集》刊刻及题襟馆建立的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
关于曾燠扬州题襟馆的建立,史载颇多。钱泳《履园丛话》载:
南城曾宾谷中丞以名翰林出为两淮转运使者十三年。扬州当东南之冲,其时川、楚未平,羽书狎至,冠盖交驰,日不暇给,而中丞则旦接宾客,昼理简牍,夜诵文史,自若也。署中辟题襟馆,与一时贤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简斋、王梦楼、王兰泉、吴谷人、张警堂、陈东浦、谢芗泉、王葑町、钱裴山、周载轩、陈桂堂、李啬生、杨西禾、吴山尊、伊耐园,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黄贲生、王惕甫、宋芝山、吴兰雪、胡香海、胡黄海、吴退庵、吴白庵、詹石琴、储玉琴、陈理堂、郭厚庵、蒋伯生、蒋藕船、何岂匏、钱玉鱼、乐莲裳、刘霞裳诸君时相往来,较之《西昆酬倡》,殆有过之。
叶衍兰《清代学者像传》云:
曾宾谷性爱才,宏奖风流惟恐不及。前后居扬州十余年,其地当水陆之冲,帆樯来往如此。先生为辟题襟馆于邗上,公余之暇,与宾从琴歌酒宴,无间寒暑,海内名流归之如流水之赴壑。
郭麐《灵芬馆诗话》言:
扬州自雅雨以后数十年来,金银气多,风雅道废,曾宾谷都转起而振之,筑题襟馆于署中,四方宾客,其从如云。今所传《邗上题襟集》是已。
张维屏在《国朝耆献类征》中云:
宾谷都转处淮扬靡丽之区,而澹于嗜欲,公事余闲时与宾从赋诗为乐,辟题襟馆于署后,周植花木为唱和之所。屈指官斯土者,国朝以来无虑数十辈,而若风吹网,所过无闻。独宾谷挟其纵横跌宕之才,以雄视乎当世,令人爱慕,比于香山、六一、玉局诸老,不其伟与?
以上所罗列的材料,充分说明题襟馆对扬州文坛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它也表露了关于题襟馆的若干重要信息。其一,往来于扬州的文人众多,题襟馆聚集了乾嘉之际大量的文化名流,他们觥筹交错,诗酒相连,互为影响,共同推动了清代文学的发展。其二,曾燠的个人文学雅好、爱才好士的性格及两淮盐运使的重要地位是题襟馆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曾燠少年颖慧,诗文创作颇佳,“童从宦,都下耆宿见其诗文,多折行辈与论交。”⑤早期的广泛交流为他领导扬州文坛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中叶的扬州因盐而兴,盐官的物质待遇极其丰厚,不乏有崇尚奢靡者,而曾燠能够热心于文事,公务之余与宾客唱和,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尚小明将曾燠幕府认定为诗人幕府,是有依据和道理的。其三,题襟馆的居住环境优美,适宜于诗人的往来唱和。王芑孙的《题襟馆记》曾记载,题襟馆前后种植花草树木,并且蓄养了五六只白鹤。扬州素以园林名闻天下,居所环境的优美也是文人对诗意生活的追求之一,自然环境同人文环境一样,对人的熏陶是潜移默化的。题襟馆“周植花木”,幽静淡雅,是文人宴集的理想场所,这对文人的创作,客观上会起到推动作用。其四,曾燠因题襟馆雅集而影响极大,时人不仅把他和王士禛、卢见曾相比,甚至比拟于唐宋时期的文坛巨擘白居易、欧阳修和苏轼。这自然是溢美之词,但其背后却表明了曾燠不可替代的文坛领袖地位。
题襟馆的风流雅事,不仅令居于题襟馆的士人感怀、留恋,即使没有来扬州的人,也对此赞赏不已。当时宦游京师的著名诗人法式善有《寄曾宾谷运使》一诗,云:
梅花阴薄山吐月,官阁吟声时未歇。十年饱看蜀岗云,一竿梦钓西溪雪。王扬州后卢扬州,谁能一字一缣酬。题襟馆大亦如舟,孤寒八百来从游。
法式善在诗中勾勒了曾燠在扬州十余年的行藏,并赞扬了他对孤寒之士的眷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题襟馆文事活动的影响,已不仅仅包括游历于扬州的诗人,还波及到了扬州以外的其它风雅之士,题襟馆已经成为扬州文坛的一个文化符号,扬州文学生态在曾燠的主导下,通过题襟馆这一有效媒介,继续向良性方向发展。
三、题襟馆文事活动述略
曾燠主政两淮盐业的数十年间,题襟馆以各种名目举行的文事活动从未停歇,扬州文人的创作由此渐入佳境。简而言之,题襟馆的文事活动包括如下几个方面,迎来送往的宴集,为前贤文人庆寿,对奇石等文物的妙赏,消寒的雅会以及对戏剧的观赏与品评等。下面择其要述之。
(一)题襟馆的送别活动及创作
在乾嘉文坛上,曾燠以爱才好士而著称。他任两淮盐运使的十三年间,往来于扬州的文人为数众多,曾燠皆能以诚相待,迎来送往,不废礼数。这种迎送的宴会,往往成为赋诗的重要场所,期间颇有佳作产生。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二十二有《送人之淮浦书寄频伽》一诗:
君到淮阳郡,为寻老复丁(频伽题所居曰老复丁庵)。吟多愁不减,酒薄睡常醒。寂寂题襟馆,迢迢檇李亭。一从江上别,杨柳几回靑。
该诗为曾燠题襟馆的送别之作,频伽即为郭麐,他曾于嘉庆六年游历扬州,与曾燠相见甚欢,亦作文对题襟馆加以褒扬。钱泳《履园丛话》记载了往来于曾燠题襟馆的一份很长的文人名单,郭麐包含在内。此诗作于曾燠在扬州的后期,其时,郭麐已离开扬州赴浙江,对于这个昔日共同诗酒相连的老友,曾燠在诗中表达了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思念之中有一种落寞和感伤,这虽是一首小诗,表现手法及所用意象也比较平常,却感情真挚,颇有诗味。
曾燠对来扬文人的深情,也深深感染了题襟馆的宾客,吴嵩梁在离开扬州后,曾作《京口舟中寄宾谷运使》一诗,描述了自己的生存状态,对题襟馆的生活不无追忆之感。其诗云:
别君题襟馆,三换霜与星。思君岂不劳,对酒云为停。江湖二十年,飘若风中萍。劳人故多病,安神求茯苓。衰亲况寡欢,念别先涕零。膝前一杯水,膳抵茧陔馨。吾发亦渐白,名山谁乞灵。才华悔虚掷,稍稍温旧经。以此百念俱,终岁柴门扄。卧看香苏山,江南无此青。
吴嵩梁是在题襟馆居住时间最长的文人之一,他曾先后两次居于题襟馆,第一次是乾隆五十八年,并参加了九峰园秋禊,数年后离开,又于嘉庆六年(1801)年来扬州,至少在题襟馆居住一年。第二次到扬州时,曾燠有《喜兰雪至》一诗,颇能看出两人的情谊,诗云:“渡江诗递到,君尚在人间。才子天宜惜,忧端我乍删。音书三岁少,风雪一身孱。转复愁多病,迎门审旧颜。(屡有传君死耗者,故云)”曾燠在扬州多次听人言及吴嵩梁的死讯,突然见到他,颇有“才子天宜惜”之叹,惊喜之情溢于言表。翻检《香苏山馆诗集》,吴嵩梁言及题襟馆的诗歌颇多,据此可以看出,他对题襟馆的雅居生活是极留恋的。与清代大多数沉沦下僚的士人一样,吴嵩梁晚年的生活状态颇不佳,年老多病,友朋分离,才华虚掷,意绪难平。以此反观吴嵩梁题襟馆的生活,则易知,居于题襟馆的时间或许是他人生最畅快的岁月之一。他的《别题襟馆》一诗则是一个明证,其诗云:
园花一千树,同植而殊科。灼灼桃李英,袅袅寄生萝。惠兰有本性,松桂无改柯。地气讵或偏,荣悴如君何。我如瘦梅树,生意苦不多。移根自幽磵,冰雪方峩峩。苦寒守孤芳,南枝笑蹉跎。病蕊倘一花,亦感春风和。
送别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一类重要题材,文人的送别诗大多表现对别离的不舍,对友朋的思念。吴嵩梁的别离诗则对此有所超越,他将自身沉重的生命历程蕴含于诗中,将宏大的人生体验与个体的人生离别相对接,他的诗歌呈现的是一种更复杂的悲凉意绪,既包含着别离的感伤,更蕴含着他人生的落寞和对孤寒之身的无法排遣。题襟馆的雅致生活与离开题襟馆后的现实际遇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越发使得这种悲凉意绪深厚而阔大。
(二)题襟馆消寒的文人雅会
扬州题襟馆中有史料可查的文人集会,一部分属于消寒的雅会,参加这种雅会的文人往往会有作品产生。嘉庆年间藏书家王端履在《重论文斋笔录》中云:“嘉庆甲子、乙丑间,同人岁为消寒雅集,集必征文献或出新意以为觞政,不能者罚以巨觥。”⑥这种行为颇似王羲之的兰亭之会,所谓消寒只是表象,其实质则是文人间的诗酒交流,借创作来抒发情志。清代文人的生活是雅致而富有情趣的,他们将日常生活的基本状态融入创作之中,使生活得以诗化;同时,他们的作品也是对生活的能动反映,是对生活的真诚记录或歌吟。
曾燠在题襟馆的消寒消暑之会上,吟咏颇多,其形式多样且题材较繁复,有的诗歌则是对理想的讴吟。曾燠《长至后四日,题襟馆消寒,小饮会者十四人。以“刺绣五纹添弱綫吹霞六管动飞灰”分韵得纹字》一诗云:
记得分笺写冻云(去年消寒会分赋雪诗),又看呵砚散冰纹。天涯岁月怜新鬓,汉上风流仿旧闻。诸道久劳横海将,五谷犹驻伏波军(时方捕海盗,湖南苗匪亦未平)。不能雪夜从擒贼,空策书生翰墨勋。
曾燠的时代,已到了康乾盛世末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出来,正如他诗歌中所自注的,海盗猖獗,湖南少数民族的起义此起彼伏,歌舞升平的盛世背后隐藏着重重危机。这自然不是曾燠所能解决的,在他的视域里,温庭筠及段成式的汉上唱和固然值得崇尚,但他更追羡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的精神在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这在乾嘉道的士人群体里是很少见的。
题襟馆的消寒雅集,文人创作更多的是咏物诗。咏物诗肇始于屈原的《橘颂》,此后即成为文人乐于创作的题材之一,曾燠创作有《消寒集题襟馆分咏》组诗,分别吟咏了寒芜、寒篷、寒寺、寒庖、寒笛及寒鸡,这种咏物诗的创作多以呈才为目的,少有诗人的真情实感,咏物更多的体现为诗歌创作的手段。如曾燠《铁箫吟消寒席上赋》云:
我得南星铁如意,狂歌水仙愁击碎。世间何物堪倚声,竹管匏笙不能吹。铁崖尝豢双铁龙,雌龙入海招其雄。千年干鏌两俱化,至今怒吼吴江风。玉鸾也复无消息,曾照广陵秋月白。广陵锻工摹影来,白鸾毛羽今变黑。芜城雪后风正饕,寒冰一条吾手操。弹指连珠五星见,当头明月三天高。便欲招呼箫史辈,翩然彩凤同游翱。元云之曲应天籁,世俗丝管空啁嘈。如意从今得朋庆,以之按拍声相应。池上蕤宾方响飞,江东高唱铜琶竞。此际官梅有芳信,吹彻箫声花欲迸。君不见道人铁脚诵南华,宰相铁心能赋花。
该诗极尽描摹之能事,把铁箫的形态及声音描摹得惟妙惟肖,充满了文化的张力。咏物诗的文学内核在于“不即不离”,或者说是“若即若离”,即在咏物的过程中,既要描写物体的基本特征,又要在此基础上有所升华,使诗歌有所蕴含、有所讽谏。以此标准来衡量曾燠的《铁箫吟消寒席上赋》,很容易发现这首诗是缺少情感与其寄托的。实际上并非曾燠没有寄托,相反,他是一个对生活、对社会及对官场都有深入思考的人,他只不过是没有在咏物诗中渗透自己的意绪,咏物诗成为了诗人刻意创作的一种手段或是工具,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诗人的有感而作。
在题襟馆消寒中,除了吟咏襟怀和呈才负气类的创作之外,更多的则是文人对日常生活的诗意表达,这种表达的背后则蕴含着诗人对现实的深刻思考。曾燠《赏雨茅屋诗集》卷二有《寒芜》一诗,云:“念念黄云近复遥,荒荒白草自飘萧。平田乍有孤鸿起,大道横来万马骄。频转尘沙风不定,暗霑衣履雪初消。明春绿徧经行处,忘记前村野火烧。”这也是一首咏物诗,却与《铁箫吟消寒席上赋》不同,诗中充满了萧索与惆怅,寒芜即是冬日的野草,对它的吟咏隐含着诗人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际遇,或者是包含着诗人思想深处的诸多隐忧。细品此诗,它与阮籍《咏怀诗》颇类似。曾燠被清人张维屏称为“热官冷做”之人,“‘热官冷做’是一种特有心态,构成这种心态的基因乃是宦海中人对时势运会的潜在感知。”⑦曾燠的隐忧是不无道理的,他晚年任两淮盐政期间,两淮盐业已衰弊不堪,他因无力回天而受到了道光皇帝的申饬,曾经的二品大员最终竟以五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卒于京师。
(三)对名砚、奇石观赏的文事活动
作为一个以诗文著称的地方官员,曾燠对名砚、奇石等具有浓厚人文意象的物品十分感兴趣,每有所得,则召集题襟馆宾客赏玩、赋诗。如前文所述,九峰园秋禊也是因为得到一枚兰亭春禊砚而举行的,王芑孙于嘉庆元年访扬州,曾与曾燠共赏文天祥的绿端石蝉腹砚,二人皆有诗作。曾燠以这些名砚或奇石为吟咏对象时,往往会产生林泉之志。他有《石琴以诗遗小砚山次韵奉谢》诗二首,云:
缥缈峰皴孤,玲珑窍吹万。下临紫石潭,波影骇龙噀。救我书田荒,夜来雨三寸。
君已恋泉石,云程息九万。(石琴不赴公车)我犹困风尘,归耕无下潠。一诵小山篇,幽期讬方寸。
这是两首赠答诗,诗中的石琴即是詹肇堂,曾参加九峰园秋禊,后居于题襟馆。第一首是对砚台外形的生动描摹,从形状、色彩及用途着眼,比喻生动,联想丰富,一块普通砚台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第二首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引申,“我犹困风尘,归耕无下潠”是清代士人普遍具有的归隐之思,“下潠”典出于陶渊明,陶渊明有《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一诗,诗中有“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一句,归隐之意极明。
曾燠这种隐逸情怀是有原因的。清代士人始终在仕与隐中徘徊,江湖上的文人固然追求入仕,而他们一旦进入仕途,则又以归隐为念。这种隐逸心态与其人生际遇相关,更是为了缓解官场上的压力。在清代,陶渊明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他所代表的的隐逸精神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行为力量,一直感染着广大士人。于是,陶渊明成为清代文人极力尊崇的前贤,曾燠《赏雨茅屋诗集》卷十二载有其和陶诗,题为《岁暮和渊明次韵》,诗云:
日日观日驭,曲阿必虞泉。四时会岁暮,老至余何言。知命宜乐天,但苦人事繁。省躬多不逮,竭虑恒有愆。知叟笑愚公,颓龄欲移山。安能如岁运,明旦春复还。渊明浩荡人,不宜为俗缠。抚已亦增慨,素顏思盛年。常年饮屠苏,每饮情屡迁。若为后视今,把盏心茫然。
曾燠此时的心态是复杂的,面对时间的流逝,既为公务人事所困扰,又为无所适从所忧虑。但他认为“渊明浩荡人,不宜为俗缠”,却终究没有摆脱世俗的决心,这也是清代士人的普遍心态。所以,士人在进行文事活动时,时时产生归隐之志,是对他们想做而有无法实现的隐逸思想的一种慰藉。
题襟馆观砚、赏石的文事活动,体现了清代士人雅致的生活状态,具有鲜明的文化意义。它对文化的传承及文物的记录与保存,更是弥足珍贵。曾燠《赏雨茅屋诗集》卷四《黄石斋先生断碑砚歌》云:
衢州尺土非其有,湖州片石藏谁手?此是黄公不转心,百年未与秦灰朽。残瓦断碣公摩挱,爱他妙墨存东坡。东坡文字得迁謫,公亦危言婴祸罗。抱璞区区成一哭,墨花皱染蛮烟绿。幕府勤劳玉带生,孤臣心迹桥亭卜。公之前辈王文成,一段碑曾题驿丞。(王文成有墨妙亭碑一片,题曰驿丞署,尾砚盖谪龙场时所得。)盘错偶然成利器,鼎鐘因得共勋名。石友遭逢亦何定,乌乎经济需时命。我朝褒谥黄忠端(高宗纯皇帝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黄公蒙赐,谥忠端。),当日平台斥为佞。
该诗前有诗序,曰:“坡公题《墨妙亭诗》断碑一片,广三寸七分,长三寸四分。存十六字,凡四行,一行曰‘吴越胜事’,一行曰‘书来乞诗’,一行曰‘尾书溪藤’,一行曰‘视昔过眼’。以背面作砚,右偏之上刻‘断碑’二隶字,下刻‘道周’二字,印篆左偏刻竹垞铭,曰‘身可污,心不辱。藏三年,化碧玉。’为八分书。予得之广陵市上。”曾燠吟咏的是黄道周的断碑砚,黄道周是明末学者、书画家,因抗清殉难。
曾燠的吟咏及题序包含了很多的重要问题,其一,曾燠在诗中对黄道周及断碑砚命运的感叹,也包含着对自身命运的深刻感知。“石友遭逢亦何定,乌乎经济需时命”虽包含着一种宿命感,实际却是对命运无法把握的慨叹。其二,黄道周断碑砚在清中叶为曾燠所得,这种记录是极有价值的,使得此砚的流转有迹可循,后此砚为清后期戏剧家黄钧宰(约1826—1895)所得,黄钧宰在《金壶七墨》“断碑砚”条下曰:“家兄仲勤以千钱购断碑砚一方,背镌十六字,书法遒劲。平列四行,第一行曰‘吴越胜事’,次行曰‘书来乞诗’,再次曰‘尾书溪藤’,曰‘视昔过眼’。即售者亦不辨为何语。他日读坡公《墨妙亭诗》,适与前字相合心焉,疑之。及阅《秋雨盦随笔》,乃知为黄公石斋之砚,所刻果是苏诗。曾宾谷都转尝得之广陵市上,并载右偏有道周篆印,左有竹垞铭语。均剥蚀不可辨,以黄氏故物历今二百余年,仍归吾家,可喜也。”⑧坊间尚存黄道周断碑砚,只是没有权威专家鉴定真伪。但依据黄钧宰“均剥蚀不可辨”的记录,此砚可能系伪造。
四、题襟馆与扬州文人的生存状态
居于题襟馆的文人大多为寒士,曾燠依靠的两淮盐业庞大的经济资源,为他们提供了居所和日常生活资源,由是,他们的创作和生存都进入了较佳的状态。
(一)曾燠的经济实力与寒士的生存状态
由于个体生命际遇不同,出身条件及人生追求不同,特别是科考的命运不同,清代士人的生存状态是千差万别的。但就某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如行走于江湖的布衣群体,他们则具有一种普遍的人生志向和共同的人生追求,对贫寒的抗争,对人生的思考,对痛苦的宣泄,构成了他们悲凉的人生底蕴。清代中叶,一部分下层寒士已经贫乏而不能自存,对官宦势力的依附已经成为生存的常态。这种行为使得文人能够聚拢到一起,同声相和,同气相求。文人的基本生存得到了保证,创作也就有了向上的空间,但这有与其所处幕府的幕主提倡有关。清人钱泳说:“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之与朱检讨,国初之提倡也。沈文悫之与袁太史,乾隆中叶之提倡也。曾中丞之与阮宫保,又近时之提倡也。”[5]生存上的保障与创作上的支持,使这些寒士得到了暂时的安歇,其生存状态亦进入佳境。曾燠扬州的题襟馆就是为寒士提供这种生存状态的一个场所,正如法式善所说,“题襟馆大亦如舟,孤寒八百来从游。”
曾燠题襟馆聚集了嘉道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诗人,尤以寒士居多。若没有官宦的依靠,其生存堪忧。郭麐在《樗园销夏录》中记录了他求馆之遭遇:
庚戌岁,余游金陵,将求一馆,以为负米之养。当路贵人皆素相识者,莫为力。旅食半载,困而归。中寄家书,不敢明言,恐贻老母忧。典衣寄银,云出自馆谷,或不足。
这是发生在乾隆五十五年的事,以郭麐之才求一馆尚不可,可见在清中叶,寒士的生存环境是极差的。郭麐于嘉庆六年来扬州进入曾燠题襟馆,并与陆继辂、乐钧为文酒之会,当年典衣寄银之事如过往云烟,不复存在了。
为游历于扬州的文人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需要庞大的经济支撑,在扬州,只有任两淮盐运使的曾燠能够做到这一点。据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考证,“在十八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盐运使实际上是该城(扬州)以及扬州府最有权势的官员。其衙署占据了新城的好几条街道,里面除了他自己以外,还有四名署官、十名吏目,以及大量编外人员。”⑨曾燠担任两淮盐运使时,其养廉银为每年2000两,而这个职位在乾隆初年养廉银曾高达每年6000两。曾燠的养廉银虽然比前任低,但仍是很可观。题襟馆重要幕宾乐钧曾云“东南财赋重盐差,金多最足征风操。”⑩清人李兆洛(1768-1841)在《养一斋文集》中曾对文人游幕及扬州的经济条件有所陈述:
邗上当雍正、乾隆间,业盐者大抵操赢,拥厚资,矜饰风雅以市重,一时操竽挟瑟,名一艺者寄食门下,无不乘车揭剑,各得其意以去。至嘉庆时而盐贾亟亟,自顾不暇,无复能留意翰墨。
李兆洛虽然以两淮盐商为考察对象,但足以看出乾隆年间,扬州经济富庶,文人往来众多,文事极其繁荣。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嘉庆朝,即在曾燠担任两淮盐运使期间,扬州盐业已在走下坡路,从扬州盐商的情况和曾燠的养廉银数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尽管如此,曾燠仍然占据着庞大的经济资源,他已无力像卢见曾那样举行大规模的虹桥修禊,但建立题襟馆,为来扬文人提供片瓦之居,是没有问题的。
(二)题襟馆文人的生活意绪与人生思考
居于题襟馆的文人,其表面生活是快意的,充满了轻松与愉悦。这与曾燠的爱才好士有关,也说明文人对官宦的依附性已经相当稳定,在心态上,他们对彼此之间的主客关系是认可的。但在他们思想深处,却对自身人生的忧患无法释怀,一时的轻松与快意无法消去内在的困顿与不堪。重要的文人雅集自然需要赋诗,即使一次偶然的美食,也会让诗人诗兴大发,并浮想联翩。吴嵩梁《食黄獐同宾谷都转赋》诗云:
将军射生致佳贶,使者召客开官庖。黄獐作脍美无匹,缕金细切堆盘高。题襟馆外冻云合,积雪成海铺银涛。今夕何夕不痛饮,孤负二分明月寒梅梢。君不见羊羔美酒党太尉,美人如花共沉醉。又不见残杯冷炙杜陵客,牛肉一饱死亦得。我生幸未沟壑填,老饕赋就空馋涎。文章自喜亦何用,聚散无端真可怜。明日雪晴雕满天,诸公射猎临甘泉。山名彩旗十丈翻,云烟劲弓怒发三。獐连热血一斗饮,马前壮哉且赋城南篇。
吴嵩梁在诗中对黄獐美食做了精致的描摹,“黄獐作脍美无匹,缕金细切堆盘高”,写出了题襟馆宾客饮食的奢华,时值寒冬,室外云低雪积,室内则温暖如春,面对此情此景,惟有痛饮才能一展胸怀。但黄獐与美酒只能满足一时的快意,诗人人生的创痛在酒后表现得更加分明。吴嵩梁在诗中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宋人党进,宋代无名氏《湘湖近事》载,“陶谷学士,尝买得党太尉家故妓……妓曰:‘彼粗人也,安有此景,但能销金暖帐下,浅斟低唱,饮羊羔美酒耳。’谷愧其言。”又举了诗圣杜甫的例子,言其“牛肉一饱死亦得”。一富贵,一贫穷;一官宦,一文人。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吴嵩梁酒后的人生意绪,正所谓是“文章自喜亦何用,聚散无端真可怜。”曾燠题襟馆只能给文人提供一时的居身之所,至于人生的坎坷与困苦,个人理想的张扬与实现,还需要他们自己去处置。
洪亮吉与王芑孙都曾作过《题襟馆记》,洪亮吉并未参加题襟馆的唱和,所以他的《题襟馆记》在描写题襟馆诗酒生活的同时,主要是对曾燠主持风雅的赞誉。王芑孙的《题襟馆记》却蕴含着个人的深刻思考,其文结尾曰:
昔班孟坚氏记丞相客馆,自公孙宏以后废为车库马厩,其事盖亦人世废兴之常然,余考之,竟汉世未有能复者。矧此区区题襟一馆,固前转运使之车库马厩也,即由车库马厩而为今日之馆,奚遽不由馆而复为异日之车库马厩?以天地无终极视之,盖其为车库马厩之日长,而其为题襟馆之时暂也。然而以宾谷为之,则题襟馆之在天地间,将必不以车库马厩为存亡。夫有其不与车库马厩为存亡者,则题襟之馆不可以无图。而余之记题襟馆,又何可无言也哉?于是乎书。
王芑孙的视野是宏阔的,他把题襟馆放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轴上,推演题襟馆的兴衰,对题襟馆存在能否永恒的思索,实际上是对文人命运的极大关注。类似于题襟馆一类的文人馆舍的兴衰是文人的命运好坏的晴雨表。西汉公孙弘的丞相官舍,在公孙弘去世后,即沦为车库马厩,文人自然没有了栖身之所,那么,题襟馆的命运又该如何呢?当个体命运面对历史的兴衰,个人的不平、悲叹乃至仇怨都变得平淡,这或许是理性意识对人生的积极作用。
王芑孙对曾燠的标举是有道理的,题襟馆自建立后,一直到曾燠离开扬州,它始终接纳着往来的宾客,承载着扬州文学的兴衰。题襟馆成为众多往来于扬州文人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驿站,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永远停留在他们的意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