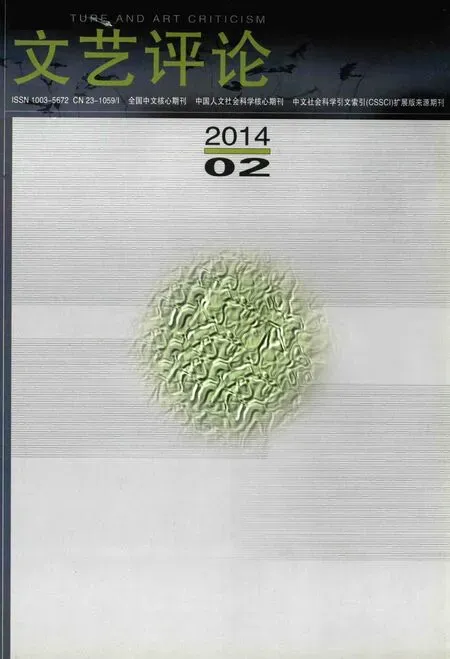癫疾与八大山人的怪诞绘画
2014-09-29陈玉强
陈玉强
八大山人(1626—1705),姓朱名耷,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清初文人画大师,明亡后,出家为僧,后患癫疾。八大山人疯癫之前,画风省净恬淡;疯癫之后,画风渐趋狂怪,开始出现怪鱼、怪鸟等怪诞图像。癫疾影响了八大山人的绘画创作,对此,美国学者高居翰已有论述①,但对癫疾影响八大山人绘画的机制,未有深入探讨。本文以传统中医学及现代精神病症状学为视角,分析八大山人癫疾的症状,进而探究癫疾对其绘画的影响机制,有助于诠释八大山人怪诞画风的成因。
一、八大山人癫疾的症状
从现有史料看,八大山人曾于1678年、1680年两次癫疾发作②。八大山人第一次患癫疾的情况,裘琏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夏天的《释超则诗序》有记载:“又二三年,予再游临川,闻雪个病颠,归老奉新。予疑其有托而云然。”③根据汪世清的考证,裘琏再游临川是在已未(1679)春天,这时听闻八大山人病癫的消息。八大山人病癫必在戊午(1678)初夏以后,已未(1679)年初以前,约言之,在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④。但裘琏对八大山人病癫的传闻,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八大山人可能是佯狂;他对八大山人癫疾的症状也没有描述。
1680年,八大山人在临川第两次癫疾发作。邵长蘅《八大山人传》记载道:
临川令胡君亦堂闻其名,延之官舍。年余,意忽忽不自得,遂发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还会城。独身猖佯市肆间,常戴布帽,曳长领袍,履穿踵决,拂袖蹁跹行,市中儿随观哗笑,人莫识也。某侄某识之,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⑤
邵长蘅《八大山人传》是他在北兰寺会晤八大山人后所写。此次“发狂疾”是八大山人向邵长蘅亲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邵长蘅详细描述了八大山人在临川突发癫疾的症状:哭笑不止,踄跔踊跃,撕烧僧服,出走远行,披长领袍,穿破烂鞋,鼓腹高歌,蹁跹起舞。从现代精神病症状学分析,八大山人出现了精神病患者的行为障碍,比如衣裳倒错症、仪表不整、破坏行为、冲动行为、出走、漫游症⑥。
传统中医学对于癫疾的研究由来已久,《黄帝内经》所论癫疾的证类颇多,归其大类,约为三证:阳盛癫狂证、阳虚癫狂证、气逆癫痫证。《灵枢经·癫狂》谓癫疾“喜忘,苦怒,善恐”,“狂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素问·阳明脉解篇》又谓癫疾“病甚则弃衣而走”,《素问·厥论篇》“癫疾欲走呼”,这些症状描述与八大山人的病情是吻合的。传统中医学认为有火盛阳亢病性特点的癫疾,就是阳盛癫狂证。《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诸躁狂越,皆属于火。”《古今医统大全·癫狂门》:“癫狂之病,总为心火所乘,神不守舍,一言尽矣。”作为明宗室遗民,八大山人憎恨清廷,汨浡郁结,火盛阳亢,无法排解。从其癫疾症状看,八大山人当是患上了阳盛癫狂证。
八大山人的两次癫疾,都很快治愈。然而,癫疾依然对他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良影响。由于癫疾,八大山人出现了语言功能障碍。传统中医学认为瘖哑是由于阳气入中所致。《素问·脉解篇》:“所谓入中为瘖者,阳盛已衰故为瘖也。”王冰注曰:“阳气盛入中而薄于胞肾,则胞络肾络气不通,故瘖也。胞之脉系于肾,肾之脉侠舌本,故瘖不能言也。”八大山人患阳盛癫狂证,阳气入中,又致瘖哑。有学者认为八大山人患有遗传性哑疾,这种说法不正确。陈鼎《八大山人传》记载八大山人:“父某,亦工书画,名噪江右,然喑哑不能言。甲申国亡,父随卒。人屋承父志,亦喑哑。”⑦陈鼎认为八大山人有遗传性哑疾,但陈鼎晚生一百余年,未见过八大山人,他所据的传闻并不可信。1677年秋天,八大山人到进贤介冈菊庄拜会饶宇朴,为《个山小像》求跋。饶宇朴的跋记载八大山人:“丁巳秋,携小影重访菊庄,语予曰:‘兄此后直以贯休、齐己目我矣!’”时年八大山人52岁,语言功能正常。但1680年八大山人第二次癫疾发作后,他的语言功能受到影响。1690年邵长蘅作《八大山人传》,记载他与八大山人“夜宿寺中,剪烛谈,山人痒不自禁,辄作手语势,已乃索笔书几上相酬答”⑧,此时八大山人已有明显的语言功能障碍,不得不借助手语与笔书。
二、从癫疾到佯狂
八大山人究竟是患癫疾还是佯狂,已有的研究各执一词⑨。从现有史料看,八大山人1678年那次癫疾存疑,但1680年患癫疾,则确定无疑。疾愈后,八大山人为避祸又装疯佯狂。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记载八大山人“既而蓄辫发,往往愤世佯狂”⑩,蓄辫发还俗是八大山人第二次癫疾痊愈之后的事情;而龙科宝与八大山人有过交往,他的说法有较高的可信度。这表明八大山人疾愈后,依然佯狂。
所谓佯狂就是装疯。1682年,八大山人《春瓮》诗:“若曰瓮头春,瓮头春未见。有客豫章门,佯狂语飞燕。”⑪八大山人遇见不愿意交谈的人,就装疯佯狂与天空中飞行的燕子说话。八大山人之所以佯狂,与他的自身处境有关系,他是明朝宗室遗民,有亡国丧家之痛,不满清廷,又无力反抗,只能佯狂避世。1682年,八大山人《毕瓮》诗:“深房有高瓮,把酌无闲时。焉得无闲时,翻令吏部疑。”⑫八大山人之所以喜欢醉酒,是因为他怕清醒时遭受官府怀疑。可见,八大山人佯狂避世是为了避免清廷的怀疑与迫害。正如邵长蘅《八大山人传》所言:“山人胸次汨浡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如湿絮之遏火,无可如何,乃忽狂忽喑,隐约玩世,而或者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浅之乎知山人也。”⑬
八大山人佯狂有不得已的苦衷,并非乐事,但佯狂必然会使他回忆起曾经病癫时的精神状态。如果八大山人不患癫疾,他纵然佯狂也无法体验病癫时的精神状态;如果八大山人患癫疾一直不愈,他也无法进行绘画创作。由癫疾到佯狂,令八大山人在较为理性状态下体验曾经的疯癫状态,对他的绘画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八大山人的题识、钤印映证了疯癫体验对他绘画创作的影响。1677年,八大山人《梅花册》中出现了“掣颠”印章,在《个山小像》戊午(1678年)中秋后二日自题下也钤有“掣颠”的白文长方形印。从语源上看,“掣颠”是禅语。《五灯会元》曰:“师掣手便去。临济一日与河阳木塔长老同在僧堂内坐,正说师每日在街市掣风掣颠。”⑭“掣”解为“抽”,所谓“师掣手便去”,即师抽手便去。可知,八大山人所谓“掣颠”,就是抽颠,表明他的画作与癫疾存在关联。“掣颠”并非制止疯癫,而是驾驭疯癫为艺术创作服务。1701年,八大山人题石涛《兰花》曰:“苦瓜子掣风掣颠,一至于此哉!”⑮所谓“掣风掣颠”意谓抽风抽颠,是称赞石涛画作的狂怪风格。“掣颠”不无禅宗的影响,也与八大山人的癫疾有联系,他正是借助疯癫体验,对绘画创作进行了彻底的变革。
八大山人经常以酒为引,沉入疯癫体验中,然后绘画。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亲眼看到八大山人痛饮后绘画,“旁有客乘其余兴,以笺索之,立挥与斗啄一双鸡,又渐狂矣”⑯。邵长蘅《八大山人传》提到八大山人喜饮酒后作画:“饮酒不能尽二升,然喜饮。贫士或市人屠沽邀山人饮,辄往,往饮辄醉,醉后墨沈淋漓,亦不甚爱惜。”⑰陈鼎《八大山人传》评曰:“山人果颠也乎哉,何其笔墨雄豪也!余尝阅山人诗画,大有唐宋人气魄。至于书法,则胎骨于晋魏矣。问其乡人,皆曰得之醉后。呜呼!其醉可及也,其颠不可及也。”⑱借助于疯癫体验,八大山人创作了一系列意味深远的怪诞绘画,在清代文人画中独树一帜。
三、疯癫体验对八大山人绘画的影响
疯癫是人类极端、边界的精神状态,疯癫之中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绘画创作;疯癫体验则是对曾经疯癫经历的回忆与假想,却有助于激发画家的想象力。福柯认为疯癫体验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最好的想象⑲,杰米森描述了疯癫体验带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⑳。八大山人经历疯癫后,创作了大量风格怪诞的作品,这并非孤立的文艺现象。1888年,荷兰画家凡高(1853—1890)在疯癫中割下了右耳,此后他的画作《星夜》(1889)、《丝柏》(1889)、《丝柏与群星》(1890)、《群鸦乱飞的麦田》(1890)以扭曲旋转的星云、夸大变异的星光、橙黄如桔的月亮、墨绿如焰的柏树,构成了迥异于现实的幻象。凡高是在发病间隙作画,八大山人则是病愈后佯狂作画,疯癫体验对于他们的艺术想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精神病症状学的研究表明,疯癫者描述外物不循常理,他们对物体的幻想在数量、大小、形状、空间及时间关系上会发生改变㉑。八大山人在佯狂中形成疯癫体验,激发了想象力,创造出一系列改变形状、大小及空间关系而又独具审美意蕴的艺术形象。
第一,八大山人笔下的动物形象产生了形体异化。1684年《个山杂画册》中的兔㉒,形状怪诞,兔身似驴似马又似牛,兔眼则像熊猫眼,除了两只耸立的耳朵还表明兔子的属性外,兔身无一处似兔。这种“兔非其兔”呈现出一种异化感,似乎是八大山人“人非其人”、自身异化的一种象征。作为明宗室遗民,八大山人的身份不容于清廷,他是一个异类。异化主题在八大山人的画作中频频出现。《鱼轴》中,鱼身似山,宛如石化,右上角有题名“稚震”的跋:“此等笔墨,近世罕有,人莫能识,不意在徐青藤后复有一徐先生在也。”㉓徐渭也曾患有癫疾,且画风狂怪,稚震评八大山人乃隔世之徐渭,正着眼于此。然而细加品味,两人画风又有区别:徐渭画作狂放恣肆,迸发出难以扼制的激情;八大山人则背负了更多的愤世嫉俗之情和国破家亡之痛,他的画作更为安静、内敛,多以变形夸张的手法,在花木鸟兽身上融进主观的象征性蕴含。比如八大山人对动物形象的石化表现,颇为多见。《鸟石图页》㉔中,立于岩石上的鸟与岩石融为一体,而岩石又似展翅之鸟,鸟与岩石形成了有意味的比照。《猫石图轴》㉕中,两只猫分卧于一高一低的石头上,猫身与石头融为一体,只剩下匍匐于石上的猫首依稀可见。这种石化不是天人合一式的静穆自在,而是强迫性的异化,透露出荒诞与无奈。
郑板桥《靳秋田索画》曾经比较过八大山人与石涛的画风:“然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何哉?八大纯用减笔,而石涛微茸耳。”㉖八大山人名声胜过石涛,因为前者使用“减笔”,而后者“微茸”。所谓“减笔”是对事物自然面貌的有意删减,形成“有意味的形式”。八大山人1693年《书画册》中有一幅竹石图㉗,画中只有几片无枝的竹叶,石头一片墨色,不可辨识,款题“涉事”。无枝的竹叶似乎隐喻八大山人失国丧家的无根心态,黑不可辨的石头似乎象征乌云般的政治环境。《鸟石图页》㉘中,一条鱼硕大无比,瞪眼向人,最为怪异的是鱼鳍、鱼尾用墨笔晕成,一片模糊。乍一看,这条鱼好像从尾部开始燃烧,化成一团墨汁消融于水中。这条鱼的残败,体现出八大山人绘画的异化主题,因为鱼之不能容于水,好比八大山人不能容于清廷。
第二,八大山人画作改变了事物的大小关系。他擅长利用不恰当的比例来隐喻现实的不合理。1695年《鱼鸟图轴》㉙中,岩上一只瞪眼鸟,岩下两条一大一小的瞪眼鱼,大鱼占到整幅画宽,与岩石不成比例,似乎象征着世界的荒诞与不协调。1700年《椿鹿图轴》㉚中,岩石比鹿的身体还要小,鹿立于其上,两眼瞪大,不知所措,似乎隐喻着八大山人明宗室遗民身份难以立足的尴尬。1694年《书画册》中有一幅竹石图㉛,危岩之下的几棵竹子矮小如同小草,压弯身姿,似乎象征清廷的压迫与八大山人的弱势。八大山人画水仙㉜,宛如巨树,硕大无比,占据整幅画面,高大远远超过其后的山峦;画“灵芝”㉝孤零零地立于画中,巨大无比;画“玉兰”㉞也占满整幅画面。水仙、灵芝、玉兰这些植物在中国古代象征着士人傲岸的精神,八大山人放大比例的描绘,是他主体精神高扬的象征和狂傲性格的隐喻。
第三,八大山人画作改变了事物的空间关系。1689年《竹荷鱼诗画册》,四条鱼在空中飞行,题识曰:“从来换酒金鱼子,户牖平分是一端。画水可怜三五片,浔阳干过两重山。”㉟画中连“三五片”水都没有,鱼飞行空中,极为荒诞,有着极深的寓意。国破家亡的八大山人正如同这条离水之鱼,被悬置于空中。1689年《瓜月图轴》,本在天上的月亮却被放置在地上与西瓜并排,题识:“昭光饼子一面,月圆西瓜上时,个个指月饼子,驴年瓜熟为期。”㊱将月亮喻为饼子,与西瓜并列,这种空间关系十分怪异。
第四,八大山人画作存在不恰当的事物组合。“鹰蟹图”㊲中,一只鹰立于岩上俯视岩下的一只蟹,蟹则张螯向鹰,这种对抗与搭配荒诞无比,似乎象征着八大山人与环境的不协调与不妥协。1694年《晚安册》中的瓶花图㊳,瓶身满是裂纹,如同僧人的百衲衣,瓶子尚不知存在多久,插于瓶中的枝叶更是前景不妙,正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上述画作对事物常规形状、大小、空间关系等的改变,体现出八大山人独特的艺术想象力,而艺术想象力的激发又与他的疯癫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没有佯狂而致的疯癫体验就不会产生八大山人晚年的怪诞绘画。
八大山人疾愈后的画作虽然狂怪,但充满冷静与隐喻。他将疯癫体验融入绘画图像中,图像的意蕴则是他的理性体现。疯癫体验对于时空、形态的改变有助于八大山人在绘画中展现他一贯的异化主题。1693年鱼鸟图卷中,两只鸟立于石上,一条鱼则在天空游弋。画中有八大山人的三段题识,左下角的题识为:“东海之鱼善化,其一曰黄雀,秋月为雀,冬化入海为鱼;其一曰青鸠,夏化为鸠,余月复入海为鱼。凡化鱼之雀皆以肫,以此证知漆园吏之所谓鲲化为鹏。”㊴八大山人认为鱼、鸟互相异化,夏天鱼化为青鸠,秋天鱼化为黄雀,其他月份鸟又入海为鱼。另外两段题识,一段是说沈约因为博学而得“隐囊”的称呼,八大山人“品意”而作此画;另一段题识则解释了八大山人画作中所题“涉事”二字的由来。王二画石、大戴画牛求形似,而八大山人的画只曰“涉事”,强调图像的指涉性和象征性。这三段题识证明了八大山人画作中的图像大都是有所指涉、有所象征的,这也是我们解读八大山人画作意蕴的逻辑起点。正因为八大山人认为鱼和鸟存在互相转化的情况,所以他的鱼鸟画就别具意味。八大山人的鱼鸟图大都是岩上鸟与岩下鱼的对望,不同时空、不同形态的鱼鸟共居一处,互相瞪视,宛如前生与今世的对望,荒诞而有哲理。
结语
八大山人罹患癫疾,痊愈后,为避祸又装疯佯狂。佯狂是对疯癫的戏剧性模拟,导致对事物的正常形状、大小及时空关系的扭曲性体验,这对于绘画结构外物的方式有着积极意义。八大山人笔下怪诞的动植物改变了其自然属性,本质上是一种幻象,是他的观念载体、本质体现及灵魂隐喻,蕴含着他对意识形态的指控。福柯说:“艺术作品与疯癫共同诞生和变成现实的时刻,也就是世界开始发现自己受到那个艺术作品的指责,并对那个作品的性质负有责任的时候。”㊵八大山人的怪诞绘画可以看作是他对清廷的指控,是“一种似乎被世界所湮没的、揭示世界的荒诞的、只能用病态来表现自己的作品”㊶。明朝的覆灭及清廷对明宗室遗民的迫害,对八大山人的内心产生了难以磨灭的消极影响,其怪诞绘画的图像喻义、结构方式有着反意识形态的意义,故而不能把八大山人画作中的怪诞图像视为精神病的涂鸦。
八大山人经历疯癫后,满腔苦涩、悲愤与孤寂,在艺术领域里得到了释放,疯癫体验与意识形态指控融为一体,形成了八大山人狂放不羁、冷纵怪异的画风,从而将清代文人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