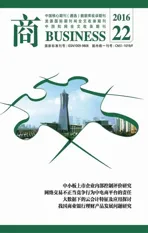话说启蒙
2014-09-28刘静
刘静
一,何谓启蒙。
何谓启蒙,启蒙一词,最早见于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84年11月发表的题为《什么是启蒙》。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人们对原有的自己的一种状态的摆脱和超越。人们不满意自己的一种不成熟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理性和勇气去摆脱这种状态,要摆脱这种状态总是要借助于他人的力量,自己的知性也不能充分的得到发挥。所以,康德明确提出口号:勇于使用自己的理性。紧接着法国哲学家福柯就发表了明确讨论启蒙的文章《什么是启蒙》,他从整个欧洲的发展来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启蒙,更不要将启蒙归为一件独立的事情,他是处于欧洲社会发展中的一种持续。我们再看看美国学者的解释,托马斯·奥斯本在其著作《启蒙面面观》作如是说:“从最宽泛、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启蒙指的是将理性应用于人类事务。启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首先在自由的名义下,理性被运用于人类既存现实的各个方面。”翻开《辞海》,我们可以看到这样解释启蒙:“开发蒙昧”。首先,他是一种自主自觉的行为,是人自身意识的觉醒,是要让人重新审视自己,达到身与心的双重自由;其次,启蒙是让人看到外面,看到外面的光和外面的世界,了解事实的真相,让人去书写人的历史,摆脱神的桎梏。欧洲在启蒙运动之后,诞生了伟大的现代科学,民主和自由响彻天空,制约人们几千年的神学思想开始动摇,民主和自由取而代之,人的解放和个人的觉醒空前高涨,随之而来的英法革命,更使得传统的专制制度得到空前的挑战。
李慎之在《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中说到:“五四的精神是启蒙。而所谓启蒙,就是中国人真正抛弃禁锢了几千年的思想,抛弃传统思想中的糟粕,抛弃专制和蒙昧。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以现代知识来‘重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的‘一种新态度”。五四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他启蒙了一批中国的先驱,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吹响了中国民主的号角。
二,三种声音。
需要强调的是,“五四”在这里是作为一种广义的概念而指的,非狭义的单指“五四运动”而言。傅国涌在其著作《真正的五四是什么》中这样说到:“我们不能将五四看做一个单独的概念,真正的五四绝不是孤立的,也不可能仅仅只是指1919年那一场上街游行示威的学生运动。五四是一个跨越性的概念,他代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时期,从1914开始至1925结束这样一个大概十年的历史进程。在这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到了最关键的转折期,而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不管是政治还是文化的发展,都到了一个重要时期。所以,我们可以说,五四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的启蒙时期,發渊于思想文化领域,继而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长期以来,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对“五四”启蒙精神的解读在我国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在激进主义者看来,五四的首要任务和精神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学生运动,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而另一种激进主义的声音来自毛泽东。他在其著名的《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都对五四运动做过一定的阐述。他认为,五四运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他的革命精神同样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首先打响的新文化运动和后期不断掀起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都是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的。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是一场革命的运动,他反对政府的卖国行为,他的目的具有革命性”,“五四运动代表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文化革命的角度,“五四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而对封建主义文化所进行的批判是伟大而彻底的,是超越任何一次的文化革命的,是彻底反对旧道德和旧文学,积极提倡新道德和新文学的伟大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分成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派别,不同于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以胡适、蔡元培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则显得温和得多。与激进主义凸显政治意义、突出救亡色彩不同,自由主义更突出“五四”凸显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精神。胡适是五四启蒙中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发言人,他主张只谈文化不谈政治,调侃陈独秀等人是政治兴趣浓厚的朋友。他的《纪念“五四”》中,有关于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两者关系的理解,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的起源,他说:“我们在这纪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细细想想今日是否还是‘必有赖于思想的变化。因为当年如果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
同时,在“五四”时期,还存在这样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对五四运动的激烈反传统反文化持批评态度,认为全盘西化或者全部抛弃传统是不可取的,对这种主张取保留态度,但是他们对五四所代表的启蒙精神,特别是提倡的民主与科学采取积极拥护的态度。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他的代表作《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明确表态赞同和支持陈独秀等提倡的民主与科学,认为《新青年》所代表的激进主义才算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了,而且认为自己所提倡的东方化与传统顽固旧势力所拒绝的西方化是完全两个概念,是完全承认和支持民主与科学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五四启蒙精神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从而肯定其合理性和历史功绩。
三,中断还是继续。
“五四”的启蒙精神发展到后期,是出现了中断还是转向了启蒙的另一种继续,关于这一点仍是学界争论的热点。
持“中断论”的以李泽厚和汪晖为代表。李泽厚在其《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说“: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对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如上引陈独秀的话,这个‘最后觉悟之觉悟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同时,汪晖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提出“五四”的中断是“方法统一性的缺乏和态度统一性的瓦解”。
而一大部分学者都是持“继续论”或“转向论”的。刘书林就持这一观点,并极力推崇这一启蒙“,五四运动期间和五四运动之后,启蒙运动并未止息,更没有被‘救亡所压倒,而是改换了面貌,走向了科学,提高了层次。这时的启蒙,不再是弘扬资产阶级文化,而是弘扬更加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这时的启蒙,从追求法兰西式的民主提升到追求社会主义的民主;从启蒙极少数人,提升到启蒙大多数人;从简单的追求自然科学提升到追求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一句话,新的启蒙是旧的启蒙无法相比的。”沙健孙的看法是相同的,“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的武器向封建的思想文化开火的时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思想家的弱点,从而把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向前进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不愿意说“五四”启蒙夭折了,我们更愿意相信她给中国带来了进步,更愿意相信“五四”先贤们所追求和致力的事业仍然会继续。八十年的经历虽然使我们感到有些挫折感,但是并不足以使我们感到沮丧。因为五四先贤所要进行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它的成功可以推迟,但是决不会归于失败。要记住胡适的话:“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入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免不了的。”我们只有屡败屡战,再接再厉,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作者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