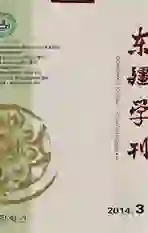《源氏物语》创作的伦理旨向
2014-09-26张楠
[摘要] 《源氏物语》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日本民族文化有机融合的文化底蕴。整部物语故事表达的“不论善恶,都是世间真人真事”的伦理旨向,不是儒家倡导的“兼济为本,尊卑别序,致身尽”的道德说教,也不是宣传人生虚无感和追求彼岸极乐情怀、叙说“烦恼即菩萨”的佛学真谛,而是真正领悟了道家“法天贵真”的人性论,以女性作家特有的虚静灵明之心,真实描绘出了当时都市生活中人性、人情的自然状态,使人知物哀。
[关键词] 《源氏物语》;紫式部;伦理旨向;儒家;佛家;道家
[中图分类号]I313.07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007(2014)03002206
[收稿日期] 2014-04-18
[作者简介] 张楠,女,日本创价大学人文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日本古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南京210094)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小说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艺术地描绘社会生活并表达作家的人性观和审美追求。所以,它总要贯穿表达善恶的伦理旨向,紫式部创作的《源氏物语》亦如是。《源氏物语》中,作者直抒胸臆对主人公或故事情节加以议论之说被称为“草子地”。《萤》卷中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草子地”,可以看做是紫式部对《源氏物语》创作主旨的总论式评述:
故事小说,虽然并非如实记载某一人的事迹,但不论善恶,都是世间真人真事。观之不足,听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写作。因此欲望写一善人时,则专选其人之善事,而突出善的一方;在写恶的一方时,则又专选稀世少见的事情,使两者相互对比。这些都是真情实事,并非世外之谈。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各异;同是日本小说,古代与现代亦不相同。内容之深浅各有差别,若一概指斥为空言,则亦不符事实。佛怀慈悲之心而说的教义之中,也有所谓方便之道。愚昧之人看见两处说法不同,心中便生疑惑。须知《方等经》中,此种方便说教之例甚多。归根结底,同一旨趣,菩提与烦恼的差别犹如小说中善人与恶人的差别。[1](1)
日本学界针对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的伦理旨向,通过解析这段话形成了三种最具代表性的看法:一是它以儒学为底蕴,仿效《春秋》采善贬恶的笔法;二是它以天台佛学为旨要,叙说“烦恼即菩萨”的真谛;三是它以庄子寓言为本或者写法上以庄子寓言为趣。[2](50)诚然,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底蕴在《源氏物语》的创作中都有所彰显,但通读《源氏物语》文本,我们就会发现紫式部所表述的伦理旨向,既不是儒家的道德说教,也不是佛家的出世之说,而是“法天贵真”的道家人性论。
一
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师本居宣长评述《源氏物语》时指出:“外国的书籍与我国的物语等,意趣完全不同,简直有云泥之别。外国的书,无论是什么书,对待人物喜欢严格论定其善恶是非,喜欢讲大道理,每个人都极力证明自己的贤明。即便是在风雅为宗的诗文中,也与我国的和歌大异其趣,并不着意表现人情,而是讲道理、显才学。我国的物语则无拘无束、随心所欲,丝毫也不卖弄才学,自然而然地写出了细腻丰富的人情。”[2](51)紫式部对《源氏物语》创作主旨的阐释,本居宣长对紫式部创作态度的分析,都点明了《源氏物语》与他眼中的中国书籍“严格论定其善恶是非,喜欢讲大道理”的不同之处。
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之一。儒学的本质是“人道”,即教人如何做人。其价值取向是强调对人的伦理政治教化,奉行的总纲领就是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论述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条总纲领是儒家人生价值观的根本要求,实践这条总纲领是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塑造理想人格的基本思路。受儒家育人总纲领的引导,中国各类文学作品都追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3](1764)或者“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咏志,莫非自然”。[4](68~69)这里的“物”、“事”与日本物语创作中仅指与个人情感相关的事物不同,更多的侧重于社会政治与伦理教化的内容;感物而生的“情”与日本物语所表达的“物哀”之自然情感、个人私情也不同,是基于社会理性化的“志于道”基础上的情,是体现“据于德”的情志合一、情理合一。中国的文学创作态度强调“发乎情而止乎礼”,注重讲孝亲、忠君、修齐治平的大道理,以仁义礼智的规范、采善贬恶的要求去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
日本平安时代以中国传入的儒家学说为政治显学,它是贵族子弟们升官晋爵的敲门砖。当时的日本大学设有“大经”、“中经”、“小经”等训教课程,还兼学《论语》、《孝经》等。[5](48)对此,《少女》卷中有如下生动的描述:“此时大学甚为繁荣,不亚于古昔全盛之时。上中下人各级官员子弟,竟尚此道,集中于学术研究。因此世间多才多艺之人,日益增多。”“大学考试之日,王侯贵族的车马云集大学寮门前,不可胜数。几乎满朝公卿全部来到了。”然而,在紫式部看来,贵族子弟如此趋之若鹜地专研儒学只是为了“将来学优登世,身为天下柱石。”(《少女〉卷)。她认为,儒学宣扬孝悌忠恕、仁义礼智之说及其采善贬恶的价值取向,归根结底是为维护”尊卑别序“的权利地位服务的。其礼仪规矩限制着人间最基本的自然情感,会造成自然人性的扭曲。
同样,在紫式部笔下,那些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对儒家礼仪过分循规蹈矩、寄生于权贵的儒生,简直就是一些不懂人情的行为僵化的小丑。《少女》卷对此有极生动的描绘:“源氏在东院的东殿为夕雾入大学寮而举行取字号仪式,朝中高官贵族以及殿上人等都来参加了……那些儒学博士上殿来,看到这富丽堂皇的场面,反而觉得畏缩了……他们都努力镇静,装作泰然自若。有几个穿着借来的衣服,不称身体,姿态奇特,也不以为耻。他们的面貌神气十足,说话声音慢条斯理,规行矩步,鱼贯入座,这光景真乃先所未见。”由于“儒家的礼仪过分别致”,会上的招待人虽然小心谨慎地捧着酒爵敬酒,也是“终不合法,常被儒学博士严厉指责。有一儒学博士骂道:‘尔等乃一奉陪之人,何其无礼!某乃著名儒者,尔等在朝为官而不知,无乃太蠢乎!众人听了这等语调,都噗嗤地笑出来。博士又骂:‘不准喧哗!此乃非礼之极,应即离座退去!……天黑下来了,他们的脸在灯光之下,竟像戏剧中的小丑,憔悴而古怪,却又各人不同。”
除此之外,在紫式部笔下,儒学的本质与体现上善若水、柔弱不争、恬淡虚静的女性生命本质是背离的。女人如果崇尚儒学,沉迷于儒家的礼仪规范,也就没有女人味了。紫式部在《帚木》卷中曾明确表态:“一个女子潜心专研三史、五经等深奥的学问,反而没有情趣。”而且,用儒学来指导文学创作,紫式部是不赞成的。这一点我们从她在《少女》卷中对夕雾和光源氏的诗作进行比较时可以窥见。夕雾“作出之诗,也表明刻苦求学之大志,而且每句都富有意味”。诗中引用了映雪读书的典故,被人赞誉“此诗即使传入中国,也不失为优秀之作。”“至于源氏内大臣的大作,精美自不待言。其中热诚地歌咏着父母爱子之心,读者无不感动而流泪。”此后,紫式部笔锋一转,写道:“作者女流之辈,才疏学浅,不宜侈谈汉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紫式部以女性作家的特质,体悟到文学创作不是道德教化,而是要以恬淡虚静之心去描绘出生活中真实的人性、人情和各种人物本色天然的内心世界;女作家如果沉迷于儒学的伦理旨向,就会丧失本身的真性情,写出来的作品也将是“伪情”、“伪作”。
二
紫式部在谈到自己物语创作的主旨时,曾说:小说所展现的故事情节,不是对人们毫无益处的“空言”,而是与“佛怀慈悲之心而说的教义”有相同的旨趣。《源氏物语》中,对于佛教尤其是天台佛学与民间信仰相结合,向众生求方便而形成的一些特有的风俗仪式、男女奉佛出家等,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但是,《源氏物语》所展现的伦理旨向,即它对善恶的评价及其艺术价值与佛学是根本不同的。它对人物故事的叙说和描写中虽然涉及了不少学佛、修行、出家、赠送佛像、祈祷还愿等情节,但主要是作为当时的风俗来展现的。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的主旨不是揭示“烦恼即菩萨”,把人的生命归宿引入空灭之境,而是关注都市生活中各阶层人物的真实生活,破除人为的善恶观念的束缚,寻求永恒的人性和自由精神。
紫式部言道:“对于好人,就专写他的好事”。源氏就是她在物语中作为“好人”来描写的第一人。源氏一生行径,其好色行为甚多。他与夕颜、胧月夜、源内侍等人的“淫乱”行为,特别是与其继母藤壶女御发生的乱伦之恋,在佛家看来都非寻常之过,而是罪大恶极的行为,但紫式部却把这样一个人作为“好人”的典型来写。《源氏物语》中,随处可见对源氏的颂扬。与佛教“善恶有报”的教义相悖,源氏的贪淫好色“恶行”并未得到恶报,反而因祸得福,受一双儿女以后荣立为冷泉帝和明石皇后的福荫,官至准太上皇之位。紫式部当然不是把淫乱本身看做好事和善事,她要描绘的是真实的人性、人情。而色欲与人的感情关涉最深,真实地描绘出男女之间的好色之事,就是通达自然的人性、人情。如果从佛学的角度来理解紫式部的创作态度,就会陷入伦理的误区。各种佛经传播的“方便”也好,“实教”也罢,其根本宗旨都是讲世上一切事物的实相都是“空”,人生烦恼的总根源在于对“一切皆空”的实相“无明”,因而人的命运归宿只能是灭“无明”而归于寂灭。紫式部执著于现世生活,将都市生活中各阶层人物真实的苦乐情感和善恶活动在其物语创作中一一描绘出来。
《源氏物语》中有两段描写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段是《夕雾》卷叙说紫姬的心理活动:“女人持身之难,苦患之多,世间无出其右了!如果对于悲哀之情、欢乐之趣一概漠不关心,只管韬晦沉默,那么安得享受世间荣华之乐、慰藉人生无常之苦呢?况且一个女子无知无识,形同白痴,岂不辜负父母养育之恩而使他们伤心失望呢?万事隐藏在心中,像古代寓言中所谓无言太子,即僧人引为苦难之典型者,明知世事孰善孰恶,却将意见埋藏胸底,毕竟也太乏味了。”另一段是《魔法使》卷,明石姬对源氏谈出家向佛的看法:“即使是别人看来毫不足惜的人,本人心中自然也有种种牵累。何况尊贵之人,岂能安心舍离人世?草草出家,反被世人讥为轻率,请勿急切从事为要。慎重考虑,看来似是迟钝,但一经出家,道心坚固,绝不退转,此理当蒙明察。试看昔人事例:有的为了身受刺激,有的为了事与愿违,便萌厌世之念,因而遁入空门。但这终非妥善之事。”这里表达的对佛学的体悟,包括书中写到的许多为尼、为僧的贵族人物,并没有明瞭人生苦痛的根源在于对大千世界“诸法无常”、“一切皆空”的“无明”,从而断绝一切欲望,以寂灭的心境来看待人生,进入“诸法无我”的境界。相反,他们很执著于“我”的存在,我的自然性情和社会欲求,即使出家者也无法摆脱“我执”的苦恼,而采取人为的回避态度,其僧衣之下跳动的,仍就是一颗牵挂红尘的凡心。
不仅如此,紫式部还在《源氏物语》中对佛理、对僧侣都提出过质疑。例如《槿姬》卷写道:源氏“访问五公主”,老迈的五公主“噜哩噜苏”地讲起往事,源氏“但觉毫无兴趣”,这时又遇见了更加老迈的但“照旧装出撒娇撒痴的姿态来”的昔日放荡的源内侍。源氏觉得此人既“讨厌”又“很可怜”。他回思往事:在这老婆婆青春时代,宫中争宠竞爱的女御和更衣,现在有的早已亡故,有的零落漂泊,生趣全无了。就中像尼姑藤壶妃子那样盛年夭逝,更是意料不到之事。像五公主和源内侍之类的人,残年所余无几,人品又毫不足道,却长生在世间,悠然自得地诵经念佛。可知世事不定,天道无知!”源氏的心理活动,明显含有对佛教基本理论“业报”说的怀疑。在佛教文化的理解中,人生的贫富贵贱、吉凶祸福,并不是上天或人格神的意志,完全是人自己作“业”的结果。而源氏却以自己的人生阅历总结出:人们现实的寿夭并不同善恶果报相联系,世事变迁、自我命运的走向都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切还是取决于“天道”的必然性。
三
紫式部所生活的平安时代的文化,以儒学为政治显学,倡导“兼济为本,尊卑别序,致身尽”。这制约和影响着当时贵族阶层的人生价值观。另外,天台宗和密宗的佛学教义也渗透到当时的都市生活中,人生虚无感和追求彼岸极乐之情已融于社会风俗。这样一来,人们本真的性情、喜怒忧思悲恐惊等自然情感的宣泄,往往也受到后天人文教化的限制,受到虚空寂灭感的左右,难现素朴的原初状态。紫式部以女性作家特有的虚静灵明之心,深刻体悟到道家文化倡导的“道法自然”、雌柔不争的生命智慧。她创作《源氏物语》就是要真实地描绘都市生活中的世态人情,“不论善恶,都是世间真人真事”(《萤》卷)。要描述源于人的自然禀赋的真情实感,就不能强调后天的人文教化,不能追寻空灭的彼岸生活,而要自然地抒发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使人知物哀。表现出鲜明的道家文化伦理旨向。
道家文化的精神支柱——老庄哲学,主张在以“道”为天人分际的架构下,保持人的天然纯真本质的情感,即天真如婴儿赤子之情,寻求一种不矫情、不伪作、合乎自然自在的生活态度。老子的人性论反复强调:“戴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庄子与老子一样,赞赏人的本真性情爱与天性,应不拘于俗,不禁于伪,回归婴孩儿般纯真自然状态,即“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紫式部体悟了道家人性论的意旨,认识到人在社会生活中不能不读书、识理,不能不关心今世命运和来世“幸福”,最难得的是不丧失素朴的童心。“一般而论,真实的人情就是像女童那样幼稚和愚懦。坚强而自信不是人情的本质,常常是表面上有意假装出来的。如果深处其内心世界,就会发现无论怎样的强人,内心深处都与女童无异。”[6](106)紫式部就是以素朴的女童之心来创作《源氏物语》的。书中的故事情节没有装潢门面、照着镜子刻意打扮的伪情描写,没有冠冕堂皇地表现为君效命、为国损躯的英雄壮举,没有炫耀人文教化的大道理和佛学教义的真谛,而是真实地描绘人性、人情的自然状态,细腻深刻地揭示和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宛如明镜照影,无所遁形。
为了体现这种道家文化的伦理旨向,紫式部精心塑造了光源氏这一艺术典型。《匂皇子》卷写道:“昔源氏有 ‘光君之称,桐壶帝对他宠爱无比。但因妒忌之人甚多,又因他的母亲没有后援人,以致处境困难。全靠他能深思远虑,圆滑应付世事,韬晦不露锋芒。因此后来世局变迁,天下大乱,他终于平安无事地度过难关,依然矢志不懈地勤修后世。他对万事不逞威福,故能悠然度送一生。”这段文字是对源氏这一艺术典型的总体人生评价,其老庄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源氏具有“见素抱朴”的人格修养。道家哲学把论说宇宙本体的“道”应用到揭示人性和人格的本质上,强调“见素抱朴”。就是说在人生活动中,人要本着素朴的原初生命本性去待人接物,才能具有谁也无法支配的力量;在人格修养上,人的内心要保持、守定自己的本真人性,外在行为要体现自己本性的自然状态。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摆脱物欲的控制,追求人格上的内在超越和精神自由,在接人待物中不受是非、功利等情感目的的左右,一切顺应事物的本性活动。源氏一生的所作所为就很好地体现了道家文化的这些要求。譬如,《新菜》卷叙说了一段朱雀帝对源氏的评价:“当他端居庙堂、策划政务之时,威风凛凛,令人望而却步。但当他放任不羁、戏谑调笑之时,则又风流潇洒,令人觉得异常可亲可爱。……他自幼生长在宫中,先帝对他异常疼爱,悉心抚育,几乎不惜身命。但他绝不因此骄纵,反而谦恭克己。”可见,源氏不因出身高贵、权势显赫而骄纵,始终保持平常人的恬淡之心,既不无节制地发展自己的私欲,与人相处又能始终保持淳朴的“愚人之心”。
这一点在《薄云》卷源氏和梅壶女御的谈话中表现得更为直接。他说:“我回京以后,复官进爵,身为帝室屏藩,但我对富贵并不感兴趣,惟有风月情怀,始终难以抑制。”“风月情怀”是人内在生命的自然欲求,是受人情感支配的生理本能,这是人的理性所无法抑制的;对“富贵”的追求则是超出生命本能之外的理性作用,受社会伦理观念的支配。源氏的态度表明,他是“少私寡欲”,努力保持自然本性,不让“富贵”等社会因素异化自己人格的人。源氏与人相处鼎诚相待,不用技巧,不使奸诈,乃至以德报怨。弘徽殿太后满脑子权利欲,妒忌良善,排斥异己,迫害贤达,可谓是个大恶人,更是源氏的仇人。源氏由须磨返京后时来运转,由于冷泉帝接替让位的朱雀帝,源氏升任内大臣。“此时天下大权平分为二,由太政大臣与内大臣翁婿二人协力同心,随意管领。”(《航标》卷)弘徽殿太后开始“悲叹时运不济了”。但手握重权的源氏绝不骄纵自己,仍然谦恭克己。“源氏内大臣每有机会,必关怀弘徽殿太后,对她表示敬意。世人不平,都认为这太后不该受这善报。”以恬淡的情怀来对待自己宦海沉浮的现实,不计前嫌,不怨天尤人,以豁达的心胸来以德报怨,正是道家恬淡无为的人格表现。
其次,源氏具有柔弱不争的人生态度。如《夕颜》卷写道:“源氏公子说:‘柔弱,就女子而言是可爱的。自作聪明、不信人言的人,才教人不快。我自己生性柔弱,没有决断,所以喜欢柔弱的人。”源氏柔弱不争的人生态度,体现的正是道家生命哲学的本质。《老子·七十六章》有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即把“柔弱”看作人生命的本质特征。柔弱作为生命的本质有两方面内涵:一方面是“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就是说为人处世始终保持谦恭忍让的态度,更能激发人的进取心,循循向上,永不停止;而争强斗狠,急功近利,会导致荣耀的盈满而骄,播下败亡的种子。紫式部塑造的源氏这个艺术典型,就是在人生活动中“柔弱胜刚强”的典范。他从不因出身高贵、后来又权倾天下而骄纵自己,始终保持普通人的恬淡之心,为人处事流露的都是自然的人性、人情。即使“时局变迁,天下大乱”,他也能“深思远虑,圆滑应付世事,韬晦不露锋芒”,所以能“悠然度送一生”。《源氏物语》描写源氏,一生经历过无数坎坷,“有过离经叛道的不义行径,风流好色成性,却一生荣华富贵,在世上几乎无事不遂,而且子孙繁昌,并获得了一个‘太上天皇的尊号。”[10](86)另一方面是肯于居下而不争。道家体悟柔弱的生命本质得惠于水的灵性。《老子·八章》有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柔弱谦下,忍辱纳垢,却是世界上的生命之源。它以自身渗透万物、随机应变、回旋自如的灵活性,具有攻坚强者的巨大威力。在人生活动中,具有“水”一样至德之人,一定具有谦恭的肯于居下的胸怀,不为争功逐利而费尽心机,反而能保持功利不失。源氏就具有水一样的谦恭居下的美德。他一生“深思远虑,圆滑应付世事,韬晦不露锋芒”,不争功利,不计荣辱,不善权谋心机,一切顺应自然行事。虽然仕途中历经坎坷,但最终却不失功利,荣耀至极。他“生子女三人,其中兼有天子和皇后,最低者太政大臣,自己则尊为准太上皇。”
最后,源氏具有慈而重生的人生境界。道家文化主张在等级社会的身、家、国、天下四重关系中,要以“身”即个体生命为本位,“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道家心怀天下,但前提是以生命个体的自身得道为前提,将天下视为己身,提倡重身、修身、爱身,关注人的现世生活,关注人生命的价值,关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性和人情。《源氏物语》对源氏重视人的现世生活、关爱个体生命的性情做了多处描写。其中较生动的如《贤木》卷中的描写:源氏因与藤壶女御发生乱伦之恋的“烦恼“,“赴云林院佛寺游览,乘便观赏秋野的景色。亡母桐壶更衣的哥哥是个律师,就在这寺里修行。大将在这里诵经礼佛,滞留两三天,倒也很有趣味。木叶渐次变红,秋野景色清丽,令人看了浑忘家乡。源氏大将召集一切有学问的法师,请他们说教,向他们问道。由于地点所使然,令人彻夜痛感人生之无常,直到天明。然而正如古歌所云:‘破晓望残月,恋慕负心人。不免使他想起那意中人来。将近天明,法师等在月光之下插花供水,发出杯盘叮当之声。菊花和浓淡不同的各种红叶,散置各处,这景象也颇有趣致。源氏大将念念不忘地想:‘如此修行,可使现世不致寂寞,又可使后世获得善报,这虚幻无常的一身还有什么烦恼呢?律师以尊严之声朗诵‘念佛众生摄取不舍。源氏公子听了觉得深可羡慕,想道:‘我自己何不决心出家呢?此念一动,便首先挂念紫姬,真是道心不坚!他觉得从来不曾如此长久离开紫姬,便频频写信去慰问她。有一封信中说:‘我想尝试一下:脱离尘世是否可能?然而无以慰我寂寥,反而更觉乏味。”身处佛寺,聆听佛法,试图以寂灭的心境体验佛家的“无物常住”、“诸法无我”的真谛。但受儿女私情的自然本性驱使,实在割不断对藤壶和紫姬的热恋,使源氏无法破除“我执”,更执著于现世生活的男欢女爱,更珍惜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价值。他通过尝试“脱离尘世是否可能”的心得是,出家避世“无以慰我寂寥,反而更觉乏味”。重视现世生活,珍惜天性自然的个体生命价值,必然引出慈爱待人、与人为善的救世之心。
《源氏物语》描写源氏与诸多“可敬可爱”的女性们交往,发生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时,就处处表现出他慈爱待人,与人为善之心。对藤壶、紫姬、明石姬、女三宫等事实上的妻子们,他关怀备至,处处用心,自不必说。就是相貌丑陋的花散里和末摘花这两个情人,也得到了源氏的充分信任和关爱。花散里性情温和,心地善良,源氏信赖她并委托她培养自己的儿子夕雾,成为夕雾的继母。还与秋好皇后、紫姬、明石姬共同成为六条院四个区域的女主人。丑女末摘花在源氏谪戍期间,“躲在荒草丛中,度送了长年的辛酸生涯”,坚守着对源氏的爱。源氏敬重她对情爱坚贞不渝的意志和待人谦恭退让的品质,在时来运转而重返京都后,了解到末摘花的生活状况,“把末摘花看做了不起的人物”,“末摘花家,万事都由公子亲自仔细调度。”(《蓬生》)
对于已故情人的遗孤,源氏也慈爱有加、精心呵护。例如,六条妃子临终前嘱托源氏照顾其孤女前斋宫,源氏真心诚意地照顾这位前斋宫。为使她成为冷泉帝的女御,源氏“安排入宫一切事宜,像父母一样操心。”(《赛画》)正是因为源氏与情人之间的爱恋不是一时冲动的色情行为,而是觉得对方的人品可敬可爱,因而能主动负起男人的责任。源氏具有慈爱的胸怀,对情人的遗孤能主动承担起父亲的责任,精心规划她们的前途,细心安排她们的起居生活。即便是情人的侍女,源氏也给予多方关照。例如,《玉鬘》卷写道:“虽然事隔十六年,源氏公子丝毫也不曾忘记那个百看不厌的夕颜。而夕颜的侍女右近,虽然不是十分出色的女子,但他把她看作夕颜的遗爱,一向优待她,叫她和老待女们一起在邸内供职。”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源氏不但不依仗权势而鄙视下人,还将与自己心爱之人的亲近者统统视为亲人,给予无私的呵护与关爱,其慈心爱人、爱人而重生的品德可见一端。正如《早莺》卷所叙说:“源氏太政大臣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绝不盛气凌人。其待人接物,均按照地点与身份,普施恩惠。许多女人就仰仗着他的好意,悠游度日。”(《早莺》卷)这不正是道家理想中的“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老子·二十七章》)的好人吗?
综上所述,紫式部以女性的虚静之心创作的《源氏物语》,深刻体验和感悟了道家哲学的生命智慧,描绘出古代日本都市生活中各阶层人物真实的苦乐情感和善恶活动。通过对爱情这一人类永恒主题的叙说和揭示,展现自然人性与现时礼法间的种种矛盾冲突,以生发“物哀”之情来透视人的心灵,在不断追问人们生命意义的基础之上,探究平安时代现实境遇中真实的人性架构与缺失,从而对根本的伦理意识进行深刻的探究。
参考文献:
[1] [日]紫式部著、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2] [日]本居宣长:《紫文要领》,日本:岩波书店,2010年。
[3]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5] [日]大野出:《日本の近世と老庄思想》,东京:东京べりか人社,1997年。
[6] [日]本居宣长著、王向远译:《日本物哀》,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
[7] [日]紫式部著、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责任编辑 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