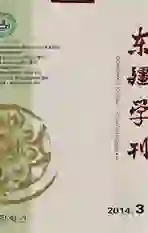论《华语类抄》的汉语音系特征
2014-09-26金哲俊
[摘要] 《华语类抄》是19世纪末在朝鲜刊行的一部汉朝对译词汇集。全书分天文、地理等63个类别,收2400个汉语词汇。每个词条的每一个汉字都用朝文字母注音,而且用朝文对译。《华语类抄》具有以下几点特征:(1)北方话的颚化到19世纪末才全面完成。(2)日声母字的零声母化。(3)ü的注音较混乱。(4)鼻音韵母-m到了19世纪末已经消失。(5)很难看出舌尖音化。(6)为了标记北京话,使用了人为的符号。《华语类抄》的刊行年代正处于近代汉语时期(13世纪到19世纪),因此,《华语类抄》对研究近代汉语音系的音值及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华语类抄;近代汉语;音系
[中图分类号] H11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007(2014)03004005
[收稿日期] 2013-10-15
[作者简介] 金哲俊,朝鲜族,博士,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朝鲜语言。(延吉133002)
目前,国内学者对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研究论文所引资料一般限于中国的各种文献资料。但由于中国的文献资料是用汉字标记的,所以在音值的构拟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局限性。朝鲜具有悠久的音韵研究传统,并且在音韵学方面保留着用拼音文字——“训民正音”注音的丰富的文献资料。朝鲜的注音韵书、对译辞书以及谚文书对中国近代汉语音系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通过朝鲜文献研究近代汉语语音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1](1)。
本文的研究对象《华语类抄》是19世纪末刊行的一部汉朝对译词汇集。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木活字本;另一个是本刻本。前者是金日成综合大学复印资料,后者是浙江省图书馆复印资料。本文利用的版本是金日成综合大学复印资料。全书分天文、地理等63个类别,收2400个汉语词汇。每个词条的每一个汉字都用朝文字母注音,并用朝文对译。本文以用朝文注音的汉字为研究对象,采用译音对勘法考察研究19世纪末的汉语音系特征。所谓的译音对勘法,就是用汉语和其他语言对音材料分析汉语古音的音值和音类的方法。对音材料可以分为三类:历史上的借词、历史上的对音字、不同语言之间的注音字。其中,注音字主要是指用外国的或外族的拼音文字给汉字的注音[3](261)。《华语类抄》正属于这一类。
我们把一类对音材料中的用字排比出来,从大多数字的对音中总结出规律,可以推究出古代或近代汉语的音。同类音的材料越多,表现形式越一致,证明其作用越强,但是,对音的两方不都是同样的音恰好等值相对,其中有很多复杂情况[3](261)。比如汉语和朝鲜语的语音系统有差别。汉语里有些音在朝鲜语里没有,对译汉语遇到了困难,就只能用比较接近的音来代替。在这种情况下,朝鲜语读音到底代表了哪种汉语读音,是要费神推敲的。所以,对对音材料的使用,学界曾经出现过很多不同的态度,有肯定的,也有怀疑乃至否定的,还有既肯定对音的用处也感到其中问题较多而采取比较审慎态度的[3](264)。
本文不会因为对音本身存在问题而否定它的价值,相反,还要充分肯定对音的用法,并利用它来研究近代汉语语音。
将《华语类抄》中的某些汉字的音与这些汉字的现代读音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对应规律,即,声母 “醞∶x ”,韵母 “預∶ie” 的对应规律。为照顾更多的读者,本文对现代汉语的标音尽量使用汉语拼音,个别必须使用国际音标的地方,用[ ]表示。
因为朝鲜语没有声调标记,我们只能进行单一的比较。朝鲜语的“醞”与汉语的“x”对应,朝鲜语的“預”与汉语的“ie”对应。以同样的方法来考察《华语类抄》的汉语音系特征。
一、《华语类抄》所反应的近代汉语音系特征
(一) 与现代汉语声母的对应及特征分析
特征1:g、k、h的颚化
在《华语类抄》中,出现最明显的语音变化是喉牙音见晓组声母的颚化。即g、k、h变为j、q、x。从这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北方话的颚化到19世纪末才全面完成。见晓组字的颚化是18世纪中叶开始,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有所增加,但仍处于过渡阶段,而到19世纪中叶以后基本上完成了[2](133)。
《重刊老乞大谚解》(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里没有颚化的“价、甲、俭、监、建、见、件、结、界、芥、吉、季、金、禁、今、筋、襟,经、角、交、脚、绢、眷、驹、舅、九、劝、弦、行、杏、瞎、下、匣、夏、香、现、县、胸、兄、学、靴、眩”等字,在《华语类抄》中都已颚化。对此,《华语类抄·序》中说:“古之初声?者今多从?,如家字古音?,而今以鉈释之……”。同时,与《华语类抄》同时期的《华音正俗变异》《华音正俗变异》是附在《华音启蒙》一书卷末的正音和俗音对比字表。《华音正俗变异》收千字文中288字,百家姓中的68字,共356字。这些字是从千字文、百家姓中抽出有古今正俗音字的,每字下用朝文字母注两种音,右边是正音,左边是俗音。估计《华音正俗变异》所反映的是从近代汉语过渡到现代汉语时期的语音特点,也可能是反映一些这一过渡阶段的方言情况。中的134个见晓组字也全部颚化,但在《华语类抄》中还可以发现有些见晓组字,即“缰、笕、菊、苣、谲、蚯、蟹”等字仍没有颚化。
有的学者认为汉字的颚化始于16世纪,完成于18世纪[5](82)。而这显然与从朝鲜对音资料《华语类抄》中得出的结论有些差异。
特征2:使用复合文字 “醞郪、 醞?、?”标记北京话的一些特征
这类复合文字不同于过去15-17世纪文献里的复合文字,即并不表示朝鲜语的紧音或汉语韵书里的全浊声母字,它们的实际音质是复合文字的第二个字母的音。
朝鲜人学习汉语更重视官方外交上的需要,所以有关朝鲜谚文注音的著作都是为了方便朝鲜人学习汉语官话而出版的。朝鲜人学官话受到了中国官方正音的影响,其注音课本,既要以口语为基础,又要顾及官韵。《华语类抄》的编者也可能受到了类似的影响。
特征3:日母字的零声母化
在《华语类抄》中,声母系统中的日母字都变成了零声母。18世纪的对音资料中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变为零声母的只是少数。例如:《朴通事新释谚解》占21.4%,《汉清文鉴》占16%,《重刊老乞大谚解》占40%[2](136)。但在《华语类抄》中的23个日母字除“饶”字这可能是错的注音,因为注音者可能把它读成[shao]。以外都变为了零声母。并且,与它同时期的《华音正俗变异》中的日母字也全部变为了零声母。因此,我们断定日母字到19世纪末已经全部变为零声母。例如,沈阳人习惯把“人、日、热、如、软”等字念成in、i、ie、yu[y]、yuan[yan][2](137),这与《华语类抄》一致。《华语类抄》序中说:“……盖近日京音如是,故不能不尊然。至于各省语之或有异同者不得尽从”。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华语类抄》的汉字音应该是北京次方言辽东话。
特征4:“?、銴、醞”不能分辨汉语中的正齿音和齿头音以及精系字的颚化与否[4](102)。
《华语类抄》用“?、銴、醞”来分别为汉语拼音声母zh、z、j,ch、c、q,sh、s、x注音。这样的注音法是因朝鲜语声母系统中只有一套塞擦音,不存在卷舌音(舌尖后音)、舌尖前音和舌面前音的区别,即音韵学所谓正齿和齿头的区别而引起的。15世纪中叶,朝鲜人为了区别中近古汉语齿音即塞擦音的正齿与齿头,创制出了“?(精)、銴(清)、靭(从)、(心)、(邪)”左边长和“?(照)、銴(穿)、靭(休)、(番)、(禅)”右边长等文字。前者用于齿头音,后者用于正齿音。但至少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朝鲜人观察的北方音之齿音已有了齿音、正齿组……他们无法掌握这些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用朝鲜语里的一套齿音“?、銴、醞”来注音。……在朝鲜语中自古以来卷舌音、舌面音、舌齿音一直都是非辨音。因此朝鲜人学习中国话今古都有分不清卷舌、舌面、舌齿音的情形,都一律听为同一个齿音“?、銴、醞”[4](135)。因此,在近代汉语舌根音和舌尖齿音中很难找出有规律的对应关系。如果这些文字能保留下来的话,我们就能准确标记汉语的正齿音和齿头音。也就可以区别汉语的正齿音和齿头音。
如不考虑朝鲜语声母没有卷舌、舌面、舌尖前塞擦音的区别,我们可能误认为近代汉语的舌面、卷舌和舌尖齿音与朝鲜语声母的对应关系依然混乱。
二、与现代汉语韵母的对应及特点分析
特征1:《华语类抄》里出现的汉语韵母为49个,比现代汉语的韵母多13个,而且与韵母的结合关系多出现一对多或多对一的情况。
在开口呼里多出现7个韵母,在齐齿呼里多出现2个韵母,在合口呼里多出现2个韵母,在撮口呼里多出现2个韵母。
特征2:有些韵母尚未单纯化
特征3: ü[y]的注音较混乱。
特征4:17世纪末的鼻音韵母“-m”到了19世纪末已经消失
中古汉语韵尾“-m”在北方话里的消失是近代汉语的显著特征之一。但是对于它消失的年代,学者们有不同的推测,至今尚无定论。王力先生推测为16世纪以前,而金基石推测为15世纪在北方音中就已经消失,他甚至推测14世纪末“-m”韵尾已经开始消失或安全消失了[4](288) 。因此我们推测-m早在14-15世纪中叶以前在北方话中开始消失,到16世纪初完全变为“-n”。
特征5:很难看出舌尖音化。
汉语的[]和[]是依赖于其前面声母的非自主性元音,[]出现在z、c、x之后,[]出现在zh、ch、s之后。在《华语类抄》里,“顆”与“?”没有严格的区别,但是大部分时候用“顆”。事实上,《华语类抄》中的汉语对音没有“△”, “△”是朝鲜学者在编撰韵书及谚解书时,为了表示汉语的舌尖元音而造出的韵母韵尾,一般用“鉸△”(精组字)和“鉾△”(知组字)来表示韵母的舌尖音化,所以单从朝文字母注音很难看出舌尖化问题。金基石先生对朝鲜韵书中的谚文注音考察后指出,《洪武正韵译训》时期支韵齿音的庄、章、知组韵母已向舌尖音过渡[4](229) 。
三、结语
虽然《华语类抄》是用表音文字做注音符号的,但是符号本身的音值并不十分精确,哪些字母代表哪种汉语音值也很模糊,所以需要透过注音形式分析它们所代表的真实读音,而不能把注音字母直接当作汉语的本来读音[3](288)。加之,朝鲜语属于黏着语,它的语音体系毕竟与汉语不同,因此,根据《华语类抄》的材料研究19世纪汉语的语音,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所以,从《华语类抄》的材料上所拟出的音系不能完全当作近代汉语的音系,至多只能算是近代汉语音的一个粗糙轮廓。
《华语类抄》是在韩国古代朝鲜朝时期刊行的文献资料,它的刊行年代正处于近代汉语时期(13世纪到19世纪)。因此,它为近代汉语音系的音值及演变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根据。近代音在时间上距离现代汉语很近,语音系统与现代汉语大同小异,因而分辨的准确度较高。近代的对音和古老的对音,一定有很多共同的规律,近代对音研究所总结出的规律对于研究中古以至于上古的音都有参考价值[3](289)。就此而言,《华语类抄》的汉语音系研究对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具有一定的助益。
参考文献:
[1]李得春:《朝鲜对音文献标音手册》, 哈尔滨: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2年。
[2]李得春:《韩文与中国音韵》, 哈尔滨: 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98年。
[3]耿振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金基石:《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 哈尔滨: 黑龙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3年。
[5]杨剑桥:《现代汉语音韵学》,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6]王力:《汉语语音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年。
[7][韩]金哲俊:《华语类抄的词汇研究》,首尔: 亦乐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 张克军]
特征3:日母字的零声母化
在《华语类抄》中,声母系统中的日母字都变成了零声母。18世纪的对音资料中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变为零声母的只是少数。例如:《朴通事新释谚解》占21.4%,《汉清文鉴》占16%,《重刊老乞大谚解》占40%[2](136)。但在《华语类抄》中的23个日母字除“饶”字这可能是错的注音,因为注音者可能把它读成[shao]。以外都变为了零声母。并且,与它同时期的《华音正俗变异》中的日母字也全部变为了零声母。因此,我们断定日母字到19世纪末已经全部变为零声母。例如,沈阳人习惯把“人、日、热、如、软”等字念成in、i、ie、yu[y]、yuan[yan][2](137),这与《华语类抄》一致。《华语类抄》序中说:“……盖近日京音如是,故不能不尊然。至于各省语之或有异同者不得尽从”。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华语类抄》的汉字音应该是北京次方言辽东话。
特征4:“?、銴、醞”不能分辨汉语中的正齿音和齿头音以及精系字的颚化与否[4](102)。
《华语类抄》用“?、銴、醞”来分别为汉语拼音声母zh、z、j,ch、c、q,sh、s、x注音。这样的注音法是因朝鲜语声母系统中只有一套塞擦音,不存在卷舌音(舌尖后音)、舌尖前音和舌面前音的区别,即音韵学所谓正齿和齿头的区别而引起的。15世纪中叶,朝鲜人为了区别中近古汉语齿音即塞擦音的正齿与齿头,创制出了“?(精)、銴(清)、靭(从)、(心)、(邪)”左边长和“?(照)、銴(穿)、靭(休)、(番)、(禅)”右边长等文字。前者用于齿头音,后者用于正齿音。但至少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朝鲜人观察的北方音之齿音已有了齿音、正齿组……他们无法掌握这些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用朝鲜语里的一套齿音“?、銴、醞”来注音。……在朝鲜语中自古以来卷舌音、舌面音、舌齿音一直都是非辨音。因此朝鲜人学习中国话今古都有分不清卷舌、舌面、舌齿音的情形,都一律听为同一个齿音“?、銴、醞”[4](135)。因此,在近代汉语舌根音和舌尖齿音中很难找出有规律的对应关系。如果这些文字能保留下来的话,我们就能准确标记汉语的正齿音和齿头音。也就可以区别汉语的正齿音和齿头音。
如不考虑朝鲜语声母没有卷舌、舌面、舌尖前塞擦音的区别,我们可能误认为近代汉语的舌面、卷舌和舌尖齿音与朝鲜语声母的对应关系依然混乱。
二、与现代汉语韵母的对应及特点分析
特征1:《华语类抄》里出现的汉语韵母为49个,比现代汉语的韵母多13个,而且与韵母的结合关系多出现一对多或多对一的情况。
在开口呼里多出现7个韵母,在齐齿呼里多出现2个韵母,在合口呼里多出现2个韵母,在撮口呼里多出现2个韵母。
特征2:有些韵母尚未单纯化
特征3: ü[y]的注音较混乱。
特征4:17世纪末的鼻音韵母“-m”到了19世纪末已经消失
中古汉语韵尾“-m”在北方话里的消失是近代汉语的显著特征之一。但是对于它消失的年代,学者们有不同的推测,至今尚无定论。王力先生推测为16世纪以前,而金基石推测为15世纪在北方音中就已经消失,他甚至推测14世纪末“-m”韵尾已经开始消失或安全消失了[4](288) 。因此我们推测-m早在14-15世纪中叶以前在北方话中开始消失,到16世纪初完全变为“-n”。
特征5:很难看出舌尖音化。
汉语的[]和[]是依赖于其前面声母的非自主性元音,[]出现在z、c、x之后,[]出现在zh、ch、s之后。在《华语类抄》里,“顆”与“?”没有严格的区别,但是大部分时候用“顆”。事实上,《华语类抄》中的汉语对音没有“△”, “△”是朝鲜学者在编撰韵书及谚解书时,为了表示汉语的舌尖元音而造出的韵母韵尾,一般用“鉸△”(精组字)和“鉾△”(知组字)来表示韵母的舌尖音化,所以单从朝文字母注音很难看出舌尖化问题。金基石先生对朝鲜韵书中的谚文注音考察后指出,《洪武正韵译训》时期支韵齿音的庄、章、知组韵母已向舌尖音过渡[4](229) 。
三、结语
虽然《华语类抄》是用表音文字做注音符号的,但是符号本身的音值并不十分精确,哪些字母代表哪种汉语音值也很模糊,所以需要透过注音形式分析它们所代表的真实读音,而不能把注音字母直接当作汉语的本来读音[3](288)。加之,朝鲜语属于黏着语,它的语音体系毕竟与汉语不同,因此,根据《华语类抄》的材料研究19世纪汉语的语音,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所以,从《华语类抄》的材料上所拟出的音系不能完全当作近代汉语的音系,至多只能算是近代汉语音的一个粗糙轮廓。
《华语类抄》是在韩国古代朝鲜朝时期刊行的文献资料,它的刊行年代正处于近代汉语时期(13世纪到19世纪)。因此,它为近代汉语音系的音值及演变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根据。近代音在时间上距离现代汉语很近,语音系统与现代汉语大同小异,因而分辨的准确度较高。近代的对音和古老的对音,一定有很多共同的规律,近代对音研究所总结出的规律对于研究中古以至于上古的音都有参考价值[3](289)。就此而言,《华语类抄》的汉语音系研究对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具有一定的助益。
参考文献:
[1]李得春:《朝鲜对音文献标音手册》, 哈尔滨: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2年。
[2]李得春:《韩文与中国音韵》, 哈尔滨: 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98年。
[3]耿振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金基石:《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 哈尔滨: 黑龙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3年。
[5]杨剑桥:《现代汉语音韵学》,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6]王力:《汉语语音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年。
[7][韩]金哲俊:《华语类抄的词汇研究》,首尔: 亦乐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 张克军]
特征3:日母字的零声母化
在《华语类抄》中,声母系统中的日母字都变成了零声母。18世纪的对音资料中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变为零声母的只是少数。例如:《朴通事新释谚解》占21.4%,《汉清文鉴》占16%,《重刊老乞大谚解》占40%[2](136)。但在《华语类抄》中的23个日母字除“饶”字这可能是错的注音,因为注音者可能把它读成[shao]。以外都变为了零声母。并且,与它同时期的《华音正俗变异》中的日母字也全部变为了零声母。因此,我们断定日母字到19世纪末已经全部变为零声母。例如,沈阳人习惯把“人、日、热、如、软”等字念成in、i、ie、yu[y]、yuan[yan][2](137),这与《华语类抄》一致。《华语类抄》序中说:“……盖近日京音如是,故不能不尊然。至于各省语之或有异同者不得尽从”。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华语类抄》的汉字音应该是北京次方言辽东话。
特征4:“?、銴、醞”不能分辨汉语中的正齿音和齿头音以及精系字的颚化与否[4](102)。
《华语类抄》用“?、銴、醞”来分别为汉语拼音声母zh、z、j,ch、c、q,sh、s、x注音。这样的注音法是因朝鲜语声母系统中只有一套塞擦音,不存在卷舌音(舌尖后音)、舌尖前音和舌面前音的区别,即音韵学所谓正齿和齿头的区别而引起的。15世纪中叶,朝鲜人为了区别中近古汉语齿音即塞擦音的正齿与齿头,创制出了“?(精)、銴(清)、靭(从)、(心)、(邪)”左边长和“?(照)、銴(穿)、靭(休)、(番)、(禅)”右边长等文字。前者用于齿头音,后者用于正齿音。但至少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朝鲜人观察的北方音之齿音已有了齿音、正齿组……他们无法掌握这些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用朝鲜语里的一套齿音“?、銴、醞”来注音。……在朝鲜语中自古以来卷舌音、舌面音、舌齿音一直都是非辨音。因此朝鲜人学习中国话今古都有分不清卷舌、舌面、舌齿音的情形,都一律听为同一个齿音“?、銴、醞”[4](135)。因此,在近代汉语舌根音和舌尖齿音中很难找出有规律的对应关系。如果这些文字能保留下来的话,我们就能准确标记汉语的正齿音和齿头音。也就可以区别汉语的正齿音和齿头音。
如不考虑朝鲜语声母没有卷舌、舌面、舌尖前塞擦音的区别,我们可能误认为近代汉语的舌面、卷舌和舌尖齿音与朝鲜语声母的对应关系依然混乱。
二、与现代汉语韵母的对应及特点分析
特征1:《华语类抄》里出现的汉语韵母为49个,比现代汉语的韵母多13个,而且与韵母的结合关系多出现一对多或多对一的情况。
在开口呼里多出现7个韵母,在齐齿呼里多出现2个韵母,在合口呼里多出现2个韵母,在撮口呼里多出现2个韵母。
特征2:有些韵母尚未单纯化
特征3: ü[y]的注音较混乱。
特征4:17世纪末的鼻音韵母“-m”到了19世纪末已经消失
中古汉语韵尾“-m”在北方话里的消失是近代汉语的显著特征之一。但是对于它消失的年代,学者们有不同的推测,至今尚无定论。王力先生推测为16世纪以前,而金基石推测为15世纪在北方音中就已经消失,他甚至推测14世纪末“-m”韵尾已经开始消失或安全消失了[4](288) 。因此我们推测-m早在14-15世纪中叶以前在北方话中开始消失,到16世纪初完全变为“-n”。
特征5:很难看出舌尖音化。
汉语的[]和[]是依赖于其前面声母的非自主性元音,[]出现在z、c、x之后,[]出现在zh、ch、s之后。在《华语类抄》里,“顆”与“?”没有严格的区别,但是大部分时候用“顆”。事实上,《华语类抄》中的汉语对音没有“△”, “△”是朝鲜学者在编撰韵书及谚解书时,为了表示汉语的舌尖元音而造出的韵母韵尾,一般用“鉸△”(精组字)和“鉾△”(知组字)来表示韵母的舌尖音化,所以单从朝文字母注音很难看出舌尖化问题。金基石先生对朝鲜韵书中的谚文注音考察后指出,《洪武正韵译训》时期支韵齿音的庄、章、知组韵母已向舌尖音过渡[4](229) 。
三、结语
虽然《华语类抄》是用表音文字做注音符号的,但是符号本身的音值并不十分精确,哪些字母代表哪种汉语音值也很模糊,所以需要透过注音形式分析它们所代表的真实读音,而不能把注音字母直接当作汉语的本来读音[3](288)。加之,朝鲜语属于黏着语,它的语音体系毕竟与汉语不同,因此,根据《华语类抄》的材料研究19世纪汉语的语音,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所以,从《华语类抄》的材料上所拟出的音系不能完全当作近代汉语的音系,至多只能算是近代汉语音的一个粗糙轮廓。
《华语类抄》是在韩国古代朝鲜朝时期刊行的文献资料,它的刊行年代正处于近代汉语时期(13世纪到19世纪)。因此,它为近代汉语音系的音值及演变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根据。近代音在时间上距离现代汉语很近,语音系统与现代汉语大同小异,因而分辨的准确度较高。近代的对音和古老的对音,一定有很多共同的规律,近代对音研究所总结出的规律对于研究中古以至于上古的音都有参考价值[3](289)。就此而言,《华语类抄》的汉语音系研究对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具有一定的助益。
参考文献:
[1]李得春:《朝鲜对音文献标音手册》, 哈尔滨: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2年。
[2]李得春:《韩文与中国音韵》, 哈尔滨: 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98年。
[3]耿振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金基石:《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 哈尔滨: 黑龙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3年。
[5]杨剑桥:《现代汉语音韵学》,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6]王力:《汉语语音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年。
[7][韩]金哲俊:《华语类抄的词汇研究》,首尔: 亦乐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 张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