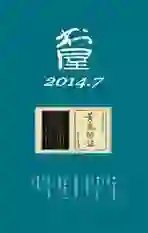访台湾逢甲大学高承恕教授 (二)
2014-08-18燕妮
燕妮
因缘际会:父亲筹钱办逢甲
高教授对家庭历史的回顾,使我深深感到,他的父亲高信先生从自己童年和少年的经历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办教育可以提供人生中最关键的改变机会。他一旦有机会,有能力,就想要创造条件办教育。同时我也约略知道,高信先生的人生道路虽然得益于教育,但他的事业并非从教育开始。他其实是宦海沉浮之人,长期在国民政府里任职。1949年底,他从成都辗转飞到台湾去以后,还继续在某些部门中担任了不同的职务。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得以让他在办私立大学上施展拳脚的?而又是什么原因,让高承恕教授也同样热衷于教育事业,而且矢志不移,这也是我非常想了解的。
王:您能否讲一下,您父亲到台湾以后在当局任职的情况?还有他当逢甲校长和董事长的经过。
高:我父亲从德国留学回来就到南京国民政府任职,一直都在政界服务,曾经在广东省当过地政局局长,还当过广东省政府的秘书长,在1949年以前,他官至国民政府内政部的次长。当时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时候,正是在内政部当次长。到了台湾以后,继续当了两年所谓的“内政部次长”,然后在教育部门当了八年“次长”。从1952到1960年,实际上他做的都是跟教育有关的事。有一段时间,大概有四年时间,他从教育部门副职的位置上下来了,赋闲在家,没有事情做,处于半退休状态。
王:半退休状态?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高:蒋经国上台以后,有一次亲自到我家里。那次我刚好放学回家,看到弄堂口全部戒严了,有很多保镖站在那里。蒋经国那次是在弄堂口就下了车,一直从外面走进我家的。那次蒋经国对我父亲说,教育部门要换人了,要我父亲下来,不再当教育部门的次官了。
我父亲当时想,可能不见得再有机会在政界有什么前景了,也就因为这样的因缘际会,有了这么一个空档,父亲才可能到台中去接办逢甲工商学院。那时候刚好碰到逢甲工商学院经营不善,整个董事会要改组,我父亲就是这样接手来办学的。父亲把学校搬到现在西屯这个新的校址,一切重新来过。他在1962年当了逢甲工商学院的院长。
王:我从查到的资料中看到,这所学院最早是由丘逢甲先生的儿子丘念台先生在1960年创办起来的。为什么您父亲去接手呢?
高:逢甲大学最开始开办的时候,并不是我父亲在经营,当时是丘逢甲先生的儿子丘念台先生,为纪念他的父亲创办的这所学校。但是,学校从1960年起开办,遇到一些困难,经济上出现了一些状况。丘念台先生跟父亲很熟,他们抗战之前就相识了,他来找我父亲,希望能找到适当的人来接手办这个学校。
我父亲要接办学校的时候是在1961年。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已经念初一了。父亲认为办学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一直都很想办学,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但是,当时这件事遭到了我母亲的坚决反对。母亲和父亲吵架,因为,一来,家里没有钱;二来,逢甲当时的情况又不太好。我母亲说,你去收这个烂摊子干什么呢?!
我父亲虽然一直是在当局做事,有地位,但是没有钱。虽然没有钱,但他还是想要办学校。我母亲虽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听从了父亲的话,找我外祖父拿钱来办学。母亲家里也是华侨,我外祖父是加拿大的华侨,他在加拿大开了两家餐馆,经营得还不错。我母亲自己拿了一些钱出来,还跟别人借了一些钱,就这样筹措了一些资金来接办逢甲。
父亲接手做了逢甲工商学院的院长之后,重组校政,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迁校址的决定。原来逢甲不是在现在的地方,是在大屯,我父亲决定把原来的地方切割掉,然后把学校搬家搬到西屯。西屯这个地方,早期还很偏僻,地也很便宜,都市的发展还没到达那里。
王:逢甲开始的时候是怎样运作的?
高:父亲筹到钱建了一栋教学楼以后,就马上开始招生。收了学生,收了学费,然后再去还债,那时候基本上是滚动式运作。当时台湾的大学很少,所以,招生基本上不是问题。有了生源,学生交了学费,学校就有一定的固定收入,大约有了百分之六十的经费。用招生的收入,然后再借一部分钱,也就能够滚动起来,学校就能运转了。
现在回头想,其实那时候是很艰难的,但父亲他老人家就是有这个意志力。父亲因为干了八年所谓“教育部的次长”,有一些人脉,看他的面子,可以邀请到很多好的老师来任教。刚开始办学有好老师是很重要的,一个学校不见得要有大楼,只要有好的老师,就会有学生来。只要你规规矩矩地办学,也不会缺少学生。逢甲开办的时候因为是以工和商为主,正好那时候台湾的经济也慢慢开始发展,所以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也不是大问题。
王:您父亲当院长一直当到哪年?
高:这中间还出现一段插曲。我父亲办学大概办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吧,我还记得很清楚,是在一个星期六,我在家接了一个电话。是谁打来的?是陈诚办公室。陈诚那时候是所谓“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他们问我,父亲在不在?我说不在,我父亲在台中。他们又问,能不能尽快找到你父亲接电话?
我只知道这是个很重要的电话,那时候也没有手机,转了好几个弯,辗转找到了我父亲。我告诉父亲,“副总统”要召见他,父亲连夜就从台中赶回台北来了。陈诚对父亲说,侨务工作你要负责啰。就这样,我父亲又接任了侨务部门的负责人。
虽然如此,但父亲始终也没有放弃办教育这件事,父亲把逢甲大学的院务、行政工作,交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张希哲。张希哲那时候是台湾的“立法委员”。父亲让张希哲来替代自己当逢甲的院长,而他自己就当了逢甲的董事长。到现在,台湾还是这样规定的,你如果是从政,就不能兼职,要避免利益冲突。我父亲当了董事长以后,就不用每天花很多时间处理学校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在逢甲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他就管决策中的一些大事情。
父亲因此而在逢甲建立了一个体制:董事会管大的方向、大的决策和规划等事情;而院长则是管理日常的行政工作。这就出现了一种明确的分工,董事会有董事会的职责,校长有校长的事。我回头一想,这样一个体制是很好的。endprint
我父亲在当局做了九年多快十年的侨务工作,一直做到退休。退了之后就有更多的时间呆在逢甲了。
王:办学需要资金。高信先生在当学校的董事长的时候,还是需要为学校筹集办学的资金吧?
高:对,父亲还是要去为办学借钱、筹钱。他刚开始办学的时候,经费一度很困难,薪水都发不出来,我母亲为此到处去借钱,甚至把她自己的首饰拿去变卖。一个学校在刚开始办的时候确实很难,学生才那么几百个人,资金根本周转不过来,收的那一点学费根本不能支持几个月。开始时是想滚动式地经营,借钱、筹钱,招学生收学费,但是有一段时间根本就入不敷出,钱不够用,那就只好跟银行贷款,等到下个学期收了学费,才把银行的钱还掉。反正就是这样不断地循环,借钱、还钱。好在当时银行也很愿意借钱给学校,相对来说,借钱给学校还是比借钱给企业风险小,因为学校每年都在招生,可以收到学费。
那时候办学校,碰到一个较好的大环境:台湾的经济正在开始起飞,正在进入一个扩张期,对人才很需要。这样,学校一定能招到学生,学生毕业了一定能找到工作。因为经济在发展,总体的氛围算是安定,没什么动乱,没什么运动,大环境在往上走,所以那时候也是逢甲扩充得比较快的一段时间。我讲这个就是说,办学也要掌握时势。加上前面讲过的,父亲在教育界有广泛的人脉,使得他能够找到很好的老师来逢甲给学生上课,这对招收学生很有利。所以,这个阶段逢甲一直是往上走的。到1980年,教育部门就准许逢甲正式升级,从学院升到大学。升到大学以后就又是另外一波的发展了。从经营角度讲,一般超过六千到七千人以后,经济规模就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了,可以有规模经济收益了。
证明自我:学校氛围再突破
高承恕教授于1965年夏天考入台湾东海大学,那年他十七岁。后来去美国留学,三十岁时学成回台湾。为了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回避与父辈的关系,十几年一直不去逢甲大学,而在东海大学任教、带学生,开创自己的事业。他对东海大学充满了感情。2013年春天,他还在《绿苑春浓》一文中写道:“年少的心怀着对东海自由浪漫的憧憬,走进了校园。这是我一辈子学习、成长、工作、生活最重要的地方。”直到父亲快九十岁,他才蓦然回首,发现自己若再不介入逢甲大学的事务就对不起父亲,这才开始担任逢甲大学的董事。而他的介入,又有自己的理念并努力去实现。
王:高教授,您是在什么时候担任逢甲大学的董事的?有什么机缘没有呢?
高:我现在讲讲我自己介入逢甲的原因。我在美国留学,学成以后三十岁就回到台湾,在东海大学教书。前面十几年我从来不去逢甲,当时我父亲是想要我去逢甲的,但是我不去。我是想,我不只是要证明我是父亲的儿子,更要证明我就是我。后来我怎么会在东海大学社会学界带着一批学生呢,其实很简单,我实际上是回避跟父辈的关系。现在回想,那时候我是极其无理的,很对不起我的父亲。人都是这样,你想要证明你自己,干嘛要继承啊!所以,有十几年,我一直不去逢甲,回家就只是吃饭,谈都不谈这个事。
后来,一直到我父亲快九十岁了,他也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就到我家里来,对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加入董事会?你在东海是办教育,在逢甲也是办教育。那时候他说的一句话,让我有些改变,有些想法了。父亲说,你在东海是可以带一批学生,但是,你如果把一个大学搞好了,你一年培养两万个人,十年你就能培养很多人了。我觉得父亲的这个话好像是很有点道理,因为那时候东海大学跟“台大”是平起平坐的,而逢甲大学是落在后面的,这让我觉得很有一些挑战性。
为去逢甲当董事的这个事情,我也磨蹭了一段时间。当时我在东海大学已经是社科学院的院长,刚好东海要换校长,学校也有一批老师要拱我出来竞选东海的校长,正好是在这一个点上。是继续留东海?还是到逢甲来?好像是处在一个路口上。父亲年纪大了,他跟你讲一个事,你开始会想一想了。年轻的时候自己会一心要证明自己,后来就会想一想父亲的话了。最后我是来了一个折中,继续在东海教书,逢甲这边我先进董事会,只担任董事的角色,也不当什么董事长。
王:您进了逢甲大学董事会以后,是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董事,还是有什么举措?
高:我进了董事会以后,好像有了一个新的平台。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可以讲讲的,假如说中国大陆有想办特色教育的人,也许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参考吧。
我在逢甲当了董事后,父亲就退了,他不再担任董事长了。有一天我跟父亲说:爸,如果我要做,我就要做一件事情:三年内,我要聘一百个博士,而且大部分是国外回来的。这话把我父亲吓了一大跳,他说:儿子,那要多少钱哪?!我说,这样才能使学校从量变到质变;也就是需要三年,聘一百个国外好的大学的博士,挖一百个人回来,逢甲就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
王:董事会其他的人对你的想法怎么看?
高:记得在开董事会的时候,我的这个建议被老一辈的人骂得一头疱。他们说,你这个败家子,聘人不要钱哪!大家都反对。但是,我还是坚持,所有我要挖来的人,薪水通通要再加三分之一,即要比公立大学高三分之一。这就像喝咖啡一样,是咖啡多还是水多?你不到那个浓度就没味道嘛。
后来,我真的三年就搞了一百多人来,他们的薪水就是比公立大学多加了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从美国的大学、欧洲的大学回来的最好的人才,他们的到来,一下子就把学校的生态氛围改变了。我觉得这是一条很好的经验。如果大陆真的有私人要办教育,简单地说,首先就是要找好的老师,要找对人。有了好的老师,自然就有好学生,讲穿了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王:这个道理和您父亲当年利用人脉关系找好老师来逢甲是一样的。
高:表面看,逢甲一年多支出很多人事费用,但正是因为有人了,这些人又带来很多新的资源,这就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你找到大和尚,他肯定有能力化缘。这就形成了另外一种Cycle,即另外一种循环。其实,坦白讲,这十几二十年,逢甲能够有点突破,完全是在于人。有好的老师,有好的课题,你再配上好的设备,它自然就会动起来。endprint
办教育这个事,抗战的时候,西南联大有什么物质条件呢?它一样可以培养出第一流的科学家,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这些人。
王:高教授,能讲讲您在逢甲大学董事会中的职责和待遇吗?
高:我在东海大学当专任教授的时候,就不能担任另外一个大学比如逢甲大学的专任教授;也不能任逢甲大学的执行董事、专任董事长之类的职务。我是靠在东海教书的工资养家糊口。当董事,不能拿工资,只能有一些车马费。所谓的车马费,是每当有任务,比如去开会,就可以报销路费和住宿费,但那是不足以养家糊口的,所以我一定要在东海教书,这样才有专职的收入。台湾教育部门有规定。这个规定是为了避免利益的纠葛。现在我在东海大学退休了,就可以拿逢甲大学这边的工资。我在逢甲当副董事长,工资跟在东海大学当教授的工资是一样的。
在逢甲大学当副董事长是实际管事的,但是我不管日常的事物,我是管大方向、大原则这种事。日常的事情有校长弄得好好的。董事会只管决策中的大方向,或者财务上的事。这是一种分工,这也是我父亲早年接手逢甲时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体制。这几年当局规定私立大学董事会中可以有一个执行董事是专任的,执行董事的工资跟教授是一样的。我拿的就是这份工资。
王:我看到几篇对大陆私立学校的调研报告,这些学校的投资人像股份公司的投资人一样可以分红。在逢甲大学是怎样的?
高:这方面当局有规定,不能分红。说什么今年有盈余,我们几个董事大家分了,这是绝对不行的,一毛钱也不行!当局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去年逢甲大学大概有几千万的盈余,每一毛钱都要再回到学校,作为学校进一步发展所用,完全没有分红这个东西。除非你偷鸡摸狗,巧立名目,但如果逮到你,你就是犯法了。按照法律规定,任何私立大学的董事,全部都是不能分红,不能拿工资的。近些年当局允许有一位专职执行董事,是可以拿工资的。当然,有些学校不那么上轨道,既然不能公开分红,也许他们会做一点变通的事情。逢甲大学有自己的理念,自然不会那样做。台湾有一百多所大学,它不可能平齐,有严格的规范是对的,只有用法律来规范它。我们中国人老喜欢说“凭良心办事”,那是难做到的,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良心。
王:当局会来检查学校的账目吗?
高:不但是教育部门来查我们的账目,而且我们还自己掏腰包,请了国际的会计师事务所来查账。我们的财务,收支、预算,关于预算的所有事情,你上网都可以看得到,全部都公开、透明。包括教育部门的奖励、审查,我们跟别的单位的合作等等,学生上网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可以做到这样。
学校有公信力,别人都知道你不会乱搞,所以,我们的产学合作,比很多公立大学都要多。他信任你,你是透明的,他知道你不会怎么样。这是一种Trust,不是个人的信任,是一种制度性的信任。我相信你这个组织,即Institution,而不是信任某个人。我摊开来让你查,财务是公开的。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排,我的总务,我的会计,都不是跟我有关系的人。我们是用人唯才,专业为本,所以,我的会计主任跟我是没有任何私人关系的,总务长跟我也是没有任何私人关系的,所有的采购,通通照规定的程序来。
对我来讲,这些跟我以前教书的那个理念是一样的,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誉,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尊严,也算是一种成就感吧!
王:在贷款方面,有什么有利于教育的做法吗?
高:我不知道大陆的情况怎样。台湾的利率不高,贷款利息只有百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可以分二十年还款。这样我就有法子了,比如说我借两个亿,分二十年还,每年本跟利也就是分期付款嘛,我每一年是可以负担得起的。而且,我投入了,是会有产出的,有形或者无形的产出。我们就用这种温和举债的方法来做。学校要买仪器,买设备啊,如果光是靠学校的结余,那是绝对不够的,那你就要靠其他的资源来帮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但是有一点,预算一定要严格的管控,钱要花得到位。比如我现在有两万多学生,专职教师就有六百多位,还有一些兼职的教师,兼职教师大概有一千多位,但是,职员和非教学的人员只有六百多位。我的意思是说,预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自己一定要很清楚,你这一年都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资源应该怎么配置,要实现哪一些目标。钱不能乱花,也不是齐头并进。学校这一年发展的重点在哪里,比如,一、二、三,这是重点,该花的钱就花,不该花的钱不能乱花。
我们每半年就对预算的规划和执行做检讨,不适当的地方就做调整。其实,当局只是要求我们一年做一次检讨,但是我们自己是半年做一次,因为一年一次就晚了,钱已经花出去了,覆水难收。半年检讨一次就可以及时发现漏洞,及时进行调整。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心得吧。
王:私立大学作为非营利财团法人,在财务运作中不会有盈余吗?有盈余如何使用?
高:我们逢甲有学校的校务发展基金。在经营了若干年后,我们也存了一点钱。因为我们没有分红等这类东西,所以有盈余的话,就进入到这个发展基金中。这个基金不是只摆在那里成为一个静态的东西,它不断地在滚动:存一些在银行,做一些投资,买一些股票、债券。学校里有一些专业老师,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做分析,做投资。虽然这几年经济起起伏伏,有涨有落,但是总的来讲,他们还是为学校赚到了钱的。
王:台湾当局会给私立大学补助吗?
高:台湾的教育格局是这样的,公立大学,它当然有当局的预算支持;那私立大学呢?就看你的表现了。当局规定:对私人经营之教育事业,优良者给予奖励和补助。对私立大学的奖励和补助,是根据你的教学,你的研究,特别是你的行政,你的账目、财务等绩效,通过评鉴来给予的,表现得好的学校,就多给你一点补助。
王:补助的钱大概占预算的多少呢?
高:从近几年来讲,逢甲大学是私立大学里面教育部门给钱给得最多的,大概占我们一年财务总预算的百分之六、七,还不到百分之七。当局有这么个预算,一年五十个亿。endprint
王:能讲讲当局评鉴私立大学的情况吗?
高:早在1975年,台湾教育部门就开始了对大学的评鉴。近四十年来,历经直接办理,委托专业学术团体办理,至2005年改为组成财团法人团体“高等教育评鉴中心”负责办理。当局依据行政部门在2007年颁发“大学评鉴办法”作为重要的法源,通过一个由专家学者组成的类似评鉴协会的组织来评量,这个评鉴协会全部是学术界的专业人士,他们针对不同的学门,组织邀请这个领域里的专家,专门针对这个学门来评定,那就是硬碰硬了。大概采取的是一个打分制的方法,然后,根据评定的结果来给予补助。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很完备的评分规则,而且大家都很清楚这个规则,是很公平、公开的打分制。
当局通常是三年评定一次,当然,针对不同的项目有所不同。基本上是建立一个相对客观的评量体制来评量。虽然也有很多人抱怨:搞得大家都很累,每次评定都是搞得人仰马翻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比较公平的,不是哪个人说了算。实际上当局也是用这种方法对私立学校有一个监管。办不好我就不支持你了。被新闻媒体一登,如果是好的,你就好了;如果是不好的,就名声扫地,也就没有人来投考了。
王:招生竞争激烈吗?
高:学生报考学校,有很多人都是同时考好几个学校的,比如我们台中,好几个学校都有EMBA,那到底去哪一个学校?这就有一个比较。当然他们会选择去最好的学校了。这对学校来讲就是一个强烈的竞争。在台湾来说,我们私立学校也要跟公立学校竞争,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民间的学校可以跟公立的学校去竞争,我今年不行,但明年我就要超过你!
王:私立大学收取的学费是不是比公立大学高?
高:是的。私立学校虽然收取的学费比公立大学稍高一点,但我们遵循市场竞争原则,以质量求生存,以便提供给民众更多的选择。
要让更多人来选择你,你要怎么办?这对我们来说就会激发一种新的力量。像这次来成都搞研习这样的活动,我们一直是带头去做的。这种研习对学员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他们会形成一个网,他们之间会互相联系。同届之间,上下届之间,他们都会去谈,去说,大家都会因此而互相提高。
王:毕业生会回馈学校吧?他们的回馈对学校的经营应该很有好处。
高:这么讲吧,回馈有多种形式。有一些毕业生设立了学术发展基金,他们办很多促进学术发展的活动,用这种方式来回馈学校;另外,有的人就直接把钱捐到学校。
王:是不是像香港那些大学,学生回馈学校,建教学大楼?
高:台湾一般都是聚沙成塔,很多人,一人捐一点。我们五十周年校庆时就是这样,完全是校友捐款,有的人捐得多,有的人捐得少,最后弄到一亿多。
逢甲的向心力、凝聚力特别强,这算是一个文化吧,我们也很重视这个东西。比如在我们学校,校长也好,老师也好,对学生的事情,对校友,都非常关心,这变成了一个风气,成为了一种文化。我们并不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让校友捐款,我们讲人情,建立感情。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办教育的精神。我们很强调的是,在校的学生跟毕业以后的学生要互动。讲老实话,我这次也可以不带这班学生出来。我跟他们出来,也是跟他们一样,坐飞机坐的经济舱。长期以来,这变成一种风气,我们的校长、老师,参与学生的活动比较积极,这样一来,大家就会有感情,有较深的交流。是不是说就是为募款,那也不是,像他们这个EMBA高阶班,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没有向他们募过款,他们有主动捐助的,但是我们没有募过款。但是我要强调一点,他们自己会主动做很多事情,他们自己会办很多活动,那我们的招生就不用宣传了,我们也不用自己花钱去做广告了。
(未完,待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