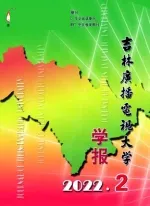文化创伤视角下哈罗德·品特戏剧阐释——以《送菜升降机》为例
2014-08-15任俊玉
任俊玉 贺 萍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长春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10.10——2008.12.24)被认为是继萧伯纳之后英国最重要的戏剧家,因“在其剧作中,揭露了日常闲谈掩盖下的危局,直闯压抑的密室”①而被授予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随后“品特派风格的”一词被列入《牛津辞典》,从而划定出具有鲜明地貌特点的“品特领地”。品特早期的戏剧颇受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等荒诞戏剧大师的影响,被划归为“荒诞派戏剧”。英国评论家欧文·瓦尔德首次将哈罗德·品特的戏剧称作“威胁喜剧”,以其早期创作的《房间》、《送菜升降机》、《生日晚会》、《微痛》为代表,戏剧以封闭、狭小的空间为背景,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等方面来展现复杂而又含混的矛盾冲突,凸显了饱受外来威胁的人类异化的生存状态,而后“威胁喜剧”成为品特戏剧的独特旗帜。国内的品特研究主要侧重从文本和主题两方面着手,运用历史社会批评、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批评方法来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以文化创伤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对品特的戏剧《送菜升降机》进行阐释。
*童年记忆与文化创伤的双重合谋
弗洛伊德曾说:“童年的创伤更加严重些,因为它们产生在心智发展不完整的时期,更易导致创伤”。②童年的经历对于人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童年时代经历的创伤更会如同幽灵一般伴随其成长,它会改变当事人对人、生活以及未来的态度。1930年哈罗德·品特出生于英国伦敦哈克尼区一个葡裔犹太家庭,年轻品特的创伤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犹太血统,在以后的采访中他曾回忆说:“14岁我被家人带回伦敦,就在抵达的当天,我亲眼目睹纳粹德国投下的炸弹在头上呼啸而过的恐怖情景”。③在随后的两次被征召兵役事件中,他都将自己登记为反战者,这种切身的童年经历为二战烙印在品特脑海中的创伤记忆的萌生埋下了种子。
“文化创伤”这一概念是21世纪初期西方社会学家为研究人类历史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大屠杀、911等)而提出并使用的。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曾说:“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④文化创伤理论认为事件本身并不一定伴随有创伤性,创伤是通过当今社会文化为其构建的媒介而产生的,它具有一种反身性取向,并且认为“唯有集体的模式化意义突然遭到驱逐,事件才获得创伤地位。是意义,而非事件本身,才提供了震惊和恐惧的感受。意义的结构是否松动和震撼,并非事件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过程的效果”。⑤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构建和书写创伤记忆的工具,作家通过回忆创伤让“记忆来临”,从而达到缓解和修复心理创伤的目的,因此“借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⑥
作为一名犹太后裔,品特血液中的来自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创伤感支配着他的写作,诚然,创伤叙事是人在遭遇现实困厄和精神磨难后的真诚的心灵告白,他的戏剧“脱口而出的对白话里带刺,简短的话语可以伤人,半句话就能把人打垮,而沉默不语则预示着灾难降临。”⑦戏中人物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他们相互威胁、嘲讽,在这里威胁、暴力统治一切,沟通形同虚设,他将扭曲的人性和弥漫于二十世纪末复杂的绝望情绪发挥到淋漓尽致,而这一言说的终极目的是“藉由让广泛的公众得以参与他人的痛苦,文化创伤扩大了社会认知的同情的范围,提供了通往新社会团体形式的大道”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为戏剧家的哈罗德品特深厚的人文关怀。
二、《送菜升降机》——死亡与异化的创伤记忆
《送菜升降机》写于1959年,是一部独幕剧,属于品特早期戏剧中的扛鼎之作,剧中的主人公班和格斯是两个被秘密组织雇佣的神秘杀手,他们在一间带有送菜升降机的地下室随时等候命令去完成杀人的任务,两人于百无聊赖的等待过程中互相心生怀疑,随着剧情的发展,楼上的人要求他们接连不断地送菜品,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格斯转身去厨房之时,班接到上级的命令,出人意料的是班将枪口指向了上装、背心、领带、枪套和手枪都被剥光了的同伴格斯,戏剧在两人长时间沉默言与对视中落下帷幕。
(一)充满威胁与死亡的房间
童年品特在二战的颠沛流离中体验了生与死的界限,品特没有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切身体验,但那里却是犹太人噩梦的开始---一个大屠杀的场所。品特作品中的“房间”就是一个意象化的“大屠杀”场所,从1957年开始创作的戏剧《房间》开始,品特早期的“威胁喜剧”始终被框定在一个幽暗、封闭又狭小的私人空间之中。
《送菜升降机》的故事背景依然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一间仅靠一架送菜升降机与外界获得联系的地下室。班和格斯是两名杀手,除此之外,关于两人的背景、组织的名称再无多言,他们被禁闭在一个地下室随时等待老板的命令去完成杀人的任务。戏剧以班和格斯两人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之中谈论着报纸上的新闻内容作为开端。
班靠!
【他捡起报纸。
有这种事?听听这个!
【他念报纸。
一个八十七岁老人想要过马路。可是车来车往,明白吗?他不知道该怎样过去。因此他爬到一辆卡车底下。
格斯他干吗啦?
班 他爬到一辆卡车底下。一辆停着的卡车。
格斯不会吧?
班卡车一开动了,从他身上碾了过去。⑨
剧作开场便是这样一则让人不寒而栗的死亡消息,一个老人因交通拥挤在众目睽睽下爬到卡车底下,行人居然无人阻挠,任凭一条鲜活的生命顷刻间消失,公众的冷漠可见一斑。对于一个死亡的消息,格斯和班显然已经达到了麻木的状态,他们只是当做一个笑话来打发自己的无聊时间,他们嘲笑老人的愚蠢却无半点同情。第二则新闻则更加令人震惊——一个11岁的哥哥杀死了一只猫,却将罪责嫁祸到自己8岁的妹妹身上,天真无邪的儿童却做出这等让常人难以接受的残忍事件,天使瞬间变成恶魔。两则简短的负面新闻轻而易举就为我们营造了一种无处不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氛围,仿佛人类的存在就是荒诞与死亡的结合。除此之外,突如其来的厕所冲水声、从门下悄然递进来的信封、迅速落地的大木箱和组织下派命令的纸条等,一系列的神秘事件更加重了地下室演变成屠杀场的预设。
(二)无法挣脱的外部力量——人性疏离与异化的根源
古老的犹太民族自其诞生之日便开始了自己的艰辛之旅,经历了多次民族大迁徙,犹太人生活在一个异国的、敌对的世界尤其是缺失一种可以把群体感受巩固下来的任何一种宗教形式。这种民族的分散性导致了犹太民族深感自身与他者的疏离感。就是这样一个饱受灾难的民族,在二战中遭受了来自德国纳粹惨绝人寰的屠戮,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浩劫更是犹太民族内心难以抹去的文化创伤。品特的威胁戏剧《送菜升降机》影射了这种文化创伤的表征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它营造出的封闭房间意象只是一个大屠杀的场所,而真正所要表达的正如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在他的著作《如果这是一个人》当中所描写的纳粹集中营中的人类走向非人化以及彻底异化的过程。每个个体麻木地听从命令并以取得同伴的性命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听我说,孩子。不要忘了你是在集中营。在这里,每个人都为他自己,你不能考虑别人,即使是你的父亲。在这里,没有父亲、兄弟、朋友这件事。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生死。听我给你的好建议:不要再把你那份面包和饭汤送给你的父亲。你不能再帮助他了。”⑩
戏剧主人公格斯和班是多年共事的老搭档,纵观整篇戏剧,让我们感到的不是两人的友谊而是班对格斯的绝对统治。
格斯 嗯?
班 去点上。
格斯 点什么?
班 水壶。
格斯你是说煤气。
班 谁说的?
格斯 你说的。
班(眯起眼睛。)你说什么,我说的是煤气?
格斯嗯,你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煤气。
班(有力地。)要是我说了去点水壶,我的意思就是去点水壶!11
在此处“点水壶”与“点煤气”已经不仅仅是语言的“能指”,它背后所影射的是语言的“所指”:话语权力之争。格斯最后屈从于班所说的无稽之谈——“点水壶”,其实是表明了格斯的从属地位,“笨蛋”、“蠢人”是格斯对班的惯常称谓,“别唠叨”、“闭嘴”这些命令式的言语在剧作中随处可见,语言成为人们相互攻击、相互威胁的武器。班和格斯只不过是巨大齿轮上的渺小一环,真正的主宰乃是来自房间外部的“闯入者”——幽灵般的上司,他高高在上地导演着这场戏,他于无形中控制着一切,他要求下层绝对的服从。班冷血无情,他拒绝人性的复苏与救赎,俨然一个杰出的杀手。与班的绝对服从不同,格斯班越来越不满意屋内非正常的生活,从格斯深思那个无辜被害的姑娘开始,“我在想关于那个姑娘的事,就是这么回事。”表12明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和自责。格斯的这些“反常”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反抗意味着自寻死路。果然,随着一声哨响,命令到达,当班准备好一切将枪口指向门口之时却发现门后的格斯。
如果将房间预设为屠杀地,班和格斯就是惨遭迫害的犹太人,而这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则是对纳粹势力的极端影射。戏剧通过对大屠杀创伤记忆的诉说,向我们展现的是格斯与班异化的形象:“一个憔悴的男人,他低着头蜷着肩,在他的脸上和眼中看不到一丝思想的痕迹。”13他们麻木、循规蹈矩,不知生命的价值所在。但是,品特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把对于大屠杀的反思降格为专属犹太人的生存、道德或宗教问题,而且要涉及对整个现代性工程本身的反思,从而把避免欧洲犹太人遭受的悲剧再次发生当成我们必然承担的普遍责任。品特血液中的犹太性,促使他形成这样一种集体认同与反思:两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给人类心灵造成的创伤仍难以平复,上帝、科学与理性的光辉并没有阻止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惨剧的发生,现代文明并没有带给我们预期的光明与解放,相反人们越来越囿于自己心灵的枷锁当中,缺乏沟通、相互威胁,隔膜、孤独与日俱增,人类被异化,既渴望人际间的交流以摆脱孤独又心存防备,互相伤害走向更为深切的孤单。人们变成没有面孔的人,不能在别人的脸上发现思考的乐趣,因为情绪、信仰的缺失而失去自己的身份和内在的生命,这种信仰的缺失造成了上帝的缺失和个人良知的丧失,现代文明的危机是一种双重的放逐——人类的放逐以及上帝的放逐。造成人类这样生存困境当归咎于神秘的外部力量,它是一种霸权更是一种极权统治。品特将格斯的命运设定为被班杀死正是对极权主义的控诉,他的反战言论频频见诸各大报端,品特身体力行放弃戏剧创作而投身政治事业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品特作为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能动者,将这种创伤再现并进行传播,从而使得文化创伤的构建得以逐渐完成。正如亚历山大所认为的,“这是论及某种根本损伤的宣称,是令人恐怖的破坏性社会过程的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象征上加以补偿和重建的呼吁。”14
“文化创伤”与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哈罗德·品特作为一个犹太后裔,他是祖辈创伤记忆的承受者之一,无论是早期的“威胁喜剧”《送菜升降机》、中期的“记忆戏剧”《无人之境》还是后期的“政治戏剧”《山地语言》,他始终致力于正义的伸张和人性的探讨,这种创伤记忆的言说与反思始终徘徊于品特的戏剧当中,作为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戏剧家,对于创伤记忆的构建恰恰能够成为抚慰现代人心灵的良药。
①⑦⑨11 12哈罗德·品特.华明译.送菜升降机[M].上海:译文出社,2010:1,3,142,156,162.
②Freud,Sigmund.”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1963(16)
③邓中良.品品特[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4,5.
④⑤⑥14Jeffrey C.Alexander,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Jeffrey C.Alexander(ed).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⑧陶东风.文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1).
⑩13 See Frunza,Sandu.“The memory of the Holocaustin Primo Levi’s if this is a man.”,Shofar.27.1(Fall 2008):36(22).Academic OneFile.Gale.St Marys Colleage-SCELC.28 Oct.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