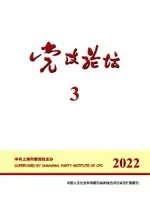社会反腐必须走好群众路线
2014-08-15张树俊
○张树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了制度反腐这一要求。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才能取得反腐的根本效果?习惯认为,反腐是党内的事,是干部的事,因为腐败主要出在领导干部身上,反腐必须从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做起,党的组织必须通过严格规范和一系列制度对领导干部的行为进行约束,对于腐败了的领导干部必须进行严肃查处,所以反腐制度建设重点是党的廉政制度建设。但从腐败产生的根源、腐败行为的制约、腐败案件的查处来看,仅靠党的制度建设是不够的。笔者认为,要取得反腐的根本效果,必须建立社会反腐机制,尤其要走好群众路线,激发群众的反腐力量,打一场反腐的人民战争。
一、走群众路线,推进社会反腐,必须建立疏通机制,拓展群众反腐渠道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样,没有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反腐败斗争也不能进行到底。因为腐败问题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对此深恶痛绝。群众是我们遏制腐败行为和解决不良风气的基本队伍和根本力量。只要我们走了群众工作路线,动员和依靠群众,一些疑难案件就可以找到突破口,查个水落石出。
近年来,广大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满意度越来越高,对反腐败斗争的前途越来越有信心。从已经查处的贪官来看,多数是被群众举报的,并有多数是群众通过网络揭发的。人民群众是反腐败的主体,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为开展反腐败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反腐还只是少数群众参与,大多数群众没有参与到反腐的行列中来。有关研究指出,香港的廉政风气较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举报腐败的积极性很高,97%的腐败案件是通过举报发现的,而我国内地的腐败案,固然也有不少是因群众举报发现的,但比例没有香港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与反腐渠道狭窄及其执纪执法不力有关。
一是纪检不够公开。我国关于惩治腐败的若干规定、条例、通知、意见、办法和有关法规,群众的知晓率不高。有的规章制度还处于纪检监察部门内部掌握的状态,查阅很不方便。一些比较隐蔽的行为群众不太清楚是否属于腐败范畴。一些阶段性、专项性反腐败活动,群众不十分了解,因而也就难以及时有效地举报腐败行为。再如,政务透明度不高,组织活动的操作程序和纪律,如实行听证和质询、网上行风评议等制度也不够严格;政府或权威部门的运作过程透明度小,神秘性比较大,人们缺乏公开地对权力的监督;容易滋生腐败的特殊部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的腐败行为通常都十分隐蔽,普通群众、一般干部难以知晓,因而群众参政议政的意识和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不高。
二是反腐渠道不畅。群众对腐败事件与腐败人员的举报,是实现群众监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尽管不法分子从事贪污受贿等不法活动总是隐秘的,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总会从蛛丝马迹中识破他们。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举报渠道不畅削弱了一部分群众的反腐斗志。目前虽然网络发展迅速,但多数群众尤其是农村广大群众,其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依然主要通过信访的形式,现代科技手段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纪检部门虽然推行领导“下访”制度,但大多领导“下访”都是“高层访谈”,普通群众无法与领导谋面,干部与群众仍然隔着一道深深的鸿沟。
三是执法自由度大。有关研究指出,法律的功能不仅在于惩治,而且在于预防。法律如果不能起到预防作用,那么,法律的惩治功能就会削弱。反腐问题与执法力度有很大关系。事实上,由于执法不力已经严重削弱了人民群众反腐的信心。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在执法力度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对腐败分子的容忍度太大。容忍度大不但无助于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公民的财产,反而给犯罪嫌疑人或者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寻找到了法律的空隙。再比如变味的抓大放小。为什么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腐倡廉,查处大案要案,声势也很大,但给人的感觉总是成效并不明显?这与将反腐倡廉的重点放在查处大案要案而不能从小事做起有很密切的关系。古语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但在执法过程中,似乎是宽容有余而严惩不足。还有执法存在漏洞。在实际操作中对腐败者的惩治存在变异的“自由性”。如对有的腐败者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只处以“党内处分、行政降级”或“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之类的处罚,不追究刑事责任。
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是在纪检公开、群众监督与执纪执法方面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硬性制度规定。这就给群众反腐带来困难,也容易挫伤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为此,一要健全纪检制度,要从完善群众举报的体系和网络着手,规定群众举报、投诉、接待以及限期处理等各项具体制度,进一步畅通群众监督渠道。二要创新检举手段,拓宽群众检举渠道,比如充分发挥现代科技作用,大力推行网络举报、密码举报等等。三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下访”制度。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多做下访工作,主动到群众中去找线索,不能“守株待兔”,“关起门来搞建设”、“坐在屋里反腐败”。四要坚持“零容忍”原则,加大查处与执法力度,真正按习总书记的要求“老虎苍蝇一齐打”。
二、走群众路线,推进社会反腐,必须完善保护制度,激发群众反腐热情
社会反腐也需要有一个动力和保障机制,有了动力和保障机制,才能解除群众反腐的后顾之忧,调动群众反腐的积极性。但现实的问题是,这两个机制都不完善,因而群众积极性不高,使得腐败分子犹如沉在大海里的一座冰山,少部分露出水面,大部分沉在水下。
首先是激励机制不完善。目前群众个人举报的物质成本和社会成本较高,同时对举报者的奖励标准也偏低,所以对举报人缺乏吸引力。就举报奖励而言,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奖励举报人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但尚缺少附加细则,可操作性不强。各地方纪检部门、检察机关更缺少具体量的规定。贪官被“发现”往往事出“偶然”——小偷“偷”出贪官,情妇“爱”出贪官,拆房子也能“拆”出个贪官,目前不少大案要案多数是它案牵扯出来的,群众自发举报的力量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其次,举报人保护制度不完善。举报人挺身而出,勇敢揭露腐败现象,说明人民群众信任党和政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被举报的权力部门及其负责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名义,对举报人实施报复,有些人在举报以后却几次遭毒打、数次搬家、夫妻离异,人生权利受到损害,有的人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现实中,官官相护的情况也很多。举报一个人可能就触犯了某些“利益集团”,举报人即使受不到被举报人的打击报复,也会受到该利益集团其他成员的指责或打击报复,让举报者感到不自在和孤立。所以,现在绝大多数群众只在自己个人利益遭到侵害时,才进行信访举报。否则,一般只在私下议论,而不正面参与。即使参与,也只是匿名举报而已。
再次,对举报人追查制度不尽合理。根据有关规定,对举报失实甚至错告者,是要接受批评教育的,而由于腐败的隐秘性,举报者对被举报人的情况难以详尽了解,许多情况只是听说和猜测的。举报人怕承担风险,所以举报积极性不高。虽然社会上总有些人,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冒着风险,要把贪官拉下马,不过,他们的举报代价,或者说举报成本毕竟太高了,一般人望而却步。
上述问题应该从制度层面上系统地加以解决。比如,要进一步完善举报奖励制度。可设立专门的奖励基金,对支持和参与反腐败斗争有突出贡献者,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再如,要建立反腐败成本保障机制,实行经济补偿制度,让群众以最少的成本投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不因反腐败而遭受经济损失。要健全举报人保护制度,对举报人人身、财产、生活等方面提供保障;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等权利;对举报不实或错误的举报者只要不是有意诬告陷害他人的,应保护其积极性,不追究任何责任。此外,要完善保密制度,细化有关信访举报的保密制度和防范措施,特别是对信访举报中泄密行为的认定和处罚办法,要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解除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后顾之忧。在追究机制方面,应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阻挠群众参与,打击报复、威胁和恫吓群众反映问题,或发挥群众参与作用不力造成严重影响的,视情节轻重追究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者的责任。
三、走群众路线,推进社会反腐,必须建立正本机制,清除封建思想遗毒
如上所述,在反腐败的斗争过程中,群众对不法事件与不法人员的举报,是实现群众监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尽管不法分子从事贪污受贿等不法活动,总要采取各种伪装手段掩人耳目,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总会从蛛丝马迹中识破他们。然而,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识破未必举报。识破未必举报除了上述列举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群众对于腐败问题的认识。
形成全社会的反腐机制,需要广大群众的觉醒。不少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的反腐为什么这么难?原因固然很多,但封建遗毒的影响应该说是重要的一条。列宁曾经说过,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久已过去,但反映封建生产关系的种种观念仍潜在地发生作用,使人民群众在反腐方面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惰性。比如,群众畏权畏势,盲目服从权威等心理现象与封建宗法等级观念还存在。再比如,封建社会这种以裙带关系为用人标准的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任人唯亲”的用人习惯一下子难以更改,亲帮亲,邻帮邻仍被中国许多人视为一种“美德”而大加赞赏。同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钱能使鬼推磨”、“民不和官斗”等传统观念,也是制造腐败的温床,所以,对于一些党政干部用人上的腐败行为,不少群众觉得情有可原。再如,在中国的民俗文化中存在不少消极因素,如爱沾亲搭故,过浓的人情味,红白喜事、节日喜庆、探望病人、庆贺升学等,都有送财物庆贺的风俗,这为行贿受贿找到了借口。所以,反腐要解决“官”的问题,也要花大力气解决好群众反腐的心理惰性问题。
解决好群众反腐的心理惰性问题必须教育群众反封建,以彻底消除群众身上的封建残余思想。
首先要去除封建家长专制的影响。在封建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有序的组合。“修身”是途径,“齐家”是“治国”的基础,“治国”是“平天下”的基础,能齐家便能治国平天下。显然,“齐家”是关键。而在我国古代,“齐家”的基本体制则是“一长制”,因为我国古代一直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在家庭中,父亲具有绝对的专制权,这种专制权也扩展到“治国”“平天下”。如商王盘庚就曾当众宣布:“听予一人之作猷。”要人们服从他一人的指挥,把治国的关键看作是是否一人说了算。这种家长制的管理作风,一直到现在仍有很大的市场。所以要消除封建家长专制的影响,就要让群众去除下对上“贡奉”的认同,当然传统的尊亲敬上的美德还是要发扬光大的。
其次,要去除群众的权力容忍意识。我国封建社会是十分注重权力的。慎子认为,谁服从谁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品德、能力,而是取决于个人的权力。在慎子的眼里,即使尧舜那样的大圣大贤,如果没有权力也无法使别人服从他。韩非也赞成慎子的权力至上说,他认为,讲仁义之道的人越多,国家越贫弱混乱,只有讲权力才能治理好国家。封建社会这种权力至上的观念不仅反映在对权力的重视上,还反映在某些特权上。在封建社会,建立上下关系的理论依据是“天命论”。从商周时起,统治者就把君王、贵族、平民、奴隶的上下关系看作是“天”规定的。到了封建社会,大多统治者都把自己的政权神话,从而形成一种“特权”,因而统治者可以“奉天行事”,随心所欲,甚而可以胡作非为。这些权力至上和封建的特权思想不仅在我国目前的一些干部头脑中还较顽固,且在群众中得到了认同,因而不少人盲目服从权威,把某些干部的使用“特权”视为“正常”,因而自己也就失去了平等要求,进而为腐败分子创造了“自由”的空间。
再次,去除传统的“人身依附”观念。在封建制度之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超经济性质的直接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封建社会,“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人们不是作为“一般人”个人彼此发生关系的,而是作为隶属于某种共同的、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个人彼此发生关系的。这种隶属关系就形成了封建社会中特有的人身依附关系。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早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超经济性质的直接的个人依附关系,但这种依附观念并没有彻底根除。如有的干部在选人用人时,并不在乎德才标准,主要是看被选择者是否听话,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封建依附观念在作怪。为此,要促进群众反腐,就要转变群众的依附观念,不要把个人的利益需要的实现全部寄托在干部尤其是掌握重要权力的干部个人身上,也不要因为害怕权力领导的报复而任腐败分子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