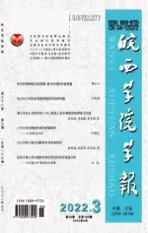异中有同律 同中有异曲——《安娜·卡列尼娜》与《米德尔马契》比较研究
2014-08-15叶梅
叶 梅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241008)
《安娜·卡列尼娜》(以下简称《安》)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不朽之作,自问世以来一直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米德尔马契》(以下简称《米》)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女性作家乔治·艾略特的代表作。出版后,艾略特的声望随之达到顶点。两部作品都发表于19世纪70年代,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个时期无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处于社会的过渡阶段。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新思想、新观念、新道德与旧的传统势力正进行着激烈的较量。英国著名评论家F.R.利维斯曾在他的权威著作《伟大的传统》中称艾略特的作品具有托尔斯泰式的思想高度。“乔治·艾略特的伟大不如托尔斯泰的那般卓绝盖世,但她的确是伟大的,而且伟大之处与托尔斯泰相同。”[1](P163)这两部小说的可比性很强,在小说结构、心理描写、女性意识等方面都有很多异同。
一、双线结构
两部小说的创作都经历了一些波折。在托尔斯泰的初稿中,他是想写一个名为《两段婚姻》的故事。当时作者只想写安娜这个人物,而且把安娜构思成了一个堕落的女性形象,列文这个人物并不存在。但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改变了这种想法,赋予了安娜许多令人同情和美的要素,同时为了突出社会问题又加入了列文这个形象。乔治·艾略特写《米德尔马契》的初衷是创作两部独立的小说,一部是讲述女主人公多萝西娅·布鲁克故事的《布鲁克小姐》,另一部是讲述医生泰迪乌斯·利德盖特故事的《米德尔马契》。后来艾略特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两部小说的主题有某种共通之处,才将两部小说合二为一。基于这样的创作经历,两部小说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双线结构。《安》中有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条是安娜追求爱情婚姻的悲剧,另一条是列文的精神探索和家庭生活。《米》同样采用了双线结构:一是理想主义少女多萝西娅的悲剧婚姻和理想的破灭,二是利德盖特可悲的婚姻与事业的失败。可以看出,两部小说都在叙述一男一女的故事,题材十分相近。安娜与多萝西娅,列文与利德盖特呈一一对应的关系。
《安》发表后,其作品的结构曾引起过评论界的争论。许多评论家认为《安》的结构是分裂的,托尔斯泰写的是“两部而不是一部长篇”[2](P1),“康斯坦丁·列文的故事是勉强插入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里去的”[2](P1)。事实上,《安》并非是两部小说的简单糅合,安娜与列文这两条线索也不是相互孤立的。正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说,《安娜·卡列尼娜》的联结方式,“不是靠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交往),而自有其内在的联系”[3](P55)。这种内在联系,指的就是作品中的两条线索统一于同一主题,即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是俄罗斯贵族受资产阶级新思想的影响,在家庭、婚姻等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国家面临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与《安》类似,《米》的情节构思也对传统的情节结构提出了挑战,小说运用对比、平行、对称、重复等手法,将两条主线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把众多的人物写了进去,成功地表现了这样一个主题:社会中每个个体都不是完全孤立的,他们的命运是相互影响,悄然相汇的。艾略特在小说中借叙述人之口表达了这种观点:“任何人,只要他密切观察人们的命运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交叉现象,他就会发现,一个人的生活怎样对另一个人的生活产生缓慢而微妙的影响,尽管我们对素昧平生的人报之以无动于衷或漠不关心的目光,这种影响却对我们发出深谋远虑的嘲笑。命运之神把我们的剧中人握在她的手里,正冷眼旁观呢。”[4](P93)
《米》中众多的人物、情节盘根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状结构。艾略特在《艺术形式笔记》中写道:“多线索的网状情节并不是各个独立的部分简单组合就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各个不同的部分具有相互吸引的特性形成网状的结构。”[5](P33)在小说松散的形式之下,各部分之间隐藏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人公多萝西娅与利德盖特往来于各主要人物之间,使两条情节线不断穿插交织,融为一体。当利德盖特为布尔斯特罗德利用,面临着身败名裂的危险时,多萝西娅不但给予他经济上的援助,还在精神上给他信任和安慰,并且四处忙碌为他洗刷罪名。因此,小说中的两条线索除了有统一于同一主题的内在联系外,还主要靠人物活动和人物交往来完成外在联系。而《安》没有这种穿插交织与相辅相成的外在联系。两条平行线一经展开便各自分流而去,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逐渐靠拢,从而达到自然和谐的衔接,形成一个非常别致精巧的拱门结构。作品沿着两条主线衍生出若干条分支,呈现出辐射状的情节结构。这就是说《米》中两条线索的联系是双重的,既有外部的联系,又有内部的联系,而在《安》中却没有这种外部联系,而是隐秘的、内部的联系。
二、心理描写
托尔斯泰是描写心理活动的大师,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心理分析几乎是使托尔斯泰的创作才能具有力量的一种极重要的特质”。[6](P31)《安》独特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取决于其出色的心理描写。《米》出版后,乔治·艾略特的心理分析手法得到评论界的一致肯定和赞扬。著名评论家巴巴拉·斯摩里为艾略特撰写专著,认为艾略特在心理描写方面为小说艺术创造了新的深度,并将艾略特视为现代小说的先驱之一。
同为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与乔治·艾略特的相同之处首先表现在心理描写的真实性上。在托翁的笔下,无论是人物的心理活动还是反映心理活动的外部世界无不遵循着真实性的原则。“没有丝毫想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杜撰、编造,所有的只是生活的血肉本身”[7](P342)。通过安娜在病危时,安娜对卡列宁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窥探出托尔斯泰在心理描写上高度的真实性。当安娜处于生死边缘时,伏伦斯基和卡列宁这两个昔日的情敌竟然失声痛哭,握手言和。此时安娜的内心处于激烈的矛盾中,对卡列宁的怜悯超过了对他的厌恶,甚至不停地为他过去的行为辩护。但当安娜痊愈后,卡列宁又恢复了其丑恶的嘴脸,并以儿子逼迫安娜就范。安娜对他也随之从厌恶转为了憎恨。“博爱”与“宽恕”是托尔斯泰所宣扬的宗教思想,但他在作品中并不拿自己的理想来取代实际生活,而是坚持真实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艾略特的出版商布莱克伍德先生评价《米德尔马契》说:“这是关于人类生活和自然的最好的研究,你(艾略特)就像一个在我们当中行走的巨人,将你遇到的每个人固定到了你的画布上,在你为我们展现的人生的画廊里,每个人物的个性特点和心理想法都在读者脑海里得到回应,并告诉他们这仿若自然,是多么真实。”[8](P480)乔治·艾略特心理描写的真实性突出表现在她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和对人物情感的真实再现上。这一点可以从“死者之手”一章中得到体现,当卡苏朋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为了满足自己卑鄙的嫉妒心,对多萝西娅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希望妻子在自己死后能够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对此,多萝西娅经历了激烈的内心冲突,在苦闷、迟疑、抵触之后还是选择了屈服。这一段心理描写将多萝西娅软弱善良的性格真实地再现出来,与托尔斯泰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是二者都善于通过描写人物的外部特征来揭示其内心世界,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和动作,都成了传达心灵世界的媒介。托尔斯泰认为人的情感本能和非言语的流露,往往比通常语言表达的情感更为真实。这样的描写在《安》中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写安娜与伏伦斯基在火车站相遇的场面,伏伦斯基注意到了安娜脸部表情的变化:“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2](P68)“被压抑的生气”巧妙地折射出了安娜潜在的精神世界,她压抑着自己内心的丰富情感,但无意中又在“眼睛的闪光”,脸上的“微笑”中泄露了出来。而在《米》中有一段描写很有意思,在小说开头的“布鲁克小姐”一章中,西莉亚与姐姐多萝西娅商量如何分配母亲遗留下来的首饰。面对西莉亚的提议,多萝西娅说:“算了,亲爱的,你知道,我们是永远不会戴它的”[4](P9),这时西莉亚脸红了,她的神情十分严肃。西莉亚之所以脸红是因为她渴望拥有这些首饰,她不像姐姐那样不注意自己的穿戴和装束,但她又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怕多萝西娅认为她爱慕虚荣。而姐姐的话刺激到了西莉亚的自尊心,所以她心中感到不自在。这里,艾略特通过西莉亚的脸红来展现其丰富的心理活动。
这两部小说的心理描写都很突出,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托尔斯泰更注重展现人物的心灵辩证过程,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不是把重点放在结果上,而是描写‘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也就是‘心灵的辩证法’。”[6](P27),并且他善于在人物心理运动中抓住最活跃的心理成分,捕捉其中最能揭示人物心理的瞬间。这种“心灵辩证法”在对安娜的心理描写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作者将她内心的爱与恨、快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信任与怀疑、坚定与软弱等复杂矛盾的情感和心理流变详尽地表现了出来。乔治·艾略特则侧重于通过人物的对话和内心独白来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状态。这在《米》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尽管乔治·艾略特的心理描写艺术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炉火纯青,但她却以独特的心理剖析手法将人物刻画的重点从外部转向内部,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
三、女性意识
《安》与《米》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安娜和多萝西娅都是追求新生活,争取爱情自由,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但二者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安娜叛离家庭,追求爱情,最终绝望地卧轨自杀。多萝西娅最终回归传统的家庭角色,平静地度过余生。毋庸置疑,托尔斯泰和乔治·艾略特在作品中对女性的命运都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二者的女性观表现为同中有异的特点。
首先,托尔斯泰和艾略特的女性观都带有一定的矛盾性。托翁女性观的矛盾性突出表现在对待安娜的态度上:一方面作者赞赏安娜追求爱情自由的勇气,认为安娜的追求与反叛是合乎人性的;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道德观来看,作者对安娜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而放弃做母亲的职责表现出了深深的谴责。她没有让安娜屈从于那个以卡列宁为代表的虚伪、冷酷的上流社会,而是同情安娜的遭遇,字里行间体现出安娜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同时他又让安娜带着深深负罪感痛苦地走向死亡。乔治·艾略特女性观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她支持女性追求独立,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她又高度赞扬女性的克己、屈从、自我牺牲等品质。两位作家女性观的矛盾性都是由时代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思想的矛盾性所决定的。处在俄国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托尔斯泰创作这部作品时,他的思想正处于矛盾与斗争之中,因此他矛盾的思想也影响到了他笔下的人物。身为女性的乔治·艾略特深知她所处社会的妇女生存状况,她自己也是经历了追求、反叛、迷茫,最终回归传统家庭的矛盾集合体。因而这种矛盾性也通过她的作品不自觉地体现出来。
其次,二者都认为家庭才是女性最好的归宿,回归家庭,相夫教子是女性义不容辞的责任。《安》与《米》中的完美女性都是“家中的天使”,比如《安》中的陶丽和吉提,《米》中的玛丽·高思、布尔斯特多德夫人。她们勤劳、正直、善良,乐于为家庭做牺牲,整日为家庭忙碌操劳,而且都具有默默奉献、自我牺牲的美好品质。在两部小说中都不乏这样的场景:吉提跟随丈夫搬到乡下生活,尽心照顾列文的哥哥,处处考虑丈夫的感受。声名狼藉的布尔斯特多德最终在妻子宽容的怀抱中忏悔了自己的罪恶,在女性慈母般的爱中找到了寄托。女性无法找到比家庭更好出路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女性无法摆脱男权社会机制的束缚。两部作品都对这种压制女性意识的男权社会表达了抗议和谴责。然而托尔斯泰的思想更趋于保守,他认为妇女的使命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忠于丈夫,尽贤妻良母之道。既不要参与政治、社会、文化活动,也不要干预丈夫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活动[9](P1)。相对于托尔斯泰将女性囿于家庭之中,而不去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观点而言,乔治·艾略特的女性观带有一定的超前性。她支持女性在职业、教育等社会生活上争取自己的权益。比如多萝西娅在婚前就独立开办幼儿园,拟建村社改善田庄居民的生活条件,还常常出钱资助公益事业,捐助教堂、医院等。
第三,两部小说都大胆揭示了女性自身的弱点。如上文所说,安娜和多萝西娅都是反抗男权社会、超越自身局限的女性探索者,她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大胆与反叛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女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性格中有某些弱点。安娜对爱情病态执著的追求带有放纵情欲的成分,她将爱情视为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在爱情中迷失了自我,以至于最终走向了悲剧的结局。而多萝西娅的思想过于理想化,她常常陷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性格中的理想主义使她选择了丑陋、自私的卡苏朋作为自己的丈夫。她将盲目崇拜误认为爱情,天真地幻想着与博学的丈夫共同攀登知识的巅峰,最后必然导致她第一次婚姻理想的破灭。
四、结语
通过比较分析《安娜·卡列尼娜》和《米德尔马契》在小说结构、心理描写和女性意识这3个方面的异同,我们得知这两部作品虽然出自不同性别、不同国度的作家之手,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多共通性,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安娜·卡列尼娜》与《米德尔马契》这两部经典之作都是世界文坛上不可多得的瑰宝,对于它们的比较研究还值得读者进一步探索。
[1](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M].袁伟,译.北京:三联书社,2002.
[2](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周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苏)叶尔米洛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 ·卡列尼娜》[M].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63.
[4](英)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M].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5]Chase,Karen. George EIiot: Middlemarch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6]倪蕊琴.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7](苏)艾·巴巴耶夫.托尔斯泰的美学思想与创作[M].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1.
[8]Frederiek Karl.voice of a century:a biography[M].New York:W.W.Norton &Co,1995.
[9](俄)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M].冯增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