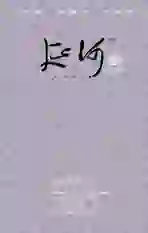遇见鸭乸湖
2014-08-12莫晓鸣
莫晓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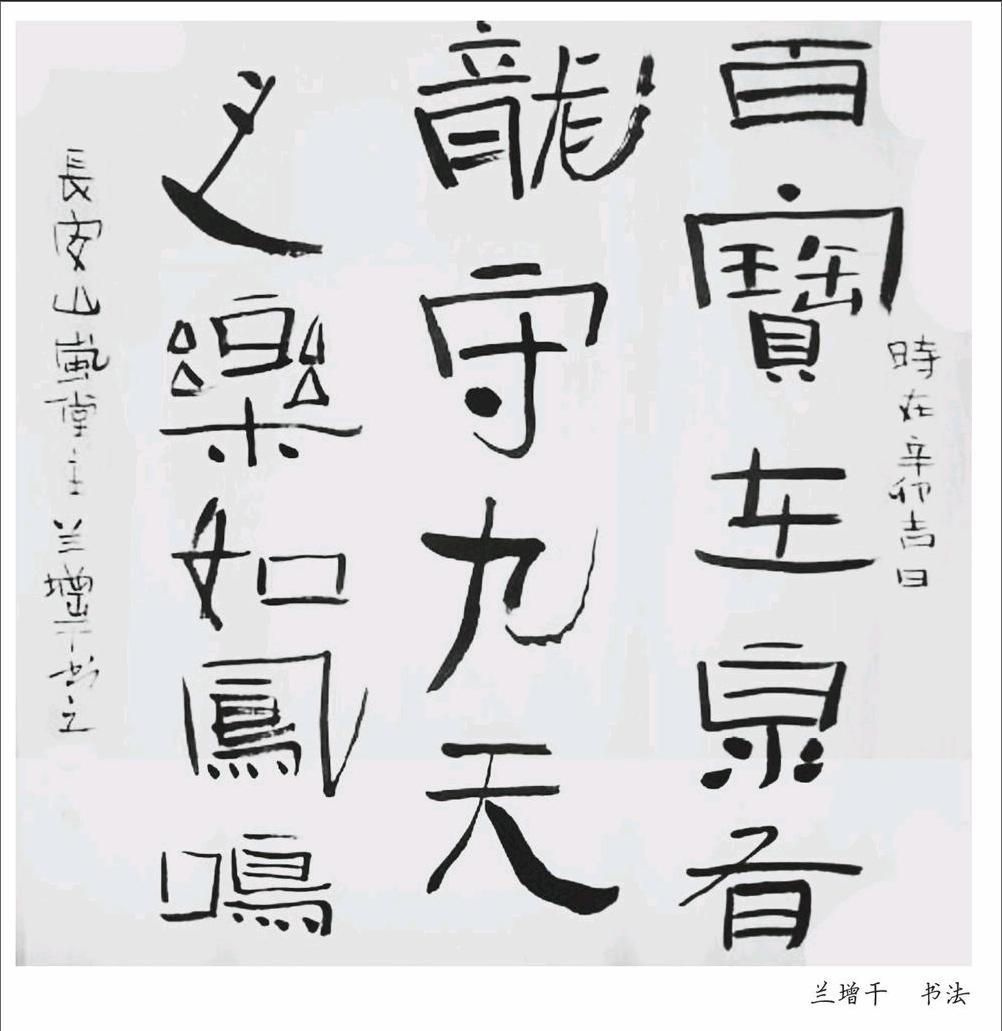
我的栖居地在另一座热带城市,对于这个叫鸭乸湖的地方,我完全是个陌生的闯入者。今天晚饭后,道路引领我穿过一条街巷,又穿过一条街巷,想不到眼睛立即被一片宽阔的湖面所吸引。这时夜幕初降湛江这座城市,湖水在朦胧的光影里安静地泛着粼粼波光,一闪一闪,仿佛回应着我的视线,仿佛用我无法破译的语言,告诉我相遇的激动和欢喜。
早先有朋友告诉过我,这个湖的来历简单而缺乏浑然天成,它不是天造地设,它的形成很偶然——在一片波涛翻涌的内海湾修建军民堤,于集体无意识中围合成湖。是什么人的一声号令导致声落湖现,我无意去查考,因为总有一些名躁一时的面孔回归平凡,然后湮没在岁月的烟尘里。但是我相信,相比天下所有的湖,这个湖最年轻,它的湖畔没有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的吟唱,也没有范仲淹“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题铭……它年轻得近乎没有历史,但是它有未来,如它湖面一样广阔的未来——在近六十年的浩浩荡荡时光中,这个湖的美好渐渐被人们探索和发现。也许这便是时间的秘密,它善于在漫长中慢慢地消磨和筛选,然后无声无息地判定世间的一切去留。
我在湖畔轻轻地迈着脚步,尽量让脚边的小花小草不发出声音,生怕惊扰了满湖的寂静。近六十年日落月升的苍茫,湖岸上的人间悲喜剧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而这个湖呢,它又经历了怎样的沧桑与欢愉?万物有灵,我知道这个湖的魂魄深藏在湖水里,如今,它回应我的却是坦荡无垠的闪闪波光。也许可以说,为了实至名归的这一天,它静静在莺飞草长中等待了几十年,不急不躁,雍容大度,完全不为岸上的喧嚣所动。此刻,尽管我的位置仍是隔水相望的位置,我惊喜自己与这个湖不再貌合神离,我理解了它,在与它的默默对视中读懂了它的性格,读懂了它无为而为的境界与追求。
今夜恰好有月光,在一片白茫茫里湖面似笼着一层轻纱,朦胧中又多了一份散淡。我的身影倒映在湖水里,借着月亮的光茫不知深浅,湖读懂我了吗?它又要给我什么启示?湖面不时飞掠起一只只夜鸟,身姿矫健,声音脆亮,这些夜色里的精灵是不是代表湖向人间宣示什么?在湖边走动的人有不同的人生,高矮胖瘦的身体里各怀心思。在湖之外,物欲却是另一种水,恣意横流,多少人沉浸其中争先恐后。活在俗世,在稠密而肆无忌惮的人群里谋食,我承认我自己也是个俗人,在众多名利场中亦步亦趋竟不觉得脸颊微微发烫。假如湖真读懂了我,该让我纠错什么呢?湖无语,只是送来一阵又一阵冷风,其实,答案我已了然于胸。面对一片广阔虚怀而又波澜安详的湖面,我只能默然。难道我该对它申辩世态遮蔽下人生选择的无奈与惊惶?
当然,我不会在鸭乸湖边流连忘返,也不会因一己的烦忧去打扰一个湖。对于鸭乸湖,我仅是一个身影匆忙的过客,明天一早,我将携带行装在舟车劳顿中奔赴海南。一个常以山水滋养心灵的人,会在无湖处发现湖。但是我会记住,今夜,我心境一片澄明;今夜,我卸下满身俗务,两手空空,但心中独占着一个湖。
卖水果的女人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走出小区左拐几步,看到这里突然多了一个水果摊,摊主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海南女人。这个女人神情惆怅,目光多愁,仿佛刚刚送走远行的亲人。往后的日子,有时我边走边随意看她一眼,总觉得她怅然若失的神情郁郁寡欢,暮气沉沉,与春绿万物的勃勃生机很不协调。
据我最初几天进进出出时的观察,她的生意并不好。小摊生意一靠吆喝,但我从不见她吆喝,仿佛张口招徕客人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退而求其次的是靠陪笑脸,然而笑容在她的脸上更是难得一现,哪怕装模作样的职业微笑都难觅踪影。我便想,这样一个木讷的女人,身后是个什么样的家呢?为什么偏偏跑来城市勉为其难卖水果?不惜让自己丧失用武之地——海南的乡下女人都以吃苦耐劳著称,几乎每一个都是扶犁驭牛的种田能手,地里顺风点头的农作物,无不让她们伺弄得神气十足日日见长。
在城市里安置一个单薄的水果摊,她总是从早上守到晚上,一副兢兢业业的样子。很多时候我深夜归来还会看到她,她瘦削的身形即便在朦胧的光影里,仍会一次次引我侧目。其实,她的水果样相很不好,可能采购时要的是便宜货。我每次看到她时总有种莫名的心酸,有时想掏钱帮衬她一下,但我曾经买过她的水果,她的水果确实是品次味寡,往后我就很少光顾。
海南的春天最不像春天,清明节一过,海口的大街小巷便热浪滚滚,劈头盖脸,连躲在树荫里的流浪狗都不停地吐着舌头。这天中午太阳同样放肆狂野,晒得呲牙咧齿的路人头重脚轻。我也是一身汗水从外头回来,远远就看见她正撅着屁股弯腰拾捡散了一地的苹果。她俯地的腰身一扭一扭,穿在身上厚厚的旧运动服特别惹目——大概是她儿子弃穿的校服,背后印着“某某中学”的字体依稀可辨。当我走近时,恰好对面开来一辆小车停在了她的跟前,散在地上的苹果不管不顾地挡住了车轮。这时她更加乱了手脚,她一边偏头谦卑地对车主道歉,一边三三两两地收捡苹果。车主是个年轻的时髦女人,对她的连声道歉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只是目光冷冷地看着车前的一切。我稍微放缓了脚步走过,脑海里不断疑问:是某双粗暴的大手将她的水果撒了?还是某只鲁莽的车轮撞倒了她的箩筐?但是,当我踏上回家的楼梯时又不禁自嘲起来:即便我知道了答案,又能如何?
四月底的一个傍晚,淅淅沥沥下着夜雨,这场自鸣得意的春雨一直从中午延续到夜里。我将潮湿的雨声关在窗外,正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看言辞闪烁的宫廷剧,忽然有一朋友来电话,说刚好在附近办完事,要顺道看看我,客套地问我是否方便。我当然不会拒绝雨夜造访人,便与他约了时间,不一会,我撑伞去小区门口迎候。
在这样一个行人纷纷急不可耐地奔向家门的雨夜,我竟然还是看见了她,不由让我心里一凛。在她日复一日摆摊的地方,她戴着海南特有的旧斗笠,身披一张透明的塑料薄膜——这种薄膜我小时候在农村很常见,现在人们普遍使用质地良好的雨衣,很少有人再用薄膜遮雨——蹲在路边一心一意守着她那让人看了就没有多少食欲的水果。
我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站定,心里不断盘算着披雨而来的朋友,该如何踮脚穿过城市积水的街道。断断续续有很多人从她的摊前经过,拖泥带水,但并没有人在她的眼巴巴中停下脚步,试图问候她躺在箩筐里的水果。
倾天而下的雨丝争先恐后扑向地面,没有半点犹豫和惊惧,黑暗的夜空变得更加深不可测。我在雨中变换了几回站姿,湿漉漉的朋友终于挟着一股水汽来到我的面前。两年不见,他胖了很多,言谈举止也气派了很多,我一下子相信了他在电话中所说的日进斗金并不是吹嘘。
就在我与他拍肩握手的时候,他一眼瞥见了身旁的水果摊,竟声音夸张地喊了起来: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岂能空手?阿姨,拣大的苹果给我来十斤。
她听后马上精神一振,连声说好好好,也许是过于激动,海南腔普通话穿过雨丝时显得有些颤抖。然后,她便伸手左掂掂,右摸摸,神情专注地拣起苹果来。
我怎能让客人当面给我买水果而不加阻拦呢?于是,我便态度委婉地推辞。这时她的眼睛望望望我,又望望他,神态卑微地等待着某一张嘴里迸出的一槌定音,连风吹跑了手里正准备装苹果的粉红色塑料袋也顾不上。只见客人挥挥肥硕的大手,倒似心照不宣地顺水推舟:好说好说,既然你不让买,我就客随主便了。说罢,两个久别重逢的身影聚拢在雨伞下渐行渐远,剩下身后一双失望的眼睛空空茫茫,这双眼睛让我在做作的说笑中不敢回头。
大概一个月后,她突然不见了,她的位置被一个修鞋的男人占领。我借擦鞋的机会试着向修鞋男人打听,才知她来自海南中部农村,丈夫前年出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变成家里一个唉声叹气的角色,她便将几亩薄田交由年迈的公婆耕种,自己独自来海口卖水果,好歹挣钱养大三个孩子。但是,生意并不如她想象那样货真钱来,她的水果生意连连赔本,最后连房租都难以为继,只好草帽遮颜悻悻回乡下。
听后我心里格噔了一下,很后悔那次不让朋友买她的水果,也后悔自己仅仅关照过一次她的生意。她曾经在这座城市里留下的足迹,转眼就会被喧嚣的市声一层层淹没,然后了无痕迹。
责任编辑:邢小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