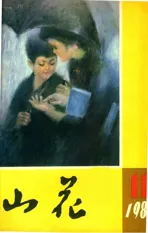诗在东北:“远方有大事发生”
2014-08-08霍俊明
霍俊明
隔着老故事餐吧以及寥落的诗人,不远处就是车流鼎沸的北京三环街头。随着时过境迁,这种残余的诗歌之梦与先锋之痛不能不经受一个不痛不痒的时代摩擦。
——题记
在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地理图景中,紧邻以北京为中心华北地区的东北三省以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属地性格造就了一批生猛的先锋诗人。豪放、粗犷、奔突、狂野的东北大地和白山黑水在这一时期闪现出少有的诗歌亮光。
1
当然就作为运动的先锋诗歌而言这一过程是极其短暂的,比如郭力家和邵春光等人的“特种兵”基本上在执行了两三个“任务”之后即宣告解体——“拣来各军兵种所有番号对对付付/缝上我这件浑身呲牙咧嘴的破衣裳/拒绝加入正规部队/是我的本性”。多年之后的2007年1月11日,在北京火车站对面的一个逼仄的胡同里,吕贵品、苏历铭和郭力家——当年东北的这些先锋诗人正在华美伦饭店里开怀畅饮。先锋诗人早已经开始发福了。2007年1月苏历铭的诗集《陌生的钥匙》最终还是采取了自印的方式,这与苏历铭很多诗集都是“戴着非法出版物的帽子面世的”“先锋性”是一脉相承的。尽管随着文化体制和出版机构的商业化转轨,一本有书号的诗集和坊间自印的诗集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区别可能仅在于出版社编辑过程中会删掉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文本——但是在1980年代自印诗集仍然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比如1985年吉林大学经济系的苏历铭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的杨榴红自费出版的诗歌合集《白沙岛》。著名诗人、时任《诗刊》主编的张志民无比激动地为这本诗集作了序言《青春的诗,诗的青春》,“读着两位年轻人的诗作,我自己,似乎也忽然年轻了!他们牵着我的手,不!仿佛是拍了拍我的肩头,不是称我‘伯伯,而是把我作为他们的同伴,拎过那来不及系好带子的旅行包,说声‘走!咱们到白沙岛去!‘走!,已经花白的两鬓,好像没有提醒我年龄上的差异,一颗还不甘褪色的心,既没有失去与他们作一次同游的兴致,也没有拒绝他们的理由,我们欣然同往了!”。这篇序言在上海的《文学报》发表,而不久之后上海出版局就在《文学报》上针对这本诗集发出了《非出版单位及个人不能自行编印出版发行书刊》的通报和批评:“你报六月二十日第二二一期第二版上发表了一则两位大学生(苏历铭杨榴红)自己编辑、自费出版、自己发行抒情诗集《白沙岛》的消息。根据有关出版管理方面的规定,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非出版单位以及个人是不准自行编印图书出版和发行的。你报发表这则消息很明显是和有关出版管理方面的规定相违背的。”为此,苏历铭和杨榴红不得不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在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的帮助下这本自印诗集最终纳入到北京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得以“合法化”地“正式出版”。1988年杨榴红先后辗转香港和美国,如今成了旅美华人。2008年1月4日杨榴红回到北京在老故事餐吧举行新诗集《来世》的首发式。关于先锋诗歌的“来世”我们无法预知,但是对于先锋诗歌的“前世今生”而言我们还是可以得出诸多观感的。在寒冷的天气里,我看到当年的很多“第三代”诗人都前来捧场,但是当年火热的场面已经无法重现。这个时代仍然只能是诗人之间小范围的互相支持。
隔着老故事餐吧以及寥落的诗人,不远处就是车流鼎沸的北京三环街头。随着时过境迁,这种残余的诗歌之梦与先锋之痛不能不经受一个不痛不痒的时代摩擦,“我们患上热爱诗歌的怪病,而这种病一旦染上,终生无法治愈。有时真想生活在久远的年代,哪怕是民国时期,战乱纷争,却可以战死疆场,痛快的生与死,远比现在不温不火的生活更有意思。精神已经苍白,财富在博弈中,名利双收似乎已成为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苏历铭:《细节与碎片——记忆中的诗歌往事》)。
2
说到东北三省,人们自然会想到茫茫的林海雪原、白山黑水间粗野、豪壮的关东汉子和高大、丰满、泼辣、直爽的东北女人。而东北文学似乎只在抗日时期呈现出了文学史家所称的“东北作家群”,也似乎只有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穆木天、杨晦、舒群、白朗、罗烽、高兰、公木、辛劳、骆宾基、雷加、丘琴、邹绿芷、铁弦、师田手等人在文坛闪现出光辉。更多的时候东北文学似乎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地理版图中并不出众,甚至可以说静寂无声。而这里的文学留给我们的印象最深的除了建国之后的《林海雪原》和1980年代电视文化开始流行时的《夜幕下的哈尔滨》,以及“说书人”王刚之外,就是三四十年代的萧红和她特有的北方女子的文学性格。由萧红的文字,时在动乱的上海闸北的鲁迅已经看见了五年之前甚至更早的冰天雪地里的北方以及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生死场·序言》)。然而鲁迅所说的萧红《生死场》中女性作者的“明丽”和“新鲜”可能是想表明女性写作与男性的不同,而就这部作品自身我们看到的却更多是沉重和北方这块土地上的悲凉和女性命运的悲惨遭际。而萧红在《生死场》中非常细腻和个性化的女性视角呈现出了东北大地上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点。夏日北方的田野、蔬菜和庄稼象征了这片土地的生机和反抗,烈日里的榆树下啃食树皮的山羊、“绿色的甜味的世界”的高粱、柳树、杨树以及菜圃上的大白菜、圆白菜、卷心菜、西红柿、辣椒、倭瓜、黄瓜、青萝卜、白萝卜和胡萝卜都一起带有东北黑土地的泥土气息。东北特殊的地理环境,空旷大地上稀落的村落和人群,异常寒冷的空间使得生长在这里的人们更渴望温暖和交流,更希望在大声说话和热气腾腾的酒桌上来驱逐寒冷和寂寞。
徐敬亚、吕贵品、王小妮、张小波、郭力家、潘洗尘、苏历铭、张洪波、朱凌波、宗仁发、张曙光等诗人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写作的确也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北方”的性格。在当时的一张照片上,这种北方性格有鲜活的体现。在一个高大的雕刻成大象模样的假山石那里,徐敬亚、吕贵品、王小妮、郭力家、白光和张峰等十一个人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男诗人一律占据了这个假山的各个制高点,在最高处侧身坐着一人——白衬衫,白礼帽。
3
当时吉林大学77级中文系的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刘晓波、邹进、兰亚明、白光等七名学生组成的“赤子心”诗社(人数最多时达到24人)成为80年代这一时期东北先锋诗群的代表。
这一诗社的成立以及几个年轻诗歌写作者的成长离不开当时著名的诗人公木的扶持。1978年9月21日徐敬亚等人已经开始筹划成立诗歌社团。当时的徐敬亚、吕贵品、张晶、邹进、陈晓明和丁临一等还亲自给住在女生宿舍326室的王小妮写了一封邀请函:“特邀王君小妮屈驾参加。余有志同者,皆十分欢迎,并请于今天下午16:00整光临207室,共商大计。”后来办刊时还是公木先生从两个备选诗社名字“赤子心”和“崛起”中敲定了前者。油印刊物《赤子心》共出版九期。从1981年开始,在当时官方刊物发表作品还很困难的情况下吕贵品已经接连在《人民文学》、《青春》、《萌芽》、《青年文学》等发表诗作。这在吉林大学以及诗人朋友们中间引起了轰动,而吕贵品的单身宿舍也成了一个文学沙龙。成都诗人万夏来到吉林大学找吕贵品的时候,万夏已经留起了漂亮的大胡子。“赤子心”诗社有一张集体合影。照片上共八个人,前排三个人或躺或坐,后排五个人一字排开成站姿。王小妮单手托腮似乎正在构思一首诗作,而徐敬亚意气风发,双手叉腰,面带自信的微笑。
可能是寒冷的气候导致“赤子心”的诗歌带有高亢的适合朗诵的大声调。即使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这些被诗歌之火点燃的东北青年们仍然在校园和南湖等处朗诵和交流诗歌。而当时王小妮和徐敬亚的爱情故事更是给他们的诗歌写作增添了传奇性。他们不仅一起切磋诗艺,也谈情说爱,在风雪中二人亲密地手拉手。白桦林中是厚厚的白雪,徐敬亚骑在一棵树上微笑着俯看王小妮,王小妮则站在树下幸福地仰望。关于徐敬亚和王小妮的爱情生活还曾有过这样一段趣闻:“为了能和小妮缔结恋爱关系,徐敬亚和吕贵品在一家小酒馆里进行过严肃的谈判,最后徐消除戒备和疑惑,大胆地宣告诗人婚姻的诞生。”(苏历铭:《细节与碎片》)。
继“赤子心”诗社之后,苏历铭和包临轩等人在1983年9月成立了北极星诗社。这个诗社延续了近十年的时间,期间所涉及到的诗人主要有苏历铭、包临轩、曹钧、王乃学、李学成、陈永珍、华本良、王占友、张锋、鹿玲、丁宗浩、野舟、马波、杜笑岩、田松等。
1980年王小妮接到《诗刊》编辑雷霆(1937~2012)的一封信,邀请她到北京参加一个诗会。这就是后来震动文坛并影响深远的首届“青春诗会”。而无论是对于南方诗人还是对于王小妮、徐敬亚这样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北京是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文化魅力的。在徐敬亚的积极争取下他以年轻评论家的身份和王小妮一起在1980年夏天离开长春前往北京参加青春诗会。临行前曲有源等诗人专门为徐敬亚和王小妮在南湖九曲桥举行送行仪式,有关单位则示意徐敬亚到北京后不要和任何“地下”刊物联系。1980年7月20日徐敬亚和王小妮到达北京车站,这时候徐敬亚想到的是食指的那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年25岁的王小妮兴奋莫名地坐在天安门广场前拍照,笑容灿烂。而对于王小妮和徐敬亚而言天安门广场确实是一个“让人无法平静的地方”(王小妮语)。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这些年轻诗人除了江河、顾城等北京诗人外,其他的都住在当时虎坊桥的《诗刊》社。这些低矮的平房却使得80年代的先锋诗歌达到了一个高峰。诗会期间,北岛和芒克、杨炼的到访在青年诗人中引起了炸弹般的反响。徐敬亚和王小妮还参加了北岛等人组织的沙龙活动以及谢冕、吴思敬和孙绍振在《诗探索》创刊前召集的青年诗歌会议。
4
在1980年代的校园先锋诗歌热潮中,黑龙江省大学生诗歌学会主办《大学生诗坛》(1984年8月创刊)有着广泛的影响。82级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潘洗尘担任主编。主要成员有程宝林、彭国梁、钱叶用、张小波、苏历铭、傅亮、陆少平、王雪莹、杨川庆、杨锦、许宝健、苏显钟、王广研、李锋、菲可、袁晓光、艾明波、唐元峰、王鑫彪、桂煜、沙碧红、李光武等。《大学生诗坛》创办半年之后,重庆市大学生联合诗社创办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大学生诗报》。主要涉及来自云南大学、兰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的于坚、梁平、尚仲敏、宋琳、潘洗尘、张小波、燕晓东、张建明、邱正伦、杨榴红、胡万俊、菲可等。
在这一代诗人身上一直有着“远方”的情结和冲动,无论是海子的《九月》等一些诗,还是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韩东的《山民》以及吕贵品的《远方有大事发生》、潘洗尘的《六月,我们看海去》、杨榴红的《白沙岛》都证明了这一点。东北诗人宋词在1985年甚至有骑着单车转遍全国的壮举。
1982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吕贵品写下这首名为《远方有大事发生》的诗:“一棵光秃秃的树下有一块石头/他习惯坐在那里/看一列又一列火车/通过辽阔的原野走向远方//每天他都这样/他已经十四岁了//他生长在火车道边/可从没有坐过火车/只能靠在树上嘴里发出火车轰轰的声音/他的父亲面对奔腾的火车/却打着哈欠//他又一次要求想坐坐火车/父亲告诉他/老了再坐/现在你的两条腿还能走//火车上有许多窗口/他记得有个小女孩/向他微笑过//他在铁道边捡了几张漂亮的糖块纸藏起来/觉得远方有大事正在发生/还有他所喜欢的一切/也都在远方//终于他决定离开那棵树/离开那块石头/去坐一次火车//轨道伸向天边/沿着轨道奔走使他兴奋/坐火车能够接近云/走了很多的路/他饿了/但他不愿离开这条轨道/他要顺着这条轨道走下去”。尽管吕贵品这首诗叙述节奏显得拖沓,但有意思的是王家新和韩东在《在山的那边》、《山民》中也采用了叙述的呈现手段,并且都设置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对话。显然,“父亲”、“儿子”对“远方”的态度是矛盾的,而这正体现了1980年代先锋诗人们的集体冲动、反叛和自由的愿望。1985年春天吕贵品完成诗作《向南走》,这似乎预示了不久之后那场轰轰烈烈的现代诗群体大展的前奏。1985年吕贵品辞去吉林大学教师的公职南下深圳与徐敬亚汇合。
曾经有人告诉过王小妮说中国有两个地方乞丐最愿意去,一个是东北,一个是深圳。理由是东北人心热,深圳人手松。而王小妮和徐敬亚这两个东北人却机缘巧合与深圳结缘,但其中的辛酸和放逐感只有他们自己最能体悟。
5
1985年1月3日,东北极其寒冷的时刻,徐敬亚几乎是两手空空独自一人从长春火车站登上南下深圳的列车。
在王小妮的印象里,徐敬亚用他那只惯用的左手抓住门边的铁扶手登上了火车。这一刻在他们看来无疑是“大抉择的时候”。火车一直向南,“他的脚再也不用落在这片雪地上”。尽管徐敬亚是被迫离开吉林,但是深圳作为一个遥远的“南方”也正好暗合了那一年代青年人所向往的一个梦想。在三个多月离别的日子里,王小妮带着幼子等待并接连写下了《车站》、《家》、《方位》、《独白》、《告别》、《冬夜》、《爱情》、《三月》、《日头》、《岔路》、《晚冬》、《完整》等近二十首诗歌。在《车站》这首诗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别离的惆怅以及命运的无奈感。也许此刻只有相互安慰和彼此撞身取暖,“手紧插进大衣口袋/你的车厢终于隐去/很好/束着肩,匆匆走过窄路/一团浓厚的烟/使我们彼此再也不能望见//眼泪开始流动/这什么也不说明/路轨走向车站/就是为了曲折错杂/很好正合你意”。分别数月之后,王小妮也终于坐上开往“中国最南面的边界线”深圳的火车,“从当时那个很狭窄的小火车站里走出来。迎面看见大幅的美国香烟广告,还有一棵过于茂盛、仿佛正在爆炸之中的亚热带大树。那是我一生中呼吸最畅快的时刻。我是轻松而宽纳地一步步走进广东话奇形怪状的密网。我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走,但是它当时是我想象中的自由之城。”(王小妮:《一直向北:我的人生笔记》)。而残酷的事实却是因为“现代诗流派大展”,《深圳青年报》社被解散,王小妮也遭到单位解职。在1987年夏天这场所谓的“驱徐运动”中徐敬亚又独自一人回到东北。正是当时这种动荡的生活以及陌生的深圳给王小妮心灵上以巨大冲击,1980年代末期因此成了她诗歌的爆发期。1988年其油印诗集《我的悠悠世界》问世。其中就有那首后来广为传颂的《不认识的就不想再认识了》:“到今天还不认识的人/就远远地敬着他/三十年中/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足够了。//行人一缕缕地经过/揣着简单明白的感情。/向东向西/他们都是无辜。/我要留出我的今后。/以我的方式/专心地去爱他们。//谁也不注视我。/行人不会看一眼我的表情。/望着四面八方。/他们生来/就不是单独的一个/注定向东向西地走。//一个人掏出自己的心/扔进人群/实在太真实太幼稚。//从今以后/崇高的容器都空着。/比如我/比如我荡荡来荡去的/后一半生命”。
同样是在1988年夏天,徐敬亚和孟浪(时为深圳大学出版中心编辑)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出版事宜坐火车来到长沙。徐敬亚还独自畅游湘江并在橘子洲头意气风发地与孟浪合影留念。这还不算过瘾,徐敬亚和孟浪还坐火车去了韶山冲。徐敬亚甚至趁管理员不在,将一只脚踩在主席故居的一张大木床上拍照。这一时期王小妮的诗歌给我们呈现的是与日常生活相关但又被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所忽略的“另一个世界”的城市景观。她以冷峻的审视和知性的反讽以及人性的自审意识抒写了寒冷、怪诞的城市化时代的寓言。而这些夹杂着真实与想象成分的白日梦所构成的寒冷、空无、疼痛与黑暗似乎让我们对城市化的时代丧失了耐心与信心。我们所看到的是灰暗城市里车站和天桥上的人流,沉暗卧室里投射进的阳光,水泥旷野里的仰望者和砸墙者,在时光的斑点中疯狂行驶的列车上颠簸动荡的灵魂,涂脂抹粉又难掩荒芜的现代城市。这一切都使得我们不断惊悚于现代化进程中一再被忽略的寒冷与真相。王小妮这种“不相信”的质疑性的姿态和冷静的观察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一场场飞降的大雪般的严酷与寒冷。一个被不断改造和拆迁的现代化城市里车流和人流都在疯狂飞奔,而诗人则是那个时时为时代踩下刹车的人。她不是旁观者,也不是道德律令的持有者。她是一个持续的发问者,是一个城市寒夜里的失眠者和心悸者。她同时也是一个孤独的介入者,她的诗歌正在等待我们的呼应。基于此,冷静的反讽成为王小妮这些关于城市诗歌写作不得不为之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王小妮关于城市的诗歌大多都带有很明显的时间性场景,比如清晨、中午、黄昏、夜晚等。而围绕着这些场景则出现了光芒与阴影,寒冷与温暖并存的平淡无奇但是又具有强大心理势能和象征力量的核心意象。在屋子里的阳光、干涸河道上的夕阳、暴风雨之夜的闪电、稀薄的月光、无光的灯以及火车窗口刺目的阳光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小妮诗歌文本中所显现的时代光影以及无处不在的巨大阴影。而与这些场景和意象相关的则是诗人的情感基调是反讽的、冷峻的、悖论的、无望的。这是否印证了对于曾经的乡土中国和具有农耕情怀的人们而言,每个人都宿命性地成为了大大小小城市里的异乡人和精神漂泊者?而对于由北方南来的诗人王小妮是不是更是如此?王小妮诗歌的视点既有直接指向城市空间的,又有来自于内心渊薮深处的。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王小妮并没有成为一个关于城市和这个时代的廉价的道德律令和伦理性写作者,而是发现了城市和存在表象背后的深层动因和晦暗的时代构造。而她的质疑、诘问和反讽意识则使得她的诗歌不断带有同时代诗人中少有的发现性质素。比如她诗歌中的这些诗句,“后面的后面”,“背后的背后”,“尸体上的尸体”等。王小妮的诗歌往往会选择一个很小的日常化切口,但是她最终袒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无可救药的痼疾与病灶。在此意义上王小妮是一个后工业时代或者一个后社会主义时代里的寓言创设者。她的“小诗歌”就是“大社会”。而王小妮也更像是一个城市里的巡夜人,她的虚弱的灯盏在城市黑暗的最前线,而她所要迎接的风雨要更为严酷。而失眠和偏头疼的诗人形象则为我们打开了寒夜里一个个窄门,当我们挤身进入的时候那迎面而来的寒冷让我们在些许清醒中重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身处的这个城市以及这个时代最为日常又最为步步惊心的真相与风暴。
6
当多年之后王小妮和徐敬亚在深圳的一个公园的草坪上平静而悠闲地合影的时候,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以及个人遭际是否也变得平静?尽管徐敬亚经受了命运的磨难,但是他幸运地赶上了(更准确地说是“创造了”)一个诗歌的黄金年代。简单举一个例子,当时江河、杨炼和顾城在北京作诗歌讲座之前,消息(确切地说是“广告”)已经提前登在了《北京晚报》上。即使是在1980年代的最后一年,当徐敬亚和宋词、温玉杰这三个东北人在珠海喝酒的时候他们也受到了公众的特殊“拥戴”和礼遇,“最后的高潮,场面感人。不知什么时候。餐厅老板已落座倾听,还听得如醉如痴。后来也一起喝了起来,中间甚至喊出了‘你们全是神人啊这样的句子。于是,整个餐厅的服务员小姐团团围成一圈,站在我们四人周围。每当妙语出笼,全场一片鼓掌声、叫好喝彩声。”(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
当我多年后在深圳与徐敬亚、王小妮以及吕贵品见面,吕贵品一边打着胰岛素一边喝酒的场景似乎意味着先锋的年代越来越远了。中国先锋诗歌经历了集体的理想主义的“出走”和“交游”之后,诗人的“远方”(理想和精神的远方)情结和抒写已经在1990年代宣告终结。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不断去除“地方性”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时代,我们已经没有了“远方”。顺着铁路、高速路、国道、公路和水泥路我们只是从一个点搬运到另一个点。一切都是在重复,一切地方和相应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不清。一切都在迅速改变,一切都快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