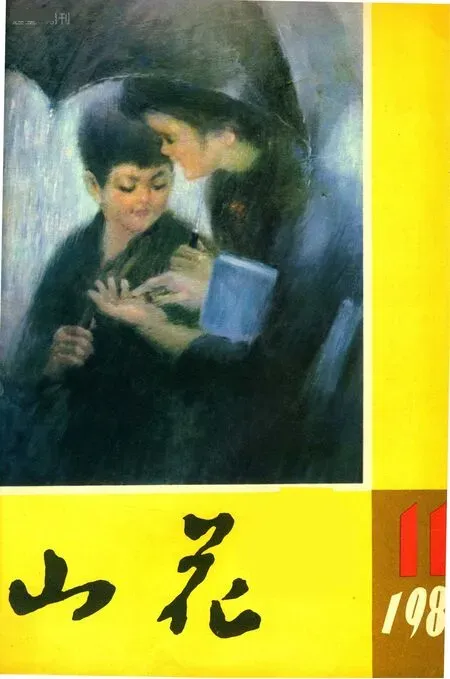少年往事
2014-08-08
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乡下的山村里度过的。那时家里穷,穿的衣服都是母亲用手工做的粗布衣服。家里没有电,点的是煤油灯。晚上去上晚自习,也是端一个煤油灯,第二天早晨一掏鼻子,鼻子里都是黑的。那时家里也没有钟表,有时早晨听到鸡打鸣就赶紧起床,有时天上还有月亮,也不觉得天黑。走到村东头破庙里的学校,在课桌上趴着等天亮。有时等一两小时天也不亮,等着等着就趴在那儿睡着了。晚上下了夜自习,有时天黑,走到村西头,没有同学做伴了,为了给自己壮胆,嘴里一边嗷嗷胡乱喊着什么,一边向家中跑。总觉得好像后边有个人跟着似的。
早晨、中午、下午放学后都要挎上篮子,拿上镰刀去地里割草,草有好多种。春天草刚露芽,所以二三斤交到队里就能换一分工。到了夏天和秋天,一二十斤草才能换一分工。那时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挣十分工,妇女和半大小子只挣七分工。每个工值一二毛钱。有时夏天中午放学后,跟父亲上山去割草,要割到队里快上工,学校快打铃时才回家。父亲担两捆在头里走,我背一小捆在后边跟着。衣服全像水洗的,胳膊、背上都起满了痱子。回到家把草晒干,每百斤干草可卖四五块钱,那是全家冬天的盐钱和油钱。
那时吃的是窝窝头和贴饼子,是玉米面和地瓜面做的。平常很少有青菜吃,更别说吃肉了。有时连咸菜也没的吃,喝粥时就在粥里放点盐。
有时去地埂或山坡上去挖原志(一种中药材),回家后把皮剥下来晒干,一两能卖一块多钱。挖几次能晒一两。有时去山坡上掀石头逮蝎子,转半天也逮不了几个。晚上拿罩灯或手电筒去逮土鳖子,用热水烫死,晒干。赶个星期天,几个小伙伴结伙去七八里外的收购站去卖。觉得卖的钱多(超过两块钱以上),就到乡里小书店去挑画本,磨蹭一两个小时,狠狠心花一两毛钱买下自己钟爱的画本,心满意足地回家。
小时,就盼着过年,过年能有新衣服穿,有饺子吃,有肉吃。
我们家穷,一下雨,住的房子到处漏,屋里把盆盆罐罐全用上了,叮叮咚咚像奏音乐,外边的雨不下了,屋里还在下。有时下连阴雨,屋里连一张床大的干地方都没有了,这时全家望着下个不停的天空,惆怅地向天祷告:勺子头,挖挖天,今儿晴,明儿干。
八九岁时,暑假、秋假都要去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拾麦穗、拣地瓜、摘棉花等。天天在毒毒的日头下晒着,衣服都粘在身上。半晌休息时,慌着到远离人群的地堰根下去解手(大小便)。有时找个高地堰根下,在荫凉里凉快一会儿。有时坐在地上,有时干脆就躺下来,望着蓝天上的云朵发呆。心里想象着山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回到家手不洗就找干粮吃,如没剩干粮,就洗块生地瓜吃。
也有快乐的时候。和几个小伙伴去西上园割草。在地里捡了一毛钱,我们高兴地去临村老汉的瓜地里买瓜吃,脆瓜要比甜瓜便宜些。我们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决定买脆瓜。因为人多,怕买甜瓜分不过来。我们嘀咕了几句,有两人围着老爷爷去摘瓜、称瓜,另三人挎着自己的草篮子,互相掩护,时不时有人弯腰摘一个瓜,放进篮子里用草一盖,若无其事地向老爷爷看一眼。等买瓜的两位买完瓜,我们一起赶紧撤了,到了离瓜地很远很远的芦苇丛里,我们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把瓜拿出来一数,连买带偷的竟有七个瓜。我自己编了个顺口溜:走到西上院,拾了一毛钱,买了七个瓜,鬼头蛤蟆眼。现在细想想,这四句顺口溜应该算是我创作历史上的第一篇作品。
那时村北的大坝里有水,夏天的午后,我们经常瞒着老师和家长去大坝里游泳。回学校的路上,要尽量把头发弄干。进了学校,坐在教室里,心里有鬼,也是提心吊胆的。老师的眼睛很毒,起立后用眼光向全班扫一遍,严肃地点几个男孩子的名,被点的人怯怯地走到讲台下,老师让每人都抬起胳膊,眼光定定地看着你。心虚的咬着嘴唇,早低下了头。老师在每人的胳膊上轻轻一划,胳膊上就出现了一条白道。没什么好说的,出教室门口去站一节课。现在想来,老师是为我们好。万一淹死了怎么办?
学校里也搞勤工俭学,割草喂羊,用不完的草晒干卖钱。大家比着看谁割的草斤量多。这次少了,下次下决心一定要多割些。有时上山撸槐树叶,回到学校晒干,再去磨面的机器上磨成面。说是卖到美国去。说人家造原子弹用。那时想,人家美国科学技术就是发达,用槐树叶竟能造出原子弹来。有时还上山逮毛毛虫,每人拿一个带盖的大号玻璃瓶子,用筷子做一个夹子。东山、南山上的柏树林归国营林场管,树林年年发虫灾,我们每年上山逮虫子。南山的树林少些,东山的树林多。东山的北头有个南天观,是过去道士修行的地方,北边有个大戏台,戏台下有一个小石屋,不论春夏秋冬,都有一股清凉的泉水从山石缝里流出。石屋北边有一水池,我曾在那里边洗过澡。那水池是七几年我父亲他们村里的石匠队垒的。我记得父亲他们早上上山,晚上才回来,中午要在山上吃一餐饭,吃白馒头,还有肉菜。那时我就想,等长大了,我也凭力气去挣白馒头和肉菜吃。南天观院里,有很多石屋子,南边是日月泉,小屋四溜全是石刻的碑文。从日月泉打上来的水,清洁润喉。院子东边是一片土坟,坟间有零星的柏树,一个人走在里边,觉得阴森森的。传说都是死去的道士的墓。我记事起,村里还有一个道士,叫谷山,住在大队的院里,享受五保户待遇。我们上学的学校,老师们的办公室,也是道士们住的地方。听说过去道院有好几百亩良田。有时逮虫子,走到油篓寨下边去。油篓寨因一座山峰外形像油葫芦而得名。此峰怪石林立,地形险要,又名天柱峰。记忆中我曾上去过两次,上去的路是一条石缝,直上直下。稍不小心,掉下来就可能摔个粉身碎骨。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有时一个人能逮二三百条虫子,大的每条一分钱,中的两条一分钱,小的三条一分钱。
不论哪个项目,只要排在前几名,都会有奖励。或是几支铅笔,或是一个带奖字的作文本。那时用的作业本上,带个红红的奖字,是件很荣耀的事情。
我家的小山村座落在东高西低的斜坡上,远远看去,是一团绿色。每家的屋前屋后都栽着杨槐、家槐、梧桐等树。一条乡间公路从村子的中间穿过,记得小时候,看到一队拉练的军队从公路上走过,心里羡慕得不行,偷偷想,我什么时候能走进这样的队伍里,走出大山,去看看山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特爱站在公路边,闻汽车开过后散发在空气中的汽油味。
记事时,村东有个东石门,在东大崖子顶上,后来慢慢塌掉了。村西南边有个小石门,崖子下是口水井,东半村的人都爱到那儿打水。村南也有个小石门,至今还在,用山石垒成的。两个人同过时,几乎错不开身子。村西北边也有个小石门,也是在崖子顶上,夏天的傍晚,许多人到这儿乘凉。有的老人坐在那儿聊天,到半夜眼皮打架才回家。我的旧家就座落在村子的最西头,奶奶住堂屋,我和父母及两个姐姐、还有弟弟住在两间低矮的小东屋里。西堂屋、西屋说是三爷爷、四爷爷的,房顶都塌了。院里有一棵槐树,是母亲生我大姐时栽的,我经常爬上去摘槐叶,洗净了做菜粥喝。到了秋天过后,用槐树上掉下的种子,砸碎了捏在高粱杆上,中间插一颗大头针,等晾干了,就是一支箭。院里还有两棵枣树,七月份,枣刚有点发白,我们就开始摘着吃,一直能吃到八月十五中秋节。
最记得生产队里割苇子的时光。每年的深秋,收完了谷子、豆子和地瓜,种下的小麦刚从地里探出头,早晚的天气已很有些凉意,趁一个好天,队里会宣布明天割苇子。男劳力们会把镰刀磨好,有靴子的穿靴子,没靴子的找一双皮底鞋。第二天,男女老少齐上阵,男人会吸烟的吸烟,不会吸烟的也吸烟,有的妇女也会红着脸来一根。因为是队里买的,整劳力还会额外多得到一包烟,有时是金菊,有时是泉城。早晨下水前,男劳力会每人喝两口白酒,他们在前边割,妇女们在后边捆,然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一直传到岸边。因为苇坑是连着的,听说别的队割苇子了,另两队会放下别的农活,也来割苇子。有时先下手的会在分界的地方多割一点,晚来的队的队长,会左看右看。气不过会找上门去,和对方的队长理论一番,才开始说话谁也不让谁,很有些火药味,有时双方的壮劳力会围拢上来给自己的队长壮威,每当这时候,总是沾光的一方,做出让步。让自己一方的人给对方拉过几个苇个子去了事。
有时割着割着,会发现一窝架在水面上的鸟蛋,有的送到岸上去,留着带回家。有的趁老婆不注意,会转给身边脸蛋好看点的姑娘或媳妇,充一回男子汉。有时发现一只水鸭子,大家齐声去追,有人会绊倒在水里,惹得大家一阵大笑。最兴奋的是吃饭的时候,每人一碗漂着油花的豆腐,有时还有一两块肉,白白的大馒头管够。男人们一边喝酒,一边逗乐。这时女人们吃着馒头,还想着家里的儿女,偷偷把半块馒头用手绢包了藏起来。
村北河边有两棵大柿子树,夏天割草,我们总是先去那儿。夏天人乏,坐下就想睡觉,有时真就坐在树下睡着了。有时爬到树上去,大家比赛看谁攀得高。有时不小心,会从树上摔下来,但总是有惊无险。河边的草长得快,我们天天就在河边转,也总是能应付过去。那时候心想日子过得真慢,盼自己早日长大,去给家里挣十分工。饿了什么都能入口,地埂上的野韭菜,野酸枣,有时到人家菜地里,装作是路过,看四溜没人,偷一个茄子或两棵葱,躲到苇坑里或庄稼地里去吃。拾点干柴火,夏天烧麦穗吃,秋天烧豆子、烧玉米棒子吃更是家常便饭。烧时几个人是有明确分工的,有人动手点火,有人放风,若被看庄稼的发现了,拔腿就跑。其实看庄稼的真发现了,也是虚张声势把人吓唬跑算完,要不是饿,谁会去干那事。大部分时候是被发现不了的,只要火灭了,上空的烟飘走了,就可以踏踏实实坐下来吃了,吃时谁也不会让谁,等吃完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一个形象,满嘴黑。用手背抹一把,黑的地方更扩大了,大家就相互指着对方大笑起来。有爱恶作剧的孩子,在和自己家有过结的人家的菜地里,选一个不大不小的金瓜,用镰刀划一个三角口,把那一块拿下来,蹲那儿向里边拉一些屎,再把那块瓜盖上,作个鬼脸逃跑了。一两天的时间那口子就完全长好了,那瓜会长得特别快。突然有一天,被主人兴高采烈地摘回家去,洗了放在案板上一切,怎么有股臭味,一看满桌稀汤,心里顿时明白了。脸气得变了色,不知去找谁算账。这样的事,又不便去骂街,只能气得自己肚子痛。
那时不兴打麻将,扑克倒是有人打。所以要是听赶集的或走亲戚的回来说,今天晚上哪个村有电影,年轻人心就动了,几个人一商量,吃过晚饭相伴着就上路了。有时我们也敢跟着去,向南去过刘庄,向西去过旧县,向东就是北崖,向北去过刘庙、纸坊。去时由于兴奋,不觉累,回来时,有时把脚都磨破了,但一点不敢掉队,人家在头里跑,你咬着牙也得跟上。不然长长的夜路一个人怎么走。有时去时三五个人,回来时可能会有十几个人。那时农村人还没见过电视是什么模样。
大姐也是在我们村上的学,那时叫高小。从刘河往南都到此上学,是个重点学校。连丁泉的姥姥娘家的表舅都是在这儿上的学,我和他儿子是高中时的同学,这是后话。姐姐是腰鼓队的,后来毕业后到生产队里劳动挣七分工,后去山西面的斑鸠店学缝纫,每星期回来拿一次干粮,和村里的几个姑娘一起去一起回,单程二十五里路,还要翻一座山。看到大姐每星期拿回的硬纸本上一个个红色的对勾,就知道姐姐学得不错。姑娘大了嫁人,会缝纫一是可以当作一门手艺,二是可以很自然地向对方提出买下一台缝纫机。那时刚时兴那机器,就是过了门,娘家人的衣服也可以拿过去做。条件好的会买一台作陪嫁,送给女儿,那得是有相当好家境的。七十年代初,三叔从东北回来看奶奶,爹和娘不知商量了多少次,狠狠心决定让姐姐跟三叔去东北找个好饭碗。一点点把女儿养到这么大,还没见尽一天孝心,一下子女儿去了千里之外,想的时候想见一面也见不到。父母心里得有多难受啊。
二姐没上几年学,就回家挣工分了。二姐特能干,除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外,还在放工后去割草,拾柴禾。记得春天家里没柴烧了,到地里也捡不来柴,没办法只能捡回干牛粪晒干了拉着风箱当柴烧。有一年过年前,二姐和几个伙伴去赶集,去时父母给她装了些粮食背上,让她卖了好过年用。回到家她心虚地小声对娘说:人家都买了花布做个上衣,我也买了一块布。你把卖粮食的钱买了布,全家还指望用什么过年?二姐受了抱怨,想想自己天天一身汗一身泥劳动一年,过年了连件新衣服都不给买,委屈地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你们别抱怨我了,我去问问看别人要不要,卖给别人。二姐很少赶集,而她每次赶集回来,总会从兜里掏出用手绢包着的两个包子,一个给我,一个给弟弟。有时我会把咬了一半的包子递给姐姐,说姐姐你吃一口,姐姐会说我在集上吃了,你吃吧好兄弟。
小时玩得比较好的伙伴,我们春夏天割草,秋冬天拾柴火总会找在一起。玩游戏也经常是这些人在一块,晚上捉迷藏,白天下一种每人九块石头的石子棋。这种棋的玩法是:每人选一种区别于另一方的石头,在平整的地上划一个棋图,每人手里各有九枚棋子,棋图就是划三个方框套在一起,每个方框的每个边的中间用直线连起来。开始下棋,你下一个棋子我下一个,不让对方组成三个石子在一条线上的布局,等摆完了所有的棋子,开始走棋,一人一步,谁先走成三个子一条线,就吃掉对方一个棋子。一直互相吃的有一方还只剩两个子,剩两个子的一方就主动举手投降了。
地堰上的草品种很多,叫得上名字的有:荠荠菜、咕咕苗、抓地秧、节节草、苦苦菜、喇叭花、甜根草、野苇子等,有时草间开满了或紫或红或白的小花,上面飞舞着几只黑黄两色的小蜜蜂。有时偶而会从地堰的石缝里窜出一条小蛇来,我们先是惊叫,把同伴引过来,然后或用镰刀或用石块把蛇弄死,扔到地里的枯井里去。有时渴得不行,就到苇坑里割几根长苇子,在下端苇节上挖两个小孔,一根不够长,再接上一根,放进地里的水井里去打水喝,井里的水很凉,虽然水量小,但多打几个来回就有了,那水喝起来真叫过瘾。用苇子打水喝,最主要的是注意安全,有时不小心会把兜里的小玩具掉下去。那时总会吓得心惊肉跳的,万一人掉下去小命就没有了,在这荒坡野地里小伙伴谁也救不了你。
春天粮食不够吃,人们就摘榆钱、家槐叶、洋槐花和面伴在一起蒸菜团子吃。山里人好面子,来了客人打肿脸充胖子,先是借一碗面,烙几张饼,再是看看鸡蛋筐子,再出去一趟借几个鸡蛋。有的过了年待客,炒一盘粉皮充一盘菜,等客人走了把粉皮洗洗放起来,来了客人又当一个菜。你问为什么没人吃?主人作菜时就根本没想让人吃,他没有把粉皮弄开。还有一种最常听到的说法:说有一家买了一两香油,每每孩子哭闹时,就给倒点水,放上点香油让孩子喝水。一年下来,一看香油瓶子,里边的香油足有一两半。
公路也是土路,割草时看到赶集的回来,手里的家什里放着点青菜,间或有一个带半个西瓜的,这家肯定有混外的(指有在外边上班的)。那时篮子里的草总是割不满,有时怕回家挨训,就在下面用棍把草支起来。村北一里多路的地方是国营林场,林场很大,东边和南边是石头墙,北边和西边靠着侯庄的大坝,只用树枝和铁丝网围起来。里边大部分是苹果树,靠西边还有梨树和桃树。有大点的孩子进去偷梨和桃吃,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试过多少次,走到跟前就不敢进了。那时就盼着早日长大,长大了就可以有胆量进去摘梨和桃吃了。我们村的大坝后也有苇坑,芦苇里有灰灰菜之类的草,但坝后不通风,去里边割草总会出一身臭汗。
有时碰上星期天是集,农活又不是太忙的时侯,跟大人去一次集市。当然是走着去,我们村到洪范有六里路,去时几乎一路下坡。我们那边的村子很稠,几乎是一里路一个村子。集上有牲口市、粮食市,剩下就是卖菜的卖土特产的。卖菜的大部分是刘河的、东西池的、书院和张海的。因为人家那儿有水地。所以这几个村的小伙子就好找媳妇。洪范是公社所在地,公社大院里有一个水池,一年四季水长流,不论天有多旱,水位一点也不下降。水从前边的龙嘴流出,绕水池一圈流出去,流到河里去了。水池的四溜是一圈石狮子,从左、右、后三边的台阶上都能上去。里边的底部和深水里长满了绿苔。水里有不少鱼,小的有麦穗那么大,大的有七八斤。有一般鱼,还有红鱼。底部银光闪闪,那是好奇的人们扔下去的硬币。你把硬币扔下去,它不是很快沉底,而是慢悠悠地漂着下去。说是这里边的鱼不能吃,这是神鱼。说水池下面有个大泉眼,叫神仙用一口大锅扣住了。如把锅掀了,油篓寨上挂杂菜(一种水生植物的叫法)。这个水池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东池、西池的人都来担水吃,太阳落山后,走在挑水的人流中,脸上露出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偶尔和认识的路人打声招呼。南来北往的路人投来的目光中满含羡慕。
洪范向东没一里路,东山根下就是书院。这是个山青水秀的小村子,有一个很大的水池在村子的正中,水从水池流向四面八方,水清澈见底,没一点杂质。这里的人家几乎没有一家有水桶,家里的锅烧热了,再出来端水都晚不了。传说这儿原是秀才读书的地方,风水极好。洪范向北再走五六里路,就是于林。于林因宋代诗人于慎行的墓在此而得名。路的东边是村庄,路西后边是粮库,前边是供销社所在地,供销社的院子很大,里边是一片在北方很少见的白皮松,粗的有一搂多粗,树都很高,下边全是荫凉。门口有十几尊倒在地上的石狮、石马、石麒麟。听说“文化大革命”时被济南来的大学生破四旧给砸了。院落的西边就是于慎行的坟,坟堆得像座小山,听说有盗墓者曾从里边盗出过碗、碟等。坟西边的河水是从洪范流下来的,向北就流向了浪溪河,东阿人捡了个大便宜,用此河的水炼出了举世闻名的福字牌阿胶。
洪范境内,书院的山东边还有股泉水在丁泉,丁泉村比书院的地势要高许多,村中也是有一古老的水池,冬暖夏凉的泉水从水池中流出来,水池的下面一年四季坐满了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妇。比起上下左右村庄缺水吃的老乡,她们的穿着看上去总觉得要干净些。夏天若连着下几天大雨,泉水就会格外的旺盛,池中的水位也会上涨许多。东峪南崖有个虎泉沟,平日里流出的水很小,若碰上连阴天,下上几天大雨,水就会从山洞里咆哮而出,从村人早就修好的盘山渠中奔向石碑楼,从半山腰一跃而下,形成村里人很少见到的瀑布,甚是壮观。附近的村人趁雨后下不了地,看那汹涌的山泉水白白流掉实在可惜,就争先恐后地背衣服赶来抢占有利地形,一边洗衣服一边亲热地拉拉家常。有心的妇人在河边看上邻村的哪个姑娘,回来就会托熟悉的村人去给自己家的儿子提亲。
小学五年级时,村子里死了个大姑娘,上吊死的。我们白天不敢去看,但上学时还是看到了送葬队伍,晚上下自习后回家就很是害怕,越是心里劝自己别想越是想。不几日,村里又死了一个老人。我没事时就老是想,人为什么会死?人死了再也不能复活,别人在这个世界上或快乐或苦恼地生活,你却什么也不知道了。原先还能埋尸,现在连尸体也不让埋了。一火化那么大一个人就成了一把骨灰。那时我就怕死,有一天上课,老师让朗读课文,我的思想又走了神,就又想到了人会死,你死掉了,世界照旧存在,活在世上的人照旧快快乐乐的。你死了也许你的亲人会记得你,别人很快就会忘了你。你的亲人一辈、二辈会记得你,三辈之后的亲人也不会记得你了。从此你就会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再也不会有人提起你。越想越害怕,越想越难过。后来老师让大家停止了朗读课文,全教室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的哭声。老师关心地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不知怎么回答。后来知道了雷锋、刘胡兰、董存瑞,我发誓长大了要做个像他们似的英雄人物,再后来我知道了文字可以流芳百世,所以我下决心大了一定著书立说。这就是我最早的文学情结。
冬天来临的时候,地里已是万物萧条。早晨上学的路上一不小心鞋子会被露水打湿,身上的衣服在母亲的喝斥下已增加了好几件。太阳懒懒地挂在天上,有气无力的样子。偶有一群南归的大雁从头上飞过,它们排成人字形,嘴里叫着相互鼓着劲,并翅前行。过年前后,早晨起来,突然发现下雪了,大地银装素裹,一片洁白。虽然天有些冷,但人的心情却出奇地好。大人会说:瑞雪兆丰年,明年一定有个好收成。上房扫雪便成了加深邻里关系的纽带,谁起得早就先上房顶,扫完自家的,把相邻的邻居家的房顶也扫一些,等邻居上来,说两句感谢的话,即使过去两家有些不快,随着这场雪也一起融化了。这是大人一年里最清闲的日子,可以上街晒暖聊天。因为怕冷,上学的路上我们会跑起来。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上完一节课,脚都是麻木的。下课了,除了上厕所,就站在教室里跺跺脚。雪后的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农村的孩子不冻脸冻手的很少。
我老家有一盘石磨。每到秋天不太忙了,就做些煎饼吃。春节前也要做煎饼,有时用生产队里的驴(队里排号)拉磨,有时就人工推磨。用驴时要用布给它蒙上眼睛,它就会不知疲倦地走下去。人站在一边,只管转几圈向磨眼里添一勺粮食,那粮食有地瓜干、玉米,过得好的还会放上些小麦,头一天用水泡上,所以从石磨下流出的是一种面糊。人工推时全家会换着干,一上来我总是推得飞快,不大一会儿就推不动了。有时就两个人一起推,那时总觉得磨道没有尽头。摊煎饼的鏊子用四块石头支起来,下面烧柴禾,用勺子把面糊倒在上面,用竹板做的拐子把面糊推平,片刻工夫就熟了。一次要做好多,够吃很长一段时间的。最后没多少糊子了,有时就做厚一点,上面撒上点芝麻,那样会很好吃。
小时村里还有两盘石碾,一盘在后沟里我家的房子西头,是在一个土洞里;一盘在村东大崖子南边的平房里。过去没钢磨(磨面机),前村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把粮食磨成面的。石碾就是把一个石滚子放在磨盘上,把石磙子两边的眼用木框固定住,连接在磨盘中心的轴心上。推一会儿就把碾过的粮食用箩筛一遍,把细的露在下面,粗的再倒回磨盘上。磨一二十斤面要用一整个上午的时间。村人的许多日子就是在这种不紧不慢的生活中打发掉的。
挑水也是要学的,开始用的水桶小一点,用井绳把桶放到水井里去,灌满水提上来。心里总是慌慌的,一是怕自己不小心掉进井里;二是怕把水桶掉进井里。站在井边往下看真是害怕,井口离水面有六七米深,水下有多深就不知道了。反正水深比井口离水面的距离还要深。灌水最需要技巧,先在水面上摇摆水桶,左摇右摇,把水桶的一边顺势砍进水里,水桶里的水就满了。越是怕水桶掉进水井里,越可能真就把水桶掉进水井里。若真掉进去了,就去村里有铁钩子的人家借铁钩子,有时三两下就捞上来了,有时好几天也可能捞不上来,有时觉得铁钩子挂住了,一拉拉不动,很可能是挂住了井底下的树根,有时捞上来了,一看不是自家的水桶,倒是村人捞了好久没捞上来的水桶。扔下铁钩子捞到水桶向上拉绳的感觉真好,手里感觉得到重量,心跳加速。就像铁钩上是一条大鱼,既有成就感,又怕“鱼”在绳子提升的过程中跑了。水桶捞上来,要把水桶里的水再倒回井里,说是这样今后水桶再掉下去好捞。
后沟里的崖子头上,是人们经常歇息聊天的地方。小脚的女人上南崖子很费劲,不但要扶墙,走到一半还要歇一歇,不是上崖子,有时就是在爬崖子。就是年轻人担着东西也得侧着身子上。小时我想等我大了当了队长,一定要修一座桥。
夏天天热得人们全跑街上乘凉去了,我自己趴在煤油灯下,一边接受蚊子的亲吻一边写稿子,记得我写的头两篇稿子,一篇叫《同工不同酬,干活没劲头》,一篇叫《男女一起劳动为什么干劲高?》。头一篇说的是干一样的农活,为什么青壮年妇女只给七分工?讲的是男女不平等的事;第二篇的内容是:男人们在一起干活没劲头,女人们在一起干活也没劲头,只有男女在一起,大家干得都有劲头。虽然是打打闹闹,但绝对出活,你说为什么?我把稿子寄给了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平阴县广播站。但盼了许久也没盼来音讯。后来我有些失望,广播电台、广播站这样的好稿子不用,你们用什么?光用后门稿子?
一个雨天,正好是星期日。我一个人待在西屋里觉得很无聊,外边的雨一直下个不停。心里觉得很压抑,忽然就想到唱歌。我学着文艺演出时的样子,先来了一个开场白: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下面请王培静同志演唱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字一句认真唱完了。然后再报幕再接着唱。唱《国际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是工农子弟兵》等,记得还有一首开头是: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调子特别悲,唱出来简直像哭。我十三四岁开的第一场个人音乐会,没有乐队,没有听众,更没有掌声。
村里有个林业队,林业队在林场东边有个苹果园。四溜种了很密的洋槐围了起来,我们割草时有时转到那儿去,站在外边,望着里边果树上的苹果眼馋。有时观察许久,找个豁口钻进去,摘几个苹果出来,放在草篮子里用草盖了,心里慌慌地逃得远远的。然后坐下来,用镰刀把还带有农药的皮削掉,美滋滋地享用。虽然苹果还有点涩有点酸,但总算解了一回馋。有时在地瓜地里的秧子下面或玉米地里会发现一颗甜瓜,上面长的甜瓜已有半个拳头那么大。就用镰刀在甜瓜下挖个坑,把甜瓜向下埋一下,或扯点秧子弄点草把那儿盖了又盖,然后离开。待不过两天就憋不住再去看看,一看瓜虽然还没熟,但好像长大了一些。待几天估摸着瓜应该熟了,怀着兴奋的心情去看,心中想着千万别叫别人发现后给吃了。走到一找果然找不到了,心中就会失落好一阵子,后悔不如上次看时吃了它。
假期里邻居家的亲戚死了人,我被叫去抬盒子。就是农村摆的供,里边是一块肉,一只鸡。还有几刀草纸。中午吃饭时,上了一盘鸡肉,也许我的动作慢了点,等我伸筷子去夹时,盘里只剩下了两个鸡爪,一个鸡头。我犹豫了一下,夹了那个鸡头,坐在一个桌上的阴阳人说:你不能吃鸡头,这桌上谁的年龄最大谁吃鸡头,你这孩子不懂事。我把夹起来的鸡头又放了回去。脸上火辣辣地低下了头。从此我恨透了阴阳人。
“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张海和纸坊来过上山下乡的知青,有男有女。出门路过那两个村的时候,看到过他们的身影。那两个村有水浇地,是全乡收成最好的两个村,他们住集体宿舍,村里还派人给他们做饭。农村人善良,干活也只是让他们干些轻活。他们和农村人没有多少不一样,只是穿得干净点,脸白一点。女孩也扎辫子,也去河边洗衣服。看他们说笑打闹的样子,活得还挺快乐。
农业学大寨时期,寒假去纸坊出工。挖土方,先把地里的好土折到一边,然后把下边的土刨松,用地排车运到低处的沟里去。才开始召开动员誓师大会,然后公社给每村划片。每村都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插几面红旗。寒冬腊月里,地下冻得很历害,用钁头一刨一个白点。上点岁数的刨土、装土,年轻的男女青年拉车推车。天下起了小雨小雪也不收工。才开始可能觉得有点冷,干起活来就出汗了。一休息身上就又觉得凉了。女青年穿得五彩缤纷,和工地上的红旗交相辉映,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家乡的天总是那么高那么蓝,夏天的太阳几乎晒得地里冒火苗子,我们爱站在路边闻汽车过后留在空气中的汽油味。好像那味道能使我们的想象跟着那汽车走出山里。总是盼望有一块云彩在天空停下来,把我们罩在下面。也有那样的景象,天要下雨,我们跑着找地方避雨,可被雨淋了也没找到避雨的地方,回头一看,刚才跑过的地方,却还出着太阳。冬天也要出去拾柴火,我们在结冰的河面上推着篮子走,有时就放下篮子滑一会儿冰。地里没什么柴火,只能拿板撅子到河边和地堰上砍野树根。有时兜内偷装一盒火柴,冻得不行的时候,点一些草叶树叶烤烤手。
在山东的南部山区里,有许多绿树环抱的小山村,我的家乡王山头就是其中的一个。那里留有我孩童时的欢乐,少年时的幻想,歪歪斜斜的足迹。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