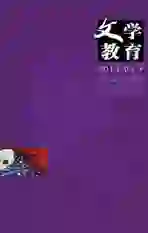莫言与余华小说阅读感受的异同
2014-07-24毛冰
毛冰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莫言与余华小说结构、语言、人物形象等因素的细致分析,阐述了作者在阅读两位作家的作品时,所产生的不同阅读感受。进一步指明二者作品存在的不同之处与引人之处。
关键词:莫言 余华 阅读 比较
七年前买了本《莫言作品精选》,看了第一篇《月光斩》,感觉不对路,就撂下了,直到今年莫言狂潮席卷而来,被冲击得站立不稳,又买了莫言两本被提及最多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坦白地说,如果不是诺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读莫言。七年前的那次短篇阅读,只能算对莫言的匆匆一瞥,所以是新读。
最早读余华是《许三观卖血记》,一口气读完,然后就毫不犹豫买了余华系列,《活着》《在细雨中呼喊》都读之欲罢不能,这个阅读经验说明,我更喜欢余华。
诺奖可以改变作者和作品的命运,但奈何不了读者的阅读口味。口味说起来好像只是感官的事,其实它很神秘地关乎一个人的性情,而性情既连着你的出生,又沉淀了岁月浇筑了阅历,说口味的时候其实在说整个人。
《丰乳肥臀》还没看完,难以做江河似的宏观评说,就拿局部的语言和余华做个比较吧。总的来说,余华的语言含蓄内敛克制,有着随意的精致考究,更耐品,更有张力;莫言的语言想象大胆,呼啸奔突冲撞,甚至恣意妄为,瞬间的爆发力让你读之胆颤心悸。如果说莫言的语言是穿膛裂石的利箭,余华的语言就是弦拉满月的强弓。读余华如温水煮青蛙,读莫言就是高空玩蹦极。莫言把想象写给你看,余华把想象指给你看。
比如《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分娩,莫言是这样写一对双胞胎出生的,先出来的是玉女,“婴儿又扁又长的头颅脱离母体时,发出了响亮的爆炸声,犹如炮弹出膛”;随即是金童,“伴随着鲜血,一个满头柔软的黄毛的婴儿鱼儿一样游出来”。我承认我被吓到了,不是被这样惊悚的生产场面吓到,而是被莫言敢想敢写的胆子吓到了,我愣在当下,不知该拒绝还是接受这样夸张的描写。如果“炮弹出膛”还嫌不够劲道,是不是可以改写成“犹如火箭喷射而出”?
再比如日本人在大栏镇报复性杀了很多人,摞满尸首的马车行进在原野上,这时莫言写道,“高密东北乡宽广地盘上的乌鸦全部到齐,像一团黑云悬在马车上空,它们呼啦呼啦地上下翻飞,发出兴奋的尖叫,排成各种队形,不断地往下俯冲。成熟的老乌鸦用坚硬的喙啄击着死难者的眼睛;缺乏经验的年轻乌鸦则啄击死者的脑门,发出‘笃笃的响声。‘老山雀(赶车人)用鞭子抽打它们,每鞭都不落空。有几只乌鸦跌下去,被车轮碾成肉酱”。不是乌鸦在上下翻飞,感觉是莫言那支放肆舞动的笔在上下翻飞。这段文字可以直接当成电影脚本,拍出的画面肯定让人瘆得慌,感官刺激绝对强,但你会怀疑这样的效果是不是用电脑特技加工过的。莫言还觉不过瘾,又写道,“众人一拥而上,与乌鸦开战,骂声、打击声、乌鸦叫声、翅膀扇动声,混成一片。尸臭味、汗臭味、血腥味、淤泥味、麦子味、野花味,搅在一起”,莫言已经来不及细描了,我想象他两手齐上,握笔的手风车似地一阵狂舞,一副色彩斑驳、形象杂乱绝对重口味的人鸦大战图一挥而就。
莫言笔下的乌鸦军团使我油然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那只乌鸦,出现在小说《药》的坟地里,孑然一只,也只有一静一动两处描写。写其静:“那乌鸦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写其动:“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我至今还记得那只乌鸦。
又比如这几句,“司马亭看着我家院子里的尸首,夸张地感叹着。他的嘴角和嘴唇、腮帮和耳朵上表现出悲痛欲绝、义愤填膺的感情色彩,但他的鼻子和眼睛里却流露出幸灾乐祸、暗中窃喜的情绪”。这里莫言直接用褒贬色彩鲜明的成语来形容人物,而且两两连用,如果出现在中学生的优秀作文里,这是可以加分的句子,可作家通常会弃用这种直白的脸谱化写法。要表现人物内心的复杂矛盾当然是有难度的,但这也是最见作家笔力的地方,你不能简单化地把人的嘴、腮帮和耳朵贴上好人的标签,同时又把鼻子和眼睛贴上坏人的标签。再说了,耳朵表现出义愤填膺,鼻子流露出幸灾乐祸,这想象也太匪夷所思了,这是一张人脸还是鬼脸?
小说中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经不起推敲的词句,像硌脚的沙砾,影响了阅读的流畅。这些词句打乱了时代界限,也使人物语言的地域特色、个性特点变得模糊,好像不是人物自己在说话,而是作者在替他们说话。这是作者仓促草就还是有意为之?你要告诉我这是作者在玩魔幻或穿越,我也没有什么话说。
比如黑驴鸟枪队队长沙月亮看上大姐上官来弟,对她说,“……我率部作战的情形你看到过,那场战斗,是英勇悲壮、壮怀激烈、彪炳千古的……”,这是一个拿刀弄枪的粗人说的话吗?
写鸟枪队闯进教堂,莫言写那28匹黑驴,“结成14个对子,你轻轻地啃我的腚,我温柔地咬你的臀,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是班主任在给学生写操行鉴定吧。
母亲带着六个姐姐往地窖里搬运过冬的萝卜,莫言有这么一段描述,“母亲背着我在地窖和萝卜堆之间来回巡视,发布着命令,批评着各种错误,表达着各种感慨。母亲的所有命令,都是为了提高工作进度。母亲的所有批评,都是为了改进工作方法,保护萝卜们的健康,使它们平安越冬。母亲的所有感慨,都在表达一个中心思想:生活艰难、必须奋力工作,才能熬过严冬”,读起来太别扭了,这是写一个乡下农妇在三四十年代的生活吗?而且用的还是排比句式。
写两个妓女打架用了一页半的篇幅细描过程,不知用意何在。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她们已咬得犬牙交错,老鹰与鹞子打架,钩爪连环,难分难解”,这句话用了四个短语做补语来形容打的状态,用词堆砌,两个成语和两个自创语混搭,不伦不类。
写女兵小唐动员妇女们剪头发,她说“……我们不搞封建迷信,但我们要拆破一切网络……”,抗战期间革命军人对乡下媳妇这样说,她提到“网络”这个词!
写母亲思念大女儿,“她抱着上官来弟的孩子,心中车轮转,双目泪婆娑”,前俗后雅的句子,不管风格的一致了,谁说混搭不是风格呢?但“心中车轮转”还真有些费解。
写“母亲奶水充足,奶汁质量高级,催得我又白又胖”,像泛滥的广告腔调,“质量高级”简直刺眼,太随意粗糙的表述了。
写元宵节的大栏镇上“人与人之间洋溢着安定团结的气氛”,莫言写的是抗战时期的景象,可怎么看都像是从节庆新闻稿中摘录的句子。
写蒋政委舀起一勺绿豆汤诱惑上官来弟,“……高高举起,慢慢往下倒,让汤的优美展现,让汤的味道扩散”,句式太一致就不说了,“让汤的味道扩散”没问题,“让汤的优美展现”总觉得哪儿别扭。
莫言的语言真是到了我行我素、其奈我何的境界,从填补空白的角度说,这何尝不能算一种创造。他的想象力在人物、情节、环境的描写上走得更远更肆无忌惮。小说中写到大姐上官来弟旁观了黑驴鸟枪队伏击日本人那场惨烈的战斗,莫言写道“眼前模模糊糊地出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景象”,这句话可以用来大致说明莫言想象力所擅长的方向,这是不是也是魔幻的特点呢?
比如写三姐在其男友被抓走后的第三天,“好像她已变成了鸟,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人称“鸟仙”,鸟仙声名远播,开始为十里八乡前来求药问卜的人开方,还大显神通惩治坏蛋,这完全就是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莫言版,可人家老蒲明说写的是鬼故事,莫言却是在写人。这一节鸟仙传奇甚至还有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家的鸟仙,蛟龙河与辽阔的大海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如此宏观的叙述居然缘于一个荒诞的鸟仙情节。读到这里,我不得不思考想象力有没有边界的问题。
写司马粮小时候由母亲抚养,“他吃着草根树皮成长……经常能看到,一团乱草从他肚子里涌上来,沿着咽喉回到口腔,他便眯着眼睛咀嚼,嚼得津津有味,嘴角上挂着白色的泡沫,嚼够了,一抻脖子,咕噜一声咽下去”,读到这一段,我联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你必须要有现代派作品的阅读经验,才能接受和消化这样的描写。
写“我”(也就是上官金童),一个刚刚由爬行到可以站立的婴儿,说的第一句话是“操你妈!”,让人以为一个叱咤风云的混世魔王将横空出世。可这却是个有“恋乳癖”的家伙,让我们扫描一下莫言怎么把男一号和“乳房”这个意象高密度的扯在一起:
“我不关心萝卜来自何处,只关心萝卜的形状,它们的尖尖的头顶和猛然膨胀起的根部,使我想起了乳房”,有一首民歌中这样唱“红萝卜的胳臂白萝卜的腿”,形状上还有相似点。把萝卜想成乳房,这需要强大的扭力。
“我从乳汁的味道上,知道母亲内心波澜滔天”,“我”在展现尝乳识人的绝技。
“我的目光越过母亲的肩头,遥远地注视着那些奇怪的女人,但见一片乳房飞舞缭乱……”,这是金童趴在母亲背上看一群妓女在冬天的井边打水。接着写两个妓女打架“手臂挥舞,乳房横飞……”,我想起毕加索那些变形的现代派画作。
“沙枣花的嘴把母亲的乳头拽得像鸟儿韩的弹弓皮筋一样长……”,这是金童看沙枣花和他争食母乳。
“我扑到六姐身上,双手准确地揪住了她的乳房”,连打架都跟乳房干上了。
“她的双乳在黑袍中剧烈摇摆着,炸开着瑰丽的羽毛,好像两只刚刚交配完的雌鸟”,这是写金童看他大姐。
“从鸟仙的袍子我想到上官来弟的袍子,从上官来弟的袍子想到上官来弟的乳房,从上官来弟的乳房又想到鸟仙的乳房”,可以进行思维训练,看能不能把任何东西都联想到乳房。
“她的那两只乳房凶悍霸道,仿佛充满了气体,一拍嘭嘭响”,挂的是篮球吗?这是写金童看他五姐。和上一句在同一页。
“有一个双乳上拴着铜铃的女人格外引我注意,她跳着一种古怪的舞蹈,让乳房上窜下跳,让铜铃清脆鸣响”,这是写抗战胜利后大栏镇的欢庆场面,和南美桑巴舞的狂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抗战胜利了,但上官金童被乳房抛弃了。我想到了死亡。我要跳井,或者投河”,没乳房,毋宁死,第一次看到这样独特的人生信念。
……
这只是前两卷中的一小部分和乳房有关的描写。恋什么的都有,“恋乳”当然也没问题,但怎么写是个问题。要用一个字形容《丰乳肥臀》的特点,那就是“粗”。构思粗放,想象粗狂,语言粗疏。莫言说,因为“胸有成竹,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平均每天六千字是让人惊叹的速度。他的创造力跑得太快,气势奔涌,语言跟不上,难免斑驳混杂。一气呵成一首诗或一篇文,没大碍;要一气呵成一部长篇确实要警惕,至少是不是一口气跑到底后,再回头仔细修改打磨。莫言属于典型的“才人胆大”,即袁枚所说的,“人称才大者,如万里黄河,与泥沙俱下。余以为,此粗才,非大才也。大才如海水接天,波涛浴日,所见皆金银宫殿,奇花异草,安得有泥沙污人眼界耶”。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得益于葛浩文的翻译。葛浩文的翻译非常巧妙,不是逐字逐句逐段,而是整体翻译的,这样的方式可以很好地规避掉作者的弱点。这是很学术很专业的看法。高产是莫言的长项,但写得太快也正是他的软肋。
(作者单位:广东深圳市罗湖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