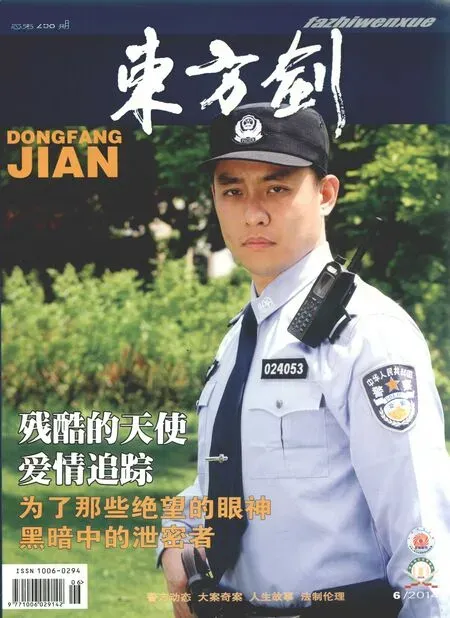致青春
2014-07-24都继恺
◆ 都继恺
致青春
◆ 都继恺

每一个走进你生命的人都不是偶然,即使相遇是短暂的,亦或是疏浅的。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名字叫马石城。或许因为彼此不同的做事风格,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俩一直交往不深,之间仅限于普通的同学关系。想起他,记忆就会闪回到大学新生见面会上,他主动请缨演唱《在水一方》,唱得很认真,但都不在调上,尤其让人捧腹的是他高音没升上去,可眼神已随着他的右手向上抬得老高老高,于是“爱显摆”成了我对他的印象。还有一个绰号与他有关——“马大吊”,那是在学校楼梯上饥饿地等候食堂开门的时候,他把军校生的饥饿感与性饥渴程度进行对比,形象地称之为“饿得跟个吊似的”,当即引来周围同学的一片笑声。很显然,他说到同学们的心里,而只有他敢说出这样的真理。他还喜欢跳交际舞,只是在我看来,别人跳得很轻盈,他却像小鸟儿似的一蹦一跳,尽管舞伴很紧张,他也决不敷衍。
当决定写这篇文章的那一刻,我的心就始终在纠结,因为交往不深,了解不多,而任何的夸大和虚构都会让我内心不安。我也不停地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要坚持写他?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是我的同学!四年军校的生活,同吃住、同学习、同训练,应该还有同欢乐,如今我们却阴阳两隔,而作为同学且有过一段同事经历的我,写些文字纪念他,好让他的名字不至于无缘无故地消失。
我私下一直认为,老马是个神经质的家伙,有点近乎偏执。记得新学员训练叠被子,为了平整,他把新的柔软的军被浸上水,再压平,叠得跟豆腐块似的。可盖在身上,那滋味肯定不会好受!有的时候,为避免叠被子的麻烦,他索性晚上不盖被子,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搞得我们这些新学员都很紧张。还有一次训练紧急集合,他怕拿不到第一,于是整夜躺在床上不睡觉,只等早上的哨声一响,他第一个背上他的“豆腐块”往楼下冲,恨不能从六楼跳下去。我不知道,这是否与他“爱显摆”有关,真够不要命的。
我们之间有时还隐约感觉到心照不宣的较量。
大一时,我有幸成为老马的“领导”,担任学员队区队长,他是九班班长。估计这事让他郁闷很久,表现出不反对、不支持的态度,我布置的工作基本被他打了折扣。这期间,我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能让他服从我的管理,能够有利于区队的团结。过了一段时间,我又第一个入党,这事对他打击更大,明显看出他的变化。那会儿,军校周日外出是有名额限制的,基本按2/10的比例。而他不请假也不销假的现象被我发现,这是军校严重的违纪行为。我找他谈话,他也当面认错,但心里不服气依旧我行我素,以此表示对我的消极抵抗。所以,在某队领导提名他入党时,我坚决反对!“如果他入党,整个区队都会被他带坏!”这是大学期间,我唯一投的反对票!这话估计很快传到老马的耳朵里,后来的日子,我们的同学关系渐行渐远。青春不忌少年狂,当年同学之间谁也不服谁是很正常的,而我要感谢老马的较劲,他练就了我的忍耐和宽容。
我和老马关系的改善,是在大学三年级上半学期,我俩同时“退居二线”,被新上来的继任者挤兑成了难兄难弟,于是就有了几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才发现他亦是很重情义的人。但我当时也搞不懂他是否掺杂着个人的目的,因为他想入党,而我曾经反对。毕业实习前夕,每个同学都在找着各自的出路,有同学说,老马原想留校,但没成功,因为他不是党员。我想,老马一定会嫉恨我一辈子!谁知毕业前一个月发生的一次变故,改变了我的想法。
那是李民兵同学被学院流氓子弟打成了小烧鸡,整个眼部红肿,脸部变形,几乎分辨不出他的模样,这群小流氓平时就经常欺负我们学员。于是第二天,当“潘狗势”同学告诉我,打“小烧鸡”那群人又来操场了,我迅速组织了十几人的复仇队奔赴现场!我拿着书包,里面装着板砖,第一个动了手。复仇的火焰被我点燃,却引发了一场“灾难”。这些被打的学院子弟家长不容分说,便把我们告到学院领导那里,说他们教书育人,反而自己的孩子被学生打。于是,我们挨个被讯问。因为是主谋、又第一个动手,我首当其冲要承担主要责任。
老马出乎意料地找到我,他主动提出为我疏通关系,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院长的好朋友。虽然协调并没有结果,但他却为我摸清了学院的态度,就是杀鸡儆猴——开除主犯!我顿时感到天昏地暗,想到羞于面对江东父老,便悔恨不已!于是狠狠地剖析自己,检讨写到了天边露出了鱼肚白,从态度到行动全力以赴弥补过失,当然,最终逃过一劫。这次事件给了我一个教训,尤其是反思对老马的误解,感激他在我危难时刻不计前嫌的雅量和鼎力相助的同学情义。应该说,他帮我是因为他乐于助人——我俩的关系没铁到他帮我的程度。也就是从那儿以后,我才主动拿着《同学纪念册》找他留言——“谨慎,沉默,执着……于是,走向成功!愿你这样!!握手,石诚 90.7.10”,字体是倾斜的,却斜而不倒、充满力量。很少留意他的字,这一次倍感亲切!
1990年毕业,从此天隔一方。那会儿没有手机,更没有QQ、微信,留的都是家庭地址,打个长途还要找关系,一度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他去了新疆,后调回西安,又转到广东……他真是为了理想不停折腾的人,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大力气!杨杼同学形象地比喻他是风一样的男子,不知道他今天在哪里,也不知他明天会去哪儿。这可能就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表现吧。
再见老马是大约1995年前后,我在北京惨淡“经营”着武警学院北京公司,是个身无分文的总经理。老马却很潇洒,西装革履,一派广东商人的样子,操着一口广东腔,透着一股牛气。他来北京给单位办事,还就是否调到机关工作征询我的意见。此外,他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他毕业后何时入党,何时成为广东出入境的一名干部。我知道,他对入党的事很在意,或许在有意暗示我当年投出的反对票。这次见面让我感觉很“不对等”,但也为他的进步感到由衷的欣慰,更为当年无意中伤了他的心而生出愧意。
再一次见老马,是在1998年的某一天,我们为王永祥同学从宁夏来北京发展组织了一次欢迎会。老马可以用意气风发四个字来形容,他已是公安部机关的一名干部。我也转业到了部直属单位,正在组织春晚创作。虽同在一个单位,却仍旧少见。唯一有过的一次工作上的交集是在2000年,我负责去香港、澳门拍摄温兆伦、黄耀明展示两岸三地的《警察故事》M TV。出发前,上报的手续迟迟没有批下来,而日程均已安排就绪,港澳警方也在不停地催到达的日程。没有办法,我只得硬着头皮去部港澳办协调此事。在那里,我意外遇见了老马,他竟然又调换了工作,正好就在这个部门。我向他说明了来意,老马说他可以帮助协调。他马上用钢笔写了请示,我也再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那歪曲且坚挺的字体!
在老马的帮助下,第三天,我带摄像及助理飞抵珠海,从珠海去澳门拍摄,再转香港,代表大陆警方完成了任务。而这一切,我至今没有向他说声谢谢,回想往事,心中又生出很多的歉意!
这之后,同学聚了几次未能约上他,多半因他忙而失之交臂。
2005年下半年,我调入部机关。我们在食堂里偶遇,他一副惊喜的样子,只是对我定为正处级产生质疑。我知道他是个认真的人,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那会儿我才知道,他是副处级,从港澳办又调到“上合组织”警方办事机构。据他何姓的同事讲:“老马很敬业、很认真,这与他在武警军校养成有关。一年多半时间都在上合成员国出差。有一次,我们共同处置了一起事件,成员国警方庆祝告破,邀请我们聚餐,当晚喝了许多酒,老马也喝多了。所有人都睡了,惟独老马夜里12点爬起来,独自一人跑到办公室把相关情况传真给国内。实际上,他完全可以第二天早上传的。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可想而知老马忙碌的程度。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至今都未到过对方的办公室,甚至说,我们没有因同事关系而加深友谊,平淡得几乎想不起对方,偶尔在食堂遇见,才知道对方的存在;偶尔聊上几句话,也都是关于他去哪儿开会、几天后又要去哪里。反正他像一个空中飞人,忙碌着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大事。也难怪,像我们这些草根阶层的干部,想干出点成绩只有两个字——拼命!
2009年某天的中午,一个同事问我,“你知道老马得病了?”我没有在意他的话,心想无非是感冒类的小病。他见我一脸轻松的样子,说,“有时间去看看他吧!怕是时间不多了……”我的心旋即被掐住了似的,顿时紧张起来。
“什么病?”
“好像是脑瘤……”
下班后,我半信半疑地来到了北京医院,找到了那个病房,最先看到的是他的父亲。听说我是老马的同学,老人拉着我的手出来,站在走廊过道里像祥林嫂一样,叙述着有关老马的信息:“石诚是累病的,每天都加班加点,极度紧张。他的办公桌周围有很多电脑,辐射又很厉害……现在只有简单的记忆……”
当一切得到证实,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老人家宽慰我说,“我是脑科医生,还有一些朋友,正在想些办法,延缓他的生命……”
我小心地走进病房,看到床边坐着的老马与我印象中的判若两人!震惊过后便是悲伤,甚至有些后悔不该走进这个房间,以留住他在我心中的那份美好。
“老马,你还认识我吗?”老马想了很久,以至于我后悔发出这样的疑问。
“你是做生意的……对!你老婆是……你叫……”老马努力回忆着,而他每发出的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我强忍住泪水,感受着他的变化。
走出那个房门,我不知怎样下的楼梯,又是怎样沿途返回,脑海里不断闪回大学时他年轻的模样——在弹琴吟唱中,在交际舞旋转中,在食堂开怀痛饮中……他是那样的青春洋溢,又是那样的风度翩翩!当这一切被残酷的现实摧毁,我的泪水肆无忌惮地流淌,仿佛在送别自己的亲人……这或许就是同学情义吧,平平淡淡、简简单单,不一定常见面,却会藕断丝连,不一定有承诺,需要时也会伸出援手……很简单,却很珍贵;看着彼此,就可以找到自己青春的痕迹。
回去后,我把当月工资的一半汇给了老马的父亲……
数月后,我看到了老马正处级调研员的任命通知……
数月后,老马悄无声息地走了……
没有人通知我去参加他的葬礼,一切平淡如昨,或许老马不想给同学们添麻烦吧……
还是在食堂,还是那位同事告诉我,主管领导经常提到马石诚的名字,表扬他认真负责,比如:老马出差的地方条件都很差,加上工作性质决定,他每次出差都一边背着电脑,一边背着打印机,很多时候,他忙碌得要命,就在飞机上起草文件、打印文件……
我的心绪再次被拨动涟漪,浮现出那个紧急集合背着“豆腐块”往楼下冲的老马,浮现出那个弹着吉他与同学一起唱着歌曲《送别》时的老马——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写到这里,泪湿衣襟……愿老马在另一个世界里,潇洒飘逸,青春永驻!
发稿编辑/冉利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