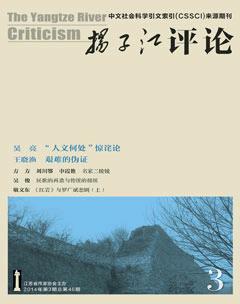从“岁月流金”到“铅华洗尽”──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发展与嬗变的观察与思考
2014-07-22潘凯雄
潘凯雄
从“岁月流金”到“铅华洗尽”──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发展与嬗变的观察与思考
潘凯雄
如果给传统的文学期刊下一个宽泛点的定义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传播文学信息的定期出版物。当然,传播文学信息的媒介很多,除期刊外,还有报纸、图书、广播、电视以及现在的各种新媒体等。之所以要将文学期刊单独拎出来予以讨论,的确是因为她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观察与思考这段时间我们文学创作、文艺思潮、文学运动、文学流变乃至整个文化生活嬗变的一扇重要窗口。
新时期以来先后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大致在800种左右,发行总量达数亿册,如此庞大的数字共同汇成了这段时间中文学期刊的汪洋大海,而正是这庞大的数字无疑给我们的考察带来了难以穷尽的困难。因此,即使作为这一时期文学期刊发展与嬗变全过程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尽管我力图描摹出其发展与嬗变的基本轮廓,但这种描摹无疑是个人化的,而随之展开的评述则更是个人的一孔之见。
在我看来,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期刊尽管品种繁多,规模不等,内容各异,但如果将其置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还是能够发现其一些共同的发展轨迹:比如大致都经历了从“计划期刊”到“市场期刊”的身份转型和从“风光无限”到“边缘寂寞”的心理落差和尴尬处境。本文也将循着这样的轨迹展开描摹与评说。
一、1978—1989:中国大陆文学期刊的流金岁月
1976年,伴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成为这一时期我们社会生活的主旋律,长期以来桎梏着知识分子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精神枷锁正在逐步被砸碎,文学创作也开始迎来了自己百花齐放的春天,而装点这个春天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众多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种类多,而且发行量大。据《文艺报》统计:1957年,全国有文学艺术刊物83种,每月发行340万册(《文艺报》1957年第7期);而到了80年代中期,文学期刊的种类则飞涨到近600种,翻了七倍多,发行总数近25亿册,翻了近70余倍(《文艺报》1986年5月6日)。如《人民文学》月发行量曾达到150万份,《收获》120万份,《当代》80万份,就连青海省的《青海湖》、云南省的《个旧文艺》这些边远省市地区的文学期刊都可以发行到30万份左右。80年代的文学期刊,无论是种类之多,还是发行量之大都高居中国期刊业之首,据统计,当时文艺期刊品种数约占全国期刊总数的八分之一,而印数则占全国期刊总印数的五分之一,足见读者之众,影响力之大。以文学批评期刊为例,按理说,因其专业性所限,其数量理应不会多,但即便是不多也有几十种,差不多大多数省份都有一两种专业的文学批评期刊,由此足见一斑。
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从外在形态上看大致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刊期上月刊与双月刊双峰并峙,前者谓之文学月刊,后者谓之大型文学月刊,顾名思义,既是大型,也就标志着篇幅大于月刊,因而容量也随之大于月刊,这种大型文学月刊批量的出现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文学期刊中一道崭新的风景,是以往文学期刊中所不多见的。第二,主办单位性质相对集中,即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部分中央部委及行业协会、部分文艺类专业出版社。如《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等隶属中国作家协会;《收获》、《上海文学》等隶属上海市作家协会,《钟山》隶属江苏省作家协会;各文艺专业出版社主办的则如《当代》隶属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界》隶属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月报》隶属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部分中央部委及行业协会主办者如《啄木鸟》之于公安部等等。第三,分布区域广泛,形成了一个密集的文学期刊网络,从中央到省、市、地区乃至县一级都有自己的文学期刊,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有相当发行量的《佛山文艺》就出自广东佛山这样一个县级市之手。第四,内容囊括文学领域的方方面面,既有统括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批评和译作等不同门类的综合性文学期刊,也有上述文体分门别类的专业文学期刊,既有刊发原创性作品的,也有选登、摘发类的选刊。
文学期刊外在形态的这些共同特点归结起来其实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品种众多,个性不足;形态各异,结构雷同。如此这般无疑为它在下一时期走向边缘和寂寞埋下了伏笔,这当然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然而,无论这些文学期刊的外在形态如何缺乏个性,如何结构雷同,但由于它们共同置身于80年代的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因而,它们对80年代的中国文学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都发挥了不可或缺、不容小视的巨大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考察80年代的中国文学发展乃至文化生活的面貌,离开了对这一时期文学期刊的考察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巨大的缺失和明显的片面。具体来说,文学期刊在这一时期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80年代的文学期刊将文学提升到了推动时代发展的新高度,创造了一种时代特色极为鲜明甚至是开时代之先的文学,中国文学发展新的历史时期由此而开辟。众所周知,伴随着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成为那一时期国人生活的主旋律,但思想的解放、乱的拨正和对“是”的追求终究都需要一个渐进和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期刊常常通过自己的行为——无论是刊发作品还是组织活动——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比如《班主任》、《公开的情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大墙上的红玉兰》、《陈奂生上城》、《古船》等一大批脍炙人口、足以令一时洛阳纸贵的文学作品都是首先通过文学期刊与读者见面,其影响力与社会反响都远远超出了文学自身,当时一些在社会还属十分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都是由文学期刊上刊出的这些文学作品提出了第一声质疑,发出了第一声呐喊,诸如“血统论”、“教育问题”、“知识青年问题”、“反右扩大化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等。我们固然不能说文学期刊刊出的相关文学作品对解决这些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它们以其敏锐的政治触角、生动的艺术形象在突破思想禁区、启蒙民众心智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再比如,自上世纪50年代末“反右扩大化”开始到十年“文革”浩劫,对知识分子身心的迫害发展到登峰造极,一大批作家艺术家蒙受不白之冤,当他们在政治上尚未被平反昭雪之前,是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悄然地将他们的名字连同其新作重新公开与读者见面,用自己所能企及的行为率先为他们洗刷了历史的冤屈,这样一种事实上的平反其影响力丝毫不亚于一纸红头文件。凡此种种,无怪乎后来有学者评说:80年代的文学轰动是成功地引爆了政治、社会的兴奋点,即使是在文学最有轰动效应的那些时候,公众关注的也并非文学,而是裹在文学外衣里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这种评说是否周全姑且不论,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时期文学期刊的种种作为所产生的社会反响。后人常以春天来描述1978年以后的中国,那么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文学期刊是这个春天里一朵朵艳丽的报春花则一点也不为过。
其次,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不时引领推动着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而文学思潮此起彼伏的涌动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从“伤痕文学”到“为文艺正名”到“朦胧诗”到“反思文学”到“文学寻根”到“文艺学方法论”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重写文学史”……这一时期由一场场文艺争鸣构成的文艺思潮大都是由文学期刊所引发并展开,一连串文艺思潮的此起彼伏不仅推动了文学本体的回归和走向多样化,而且其影响所及则远非一个文学界所能涵盖。
第三,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催生和促进了一些文体的发展,中篇小说在这一时期的异军突起就得益于一批大型文学期刊的催生。比之于一般的文学月刊,这些大型文学双月刊篇幅长,容量大,适于刊发中篇小说,从而促成了中篇小说的兴起。在当时号称大型文学双月刊“四大名旦”的《当代》、《收获》、《十月》和《花城》(另有说为《钟山》或《中国作家》)上,每期都有相当分量的中篇小说见诸于版面,而一些在当时影响甚大、成就卓著的中篇小说诸如《人生》、《天云山传奇》、《绿化树》、《布礼》等也都是先刊之于大型文学双月刊上。作为一种特定的文体,中篇小说以既针对现实作出敏捷反应,又能对一些问题作较为深入的开掘见长,它所承载的内容,短篇小说容纳不了,但又未必需要长篇小说那样厚重的积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批大型文学双月刊的催生和促进,中篇小说能够在这一时期得以如此迅猛的发展,如同在1949至1966年的十七年间,为人所称道的不是长篇小说就是短篇小说而鲜有中篇小说。与中篇小说这一文体命运相似的则还有中长篇纪实文学,这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表现则尤为突出。
第四,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对作家身份与地位的确立至关重要。如果说前面所说的一些文学期刊悄然地用自己的作为先于政治上为一些作家洗刷不白之冤的现象尚不具普遍性的话,那么,从创作与传播层面看,80年代的作家和文学期刊之间那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则无疑具有广泛的共性。一方面,80年代的作家不像现在的一些作家那样或直接出书,或依赖于网络,当他们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总是要先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然后再把散见于各种文学期刊上的作品集结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对文学期刊有一种依赖关系;另一方面,文学期刊同样需要高度重视各个年龄段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使期刊成为作家的集散地和培养作家的园地。几乎可以这样说,如果以简单的作家代群划分,出身于80年代以前的几代作家中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文学期刊而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并由此走向文坛的。
最后,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对80年代中国文学生态的初步形成也发挥了自身的作用。在文化专制和文化集权的统领下,文学所呈现的形态只能是千篇一律,谈文学生态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而当思想的牢笼一旦被冲破,文学的生态问题自然就被提到了台面。立足于今天的视角,从大的层面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学的生态描述成主流、新潮与消费三种状态,而这样一种三分天下的格局在80年代的文学期刊那里就已初露端倪。那个时期为数众多的文学期刊在某种统一化的模式里拥挤了一阵子后便开始追求不同的个性,它们的不同选择悄然孳生了文学的分流,比如《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选择了主流文学,《收获》、《花城》、《钟山》等偏向于“新潮”“先锋”“实验”,而《今古传奇》等则选择了消费,而这种分流恰恰是文学生态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难看出,从1978到1989年的这一时期,文学期刊在当时的文学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举足轻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是期刊中的文学,而且是期刊化了的文学,众多的文学期刊孕育出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称其为中国文学期刊的流金岁月一点也不过分。
二、1990—今:洗尽铅华,回归本位
当时光步入上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在中国风光无限的流金岁月渐次逝去,其实,这样一种转变还可以追溯到80年代末,只不过人们在蜜月中沉溺的时间太长了而不愿正视现实而已。当文学期刊的铅华真的褪尽时,那些期刊人一方面无限缅怀逝去的那段美好时光,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陷入惶惶然失措之中。
如果说80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关键词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初,这个关键词则为“市场”和“转型”所替代,而正是这四个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汉字将曾经处于文学核心位置的文学期刊给冲击得七零八落,直到沦为边缘与寂寞的境地。
伴随着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整体推进,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数十年一以贯之的文学体制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文化传播方式的不断丰富,使得文学期刊的生存环境出现重大转变。随着政府行政拨款的逐步减少和文学期刊发行量的锐减,大多文学期刊的生存困境日渐突显,于是关门的关门,“更张”的“更张”,为了化解市场危机而解决生存问题,众多文学期刊纷纷以“市场”为中心,树起了“转型”和“改版”的大旗,上演了一出出“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热闹。
面对“市场”与“转型”,众多文学期刊的表现明显是无所适从,因而所采取的措施自然地烙上了应急性和功利性和印记。在这个过程中,那种明显的带有商业性的炒作或是直接与商业的联姻的所谓“转型”自不用多说,而更多的是那些以所谓“文学策划”为名所进行的“转型”其应急性与功利性则要隐蔽得多,以至于一些“策划”、“命名”、“炒作”的科学性早已被置于九霄云外。归结起来,看似热热闹闹的“策划”与“命名”之手段其实也很单调:无非是其一,在一些核心概念前加上“新”或“后”一类大而无当的状语,于是就有了“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后现代”、“后殖民”之类似是而非的“策划”与“命名”;其二,简单的代际与群落划分,诸如“70后”、“80后”、“美女作家”等;其三,诸如“身体写作”、“行走文学”一类意义含混暧昧的“命名”与“策划”。看上去,这一个个“精心策划”出来的办刊手段热闹非凡,对某种文学现象也不无概括之意,但更多的还是为了“市场”的应急方案,与文学与市场的内在需求并无多少关系,这样的“思潮”与80年代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引领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撇开这些浮躁的应急“转型”办法不论,重新定位是这一时期文学期刊为了适应市场而“转型”的常用办法之一,而这种定位的调整使得原来总体上个性缺失、结构单一的文学期刊多少现出了一些差异性。归纳起来,90年代以后文学期刊的定位调整大致有五条路径:一是由“纯”向“杂”转变,即在保留一定文学板块的同时,走泛文学乃至文化路线,试图使期刊具有针对性地直面鲜活的现实社会,走出单一的文学小圈子;二是打破区域界线,特别是地方性的文学期刊突破区域办刊思路,以开放的视野与国家整体的文学态势接轨;三是走个性特色鲜明的“专”与“特”之路,对目标读者进行细分,从大众传播转化成针对某一特定人群的传播;四是变一刊为“一刊多版”,试图拓展刊物的生存空间,在保留文学版的同时,开辟若干新的试验园区;五是干脆弃文学而另觅文化、娱乐、综合、新闻等其他门类。当然,对以上五条路径的描述也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一些文学期刊对自身定位的调整不少也是在灵活地采用组合的办法而非简单地一条道儿走到黑。其间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都有必要予以认真总结与反思。
论及成功的经验,如下四条是值得记载的。即一,打破重复办刊、千刊一面的惯例,追求特色的鲜明,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个性目标。80年代的文学期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由小说、散文、诗歌、纪实和批评五大板块组成,虽也有变化者,但无非是篇幅的多寡与重心的不同,而重新调整定位后的一些成功的文学期刊则显然不同于这五大板块结构法,一些特色栏目令人耳目一新,也由此吸引了读者眼球,如《天涯》的“民间语文”、《作家》的“作家地理”、《佛山文艺》的“城市新移民”等;二,从盲目的大众传播走向相对准确的小众传播,根据读者的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所属地区等差异,对目标读者重新定位并针对这些特定目标读者的接受心理和审美趣味进行有的放矢的定向传播,比如《萌芽》将目光聚焦于中学生群体,启动“新概念作文大赛”,以此吸引了庞大的中学生群体对该刊及系列出版物的关注与追捧。三,充分做好风险评估和长期规划,稳中求变,不轻易放弃刊物原有的影响力及连续性。如同样隶属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小说家》变身于《小说月报·原创版》就是成功的一例,它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充分利用了《小说月报》已经形成的品牌效应将两刊予以重组,一个“原创”一个“转发”倒也颇成系列与规模,改了一个刊名救活了一家期刊,这是稳中求变成功的典范。四,以办刊的核心价值为统摄,追求风格的多样化与互补性。如果一家文学期刊形象模糊,而且摇摆不定,就无法拥有稳固的读者群体,反之,核心价值的基本统一,具体内容的差异互补就能形成良性互动,比如《佛山文艺》与其子刊《打工族》就是在同一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尽量考虑同一类型读者内在细微的差异,互相借力,互相提携,因而产生了共赢的结果。
反过来,对另外一些定位调整不成功的文学期刊来说,大抵也是在如下四个方面步入了误区。首先,误以为“雅俗共赏”足以包打天下,结果却往往是陷入雅俗不赏的尴尬,文学期刊的调整定位一定要有所放弃或拒绝,想什么都要的结果则常常是什么都抓不住。其次,盲目跟风,从一种个性缺失结构单一走向另一种个性缺失结构单一。当《萌芽》将目标读者定位于中学生群体并获得成功后,一时就有许多刊物纷纷办起了自己的“中学生版”、“校园版”;当《散文》推出萃取刊发于海内外报刊散文精华的“海外版”时,又催生了一批“选刊”的出笼,如此毫无个性创意的跟风期刊其结果也就注定了它们的短命。再次,轻易放弃刊物长期的优势与特色,盲目地一味迎合所谓消费者口味,在文学与市场间摇摆徘徊,导致两边都不讨好,相反,《收获》、《当代》等品牌期刊的谨慎态度倒是稳住了基本的市场份额,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只有稳定的核心价值才能抵御为善变为旨归的时尚冲击。最后,变脸过于频繁无异于饮鸩止渴,一些文学期刊在“转型”过程中频繁玩起了“变脸”的花活儿,看似随机应变,而这种随意的背后实则暴露了办刊人缺乏深入的市场调查和可行性论证,简单地视改版为包治百病的良药,以至于读者连这本期刊的基本面貌都遗忘得一干二净,这又怎么可能获得生机呢?
综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的种种嬗变,以市场为中心进行“转型”确是这一时期文学期刊的主旋律,“转型”的结果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有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即这一时期文学期刊单品的发行总册数大大下降,文学期刊在80年代那种单期多则上百万、少则几十万的“盛世”几近绝迹,最多的单期不过三四十万,能维持在月发行5万份左右当属幸事,而绝大部分文学期刊的单期发行数已下滑至万份以下,有的甚至只剩千余册。伴随着发行量的下滑,其社会影响力必然日渐式微。无怪乎一些文学期刊的从业者在谈到自己的生存状态时不无悲凉地慨叹:我们被边缘化了。尽管笔者更愿意用“常态化”来描述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期刊的生存现状与嬗变,但比之于80年代文学期刊在中国大陆的那段流金岁月,边缘化三字的描述倒也大致不谬,且生动形象。
三、从“岁月流金”到“铅华洗尽”的思考
中国的文学期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其生存境遇及社会影响力所遭遇的巨大反差难免会导致论者对其评价的莫衷一是:持“今不如昔”论者有之,他们无限眷念逝去的美好时光,痛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曾经红红火火的文学期刊给撕扯得七零八落,认为文学期刊与市场化之间与生俱来的相互排斥,市场化就意味着文学期刊的最终消亡;持“扼腕相庆”论者有之,他们更尊重市场的现实,认为80年代文学期刊在这片土地上的风光不过是一种“虚热”,昙花一现正常不过。
其实,如此巨大的反差都还只是局限在文学期刊传统的出版业态范围之内所作出的评价,倘放眼于本世纪以后愈来愈呈燎原之势的数字化大潮,情形或许会变得更加复杂。对此,笔者更愿意本着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未来的基本态度对尚未终结的文学期刊命运之变化作出以下基本判断。
首先,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80年代文学期刊对中国的文学发展、文化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不仅不应低估,而且还应给予充分的正面评价。现在时有论者以“文学性不高”为由来低估80年代文学期刊的贡献,在他们看来,文学期刊在80年代的风光不过是种种“非文学”因素所导致。我承认这种说法具有部分的事实依据,但更以为此说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文学的理解也过于偏狭。没错,从纯艺术的眼光看,80年代文学期刊上刊出的一些文学作品其艺术上确有粗糙生涩之处,其叙事远不及今天的作品来得圆润与娴熟。但这些作品从思想观念到文学观念对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大冲击以及所起到的先锋开路作用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客观存在。
其次,如果跳出单一的文学圈,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出现的嬗变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社会与思想的巨大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期刊所遭遇的“冷”恰是它本应有的一种常态。我始终认为,观察事态变化的本质固然可以有多种视角,但其生存环境在多种视角中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舍弃的。正因为如此,文学期刊从80年代的“热”到90年代以的“冷”,如此“世态炎凉”莫不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而“热”与“冷”的两相比较则不难理解何谓“常态”,何为社会的进步了。比如,80年代的文学期刊之所以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恰在于它率先提出并揭示了不少尖锐的社会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本来完全可以不由文学期刊和文学作品来提出来揭示,但当时社会种种条件的不具备、不允许,文学期刊自觉不自觉地承受了那种“生命之重”。而伴随着社会的持续开放、思想的不断解放,传播方式多了,传播渠道宽了,言路畅通了,文学期刊和文学作品难以引起轰动不就正常不过了吗?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而对文学期刊而言到底是边缘还是常态?我想只要不是囿于文学一己的小圈子而难以自拔,是不难得出正确答案的。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对曾经的文学期刊人而言或许更无奈、更残酷。面对本世纪以降方兴未艾的、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生存数字化和阅读分众化的大潮,无论是传统的纸介形态还是新兴的数媒形态,在一定时间内,文学期刊的个性化与小众化趋势同样不可逆转,至于伴随着传播工具、传播手段的不断创新,期刊这种样式本身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乃至是否还会存在或许都会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如果说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期刊开始出现的“式微”还只是单一纸媒市场需求的变化,其走向当时还未必看得十分清晰的话,那么,现在的这种判断无疑就要明晰得多,这同样是不以个人喜好与否的意志为转移。进行这样的描述看起来很残酷,但究其实只要想清一点也就释然了,那就是文学期刊本身的结局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不死、阅读永存。对文学人读书人而言,这就够了。
(本文依据笔者在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的演讲整理而成。)
※著名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