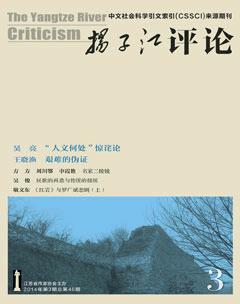方方的两翼:历史与当下
2014-07-22申霞艳
申霞艳
方方的两翼:历史与当下
申霞艳
近年来,方方创作势头凶猛,作品老到、大气、浑然。她以长篇小说《武昌城》和中篇《民的1911》深入武汉的烟尘深处;以长篇《水在时间之下》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声音低回》等中篇叙述城市下层生活;以《刀锋上的蚂蚁》开拓全球叙述空间。这是对由《风景》与《祖父在父亲心中》勾勒的叙述世界的拓展,标志着方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层次。
方方小说最动人之处既不是故事也不是技巧,而是她对这个世界的感情以及对这种感情恰如其分的节制表述。方方的小说方正而圆润,读来又心酸又温暖,二者交织犹如音乐旋律般经久回响。
方方是“入世”很深的作家,她叙述最日常的喜乐忧思,这得益于她青春时期四年的码头工人生活,这种纯体力活让她从经验层面触摸到武汉这座城市码头文化的根底,触摸到普通百姓的七情六欲。她看到了狡黠与真诚、生命力与野蛮、怯弱与勇气的交织,看到了生活的底色与花纹,看到了众生,这一切比书斋里的想象、理性的知道要更为真切,这为她日后写小说奠定了沉在水面下方的冰山。尽管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哪怕是书写知识分子题材,秉持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她也能将这一切还原于日常生活。
方方的日常不等于琐碎,而是说她一直贴着生活的心肺写,她不让想象凌空蹈虚,笔下的细节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流动。而在叙述背后却能感觉到作者传递的一股劲,这股劲柔中带刚,还带有那一代人的生存印迹,是不能被消费时代所磨灭的,可以说这是生命力、生命意志。这种意志力流淌在不同层次的人物身上,比如驻扎在我们记忆深处的“七哥”,又如“祖父”,他们的人生谱写了截然不同的“风景”,却依然能找到某种内部的一致,也许这就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风景》的面世让方方出道不久就获得了一顶“新写实”的帽子。今天回头看“新写实”,它是背对着宏大叙事自立门户,它是那一代人被“高、大、全”弄坏了胃口之后另起炉灶,是反抗和创新。当先锋作家们纷纷从西方尤其是现代主义叙述技巧那里寻找资源,方方凭女性的直觉泅入生活的深处,她不求耳目一新,但求水到渠成。她按生活内部的偶然、转折、惊喜、悲伤和诗意成全叙事。
形式在方方这里迎刃而解,因为她的写作从人物出发。经过西方现代小说浸润之后,青年作家在中短篇中致力书写生活的截面,大都是灰蒙蒙、湿漉漉的让人不安的片段,城市生活将我们分裂成不同的侧面。在城市里,我们已经不习惯四目相接,我们害怕泄露内心的秘密,我们更喜欢通过电话、邮件、手机、微信等机器去沟通。当大家不得不面对面坐在一起时,我们要么低头摆弄手机,要么将目光投向窗外,高大的建筑物堵住了视线的去向,也挡住了涌上心头的倾诉和对话欲望。个人命运的沉浮无法与时代的起伏发生回应,这不是写作技巧问题,而是内心在时代面前的撤退。
刻画人物乃古老的写作律令。鲁迅曾断言小说说到底是写人物。的确,小说的荣耀很大一部分来自想象创造的人物画廊,我们甚至觉得这些虚构的人物比邻居离我们的心灵更近。写作的风尚像钟摆一样摇来摇去,今天能让一个立体鲜活的人物迎面而来再次成为写作的难题。
一、小人物的美学原则
阿东、涂自强,就像你身边的熟人,亲近、朴实、平凡,他们不是英雄,也不是榜样,但他的一举一动会牵动我们最微细的神经,撩动我们的心,以至寝食不安。这在文学人物面目模糊的当下别具新意,这也是老子所谓“道法自然”在当下文学中的运用。方方的作品洋溢着母亲的柔软和深情,她的目光聚焦于弱小人物、边缘群体,聚焦于故乡武汉。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一个21世纪新型的“进城”故事。20世纪后期文学书写的是农民进城打拼的故事,比如路遥的《人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梁鸿的《出梁庄记》……他们都是农民,徒手空拳地进城,失败是难免的。不同的是涂自强是去读大学,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怀着憧憬,还捎带全村人的希望和祝福。
涂自强对时代处境有清醒的认识,他按照社会的要求亦步亦趋,他的梦想与“骆驼祥子”一样具体、卑微。涂自强的爱情还没开始绽放就消失了,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好不容易立志考研却因丧父而错失良机,涂自强就这样一路匆忙地与他的必然命运狭路相逢。涂自强的遭遇看上去是一连串的偶然,偶然串联起来不等于命运,命运包含着必然的时代逻辑——身份及其认同。涂自强的父亲死于强拆,他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帮他分担赡养母亲的义务,没有人可以给他提供根本性的实质性的援助。涂自强成为孤零零的个体,家、国、天下离他何其遥远,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将他与这个国家紧密联系起来。
涂自强的人生遭际显示了社会最根本的“断裂”,是不以个人意志、愿望和奋斗为转移的“断裂”,是知识也无法修复的、彻底的、不可逆转的断裂。他的个人奋斗和悲伤显得尤其惊心,具有深刻的当下性。他的悲伤是多重的:城市的繁华,是别人的;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城市重新变成了深渊,变成了薄冰,变成了悬崖。青春再也不能与梦想、爱、勇气这样激动人心的字眼联系在一起。青春的脸深埋在现实的窒息中。悲伤微不足道,悲伤又如此深重,让这个时代在狭窄的琐屑的现实里抬不头来。
只有在命运的泥淖里跌摸滚打过的人才能如此平静地写下这惊心动魄的一切。叙述的平静正是这篇文章感染力的来源之一。涂自强不叛逆、不攀比、不叹息,他在做了一个沙漠中艰难跋涉的梦后意识到这只是自己“个人的悲伤”,连悲剧都谈不上。他坦然地帮宿舍同学洗衣服,坦然地接受动心的女孩离开自己,坦然地接受父亲的死亡,坦然地接受同学请他到酒店吃饭、洗澡和嘲笑,比起谋生的艰辛,尊严已经无暇顾及。涂自强如此坦然,他在云淡风轻的日子告别故乡到城里去,又在风轻云淡的日子跟母亲、跟这个世界最后道别,这样的时刻他都没有愤怒、没有抗议、没有抱怨,他只是默默地在心里对母亲说“对不起”。涂自强的卑微与他所受到的无迹的压迫相形对照,深重的压抑随着发自内心的“对不起”从文本深处迸发出来。
方方的《声音低回》从母亲的猝死写起。涂自强丧父让他失去了扭转命运的机会;阿里姆妈的猝死会如何改变这一家呢?东亭街像我们熟悉的任何一条旧街,然而又与城市的新商业区格格不入。在这里,邻居之间仍然残存着熟人社会的温情。阿里搀扶着罗爹爹,罗爹爹让细婆做热干面给阿里吃,罗四强给阿里剃头不要钱……这种残存在城市角落的邻里亲情是方方作品温暖的底色,也是方方叙述世界建立的根基。
就像“祖父在父亲心中”这个标题一样,《声音低回》、《琴断口》、《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等作品均有重要人物非正常死亡。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常态,车祸、疾病、恐怖袭击、自然灾难,随时可以将生命带走。我们几乎习惯的是新闻上没有温度的数字和随时覆盖,很容易遗忘他人的痛苦。作家方方将这一个个具体的死亡演绎给我们看,死不是空无、不是消亡,死同样是存在,死是生的背影,是进入历史怀抱的一种方式。死是停顿而不是停止,死亡提醒我们生命的起承转合。死亡这个黑色的精灵会化成音乐、化成气味、化成细节与生活随影如形。死亡并不孤立,死亡坚硬而长久地活在健在者心中并影响他们的命运。姆妈死了,她活在阿里兄弟心中。蒋汉死了,米加珍心中还有他。杨景国死了,还在瑶琴心中长存。方方将死者埋在活人心里,逝者即使卑微,也是独一无二的、神圣的。她以宽广的理解探讨了死亡在生命中的延续,拓展人类生生不息的意义边界,给生命以温柔的慰藉。
同时,弱智阿里对正常的成人恰是一种警醒,他在三岁那年遭遇车祸智商停止了发育,所以,他的世界简单、纯洁、脆弱,他沉溺于自己的内在生活。他需要的不过是热干面和母亲。母亲几乎是他的全部,拉着母亲的手就拉住了整个世界。当代文学出现过一系列弱智形象,如《爸爸爸》、《尘埃落定》等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这是作者让我们回望人类历史、重新审视人这一主体不断物化的努力。因为越是低智的人物,越发凸显出与周围环境的巨大差距。正常的人恰恰容易因为适应环境的诱逼而异化。人类永远以脑袋、智力来征服世界,但是大脑的发达、欲望的膨胀并不能带来情感的满足。欲望推动历史的发展,却随时可能将我们带到悬崖和深渊之中。手段可能置换目的并奴役人类。
《声音低回》中的母亲与阿东、涂自强的母亲和他身上都流淌着难言的坚韧,尽管无奈,但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从方方笔下传递给我们。这些底层小人物不如古希腊悲剧中英雄那样恢弘庄严、崇高悲壮,但小小的“个人悲伤”同样会激起无限的涟漪,勾起我们的怜悯之情并陷入忧思,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是当今“时代的广大负荷者”。方方的叙事恰到好处地控制着距离,投入但不泛滥,她要的效果是沉思而不是眼泪。当时代的想象被情欲、金钱、消费所笼罩,方方另辟蹊径,她跑到景点之外看风景,欣赏低回之音。
二、知识分子与历史的纠结
在20世纪的文学想象中,知识分子要么是孔乙己般的迂腐,要么是方鸿渐一样无用,要么干脆一身腐臭需要改造,这些都只是知识分子的肖像侧面。如何刻画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是方方近年的努力方向。《祖父在父亲心中》写出了知识分子的高贵与脆弱、追求与苟且的传承和变调。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知识分子越来越被犬儒主义侵袭、被市场意识形态所挟制。方方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刀锋上的蚂蚁》出示了她对“全球化”的思考,叙事者巧妙地为这种思考穿上了小说的外套,让具体的艺术家“小我”来承载其对民族艺术这个“大我”的思考。警官费舍尔与中国画家鲁昌南的相遇具有偶然性,不过在一个开放时代,中西民族文化与性格之间的碰撞、对照与渗融则是必然的。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的交流,顶层则是文化和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明信说:“金钱是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它产生一种独特的压力和焦虑,引出新的灾难和欢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充分发展之前,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产生的作用相比。”①文化消费主义不仅改变了艺术品的价值,也从内部改变了艺术家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无疑,透过鲁昌南“全球化”的艺术人生轨迹,我们看到中国作家方方的审慎和犹疑。
画家鲁昌南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可以视为方方为当今知识分子描绘的精神肖像。《武昌城》和《民的1911》则是作家深入历史,对知识分子使命的探究和对革命的重新想象。对于历史小说,方方不像新历史小说那样完全强调个人视角,任由叙事人信马由缰地驰骋想象;而是查资料、做考证,尽量有根据有来历,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她都会据实想象;在创作《乌泥湖年谱》时就确定了自己书写历史小说的方法,“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把它换了一个方式,按照我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样会让我的小说稳稳地在一个地方,而不是飘在空中。”以学术考据的方式展开历史叙事是方方的一大特点。
历史叙事的主角不是帝王将相达官贵族就是仁人志士社会精英。文学却要扩大书写容积,要写出籍籍无名的芸芸众生,要写出广阔的日常生活。《民的1911》中的主角“我”叫民,这既是以谐音取平民立场叙事,也是对君与民关系的再思考。
“我”的父亲是剃头匠,这个身份在传统中国乃下九流者,但在革命关头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特殊的历史时代头发是身份的确认和身体的规训。头发问题表现了中国革命的纠结与复杂性,头发既是历史问题、文化传统问题,也是民族问题,清朝入关之际和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时头发都曾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头发一度分裂为“头”和“发”的对立。鲁迅曾以《风波》为题写到辫子的象征意义。在五四运动时,辜鸿铭关于身后的辫子与思想上无形的辫子的言论广为流传。在民间,皇帝遥远而抽象,大家对朝廷没有什么切身的感觉,但头上的辫子很近随时可以触摸,故而成为对头身份的文化认同。小说中的剃头匠胆小,遇事即吓得流眼泪,只想天下太平子承父业,但当世道变化,官逼民反仍会被动地积极起来,挥舞手中的剃头刀,以非常个人的方式参与历史:
黎元洪想了想,显得有些无奈,然后说:“那……辫子就剪掉吧。”他说着,看了看刚进屋的我和父亲。我父亲能亲眼见到大官,便很高兴,他上前叩拜黎元洪,嘴上说:“给黎都督叩头。”蒋翊武一把扯起他来,说:“革命了,不兴叩头。”邓玉麟笑道:“请你来不是给黎都督磕头的,而是替都督剪辫子的。”我父亲便高兴地说:“哎!这两天我已经不晓得剪了多少个人头。”我知父亲紧张,说错了,便故意吓唬他说:“你现在胆子变大了,都敢剪人头了?”我父亲吓了一跳,双膝一软,又要往下跪,嘴上说:“不不不,是剪辫子,剪辫子。”蒋翊武再一次扯住他,说:“你再下跪,就得剪掉你的头了。’
大家皆笑,连黎元洪也忍不住笑了。父亲上前替黎元洪剪掉辫子,又细心地为他刮顶,完后递上镜子,黎元洪左看右看,自语道:“原来没有辫子是这个样子。”
剃头匠以剪辫子,赵裁缝以缝旗帜,“我”、吴四贵、赵师梅则以送信、张贴布告的方式参与见证了革命,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参与革命、进入历史。正如鲁迅所言“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②方方正是从“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入手叙述革命,让革命从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地方走下来与众生紧密相连。
《民的1911》以儿童视角展现父辈剃头匠、赵裁缝、吴麻子和他们的子辈如何由惧怕动荡的普通百姓受到知识分子感染进而亲近并参与革命的过程。辛亥革命由这些虚构的普通市民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共同完成,革命的成功不只是流血牺牲,还有民心向背,需要广大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进去。历史从来不是知识分子的独奏,革命是社会各个层面的大合唱。这是小说家方方对历史丰富性的想象。
《武昌城》以1927年前后武昌战役为题材,小说无意于书写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而是致力于表达攻城、守城时的人情、人性,表达比战争本身更持久、更广阔的生活,对北洋军阀和学生双方叙述者都试图理解,拨开阶级、政治的面纱还原一群立体、活生生的个人,改写一向对于革命虚假的浪漫主义想象。人物始终是方方揣摩的核心。在具体的历史转折关头,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有更敏锐的前瞻和更大的担当,家国情怀这一最宝贵的文化传统会率先让知识分子激动并辐射到全社会,但这个群体并不能因此而被固化地想象。知识分子的信仰、舍生取义的豪情与怯弱、自私和无力感相互胶着。方方摈弃了宏大叙事关于革命、战争的造作想象,而是以重大历史拐点为契机重新呈现出知识分子群体的丰富性、局限性及其与百姓之间的互动。
《民的1911》和《武昌城》是对历史和故乡大地的深情,不溢美、不调侃,立体打量历史,书写生活的庄与谐。作家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让史实像风筝的线一样牢牢地拽在手中,想象的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也不离开视线。官与民、国与家、战争与和平都是宏大的命题,方方将大的思考融进具体的人物命运,哪怕是小孩、哪怕是草民,也在历史的浪潮之中,这是人与时代的关系,也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方方近年的创作显示了这一代作家强劲的生命力、理解力和交流愿望,青少年时期经受的历史动荡与磨难转变成财富反馈给文学,为他们提供持久的写作内驱力和广阔的叙事资源。几十年的写作历险让她的作品慢慢有了一种沧桑感和开阔性:对当下的书写使她敏锐于时代的变,对历史的书写让她执着于人性的常,这两翼让方方不断思索常与变的辩证与博弈。时代的浪花与历史的回身共同谱写出方方的交响曲,我们能够从中聆听民族精神的旋律。
【注释】
①[美]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9页。
②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7-238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课题“文化消费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研究”(12YJC75106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