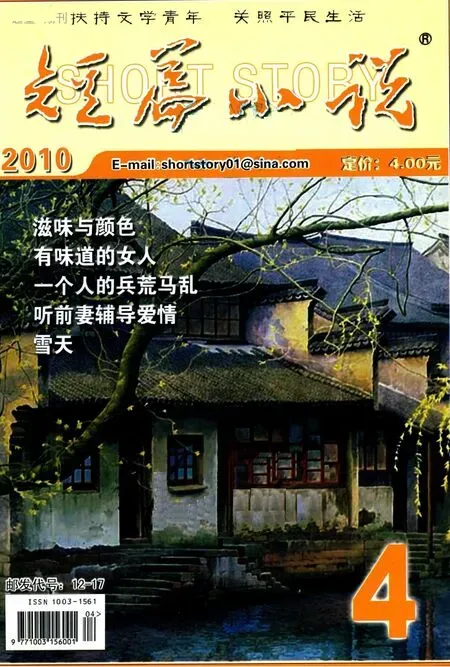乡土文学视野下的《不死的核桃树》
2014-07-14曾绍玮
曾绍玮
乡土文学视野下的《不死的核桃树》
曾绍玮
乡土小说占据着中国现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从鲁迅创作的一系列以浙东的故乡为时代背景的文学作品开始,乡土文学就正式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一方面,早期的乡土文学作家主要是精英知识分子,当他们接受了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之后,习惯于用现代文明的思考方式去审视中国的乡土社会,流露出强烈的批判色彩。正如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评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精英知识分子笔下的中国乡土世界笼罩在不幸的阴霾之下,令人无法产生快乐的情愫;另一方面,进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延续传统乡土小说创作模式的作家们进行了新的尝试,汪曾祺等乡土作家、乡土作家创作的作品展现了乡土世界中别样的风情,不仅有耳目一新之感,更让读者产生了重新认识中国乡土世界的冲动。
一、新时期乡土小说的新面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门打开之后出现在中国人视野之前的不仅是新的面孔、新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文化思潮大量被译介到国内。“伴随着 ‘文化热’的兴起,探索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选择与出路等一系列的课题就摆在了国人的面前。这些课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西方文化的横向比较,一是传统文化的纵向的自我认知,二者共同指向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与重建。”[1]对于中国文学界而言,从孕育自我身躯的家乡、从基于自己生活希望的故土去寻找精神的源头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如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等。
笔者认为作家卢海娟创作的小说《不死的核桃树》是世纪之交的文坛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意义的乡土文学作品,围绕着老高太太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展现的正是长久以来被遗忘的社会最真实的一面。当小说的主人公回到阔别已久的小山村时,她的到来并没有给山里人太多的意外。相反,母亲的一句话勾起了隐藏在她头脑深处的一段被忘却了的历史。
母亲说,她和父亲刚刚去了老高太太那里:“唉,她不知道还等什么,那口气就是咽不下。”
老高太太?叶秀文不觉脊背一凛——她可是村子里的活神仙,年龄最大不说,她还是村子里最有资格的萨满,不过这是文明世界的叫法,村里人只知道老高太太是 “领仙的”,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找她瞧过病摆过事,叶秀文也不例外。
老高太太的身份在村里人的口中是 “领仙的”,他们曾经在这位似乎具有神奇能力的 “活神仙”手中“瞧过病摆过事”。她的存在意味着一段古老的历史在现实社会的存续,也展现了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如何理解孕育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于作者而言,长期的城市生活必然对于她的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为直接的一点在于她能够从故乡的生活中提取到被他人忽视的信息。自己虽然不再相信老高太太具有神奇能力的说法,但她却能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位老太太所代表的文化意味。
这一点正是乡土文学自其诞生以来就展现出的重要价值之一,它重新认识了我们的乡村生活。在鲁迅的时代,作家们是努力发现乡村生活的落后和凋敝,试图拯救这片失去了生命活力的世界。进入到新时期之后,作家们却从久远的乡村发现了被人们遗忘的精神财富。正如评论家在界定汪曾祺的创作时指出的:“乡土文学的发端,似可追寻到发表于80年代初的汪曾祺的小说,他的小说在当时别具一格,清新悦人,无论题材、人物还是叙事方式、情感格调,都与当时风头正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拉开距离,显示出‘陌生化’的效果。”[2]
这里所谓的 “陌生化”并非转换了考察的对象,而是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去认识养育了我们的乡村社会。老高太太曾经被视为 “领仙的”,在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主人公看来,她却是 “村子里最有资格的萨满”。同样的事物,不同的称呼展现的是不同的价值观,新时期乡土文学正是以全新的价值观去考察中国乡村社会的风土人情,作者没有在小说文本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塑造方面花费太多的精力,而是将更多的审美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新时期的乡土小说并不是将寻找到某种物质性存在作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更多的是努力追索人们的思维方式带给现代人的思维冲击,并试图通过一定的方式重构适合现代人的精神性存在。
二、鲜明的地域色彩
小说《不死的核桃树》的作者所选取的故事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我们很难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找寻到萨满教的痕迹。地域正是造就乡土文学最为重要的土壤,我们能够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感受到陕北风情的“秦腔”、在莫言的笔下看到火红的 “红高粱”,都是缘于作者对于地域文化的准确把握。正如丹纳所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都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3]当地域文化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并最终成为主宰其作品灵魂的精神核心时,我们就可以将其界定为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乡土文学。
它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白山黑水之间,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信奉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在原始先民们的生活中,当他们遭遇到各种形式的困扰和麻烦无法解决时,往往将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以及解决问题的答案寄托在每一个部落或每一个村落的萨满身上。在他们看来,萨满身上具有沟通人与神之间联系的特殊能力,通过他们的帮助,将为自己的生存提供巨大的力量。在主人公童年的记忆深处,有一段关于老高太太给自己请仙的记忆。
老高太太那时满头银发,脸上皱纹密布,像冬天里干净的核桃。母亲简单说明了来意,老高太太细声应答,一会儿,她苍老干瘦的身体便钟摆一样左右摇摆起来,接着低垂的脑袋也开始慢慢摇动,火盆里此时再度发出轻响,有的核桃冒出一股细烟来,老高太太伸手把核桃拿出来,只见核桃很夸张地咧开了嘴,用手轻轻一掰,就化作两半。老高太太从腰间拔出一根针来,抠出细白的核桃仁就往叶秀文的嘴里送。想起她刚刚吐的唾沫,叶秀文急忙躲开,老高太太佯嗔地撇了撇嘴,口里说:“这孩子。”然后手忙脚乱地把冒烟的核桃拿出来,放到身边看不出颜色的炕上。
这是一段关于萨满如何驱鬼的真实记录,但视角不是学科化、理论化的学术角度,而是从儿童的角度来追述自己所不理解的一切。在这位满头银发的萨满手中,唯一的工具就是干净的核桃以及一根银针,看似简单的工具却可以发挥出主人公所无法想象的巨大的力量。当成年后的主人公再次回忆起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幕时,更多的选择了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审视这一切,而不是选择接受老高太太的神力。在主人公的讲述中,读者看到了世代生活在白山黑水的人们是如何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苦难的。他们从内心深处释放出对于自然的敬畏,与生活在其他地域的人们在面对现实的方式上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
三、民族之根的寻找
当生活在红尘俗世的人们被物欲的洪流所裹挟时,他们更多地沉沦于物质世界的追逐中,这是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很理性的选择。但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并不完全按照所谓的逻辑思维去安排自己的行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就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能够在被人们所忽视的现实存在中找寻到属于自己民族的灵魂所在。小说《不死的核桃树》正是作者面对逐渐消失的文化之根不断思索的产物,在她的笔下活跃的老高太太永远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近乎于成为这个区域中文化精髓的代表。
中国文坛对于民族之根的寻找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在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的时代背景下崛起的思考。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 “文学思潮”。“作为文学思潮的‘文化乡土’,是这个民族近代以来在东西方文化大冲撞大交汇的时代背景中所孕育的历史母题在这个时代的延续。她以文学的形式参与了东西方文化价值的取抉,这正是这个时代民族文化重建与更新的重要途径。”[4]在小说主人公的身上,读者可以很清楚地找寻到属于西方文化的痕迹。她在外面的世界生活、工作,彻底改变了自己曾经的社会定位,成为一个拥有着光鲜、靓丽外表的城市人。在主人公的头脑中,对于人生的看法以及如何面对世界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她看来,村里人抢夺核桃树枝的做法显得有些不可理解。但她没有反对身边的人做出任何举动,甚至还化身成为评判村里人行为对错的评价者。
当她认真考察了自己的故乡之后,才最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仅仅是现代文明社会在乡村世界的延续。她已经与孕育了自己的传统社会彻底地割断了联系,这使得主人公在自己的头脑中产生了浓厚的忧患意识。新时期的乡土小说正在以积极的姿态考量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当中国人逐渐遗忘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时,某些人试图以文学的方式让即将在乡土世界中消失了的精神产物以特殊的方式留存下来。但作者毕竟不是老高太太一般的萨满,她的记述与真实的存在保持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民族之根的寻找将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我们不可能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某一部文学作品或某几位作家的身上。
当一位老高太太逝去之后,她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彻底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再也无法通过任何手段将其找寻回来,曾经的汪曾祺和今日的作家们所能够做的仅仅是在自己的笔下描绘曾经的世界,让后世的读者通过小说等艺术形式与我们共同的精神祖先获得心灵的沟通。乡土将是所有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中无法逃避的历史使命,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全部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财富,最终留给我们的就只有记忆的碎片而已。
[1]张朴.新时期乡土文学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1.
[2]王铁仙.新时期文学二十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81.
[3]丹纳.艺术哲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1.
[4]季红真.忧郁的灵魂[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65.
曾绍玮(1971— ),男,重庆人,硕士在读,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信息化、数字校园、现代教育技术、影视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