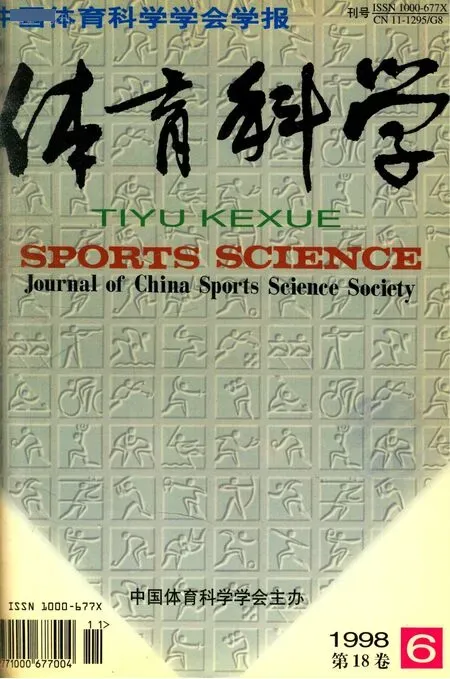国际体育仲裁中“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探讨
——兼谈未来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选择
2014-07-12熊瑛子
熊瑛子
国际体育仲裁中“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探讨
——兼谈未来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选择
熊瑛子
对体育内部事项不予审查的体育仲裁法理在具体实践中存在内涵不明晰、范围难界定等问题。建议采用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这一表述,并将审查豁免事项明确为裁判判罚决定、裁判结果决定、技术性测量决定三类;摒弃原则例外中“恶意”、“专断”等含糊的措辞,从裁判责任的分层化和裁判行为的不同性质确定原则适用的例外;借鉴各国体育法规和体育行会章程的做法,将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以成文法的形式写入国际体育仲裁的相关规则中。中国应当组建独立的国内体育仲裁制度,在未来中国体育仲裁规则中,应当对“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的具体内容进行规定。
体育性争议;裁判判罚;体育仲裁;中国
1 引言
马特·林德兰德(Matt.Lindland)是美国古典式摔跤76 kg级运动员。2000年悉尼奥运会美国国内选拔赛上,他输给了对手希拉奇(Sieracki),而他认为是裁判的判罚不公正导致他输掉了比赛。他向美国摔跤协会提出的申诉被驳回后,又向美国仲裁协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宣布比赛结果无效。仲裁员审理后做出支持运动员请求的裁决,并要求重赛一场。重赛中林德兰德获得胜利,而希拉奇对此不服,先后采取了仲裁和诉讼等法律手段。案件辗转经过美国地区法院、巡回法院及最高法院,最终,林德兰德胜诉并代表美国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一枚银牌[1]。林德兰德案件之后,关于体育内部事项能否仲裁的问题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它实质上体现了体育自治和司法干预的博弈关系。然而,学理界对这一原则的研究十分薄弱,仲裁实践中对这一原则的适用也存在诸多不足。
2 现有理论和实践之不足
从传统理论的角度来看,体育运动不应经常受到当事人向法院或仲裁庭提起的上诉打扰[3]。因此,体育学说和司法实践一直认为,法官或仲裁机构不能对严肃的体育内部事项行使管辖权。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的仲裁程序规则中对这一原则并无明文规定,而是通过“准普通法方法”,在相关案件裁决书中做了一些零星的规定。这些规定存在表述不规范、内涵不明晰、范畴难界定等问题。
2.1 表述混乱
学理界对体育内部事项不予审查原则有着多样化的表达。杰克·洛克尼尔(R.Jake Locklear)称之为“赛场判罚(field of play decision)不予审查原则”[23],米歇尔·贝洛夫(Michael.Beloff)称为“体育事项司法拒绝(judicial self-restraint in sporting matters)原则”[20],罗伯特·齐格曼(Robert Seikmann)称为“裁判规则(Lex Ludica)不予审查原则”[24]。一些中国学者称之为“技术性事项不干涉原则”[3]、“赛场判罚不予审查原则”[8]等。
除此之外,这一原则的表述在CAS的仲裁实践中也处于模糊地带。仲裁庭在不同案件的裁决书中使用了不同的措辞,如2002年OG02/007案件中称为“纯粹技术性赛场决定(purely technical field of play decision)不予审查”,2004/A/727案件中称为“竞赛规则决议(field of competition decision)不予审查”,2000年OG00/012案件中称为“技术性决议(technical decision)不予审查”。以上措辞均表达了体育内部事项不受审查的含义,但侧重点和范畴各有不同,笔者偏向于选择“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这一表述,并将在文章的3.1部分说明理由。
2.2 适用方式隐晦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墨西哥竞走运动员本拉多·色古拉(Bernardo Segura)在比赛结束后不久,被告知因为在比赛中出现了3次犯规被取消成绩,收回金牌。于是,他以国际田径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IAAF)为被申请人向CAS提出仲裁申请[16]。仲裁庭审理后认定:对赛场官员、裁判员等依据“赛场规则”做出的裁决不予审查,除非存在不法行为,如受贿等。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金圣东案件[17],引用了色古拉案件的裁决:“如OG00/13案件,仲裁庭对涉及裁判判罚的争议不予审查,除非申请人提出裁判偏私的直接证据。”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巴西马拉松运动员因场内安保工作的失误错失金牌,他向CAS上诉要求再授予一枚金牌[18]。仲裁庭在审理中引用了金圣东案件,并表示金圣东案件中提到对赛场判罚予以审查的前提是裁判恶意做出裁决,申请人需要提供直接证据。除此之外,金圣东案件还被2008/O/1483亚洲手球俱乐部诉国际手球联合会案,2001/A/354爱尔兰曲棍球协会诉国际曲棍球联合会案所引用。
上文所述体现了CAS适用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中的“准普通法”方法,即允许审查,但存在不推翻裁判决定的仲裁先例[1],以保证仲裁对体育内部事项的尊重。但由于CAS仲裁中先例的作用是不确定和任意的,仲裁庭引用先例的行为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只是仿效普通法的方法,将先例列入准法律渊源之内。因此,这种适用方式可以称为“准普通法”方法。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松散地存在于仲裁庭已裁的案件中,仲裁员只能隐晦地从其笼统的描述中考量该原则适用的标准。从上文案例裁决书对原则例外的表述来看,由色古拉案件的“不法行为,如受贿”,扩展到金圣东案件的“偏私”和“直接证据”,以及之后案例中的“恶意”等,该原则适用方式的隐晦性导致仲裁员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原则朝规范化、统一化方向发展。
2.3 范围不确定
2000年9月23日悉尼奥运会女子单人小划桨比赛中,根据官方认定的斯沃琪拍照计时器显示,白俄罗斯运动员卡斯滕(Karsten)以7∶28.141的成绩获得冠军,保加利亚运动员内科娃(Neykova)以7∶28.153的成绩屈居第二。第二天,保加利亚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Bulgarian Olympic Committee,BOC)主席写信给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和国际赛艇联合会(International Rowing Federation,FISA),声称在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七频道播出的视频资料可证明,该场比赛中保加利亚运动员先到达终点,应该获得该项目的冠军。FISA回信称,斯沃琪拍照式计时器是目前最先进的计时工具,它拥有计时触动感应系统,可精确计量比赛中运动员到达终点的细微时差。运动员对FISA的解释不服,以IOC和FISA为被申请方,向CAS提出上诉仲裁申请。仲裁庭审理后认为,本案涉及赛场计时工具的准确性问题,属于体育内部的技术性事项,不予审查,于是裁定驳回申请[15]。
2008年北京奥运会手球项目预选赛上,哈萨克斯坦男队和科威特女队分别击败日本队和韩国队,但赛后韩、日手球协会指出,两场比赛的主裁不具有国际手球联合会(International Handball Federation,IHF)颁发的资质认定证书,并在比赛中有所偏袒,甚而怀疑亚洲手球联合会(Asia Handball Federation,AHF)也存在操纵比赛之嫌。IHF召开内部会议,决定取消比赛结果,择日重赛。由于哈萨克斯坦和科威特手球队不满要求重赛的决议,重赛只有日本队和韩国队两支队伍参加。最终,日本男队和女队均战胜韩国队,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AHF携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国家手球协会向CAS提出仲裁申请,要求CAS宣布IHF所做决议无效,并请求确认原比赛结果合法有效。CAS审理后认为,该案仲裁庭审查的对象并非赛场裁判的判罚,而是基于一系列数据和证据做出的比赛是否合法有效,是否需要重赛的裁判。仲裁庭最后做出裁决:宣布IHF决议无效,并根据具体情况,维持女队的原比赛结果,否定女队的重赛结果;维持男队的重赛结果,否定男队的原比赛结果[19]。
以上案例均涉及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的适用范围。案例一是竞技比赛中常遇到的比赛器械是否符合规定的问题,它成为影响比赛结果和运动员申诉的重灾区,关于器械精准度的争议是否应和裁判判罚一样被纳入,成为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的外部范围问题。案例二涉及仲裁庭对审查对象是否属于体育性争议而进行的判断。裁判在一场比赛中的某一项判罚可引发体育性争议,而一场比赛中裁判的整体表现是否构成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的对象,涉及该原则的内部范围问题。因此,原则本身外部范围和内部范围的不确定,导致仲裁员对部分争议应当审查与否的标准是模糊的,不利于原则的长远发展。
2.4 内涵不清晰
金圣冬是韩国一名速滑运动员,他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男子1 500 m速滑决赛中一路领先,但由于出现了一次“横道违规”(improperly crossing),被裁判取消比赛成绩,金牌由原本第2名的美国运动员获得。事后,韩国奥林匹克委员会(Korea Olympic Committee,KOC)认为裁判偏私,以国际滑冰联盟(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ISU)为被申请人向CAS提出仲裁申请[17]。CAS在审理中发现,该争议涉及“赛场裁判事项(field of play decision)”,依据色古拉案件的先例,予以驳回。在该案的裁决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仲裁中遵循赛场判罚不予审查原则的例外中,有些词语是教人迷惑的,例如,专断(arbitrary)、恶意(bad faith)、渎职(breach of duty)、不当行为(committed a wrong)等,有时候这些词语也可以被蓄意(malicious intent)、其他可诉的不当行为(other actionable wrongs)所取代。加之,专断(arbitrary)等词语的含义本身也是模糊的,我们只能对它做一般化和通识意义上的理解。”
上述案例表明,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的内涵表达存在诸多模糊之处,给CAS仲裁实践带来不便。专断、蓄意、偏私等词语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什么行为构成专断、怎样证明专断,不同的人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用这些本意模糊的词语来说明这一原则,使仲裁员在具体案件实践中无从把握,对审查与否等问题难以界定,不利于维护运动员基本权益和尊重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自治权。
综上所述,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的理论构建和实际适用均存在问题。在对其进行探讨时,应首先选择合适的术语,梳理出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的基本范畴,再针对该原则的含义和范围,概括出其内涵及例外。
3 改进的思路
3.1 原则之表述
根据上文学理界对术语的选择,可归纳为三种观点:其一,赛场判罚不予审查;其二,比赛规则相关判罚不予审查;其三,广义上的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以上三种观点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不予审查范畴的界定。笔者认为,应采用第三种观点“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为宜。其一,“赛场判罚不予审查原则”的表述不能涵括上文2.3案例一中技术性器械引发争议的情形。对比赛器械、计时工具精准度的争议也涉及体育联合会内部章程和规则的适用,具有高度专业性,理应和赛场判罚一起纳入原则不予审查的范围,而“赛场判罚”的表述漏掉了这个部分。其二,“比赛规则相关判罚不予审查原则”的表述过于笼统、不够全面。比赛规则是具体运动项目中判断运动员犯规或得分的基本规范,而裁判在实际操作中还需参考大量其他文本,依据多年从业经验才能做出正确判断。因此,只规定和适用比赛规则相关的争议不予审查的表述是不全面的。其三,“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的表述范畴适中,较为恰当。一方面,该原则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体育内部管理机构的专业决议权,体育性争议可涵括涉及体育内部管理的一切事项,包括赛场判罚、技术器械等;另一方面,体育性争议的概念也可随仲裁实践的逐步发展有所增减,根据具体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灵活加以调试。
目前,学理界尚无对体育性争议(sporting matter)的准确定义,但查找相关文献可知,与该概念类似的表述是存在的,如福斯特(Foster)提出的Lex Ludica[24],指具体项目的比赛规则和运动员体育道德;齐格曼(Siekmann)提出的“体育法的硬核”(Hard Corn of Sport Law)[24],即CAS的法官造法和比赛细则。上述概念为厘清“体育性争议”的含义提供了指导。笔者认为,本文中提到的竞技运动中的“体育性争议”,是指与具体运动项目的规则相关,依据现场比赛中出现的特殊情形,由裁判或赛场官员等专业人士作出的即时性判断,包括裁判判罚、比赛器械调整、计时打分等环节所引发的争议。下文将分述体育性争议的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与具体竞技规则相关。这是判断体育性争议的首要条件。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例,一共有26个大项,38个分项,300余个小项被列入项目名册,五花八门的运动项目都有具体的竞技比赛规则,包括对得分、犯规、比赛结果的判断等。这些事项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应当被列入体育性争议的范畴。
第二,主体的专业性判断。CAS OG02/007案件中,仲裁庭对体育性争议的主体做了判定,即负责将规则适用于具体比赛项目的专业人士,称谓如裁判员(judges)、裁判(referees)、裁定者(umpires)或赛场官员等[17]。在体育运动中,抽象的体育规则需要在实际比赛过程中转变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和具有约束力的裁决,而裁判员在这项转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常是保证竞赛规则实际落实的中坚力量。除此之外,还有负责比赛器械和计时工具准确性的现场官员也应包括在内。裁判员和器械官员对具体比赛的规则具备专业性知识,只有他们做出的判断才可能构成体育性争议。
第三,决定作出的即时性。这是对体育性争议的时间要求。裁判员或器械官员在比赛进行中所作出的判断才能构成体育性争议。当然,在比赛前对器械进行调整和确认的决议也应被纳入比赛进行中的范畴。
另外,涉及兴奋剂的争议原本属于典型的体育性争议,但由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13.2.1条规定:“国际性比赛的参赛资格争议,或涉及国际性水准的运动员的兴奋剂处罚决议,只可上诉至CAS,并组成仲裁庭依据相关规则做出终局性裁决。”由于CAS对兴奋剂处罚不服的案件拥有全面审查权,不受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的拘束,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畴。
3.2 “体育性争议”的基本范围和类型
目前,依据CAS仲裁实践中出现的情形,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的范畴应当包括裁判适用规则作出的判罚决定,裁判依据规则对比赛结果的评价和官员对技术性器械的测量三个部分。
其一,裁判判罚决定,即裁判依据各项运动的固有规则在比赛中作出的运动员犯规动作的处罚,多见于对抗性运动中,如拳击、柔道、足球等,如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法国拳击运动员麦迪因为击打对手腰部以下位置被裁判认定犯规,他事后对该处罚不服,要求仲裁庭回看比赛录像判断自己并未击中对方腰部以下部位,仲裁庭审理后认为该案涉及体育性争议,裁定驳回申请[3]。
其二,裁判结果决定,多出现于比赛结果倚赖于裁判主观判断的项目,如体操、花样游泳、跳水等。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梁泰勇代表韩国队在男子体操全能赛自由体操比赛中发挥出色,但由于裁判漏加起评分导致和金牌失之交臂。韩国奥委会向CAS提出仲裁申请,最终仲裁庭认定裁判对运动员的主观打分属于体育性事项,裁定不予审查[16]。
其三,技术性测量决定,多出现于需要借助器械进行比赛的项目中,如帆船、皮划艇等。如上文2.3案例中,运动员对比赛计时工具准确性的争议理应属于体育性争议,因为它们同样涉及体育内部规则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应当由IF或其委托的机构做出终局认定。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丹麦队由于船只临时桅杆折断,借用没有进入决赛的克罗地亚队的船只参加比赛,并获得冠军。该替代性器械在事后得到了丈量委员会的追认。而比赛中获得第2名的西班牙队向CAS提出仲裁申请,认为替代器械给丹麦队带来了不正当竞争优势。仲裁庭审理后认定,该请求属于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的范围[5]。
此外,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还应涵括上文2.5案例中出现的情形。该案例涉及对裁判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和整场比赛执裁情况的考察。笔者认为,依据《奥林匹克宪章》对单项体育联合会职能的定位,它应当具备专属管理具体运动项目的权力,包括奥运会选拔赛中裁判的选择、资质认定等,重赛决议的做出只要符合程序正义,仲裁庭应不予干涉。一位裁判在一场比赛中整体的执裁表现,和他所作的某一项判罚一样,应当排除出仲裁庭可审查的范围。
3.3 不予审查原则之“例外”
上文2.2提到的色古拉案件中,仲裁庭对“体育性事项不予审查原则”这样描述:评判员、裁判等依据“赛场规则”做出的裁决不应当审查,除非适用此类规则时存在不法行为,如受贿。其中原则例外的描述是以“不法行为”这一宽泛性词语做兜底,并举“受贿”为例。这种表述易使处理案件的仲裁员产生如下疑惑:如何判断裁判是否构成不法行为?只有受贿的裁判才需要受到审查吗?不法行为的标准是违反国家层面的刑事法律?民事法律?还是构成体育内部纪律处罚即可?
这些问题在之后金圣东案件中也有出现。于是,仲裁庭自行将“不法行为”细分为专断(arbitrary)、恶意(bad faith)、渎职(breach of duty)、蓄意(malicious intent)和其他可诉的不当行为(other actionable wrongs),并要求申请人提供直接证据。这似乎是“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在实践中的发展。然而,仲裁庭面对描述更具体的不法行为又提出了新的难题:专断、恶意等词语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如何寻找构成裁判专断、恶意的直接证据?裁判的不当行为是否应当达到国内刑法中“犯罪”的标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仲裁实践中,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例外的措辞是不明确的。首先,专断、恶意等词语是日常用语,相较法律用语来说缺乏严谨性和专业性,仲裁员难以把握其界限;其次,该类词语自身含义不明确,如专断和果断、渎职和勤勉在本质上存在哪些区别也不甚清晰,不仅使仲裁实践缺乏具体可操作性,也加大了申请人提出相关证据的难度;再次,专断、恶意、渎职、蓄意等词语之间存在部分重叠或递进的关系,不能涵括原则例外应描述的所有情形,不利于该原则朝规范化方向发展。
因此,笔者建议,鉴于对原则例外描述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尝试换一种思路,即不用列举的方式描述原则的例外,而通过对裁判责任的层次化分析和事实、规范的理论化分类来确定构成原则例外的情形。
3.3.1 裁判责任层次化
裁判应为在比赛中的错判行为承担责任,而裁判的责任按递进关系可分为道德责任、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三类[14]。道德责任是指裁判的行为符合相关规则规定,但没有做到裁判手册上要求的“勤勉、恪尽职守”等义务而承担的责任。纪律责任是指裁判违反了相关体育协会的执裁标准,应当承担该体育管理机构包括禁裁在内的处罚,这类责任由体育协会内部章程来规定。法律责任是指当裁判的行为违反国内法时,应当受到的惩处,按照违反部门法的不同可分为合同责任、侵权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几类。
从上诉裁判责任的分类可得知,从裁判的道德责任到纪律责任再到法律责任逐渐加重,法律责任中从民法到行政法到刑法,裁判受到追究的可能性和力度也逐渐加重。由此,可以设想,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可否借助裁判责任的层次化,得出更为明晰的适用?
其一,裁判的道德责任不在例外之列。裁判在比赛中应当恪尽职守,但当他按照相关规定完成了执裁任务,任何人就不应对裁判的判罚结果提出质疑。这构成裁判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部分,仲裁机构也应绝对不予审查。
其二,裁判较重的纪律责任在例外之列。对于裁判构成纪律责任的情形,应当一分为二来看待。体育协会等管理机构对裁判的处罚包括警告、记过、禁裁等。对于禁裁这类较为严重的处罚,申请人可提出要求审理裁判判罚的请求,仲裁庭应将该争议视为原则的例外,并进行审理。如上文3.2提到的梁泰勇案件,由于2名裁判漏加了起评分,裁判委员会暂时停止了他们的执裁资格,对于这种情形,应做为裁判受到较重纪律处罚的证据,作为原则的例外加以处理。
其三,裁判的法律责任中刑事责任和部分民事责任应构成原则的例外。裁判的刑事责任如受贿、操纵比赛、枉法裁判等理应受到追究。这种情况下,仲裁庭可跳出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的束缚,还受到牵连的运动员以公正。另外,部分民事责任如裁判违反合同的默示义务、歧视一方当事人等也可构成该原则的例外。
裁判责任分层化更清晰地表现出裁判在比赛中的主观过错程度,通过这类分析方法来确定构成原则不予审查的例外有其优越性。首先,裁判责任较之“专断”、“恶意”等词语更具确定性,仲裁员更容易区分和把握;其次,裁判责任分层化给申请人寻找相关证据提供了便利,申请人只需从裁判是否受到内部纪律处分或受到相关国家法律追溯着手,向仲裁庭提出证据和主张。
3.3.2 事实、规范分类化
所谓事实、规范分类化方法,是指将裁判的错判行为分为事实判断错误和规则运用错误两大类。前者是裁判在比赛现场由于所处角度、视觉限制、比赛快速性推进等原因对比赛的事实情况造成误解而发生的误判;后者是指裁判因为错误理解或运用比赛规则而发生的误判。2005年足球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比赛中,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巴林,上半场第39分钟乌队赢得一个点球,主裁吉田寿光以乌队队员提前进入禁区为由,宣布进球无效,并示意由巴林队主罚间接任意球。而国际足联新规则第14章第3款中规定:“当点球主踢队员的同队队员提前进入罚球禁区或距点球点不足9.15 m时,如球入球门,应该重踢;如果球未进入球门,则应由守方队员踢间接任意球。”很明显,裁判吉田寿光搞混了规则。国际足联最终裁定,主裁判确实犯了严重技术性失误,比赛结果无效,两队须择日重赛[4]。
裁判在事实或规则这两类误判中,存在明显的主观意识差异。事实误判通常是由于裁判站立角度、视觉遮掩或比赛场地的限制等造成的,对于这类失误,是体育比赛中不可避免的,仲裁机构不应予以干预。而裁判对规则的错误适用,无论其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均违背了裁判在比赛中的主要职能——将规则恰当地转化到具体体育比赛中,应当被列入原则审查的例外。如吉田寿光的颠覆性误判是应当受到审查的,才能使利益受损一方运动队的权益得到体育管理机构和仲裁庭的双重保障。
事实、规范分类化对于厘清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及其例外有重要作用。仲裁庭可将争议判罚区分对待:对事实部分的维护有利于保持裁判的赛场权威性,对规则部分的审查有利于监督裁判更好的行使职权。同时,该区分性规定限制了申请人将体育比赛中大量的事实性争议提交仲裁庭的可能性,促进整个仲裁实践朝规范化方向发展。
另外,也可借鉴美国体育法中的“职权豁免理论(qualified immunity)”来判断是否应当审理裁判行为的问题[21]。该理论将有关行为分为两类:自由裁量行为(discretionary act)和执行行为(ministerial act)。前者是指和规则、计划、政策制定或颁行相关的,由裁判根据从业经验进行自由裁量的行为,享有司法豁免权,不应受到仲裁机构的审查;后者是指将已确定的规则运用于比赛场上的行为,这时候裁判只是将纸面规则转化为比赛中具体行为准则的“自动售货机”,这里纯粹的执行行为不享有司法豁免权,仲裁庭能够对其进行审查。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裁判责任的不同层次,还是裁判行为的不同性质分析,抑或是将比赛中的事实与规则问题分别看待,均可以成为厘清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例外的一条路径。笼统的恶意、专断、渎职等提法,不仅仲裁员无法准确把握审查与否的界限,申请人也难以找到构成原则例外的直接证据。
3.4 原则之成文化
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the United States Olympic Committee,USOC)在林德兰德案之后修改了章程:比赛中裁判的最后裁决视为赛场裁决(由裁判适用竞赛规则,自行独立做出的决断),赛场裁决不受审查,除非裁决是:1)裁判越权做出的;2)裁判基于舞弊、受贿、偏袒或其他不当行为做出的[22]。事实上否认了林德兰德案件中仲裁员推翻赛场裁判决定的做法。
除此之外,对于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很多国家的国内体育仲裁规则、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章程和《奥林匹克宪章》均有直接或间接的明文规定:
《日本体育仲裁机构体育仲裁规则》第2条(“本规则的适用”)规定:本规则适用于体育竞技及其运营中,对于竞技团体及其机构所做的决定(体育比赛中裁判做的裁判判罚除外),运动员等作为申请人,体育团体作为被申请人的体育仲裁申请案件……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章程中,如国际篮球联合会(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FIBA)章程第147条第7款:裁判组决定为最终决定,对其没有进一步的申诉权,包括向CAS申诉。
《奥林匹克宪章》第26条中规定“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对其所管辖的运动项目拥有独立和自治权力”;IHF细则第27条第1款中规定,IHF对男子和女子手球运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选拔赛享有独立的自治权。上述条文均可说明,IOC将具体运动项目管理的决定权交由IHF行使,尤其涉及体育性事项的判断,不应受到仲裁庭的审查。
笔者建议,CAS应将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及其例外以明文规定的方式纳入相关仲裁法典之中。其一,该原则是仲裁尊重体育自治的集中表现,CAS将其纳入法条,从行动上支持了体育管理机构的独立自治权力;其二,该原则的成文化将方便仲裁庭对具体案件的审理,CAS仲裁中先例裁决的作用是不稳定的,加之裁决书中对该原则不同的措辞和表述加大了具体适用中的难度;其三,现行《与体育运动有关的仲裁法典》第57条规定,仲裁庭拥有全面审查事实和规则的权力,可形成新决议取代原引起争议的决定。该条规定实质上体现了仲裁庭的全面审查权,而作为与之相对抗的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条款却没有明文规定,造成了仲裁中“审查对象和范围”的失衡。将体育性争议作为CAS全面审查原则的例外,并予明文规定,是促进仲裁朝中立、客观方向发展的重要途径。
4 对中国的启示
4.1 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可行性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领域的纠纷除当事人自行和解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实际中极少),依靠体育协会内部争议解决机构裁决,或申请体育行政部门处理[13]。第一种方式由于法官对体育技术性规则知之甚少,难以做出专业而权威的判断;第二种方式基于体育组织的内部裁判不具有终局性,不能阻止当事人继续向法院起诉或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第三种方式,由国家体育总局等行政单位直接处理大量体育投诉和纠纷的做法,不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体育争端解决机制与国际接轨的趋势日渐显著,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成为推进体育法制建设的重要举措。
首先,从法律依据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7]。这是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直接法律依据。另外,大量体育纠纷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所规定的仲裁适用范围,《仲裁法》作为全面调节我国仲裁关系的统一法典,是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基本法律依据[9]。
其次,从经验借鉴出发,国际体育仲裁院成立20余年来,逐渐发展成为独立高效处理体育争议的权威机构[12],为构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另外,美国在其国内仲裁协会(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AAA)之下设立的“奥林匹克纠纷仲裁小组”,英国设立的“体育纠纷解决委员会”,法国设立的隶属于国家奥委会的“体育仲裁委员会”,卢森堡依据《体育仲裁委员会规则》设立的专门体育仲裁机构,加拿大设立的“体育纠纷解决中心”,澳大利亚设立的“全国体育纠纷解决中心”,新西兰根据《体育与娱乐法》设立的“新西兰体育仲裁庭”,日本设立的“日本体育仲裁机构”,韩国设立的“韩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等[10],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再次,从实际需要出发,建立体育仲裁制度是及时处理体育专业性纠纷的必要途径。2005年11月,中国田径运动员孙英杰为了提出《反兴奋剂条例》中减免禁赛期的证据,向黑龙江五大连池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通过优势证明标准和自认规则,确认其体内出现违禁物质系他人陷害[11]。中国田联做出禁赛处罚时能否采纳法院的民事判决?如何平衡法院民事诉讼与兴奋剂听证中证明标准不一的矛盾?这些问题均为司法介入体育纠纷解决的固有障碍。因此,构建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对于发展体育事业意义重大。
4.2 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具体设想
中国体育仲裁制度设立的首要工作是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仲裁条例》(以下简称《体育仲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8条规定,仲裁和诉讼制度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颁布[6]。而《体育法》第33条规定,体育仲裁制度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组织立法。这是否构成上位法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立法法》提到的是国家基本的仲裁和诉讼制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涉及的是仲裁的基本法律制度。而这里讨论的是体育仲裁的具体程序规则,并非基本的国家仲裁法律制度,体育仲裁程序规则是特定行业内的特别规定,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组织起草更为妥当。
由于中国体育仲裁机构兼具民间性与体育行政管理性,建议邀请国家奥委会、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仲裁协会、中国法学会、各国内体育项目协会、体育与法律院校学者、专家共同参与起草。该条例将成为指导体育仲裁制度设立与运行的基本依据。《体育仲裁条例》的内容拟包括:总则、体育仲裁受案范围、体育仲裁协议、普通体育仲裁程序、特殊体育仲裁程序、涉外仲裁和附则等部分,并采用较为简洁的以条为单位的立法体例。
《体育仲裁条例》中设想的中国体育仲裁机构名称为“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英文名称为“Chinese Committee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简称CCAS。由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仲裁协会共同组建,其财政开支由上述机构各自负担1/3。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应是隶属于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不与任何体育行政部门挂钩,是拥有自己的章程、住所、必要财产的独立社团法人。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委员组成应当广泛吸纳体育界和法律界的专家,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决定体育仲裁员的聘任、解聘和除名;修改《体育仲裁条例》和相关体育仲裁委员会规程;以及在重大的体育比赛(如全运会)召开期间,设立临时体育仲裁庭等[2]。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设立体育仲裁员的任免标准。仲裁员的基本条件:具备国家司法从业资格,且在体育或仲裁领域从事法律实践工作三年以上。体育仲裁员可按照以下原则分配:1)1/4的仲裁员由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或国家体育总局提议的人员中选任;2)1/4的仲裁员由中国仲裁协会提议的人员中选任;3)1/4的仲裁员由国内各单项体育联合会提议的人员中选任;4)1/4的仲裁员由退役运动员或独立于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仲裁协会等机构的其他人员中选任。体育仲裁员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仲裁委员会应停止予以聘任:1)仲裁员构成犯罪或受到刑事追溯的;2)仲裁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收受当事人贿赂或违反《仲裁法》规定的其他情形的;3)仲裁员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审理案件,或不履行仲裁员职责的其他情形。
设想中的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的程序包括普通仲裁程序和特别仲裁程序两类。普通仲裁程序中受理案件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该协议可以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之后签订,仲裁庭拥有对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自裁管辖权;特别仲裁程序中受理案件的前提条件是单项体育协会章程中规定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专属管辖条款。此外,中国体育仲裁中申请与受理、仲裁庭组成、开庭与裁决、临时强制措施、执行与司法审查等具体程序设计,可参考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程序规则,并结合其他国家国内体育仲裁的具体程序规则,作出规定。
4.3 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的确立
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无疑是中国体育仲裁制度建立中一个重要议题,它涉及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体育仲裁与行业协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分工等问题。根据中国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厘清这一原则对建立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意义重大。
首先,应当对“体育性争议”进行中国化界定。“体育性争议”这一术语在中国体育仲裁的语境下,除包含上文3.2提出的竞技体育中裁判或官员做出的判罚决定、比赛结果决定和技术性测量决定外,还应包括由拟颁行的《体育仲裁条例》中规定的对体育组织内部机构、人员的选举、任职、组织流程等决议;对行政机关做出的有关体育问题的决定有异议或处分不服形成的体育行政争议;以及国际体育组织做出的决议等。这是因为国内体育仲裁机构隶属于《仲裁法》的统一规制内,对于涉及体育行政决议、体育组织决议和涉外机构决议不应予以审查。
其次,可以从裁判责任的性质角度来适用这一原则。国内比赛中裁判责任依然可以分为道德责任、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三种。申请人提出裁判严重违反纪律或法律责任的证据时,仲裁庭应视为构成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的例外,并予以审理。
再次,《体育仲裁条例》应将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纳入其中。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与用尽内部救济原则、保护运动员权益原则同等重要。建议以一个条文的形式规定于《体育仲裁条例》之“体育仲裁受案范围”部分,可表述为:“仲裁庭受理与竞技体育运动相关的一切争议,但涉及体育性争议,如裁判判罚决定、裁判结果决定和技术性测量决定或其他体育行政机构内部决议的不予审查。对裁判或比赛官员决议不服提出仲裁申请的,由申请人提供裁判或比赛官员违反刑事法律或严重违反内部纪律条例受到追溯的证据。”该条款划定了体育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也体现了仲裁庭对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的态度,并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体育性争议涵括的范围,最后还对“原则例外”由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做了清晰的规定。该条文的设计一方面传承了国际体育仲裁中一贯坚持的尊重体育自治的原则;另一方面,弥补了CAS仲裁庭适用这一原则的随意性,给未来中国体育仲裁实践提供了较为明晰的指导。
5 结语
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是仲裁庭尊重体育内部事务的集中表现。由于该原则本身的内涵不明晰,范畴难界定,仲裁员在具体适用中存在诸多不便。笔者建议:其一,选择体育性争议这一术语,界定其包含裁判判罚决定、裁判结果决定和技术性测量决定三部分;其二,从裁判责任的分层化中厘清原则的例外,必要时也可借鉴裁判“职业豁免”理论,只对执行行为予以审查;其三,学习体育单项联合会章程和各国体育仲裁规则中的做法,促进原则朝成文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其四,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具备法律依据、经验模式和实践需求,应当依据中国体育仲裁实践,厘清体育性争议的内涵,起草《体育仲裁条例》,将体育性争议不予审查原则以成文法形式纳入其中。
[1]郭树理.国际体育仲裁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409-411.
[2]郭树理.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设想[J].法治论丛,2004,(1):63-68.
[3]黄世席.奥林匹克赛事争议与仲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2-44.
[4]黄骁.细数历史经典改判,足坛呼吁实事求是[EB/OL].http://2010worldcup.163.com/10/0628/04/6A86JL3200052E97.html,2013-12-22.
[5]彭爽.从“奥运帆船案”看技术性事项不予审查原则[J].解放军进修学院学报,2011,(1):34-38.
[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3.
[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7.
[8]唐建志.论赛场判罚不予审查原则[D].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23-25.
[9]汤卫东.中国体育仲裁的程序构建探析[J].体育与科学,2009,30(2):31-34.
[10]王俊梅.新西兰体育仲裁制度探析[D].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29-31.
[11]熊瑛子.兴奋剂违禁处罚中“过罚相当”原则的适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7(4):36-40
[12]于善旭.国际体育仲裁制度与中国体育法治发展[J].体育科研,2012,33(6):12-14.
[13]于善旭,张剑,陈岩,等.建立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5,25(2):6-11.
[14]朱文英.裁判法律责任初探[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3):45-48.
[15]CASabitrationNCASOG00/012[EB/OL].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ites/CaseLaw/Shared%20Documents/OG%2000-012.pdf,2013-12-22.
[16]CASabitrationNCASOG00/013[EB/OL].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ites/CaseLaw/Shared%20Documents/OG%2000-013.pdf,2013-12-22.
[17]CASabitrationNCASOG02/007[EB/OL].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ites/CaseLaw/Shared%20Documents/OG%2002-007.pdf,2013-12-22.
[18]CASabitrationNCAS2004/A/727[EB/OL].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ites/CaseLaw/Shared%20Documents/727.pdf,2013-12-22.
[19]CASabitrationNCAS2008/O/1483[EB/OL].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ites/CaseLaw/Shared%20Documents/1483.pdf,2013-12-22.
[20]MICHAEL J BELOFF,TIM KERR,MARIE DEMETRIOU.Sports Law[M].London:Hart Publishing,1999:129-133.
[21]MITTEN,DAVIS,SMITH,etal.Sports Law and Regulation:Cases,Materials and Problems[M].New York:Wolters Kluwer,2013:912-913.
[22]PAULA PARRISH.Demand for USOC Arbitration Light[EB/OL].http://www.highbeam.com/doc/1G1-82414353.html,2013-12-22.
[23]R JAKE LOCKLEAR.Arbitration in Olympic Disputes:Should Arbitration Review the Field of Play Decisions of Officials Texas Review of Entertainment & Sports Law,2003,(4):199-209.
[24]ROBERT C R SEIKMANN.Lex Sportiva:What is Sport Law?[M].Hague:T.M.C.Asser Press,2012:12-15.
ResearchonthePrincipleof“DenialofJusticeinSportingMatter”—AndtheChoiceofChina’sFutureSportsArbitrationSystem
XIONG Ying-zi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application of the legal principle of non-reviewing of the field of play decisions.The author advice to adopt the term of principle of “denial of justice in sporting matter”,which makes it as 3 types:field of play decision,competition result decision and technical decision.The author also advice to get rid of the terms of “arbitral” and “bad faith” instead of responsibility of the referee.This principle is expected to be written in the sport related arbitration code.China should establish its own sport arbitration system,and there should be the specified principle of “denial of justice in sporting matter” in its arbitration rules.
sportingmatter;fieldofplaydecision;sportarbitration;China
2013-12-10;
:2014-04-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1CFX076)。
熊瑛子(1987- ),女,湖南湘潭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体育法学,E-mail:xiongyz312@gmail.com。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1000-677X(2014)06-0075-08
G80-0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