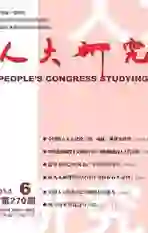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的“衡阳贿选省人大代表案”
2014-07-10李月军
李月军
作为民主化过程中的一种现象,贿选[1]与民主政治如影相随,几乎遍及世界政治的每个角落。不过,即便是在西方学术界对贿选的研究也很不系统,关于贿选的比较政治研究的系统知识更是惊人地缺乏,贿选仍然“是一个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黑匣子,对贿选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形式与含义、原因与结果,我们都知之甚少”[2]。国内学术界对于贿选的研究非常有限,集中在对村级选举方面,很少涉及贿选人大代表问题,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基本上还停留在描述与道德讨伐的浅层,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而官方的政治批判则是宣示多于分析,二者都没有从理论上深入分析贿选的发生与处理机制及其影响。发生在2012年底到2013年初的“湖南衡阳贿选省人大代表案”(以下简称“衡阳贿选案”),因其涉及众多人大代表和省、市、区县三级党政与人大机构,造成巨大官场地震,而震惊全国甚至世界。本文尝试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视角,深入分析衡阳贿选案涉案者的类型、行动、动机及其与制度之间的关联,以及案件的处理机制,阐释它对地方政治造成的全整性危机,反思地方政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并提出若干遏止贿选的可能性建议与地方政治结构改革的宏观指向。
一、案例选择与理论选择及其契合性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案例研究,可以选择多个案例,也可以选择单个案例为研究对象或样本。多案例与单案例研究的目的不同,也各有优长和不足。前者为了理解大量相似案例,或证明或证伪现有理论,而不是对单个案例进行精深研究。后者则相反,单个案例研究的优点不是验证理论,因为选择“关键”案例难以解决案例样本过少的问题[3]。当然,如果单个案例研究做得好,就可以使我们打开因果关系的匣子,找到结构性原因与被称为结果之间的中介因素。最理想的是,能让我们“看到”X与Y之间相互作用[4]。
本文之所以选择单案例,一方面是基于研究目的,即通过较为精致深入地分析研究单个贿选案例的机理与影响,而不是验证某个理论;另一方面,尽管多个案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但目前还没有获得多个相同案例,无法在统计学意义上确证相同的案例机制与影响,而可获得的若干相似案例又存在较大差异,可比较性不强,所以退而求其次,把重点放在对单个案例,适当辅之以其他相似案例来说明所要讨论的问题。另外,本文之所以选择“衡阳贿选案”作为分析样本,主要不是因为它的时效性和新闻性,而是因为它除具有贿选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如市一级人大代表几乎全部涉案,它不仅导致市级人大的全整性危机,而且还涉及省、市、区(县)三级党政与人大机关,引发了市、区(县)政权机构与人员上的大规模调整,映射出当下中国地方政治的结构性危机,其处理过程所呈现出来的机制,既说明了中国作为一个“政党-国家”的优势所在,更说明了地方政治在逻辑上的自洽性与实践中的自洽性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甚至冲突。简言之,无论是从“衡阳贿选案”涉案者的规模,还是从其影响和反映出的深层问题来说,都称得上是新中国成以来的“第一案”,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主题。如美国学者古丁所说,“当第一次遇到一个主题,或用一种非常新颖的方法去思考它时,单个案例研究比多案例研究更有用”[5]。那么,在解决了案例研究选择问题后,需要选择一种适合分析所选案例的理论视角。本文选择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立论,是因为笔者认为它的理论优势足以达成前述研究目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在继承了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结合了制度主义而形成的。大多数理性选择理论家一致认为理性选择框架包括以下元素:行动者有持续的偏好,努力使预期效用最大化,是工具理性的,基于成本收益计算作出决定,是自利的[6],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选择理论家从不将结构或集体作为行动者。各种研究制度的理性选择方法承继了上述基本假设,主张在政治行为的各方面具有相同的利己主义的行为特征,政治制度是为了实现设计者的功利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即“制度需求是因为它们能增加理性行动者的福利”[7]。同时,这一制度理论的各种变体也“关注制度的重要性,把制度作为引导和限制个人行为的机制”。理性选择方法的基本观点是效用最大化能够而且也将始终成为个人的主要动力。然而,这些个人或许认识到通过制度性的行为能够非常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目标,也发现制度塑造了他们的行为。因此,在这种观点看来,个体的理性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其在制度中的成员身份,而不管这种身份是否是他们自愿获得的[8]。
接下来,本文将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上述基本假设与观点,分析“衡阳贿选案”的相关行动者是如何根据个体效用最大化原则指导行为的,贿选,这种起初以个体效用最大化标准来衡量的“理性行为”,是如何转化为群体的非理性行为。此后,现有政治体系中的监督者又是如何从贿选的参与者、旁观者或不知情者,转变为高调惩处贿选的积极行动者。在贿选盛行时段内,约束贿选的制度为什么不起作用?而在查处贿选的非常政治中,这些约束性制度如何被唤醒,群体性贿选行为是如何败于组织化集体性查处行动的。查办贿选过程及其事后宣示所揭示出来的当下掌权者的理性选择,是没有促成人大代表选举及相关制度的实质性变革的主要原因。在这些分析中,我们会发现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案例分析之间的高度契合性。
二、贿选:从个体理性选择到群体非理性行动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的,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者的偏好、动机、行动是其理论出发点,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从理性个体行为中产生群体理性——如果没有制度规范的出现,个体行为或许导致群体的非理性——的能力”[9]。“使用理性选择模式要求分析者辨认相关的行动者,确定他们的偏好,并找出将行动归因于偏好的可信理由。”[10]而研究贿选的学者则指出:“贿选会有不同的形式,而不同形式的贿选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换言之,谁的选票被卖掉,如何被卖掉,谁在购买选票,投票者为什么会接受付款,服从是如何达成的,贿选用的金钱来自哪里,所有这些对描绘贿选各种不同的结果,都很重要。”[11]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分析衡阳贿选案中的各行动者(包括行贿者、受贿者、潜在行动者、局外行动者等等)在角逐省人大代表中是如何追求最大化个体效用的,以及以此为出发点的个体行动,如何形成一种遵循“以金钱换选票”规则的群体行动。
(一)行贿的候选人:谁贿选,为何贿选
衡阳贿选案中,有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贿选行为[12],以实际职业划分,其中企业主32人,党政官员、国有企事业负责人23人(村支书3人),基层社区党员1人。可见,企业主身份的代表占了行贿者的56%,党政官员、国有企事业负责人占43%。对于前者,在地方人大处在党政决策权力外层的情况下,如此众多的企业主不惜重金去争当人大代表,其核心动机是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里的个人利益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追求“人大代表”这一象征性荣耀;用“省人大代表”作为护身符,既可以排除一些县市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设租与寻租[13],也可以为个人和企业的不法行为提供一种保护[14];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和参加人代会的机会,编织更为广泛的人际网络,以较低成本接近地方甚至中央的政治权力中心圈,为个人及其企业谋求最大的利益[15]。民营企业主热衷于竞争人大代表,甚至为此不惜代价、铤而走险,贿选选举人或者主要官员,这其实是民营企业主的一种生存策略,希望借助于“人大代表”这顶帽子来为其企业发展谋取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尽管企业家参政的动机多种多样,但试图“运用政治资源来为其生存和发展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则是他们共同的、最核心的动机和诉求[16]。
对于党政公共部门的官僚们,现有法律党纪等制度试图把政府官员建构成公共利益代表者,但在衡阳贿选案中他们对此置若罔闻,运用贿赂手段求得当选省人大代表。他们大多来自衡阳市所辖的区县,当选上省人大代表可越过市级,获得更多接近省级党政领导的机会,也为日后晋升积累一定社会资本。正如衡阳一位当地知情者所言,这在他们之间也形成“一个倒逼效应,官员是人大代表和不是人大代表,提拔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是面子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局长,共同提名为代表候选人,最后我没选上,他选上了,说明他的名声和政绩更好,对他后来的升迁会产生作用”[17]。
(二)受贿者:谁受贿,为何受贿
贿选实际上是一个 “购买选票”和“出售选票”的双向交易过程,所以,仅仅有行贿者单方面,贿选过程不会完成,受贿者是贿选中另一不可或缺的行动者。F. C. Schaffer等学者认为,出售选票者的出售动机主要有四种:一是出于短期经济利益需求,计算直接的个人利益;二是恐惧,害怕投票下降或投票与期望存在差异,而招致报复;三是与对投票掮客个人义务的感情有关,掮客实际上买他们的选票,再卖给登门求票的地方政要或亲戚朋友;四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贿选是一种品德象征,候选人关心选民的标志[18]。在衡阳贿选案中,受贿者包括出席市人大会议的527名中的518名与68名人大会议工作人员。他们受贿的动机主要是出于上述第一种,即对自己短期经济利益的计算。代表法规定,人大代表有义务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这明显是要求人大代表做一个“公共人”和“道德人”。但他们在选举前接受贿赂,表现出来的是却是纯粹的“经济人”角色。衡阳贿选案中,总贿选金额达1.1亿元,每人平均受贿额约为20万,对于来自区县的处级或科级干部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具有极大吸引力。
市人大代表接受省人大代表候选人贿选的另一个直接动力在于,他们有不少自身就是通过贿赂县级人大代表而当选的。早在几年前,就有媒体报道,“一些代表选上县代表的时候就花了钱,因此给市代表候选人投票的时候也要收钱,然后,一些市代表在选省代表的时候也要收钱,而且信封里的数额也一级比一级多。”一些代表已经开始在讨论当代表也是一种投资,因为三级选举间隔都是一个多月,很快就可以看到第一步收益[19]。这种由贿选产生的下一级人大代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所收贿选钱款层层不断升级模式在衡阳辖区仍盛行。据在衡阳市祁东县参与贿选市人大代表的企业主黄玉彪和该县一位人大代表向媒体报料,在选举省级人大代表的过程中,“红包”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不少人在竞争市、县人大代表时花了钱,“有人花了10来万才当上县人大代表,等到轮到他投票选市人大代表时,一定会想方设法把此前的‘投资成本收回来。同样,市人大代表在选举省人大代表时,也有此种心理”[20]。在这样一种层层贿选中,代表手中原本应该用来表达民意的选票,变成了代表赚取个人钱财的私人投资基金,道德良知与政治正义逻辑完全被个人利益逻辑所替代。
在衡阳贿选案中,除了作为受贿主力军的518名市人大代表外,还包括68名市人代会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主要来自于市人大机关、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他们虽然没有投票权,但在贿选过程中扮演着“政治掮客”的角色,奔走在各代表团之间的工作人员,为候选人传递信息、分析形势和转运装有行贿钱款的信封[21],并收取“信息费用”。他们的存在与行动,使行贿的候选人与受贿的代表之间的信息沟通更加畅通,加速了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贿选的交易成本水涨船高。“有人都花了20万了,人家都在动,你不动不行。”[22]56名省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贿选钱款竟达1.1亿元,在相当程度上是这种循环竞争、层层加码的结果。
(三)监管者:谁监管,如何监管
贿选看似只是购买选票者与出售选票者双方的交易与博弈,但其内部与外部监督者或参与其中,或与双方构成一个更大的弈局,无论哪种情况,都对贿选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的产生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制度,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在这由下选上的多层制度设计中,衡阳市人大(代表)本应是其选出的省人大代表的委托人、监管者。选举省人大代表应该是市人大(代表)出于良知与正义、平等原则,辨识候选人,从中挑选合格和优秀代表的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对省人大代表候选人成为正式代表过程的实时直接监管,也罢免不合格的所选正式省人大代表,这属于事后监管。但是,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原本拥有决定性监督和任免权的市人大代表的职责与道德防线,被候选人的金钱攻破,成为贿选的合作者。
衡阳市所辖的区(县)人大(代表)是其衡阳市人大代表的选举人、权力委托人,也是其监督者[23]。市人大(代表)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的履职活动,也应该接受衡阳区(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不过,市人大代表选举哪些候选人做省人大代表,与依附于党政机构系统的区(县)人大代表个人、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无直接的利益关系,也就没有独自监督市级人大的动力和能力。另外,作为区(县)人大代表的直接选民,理论上也是市级人大代表的间接委托和监督者,但实践中,他们很少有动力和能力监督直接选出的区县人大代表,更遑论市级人大代表。
就市人大(代表)选举省级人大代表的具体工作而言,选举法、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24],也应该是选举的直接监督者。实际上,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核心是其党组,而这个党组又是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地方党委、组织部等部门是同级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实际领导者和监管者。但在衡阳人大选举省人大代表时,当时的市委书记童名谦是从邵阳调过去的,“他在衡阳是一个过渡,一两年之后可能解决副省级,从他的行事风格是相对无所作为的,不管事,他只想平稳过渡到省里去。衡阳当地政界有各种各样的官员都想把自己的人搞上去,自己的亲信或者与自己的交好的企业家,形成了多头竞争,过去如果是组织部一家控制就不可能有大面积的贿选,因为有些政治性要保证的。多头去安排的时候,最后就把价码层层抬高了”[25]。这样,直接监督者的不作为与分裂,成为衡阳贿选发生的直接原因。当然,在地方服从中央的政党体制中,地方党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和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及其领导下的相关部门(如纪委),实际上也是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间接领导和监督者。
在选举省人大代表的过程中,各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主席团是选举工作的主要领导和监督者,多数既是党组织内定的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又是作为省人大代表的选举人的市人大代表[26],主要任务是保证党推荐的候选人当选,而监督差额选举的部分动力不足。作为间接领导和监督者,湖南省委、省人大及其常委会[27],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纪委缺乏直接实时监督市级人大选举工作的信息基础,只有在贿选事件进入他们的议事日程后,才能启动监督与调查程序。
上述人大代表选举的众多监督者,或因无利益激励而无力监督,或因政治距离过远信息不畅而不能监督,或因私利直接参与贿选,整个选举监管机制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贿选的发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群体贿选的非理性行为
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理解群体现象的最好办法是看它们如何从个体的选择与行动中产生。”[28]在湖南“贿选人大代表”的案例中,个体通过贿赂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已经存在相当长时间,并在空间上不断蔓延扩散,在一些县市成为绝大多数候选人的群体性选择。对于贿选是如何从个体选择成为群体选择的,我们可以从以下思路来理解。
最初,在监管机制失效的情况下,当某个候选人以贿选行动获得预期目标和利益,这一方面打破了约束贿选规则和候选人之间相对平等的竞争地位与态势,威胁到其他候选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个体贿选没有受到及时监督与处罚,还如期当选,那么就会引发其他想取得相近的目标和利益的候选人纷纷效尤,逐步形成一种默契的群体行动。而那些遵守约束贿选规则的候选人即使不想通过贿选当选,而想通过正常制度过程当选,其机率,会随着贿选人数的增加而减少,在“当行动和结局取决于别人的行动时”,他们或退出选举,或不得不加入贿选行动。这样通过贿赂当选人大代表,成为多数群体的共享规则、理念(shared rules and ideas),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选择,从而形成一种逼良为娼的群体行动机制。如果候选人想在这样一种制度中取得成功,“就不得不很快学会适应规则和接受制度价值”[29],对选择贿选的个体候选人来说,这种制度变得越来越成功,也就会在塑造个体偏好上越来越成功,有时甚至发生在正式进入这个制度之前,正如参选企业家黄玉彪说,“这就是个游戏规则,还是顺应安排。”[30]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差额选举的候选人不得不很快学会和适应暗箱操作、以金钱换选票等规则并接受其观念。这些规则、观念虽然不是明确规定,但却被大多数参与贿选者意识到并遵循,而约束贿选行为的制度,不会给贿选的相关行动者带来即时利益,缺乏遵行者而沦为一纸空文。
在贿选从某个候选人的理性选择蔓延成为群体非理性的过程中,其实隐匿着价值评判标准的转变。如果仅从施贿方与受贿方来说,贿选似乎是一种遵守自愿平等交换规则的市场行为,且对双方都实现了各自“效用的最大化”。不过,内部效用的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具有负面外溢效应。就一般意义而言,贿选以狭隘的个人利益计算替代对公共议题的协商,“违背了民主的平等规则,因为它使天生富有的候选人能从天生贫穷的投票人那里购买民主的影响份额。它还破坏了选举作为集体决策工具所具有的意义,因为贿选还削弱了民主的平等主义精神,掏空了对政策内容的民主选择”[31]。在中国,党的首要目的是把人大构建成具有协商、咨议或提供合法性功能的机构。在衡阳贿选案中,企业主与官员垄断人大多数代表席位的现象,造成党政机关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信息沟通渠道的进一步窄化,使党的上述目标难以实现。群体性贿选行为的负面外溢效应,则主要体现在社会中的资本群体(企业主)对地方党权政权稳定及其合法性的挑战。用一名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这股势头来势很猛”[32]。从理论上讲,在仅有少数候选人通过贿赂当选人大代表的情况下,查处后,可以通过现有法律程序补选,不会影响整个地方政治结构与运行,然而当参与贿选的人大代表达到一定程度,如衡阳贿选案中,衡阳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几乎全部涉案[33],就会对地方市级政治造成全整性危机。主要有三个方面[34]:一是,衡阳贿选人大代表案发生在换届选举中,几乎全部人大代表受贿,使市人大本身失去了合法性,“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涉案面广,已经无法正常履行工作职责”[35]。二是,在新的人大代表选举出来之前,衡阳人大选举出来了“一府两院”主要领导人,其人大常委会召开了8次会议,进行的大量程序性人事任免,对重大事项作出的决定等都失去了程序合法性。三是衡阳市及其所辖的区县政局不稳定,由于涉贿市人大代表中包括各区县党委、人大和政府三大机构的主要领导人,衡阳贿选案查处前,市人大、政府主要机构及所辖区县政府带病运行长达一年之久,之后,各级三大班子频繁调整,有的官员在调查期间获得升迁。此外,还导致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不得不从原定的2014年1月推迟到2月10日召开。
总之,贿选人大代表行为从个体理性选择演化为群体性非理性选择,超过了现有体制所容忍的底线,作为外部主要间接监督者的中央与湖南省级党委启动了反制贿选的查处程序,激活了被群体贿选非理性行为击败的约束贿选的制度。
三、贿选调查处理过程中的理性选择
从对群体贿选的非理性行为查处启动及过程中,前述相关行动者的行动仍然遵循着理性选择的逻辑。不过重要的是,激活了既有的约束贿选的制度,透过查处过程、处理结果与不同行动者对查处的反应,更能反映现在约束性制度乃至整个政治体制运行的若干逻辑,甚至是导致贿选的部分原因。
(一)贿选调查启动的理性选择
对于贿选能否成为调查对象的前提之一是,相关信息进入能够启动程序的决策者,以及决策者认为贿选事件具有政治重要性,需要启动解决程序。正如有学者所说,“在中国,一个事件是否具有政治性取决于领导层对该事件的认知及其采取的行动……只有当一个事件进入了‘政治范围,并具有了政治上的重要性,高层领导才开始干预,成为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36]在开启衡阳贿选事件调查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贿选事件信息最初是由外部社会(贿选省人大代表但最终落选者)而不是政治系统内部(监督系统)进入决策层的。不同层面的监督者和决策者,对贿选事件信息的反应及其程度是不同的。市级政治系统内部监督者参与了贿选,基于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受理举报人的举报,更不用说开启调查;贿选事件信息进入省级决策系统后,省委认为案情重大,性质严重,于是启动了2013年夏天的初步调查,要求收钱的人大代表退缴涉案钱物[37],但没有启动党政纪法律追责程序,这可能是基于家丑不外扬的考虑;举报人继续向10月底进驻湖南的中央巡视组举报,巡视组把相关信息传递到中央决策层[38],并引起核心决策者的重视,作出严厉批示,认为贿选事件“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挑战”。在最高层的压力下,湖南省委纪委进一步启动了对衡阳贿选事件的追责程序[39]。在自上而下的压力下,原来约束和惩处贿选的制度被激活,通过贿赂当选的省人大代表、收受贿赂者、没有参与贿选但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者,都无力抗拒,或主动请辞,或被免职接受调查。区县人大(代表)执行省、中央的意志与命令,接受涉案人大代表的辞职请求。原来遵行贿选规则与行为模式的群体,被强大的体制内自上而下的组织力量迅速击碎、清除。
在启动过程中,我们看到原衡阳市委、政府领导涉及贿选,对举报的不理与压制,湖南省领导最初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40]。只是在贿选信息通过内参、中央巡视组传达到最高决策者,最高决策者认为事情极为严重,威胁到党的合法性时,才启动彻底查处的程序。这是一个地方官员基于自身利益或地方利益、最高领导人基于党和国家长远利益而采取的不同行动之间的理性选择与博弈过程。
(二)涉案代表处理的制度程序问题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制度的功能就在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使行动者通过合作与交换来实现共同目标。以此看来,作为规范人大代表选举的制度,选举法、代表法等法律的功能就是解决选举过程中集体行动的问题。但法律制度对人大代表选举的规定,或者不明显、不完善,或者这些法律规定,在调查处理贿选过程中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行。
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根据选举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代表,妨害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而当选的,其当选无效的规定,确认由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以下56名省十二届人大代表当选无效[41]。通过贿赂当选的人大代表,其当选无效,有法律依据,但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由原选举单位公告还是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公告。
对未送钱拉票但工作严重失职的5位省人大代表,由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公告其代表资格终止,但代表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代表资格终止的情形[42]并不包括“工作严重失职”:根据现有法律规定[43],对这些代表本可以由达到法定人数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启动罢免程序,但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不能正常履职。对他们的处理陷入一种尴尬状态:即有法可依,但无执行主体,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终止这5位人大代表的资格,并无法律依据。同时,在对于3名未收受钱物但工作严重失职的市人大代表,却适用的是辞职程序,由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决定,接受他们的辞职。相同的问题与对象,却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程序。
对512名[44]受贿的市人大代表,湖南省委纪委成立的专案组启动的是人大代表辞职程序,即通过自上而下的党组织压力或“命令”,迫使涉案市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辞职,而不是人大系统内部自下而上的罢免程序,即由达到法定人数的区县人大代表罢免所选的市人大代表。这些代表通过法定的辞职程序,分别向选举其的各区县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并获得接受。不过,根据法律规定[45],区县这些决议须报送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然而,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已经停止运行,这些市人大的辞职程序就不能完成,其资格也就没有完全终止,那么区县人大也就不能重新选举新的市人大代表,不能重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二是这代表辞职程序的迅速实施,是以党的系统有效运行为前提的。依据现有法律规定,人大代表可以辞职[46],这是自愿性的,体现的是道德责任上的一种自我反省,而罢免体现的是一种强制性法律追责机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受贿代表坚决不辞职,那么其代表资格在法律程序上就没有终止,仍然有效,原来代表的去职、重新选举代表、重组人大等程序就难以进行下去[47]。
(三)关于选举新的省市人大代表,重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问题
由于中国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代表实行间接选举制度,即下级人大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对具体选举人大代表的过程,法律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领导或者主持[48]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等职权。据这些规定,应该由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持市辖区县人大选举市人大代表,召集本市人民代表大会。但包括市人大常委会成员在内的几乎所有代表都参与了贿选,这导致层层间接选举的链条断裂了。也就是说,由受贿代表组成的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失去了合法性,不能再主持或领导市辖区县人大选举市人大代表,更不可能由它召集市人大会议,再去补选因贿选被确认为资格无效的省人大代表而空缺出来的名额。
衡阳贿选基本查清后,为尽快重组衡阳市人大,恢复其正常运转,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成立衡阳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筹备组,授予其相当于市人大常委会的部分职权[49]。这种做法当然是权宜之计,从法律程序上来讲,非常值得商榷。关键的问题是,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是不是对下一级人大常委会拥有纵向领导权。对此,现有法律无明确规定,仅有选举法第八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其他如地方组织法、代表法、监督法等法律也没有赋予省级人大常委会如此大的权力。现行《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二章规定的省人大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中,并不包括“筹备下级人大会议的权力”,第七章也只规定了省人大常委会同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联系办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现有法律明确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并对之负责。所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的上述做法,没有法律依据[50],由它成立的筹备组及其行使的职权与行为,也就没有合法性[51]。
(四)贿选案与省人大召开的法定代表数量问题
根据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议事规则的规定,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才能举行。对于湖南省人大召集的条件,《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十三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始得举行。”2014年2月15日上午召开的湖南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应到代表767人,实到代表有741人。而衡阳贿选涉及的省人大代表有61人(56人贿选,5人工作严重失职),不参加会议,并不会使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代表不足三分之二。上述法律只规定了一级人大召开所必需实到与应到的代表比例,而没有考虑到某选区代表全部不能参加上一级人大会议的情况。因此,在衡阳市人大重组后选出新的省人大代表之前,可以召开省人大会议。如此一来,那么衡阳地区的利益就没有被代表的可能了。目前湖南省考虑到了后一种情况,等衡阳市选出新的省人大代表后,才召开省人大会议,并因此推迟了省人大会议的召开。
四、衡阳贿选案的制度主义反思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制度是为了实现设计者的功利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与这种制度起源功利主义视角相适应,政治制度的变迁“似乎是发生在现在制度在满足其形成时所能满足的需求出现了某种‘失败的时候”[52],或说是当制度功能紊乱或产生次最优结果时,制度就会发生转型。衡阳贿选案引起了地方政治的紊乱,映射出人大及其所在的政治系统的结构性问题,高层对衡阳贿选案的认识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宣示的高度。尽管如此,它并没有导致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发生实质性变革,而是回向了强化党对人大控制的原路。当然,这也是在现有政治结构下快速遏制贿选的一种理性选择。但这并不能遮蔽贿选问题的实质及其反映的社会变动之后政治系统所遭遇到的结构性问题,更不能成为我们对贿选的反思止步于此的理由。
(一)如何处理党与人大关系需要从长计议
中国国家建构走的是“以党建国”的路径,作为国家建制的一部分,人大制度也是由党建立起来的。党建立人大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党的执政提供程序上的合法性,动员社会支持党的行动,为党治国提供信息与建议。党对各级人大的领导是通过党对人大的嵌入式领导体制,即在各级人大常委会成立党组来实现的,人大常委会是以党组为核心成员构成的。嵌入式体制把党自上而下的各级常委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机关嵌入了原本遵守平等和相对独立的各级人大,使党实现了对人大的实际控制与领导,党的意志可以迅速有效地通过人大变成政策,并赋予其合法性。但这种嵌入体制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可能造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一点在衡阳贿选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衡阳人大代表几乎全部受贿,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或受贿或渎职,作为衡阳市党委领导人大的中间联结组织,党组出现合法性和机构真空,不能正常运转了。衡阳贿选案导致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处于“瘫痪”状态,反映出了人大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没有及时有效地自我修复和纠错机制,只能靠外部党委系统来补救。衡阳贿选案只能由省委省纪委成立的专案组来查处。但这样的调查与处理,实际上更加加强了党对人大的控制。最明显的表现是,2014年1月,市委书记李亿龙当选为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为湖南14个市州中唯一一个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市委书记。这固然可以稳定党的权力,控制贿选的产生。但从长远来看,如何使人大制度适应社会经济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参政要求,需要从长计议。把作为党的咨议机构与程序合法性提供者的人大,转变为真正的代议民主机构,是进行制度改革,遏制代表贿选,又要激发人大的民主活力,不得不考虑的核心问题。
(二)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本身不完善
衡阳贿选案充分暴露了现有人大选举制度存在诸多缺陷。
一是现有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中,约束贿选的制度极其简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选举人大代表的内部监督主体不明确。选举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将这一职权赋予了“主持选举的机构”,而现有法律规定主持县级以上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主体,既包括同级地方人大常委会,又包括大会主席团。第二,上述对选举人大代表监督属于人大代表内部自我监督,是一种软约束机制。因为无论是人大常委会还是主席团,其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同级人大代表,难以进行自我监督。衡阳贿选案中,市人大常委会和会议期间的主席团在贿选面前几乎全军覆没,就是证明。第三,在间接选举人大代表过程中,上述监督主体只能监督实际的投票过程,难以监督投票前的候选人的行为,而贿选大多是发生在投票之前候选人贿赂行为。选举法第十条规定的选举委员会的职责包括,审查选民资格,受理对于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而没有规定“受理对候选人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使对最容易成为贿选者的候选人的监督出现空缺。第四,选举法只赋予了“主持选举的机构”监督选举的权力,而没有规定其失职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追究其责任的法律程序。第五,对当选的人大代表监督不健全,代表法只规定了代表采取多种方式,接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而没有规定代表不接受监督而应该承担的责任。在选民对代表的罢免程序难以迅速启动的情况下,上述监督往往流于形式。代表法列举了应该终止代表资格的情形仅有7种,不能涵盖现实中遇到的应该终止代表资格的复杂情况,也没有规定应该由谁采取什么方式和程序,终止其代表资格。第六,选举法对贿选的事后制裁规定仅有两条,以贿赂当选的,其当选无效,并没有规定其代表资格是自动失效,还是由原选举单位或达到一定人数的选民或代表公告。
二是处理贿选的程序的制度不完备。由于贿选行为一般出现在正式投票选举代表之前,以在私人之间进行,事前监督发现难度很大。这样,事后监督与处理就成为及时有效补救的必要手段。但现行法律对处理贿选的程序非常残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行法律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到因贿选等因素导致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全部停止运行的情况。这一方面使此类案件发生后,人大系统自身没有迅速有效的修复与补救机制,整个地方政治系统出现前述各种危机;另一方面也使查处此类案件的主体缺乏合法性,查处过程无法可依。第二,没有规定对贿选所涉及的代表,是启动辞职程序还是启动罢免程序,或在何种情况下启动辞职程序,在何种情况下启动罢免程序。如果对贿选代表启动辞职程序,而代表不主动提出辞职,应该采取什么法律手段或其他程序,法律没有规定。第三,现有法律制度所规定的启动罢免程序非常复杂,成本较高。制度设计上,选民或选举人的选举权与罢免权严重不对等。作为选举权利的重要保障和选民或代议机关约束当选者的重要手段,选民或选举人的罢免权也被设置了相对于选举权高得多的门槛。人大代表被罢免难度远比其当选的难度要大很多[53]。隐藏在背后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在选举人大代表过程中,选民自主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当选机率很小,相反党团推荐的候选人则非常容易当选,这样,正式人大代表基本上从后者中产生;而选民对罢免代表门槛的提高,实际上是在保护党团提名中产生的代表。这种为保护党团提名候选人当选为代表的制度设计,为在查处如衡阳贿选这样涉及几乎全部代表的案件中,启动罢免程序设置了非常高的启动难度与运行成本。第四,如衡阳这类几乎全部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成员都涉贿的案件,引发的人大机构及其履职合法性问题,法律没有明显规定。主要是对涉贿代表的资格,是适用公告终止程序还是自动无效程序?其资格的终止或无效是自其受贿之日起,还是自公告之日起呢?无论适用哪种程序,由于是几乎全部代表涉贿,在自涉贿之日起到失去代表资格之日止的这段时间内,他们组成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履职行动都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当然,没有前述的考虑,现行法律也就没有规定如何应对补救这种全整性危机的规定程序。
(三)监督选举与查处贿选过程中的非程序化
除了因上述约束和查处贿选人大代表制度不完善而造成的无法可依的情况,在监督选举人大代表和处理贿选案过程中,现有的约束制度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现有约束贿选的制度能被有效实施,也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贿选事件。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约束贿选的制度之所以没有得到有效实施,是没有利益相关者为之提供主体支撑,而之所以没有行动者遵行、支持这些制度,又是因为这些制度体现的是一种非私人利益,遵守这些制度不能为行动者提供可预知的直接利益,行动者也就没有遵行约束贿选制度的正向利益激励和负向惩罚约束。也就是说,遵行这些制度给他们带不来可看到的利益,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政治仕途上的,相反违反这些制度,却能给他们带来相当可观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而且被发现和处罚的概率非常低[54]。如果衡阳贿选案参与者预期到会因参与贿选而被追责任,影响甚至是结束其仕途,失去自由,承担刑事责任,那么绝大多数人不会选择参与贿选的。
如前所述,对衡阳贿选案的调查,不是由省人大常委会独立地按照法律程序启动对涉案者的调查与罢免程序,而是由省委纪委主持,其调查过程基本上是法外运行的。从党与人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角度讲,由省委省纪委主持调查当然没有问题。不过是有其他更加符合法律规范的可行路径的。宪法、地方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55]。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据此,省人大常委会可以启动特定问题调查权,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调查衡阳贿选案[56]。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最符合法律的可行路径是,根据选举法第八条、第三十七条,地方组织法第十一条之规定,由五分之一以上的各区县人大代表提议,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区县人大会议主席团主持,选举出市人大代表,再由市人大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临时召集市人大会议,选举市人大常委会,由其接受失职省人大代表辞职,或由达到法定人数的市人大代表提起对他们的罢免案,罢免其职务,然后选举空缺的省人大代表。最后,由新选代表组成的衡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原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事项进行复核确认。也可以根据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57],省级人大常委会可撤销衡阳人大常委会2013年作出的不适当或不合法的决议,交由新一届人大常委会重新决议。
五、结语
在笔者看来,衡阳贿选案的挑战不仅在于它违反了现有的制度与法律,更在于它反衬出了现有人大代表选举与相关制度有漏洞。而如何改革人大选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对人大选举及其相关制度持何种理念。正如诺斯所说,“一个社会中的某些成员可能会看到问题的‘真实性质,但是却无法改变制度。因此,必须使那些能够作出政治决策的人也具有这种想法;然而,政体能否将这种人‘安置到决策制定的位置上并不是不言而喻的。”[58]就目前的情况看,尽管官方媒体宣示“要深入剖析问题的根源,探究治本之策,从中找出制度上、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改进,从源头上加以封堵”[59],对于什么是治本之策,什么是切实的措施,对待选举特别是竞争性选举及其与贿选关系的不同理解与理念,会导致差异巨大甚至是相反的改革。从衡阳贿选案后重选代表与重建人大的实际情况来看[60],我们没有发现执政者有对人大代表选举及其相关制度进行实质改革的动向。自2000年山西河津123名人大代表受贿案、2003年云南梁河县103名人大代表受贿案以来,直到衡阳贿选案被查出,已经有十多年之久,但由这些类似案件带来的地方政治的全整性危机,至今没有引起实质性反思,补救措施仍然是收紧对人大选举的控制,而不是向公开性竞争选举方面改革,以容纳疏导社会群体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和实现自己利益的要求。这说明社会关于人大选举制度改革的知识,还很难上升为国家知识,而执政者或许是出于路径依赖(主要包括利益依赖、观念依赖、行动结构依赖),还缺乏深入反思与改革的能力与动力,人大选举及其配套制度的实质性改革还是来路遥遥。
注释:
[1]贿选,俗称“买票”(vote buying),指候选人给予投票人一定的金钱或其他形式的物质利益以换取其选票支持的行为。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湖南省衡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527名市人大代表出席会议(2人因故未能出席)。在差额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93选76)的过程中,共有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涉案金额人民币1.1亿余元。
[2]Frederic Charles Schaffer.“What Study Vote Buying?”Elections for Sale: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 Edited by. Frederic Charles Schaffer.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7, p. p.1, p.16.
[3]Robert E. Goodin, edi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138.,1142.
[4]Robert E. Goodin, edi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146.
[5]Robert E. Goodin, edi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142.
[6]Lina Eriksson,Rational Choice Theory: Potential and Limits, Palgarve Macmillan, 2011, p.17.
[7]Robert H. Bates, Contra Contractarianism: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No. 16,1988,p.393.
[8]B.Guy Peters,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hird Edition,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2, p.49.
[9]B.Guy Peters,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hird Edition,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2, p.50.
[10]芭芭拉·格迪斯:《范式与沙堡:比较政治中的理论构建和研究设计》,陈子恪、刘骥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
[11]Frederic Charles Schaffer, “Lessons Learned”, Elections for Sal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 Edited by. Frederic Charles Schaffer.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7, p. 196.
[12]在93名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中,除去的20名为组织安排的候选人(他们基本上不需要参与贿选)外,从剩余的73人中差额选出56名省人大代表,17名候选人会落选。被差额掉的17名候选人是否存在贿选行为,不得而知。
[13]衡阳属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单位经费捉襟见肘,投资环境不好,长期流传“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说法,私企业主如果有人大代表的光环,职能部门就会投鼠忌器。冯铭:《衡阳人大案1.1亿的内幕》,载《廉政瞭望》2014年第1期。2008年的报道中,参加衡阳市祁东县人大代表选举的企业主说参选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意:“企业要做大做强,如果我当了人大代表,可以融资,在纳税之类的事情上也有很多好处,工商、公安就不敢随便找我们了。”黄志杰:《衡阳私企老板贿选人大代表始末》,载《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4期。
[14]如有学者在衡阳调查得知,在企业主代表中,包二奶、超生的现象比较多,计生人员在对其进行象征性的罚款时,还得赔小心。也有企业主代表染上黄、赌、毒恶习,但依据代表法非经该本级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刑事审判。而且代表层级越高,办案难度越大。参见冯铭:《衡阳人大案1.1亿的内幕》,载《廉政瞭望》2014年第1期。
[15]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据报道,“2002年10月份,企业家何帮喜对任巢湖市委书记表达了自己想扩大企业知名度,请周帮忙给我争取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名额。通过周光全的提议,巢湖市人大把何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上报到省里,但没被选取上。但何最后在2003年6月,被选为省十届人大代表。” 欧阳艳琴:《安徽2名企业主行贿败露 1年后仍为全国人大代表》,载《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3月1日。
[16]李克诚:《民营企业家“贿选”反思》,载《南风窗》2013年第5期。
[17]《从衡阳贿选案看中国选举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mht/article_2014041
1104198.html.
[18]F.C.Schaffer(Ed.),Elections for sale: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2007,p.198.
[19][22]黄志杰:《衡阳私企老板贿选人大代表始末》,载《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4期。
[20]李克诚:《民营企业家“贿选”反思》,载《南风窗》2013年第5期;海鹏飞:《黄玉彪举报贿选这一年》,载《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2期。
[21][32]冯铭:《衡阳人大案1.1亿的内幕》,载《廉政瞭望》 2014年第1期。
[23]选举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24]选举法第八条、第三十七条,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或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
[25]《从衡阳贿选案看中国选举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mht/article_2014041
1104198.html.
[26]如衡阳贿选案中,时任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一身多任,市人大换届领导小组组长,又是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主席、市人大代表。
[27]在人大换届选举中,由原来的上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和监督下一级人大选举新的上一级人大代表的工作,是不是具有正当性,有学者提出质疑。
[28]Lina Eriksson,Rational Choice Theory:Potential and Limits, Palgarve Macmillan, 2011, p.142.
[29]B.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hird Edition,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2, p.49.
[30]《湖南自曝贿选商人:我就是要揭开贿选潜规则》,载《南方都市报》2013年1月30日。
[31]Frederic Charles Schaffer.“What Study Vote Buying?”Elections for Sale: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 Ed. Frederic Charles Schaffer.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7p. p.9.
[33]相似的过半数人大代表涉贿案例还有2000年山西运城市河津市选举运城市第一届人大代表时,多名候选人向河津市人大代表行贿,后查实的有123名代表受贿;运城市推荐的6名候选人中有4人落选,而“十人联名”产生的12名候选人中有11人当选。2003年云南德宏梁河县尹黎明、翟东旭二人通过贿赂当上副县长,该县153名人大代表中,有73名接受了尹的贿赂,30余名接受了翟的贿赂。资料来源:《山西省运城"贿选案"责任人受查处》,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china/20011019/924484A.htm, 《云南梁河县三分之二人大代表卷入贿选案 5000元买了个副县长》,载《山东人大工作》 2006年第11期。
[34]如果大规模贿选人大代表在空间上得以扩展,还可能引发省级政治的合法性危机。目前“湖南除衡阳市外,邵阳市、长沙和湘潭等贿选人大代表的情况也比较严重,长沙那边官方初步调查,有行贿行为的省人大代表15名”。沈泽玮:《衡阳重选转向暗箱操纵?》,载《联合早报》2014年2月4日。
[35]《湖南媒体披露衡阳贿选案调查经过》,载《潇湘晨报》2013年12月29日。
[36]郑永年、黎良福:《SARS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危机管理》,载《远景基金会季刊》2004年第4期。
[37]从2013年2月开始,就有群众陆续向中央有关部门、省委及相关部门举报,引起了省委的高度重视。省委随即要求省纪委调查,经初步调查,获取了部分市人大代表在市人大会议期间收受省人大代表候选人送钱送物的情况和证据。4月上旬,湖南省委听取了案件初步调查情况汇报,省委成立了由省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衡阳破坏选举案调查处理工作领导小组,省纪委成立了专案组。6月中旬,专案组赴衡阳市开展全面调查,获取了大量书证、物证,基本查清了案件事实……涉案钱物已退缴到位。《湖南媒体披露衡阳贿选案调查经过》,载《潇湘晨报》2013年12月29日。
[38]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二十九条规定,“巡视组不处理巡视地方的具体问题”,只负责收集相关信息和线索。不过,十八大以后,中央巡视组出巡时内部规定,巡视组必须查出线索,否则中央纪委会追查巡视组的责任。
[39]不过,被多家媒体曝光的邵阳大规模贿选事件,目前还没有严格查处。
[40]其实对上一届2007年底2008年初的市人大代表选举的贿选,当时媒体上已经报道了很多衡阳贿选的事,当时都报道出来了,但内部也没有处理。
[41]《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3号) 2013年12月28日。
[42]代表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代表资格终止:(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的;(二)辞职被接受的;(三)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四)被罢免的;(五)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六)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七)丧失行为能力的。
[43]宪法第一百零二条、一百零四条,地方组织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十三款,代表法第四十七条,选举法第四十六条、四十八条等条款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随时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闭会期间,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述法律中,选举法第四十八条对地方人大常委会罢免的代表没有数量上的限制。而宪法、地方组织法和代表法都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仅有权罢免“个别”代表。
[44]受贿市人大代表共518名,其中有6人(包括衡阳原市委副书记、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党组书记,现任怀化市委书记的张自银;衡阳原市委副书记、现任永州市长的严志辉;衡阳市南岳区委原委员、常委,现任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武装部政委的龙宇游等人)在调查期间调离了衡阳,代表资格自动终止,但仍需要追究其责任。
[45]选举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选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接受辞职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46]选举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间接选举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选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
[47]对于受贿的衡阳市人大代表,可以由区县人大启动强制性罢免程序,罢免的决议,须报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当然,与前述辞职程序一样,因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已经停止运行,这些区县市人大的罢免程序就不能完成,其资格也就没有完全终止,那么区县人大也就不能重新选举新的市人大代表,不能重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这需要改革现有制度安排来解决以后产生的类似问题。
[48]选举法第八条用的是“主持”,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用的是“领导或者主持”,“主持”还是“领导”的含义差异巨大,法条用语不规范,不但有损于法律统一性和严肃性,而且极易导致现实选举工作的混乱。更容易引起歧义与实际中矛盾的是,选举法第三十七条又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比如,市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省人大代表时,是不是属于“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的范围呢,如果属于,它应该由省人大常委会主持,还是市人大会议召开时的主席团主持?
[49]这些职权主要包括:筹备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事宜,接受由衡阳市选出的部分省人大代表辞职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公告,接受衡阳市所属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大常委会报送的代表资格终止的报告并公告,召集衡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筹备组下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补选衡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相关工作。《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成立衡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筹备组的决定》(2013年12月28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载《湖南日报》2013年12月29日。
[50]蔡定剑认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国家权力机关。只不过各自行使权力的层次范围不同。”“都代表所属区域范围内人民的意志,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可见,人民代表大会上下级之间没有领导关系。”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259页。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省级人大常委会可以概括为三个关系:一是法律上的监督关系;二是选举上的指导关系;三是工作上的联系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对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那么前者就应该对后者的失职甚至是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而不是授权组织重建下级人大。
[51]据笔者统计,筹备组成员共13人,以现任衡阳市委常委为核心成员,后来经市人大第十四届三次会议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共9人,其中7名来自筹备组。这等于是选定人大常委会成员,再召集人大会议,选自己做人大代表与常委会成员。
[52]Andre Lecours, New Institutionalism:Issues and Questions,in Andre Lecours, Institutionalism Theory and Analysi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p,12.
[53]对罢免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选举法规定:县级以上人大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由该级人大选出的上一级代表的罢免案。闭会期间,县级以上人大会常委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委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县级以上人大开会与闭会期间,对代表罢免案的提出的人数,在多数情况下会高于其当选时“代表十人联名”的最低限度。例如,全国人大代表由省级人大代表选出,如果省级人大代表想要罢免全国人大代表,那么在会议期间或由主席团提议,或由与会代表的十分之一(宁夏第十二届人大代表421名,十分之一约为42名;四川十二届人大代表894名,十分之一约为89名)以上代表联名提出;闭会期间则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或常委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提出,而各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少则40多人(如宁夏,五分之一约为8人),多则80多人(如四川,五分之一约为16人)。罢免案提出后,须经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54]例如,贿选人大代表在衡阳、邵阳等地盛行多年(如2008年的报道)而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查处,2013年对衡阳贿选案的查处也是在中央核心决策者严厉批示下,才得以较为彻底的查处。
[55]《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三条也规定,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全面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湖南省的遵守和执行。
[56]地方组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决定。第五十二条规定,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57]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十四项职权中,上一级人大有权“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58] 【美】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59]《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和权威》,载《湖南日报》2013年12月29日。
[60]2014年1月,衡阳人大选出的新的人大常委会主任由市委书记李亿龙兼任,成为湖南14个市州中唯一一个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市委书记,这明显是继续强化党委对人大的领导与控制。衡阳市人大代表的重新选举与人大重建的过程,都是在省委领导下,市委主要成员组成的筹备组的控制之下进行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