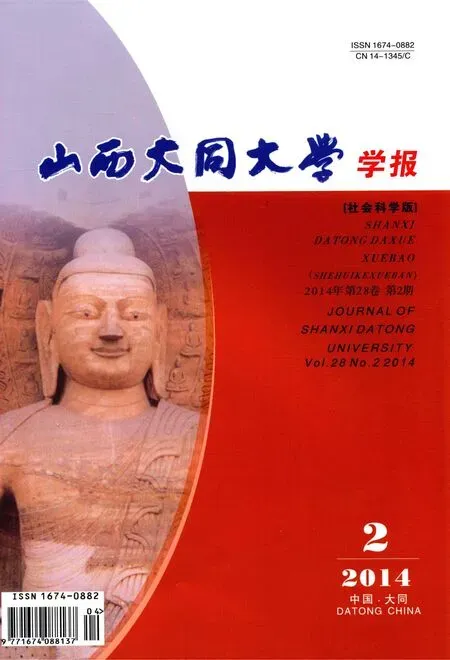李贺用典新探
2014-06-30徐步乙
徐步乙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李贺的诗歌向来以奇谲晦涩著称,读者往往在叹赏其用语之尖新、想象之丰富、意象之独特的同时,为其繁密错综的用典感到费解。
初读李贺的诗歌,第一印象便是用语新奇和用典繁密。其用语新奇多半是因为“好用代词,不肯直道物名”,[1]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已有专篇论述此问题。至于用典方面,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李贺都有其独创性,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探究。
在李贺传世的两百多首诗中,古体诗占了绝大部分 (约85%),剩下的39首近体诗,内容多写实,而少“牛鬼蛇神”之语,除《恼公》、《送秦光禄北征》外,很少用典。所以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其古体诗的用典情况。
一、用典的内容取向
(一)失意落魄的才士与可爱可恨的英主 细读李贺的诗歌便可发现其用典虽取材极博,但倾向性很鲜明,有些事典、人物反复使用。在正史和杂史中,李贺取材最多的是才高命薄的文士和雄材大略的英主,如贾谊、司马相如、东方朔、主父偃、扬雄、赵壹、潘岳和平原君、燕昭王、刘邦、刘彻等。前者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如:
长卿怀茂陵(《咏怀二首·其二》)
长卿牢落悲空舍(《南园十三首·其七》)
茂陵归卧叹清贫(《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四》)
琴堂沽酒客(《答赠》)
为作台邛客(《河阳歌》)
马卿家业贫(《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
以上诸诗屡次提及司马相如的清贫,《汉书》言其“家徒四壁立”,这位汉代大才子的一生竟如此落寞,李贺对此自有异代同悲之感。李贺本来自视甚高,又以“王孙”自居。但李贺作为皇族旁系已经两百余年,所以其家庭出身其实与一般士人无异。他本想通过科举重振家业,但因“家讳”不能如愿,后来虽谋得一个奉礼郎的小官(从九品)也郁郁不得志。他在《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中言:“辞家三年今如此,索米王门一事无。”在《出城寄权璩、杨敬之》又有“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躯。”这些诗应该多是举进士第受挫后所作,从其对司马相如的反复吟咏可见其自我期望极高,又极为消极悲观。
汉武帝也是李贺笔下常出现的人物,如上文提到的《咏怀》中有“梁王与武帝,弃之如断梗”。借汉朝故事以喻时事是唐人惯用的手法,但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视角却各不相同,在杜甫的笔下,汉武帝是一个征战无度、穷兵黩武的君主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时处盛唐的老杜已敏感到种种隐忧。而到了藩镇割据、边患日亟的中唐,李贺多么渴望再出现一位汉武帝来重振河山,这与安史之乱后绝大多数士子的心声是相吻合的。但武帝尽管雄材大略,最终还是未能重用司马相如,只能令人徒增感慨。李贺在《南园·其七》中言“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他不单咏叹司马相如,也为东方朔抱不平,因为在汉武帝的眼中,东方朔也仅仅是一个俳优。李贺感叹汉武帝求贤而不能礼贤的态度,无疑是在影射当时科举的不公正。
(二)孱弱的身躯与仙界的幻影 李贺一生体弱多病,诗中常有“宵寒药气浓”(《昌谷读书示巴童》)、“病容扶起种菱丝”(《南园十三首·其九》)、“何事还车载病躯”《出城寄权璩、杨敬之》、“病客眠清晓”(《潞州张大宅病酒》)等描写其病痛和服药的词句。甚至少年便白发斑斑,《咏怀·其二》“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其《春归昌谷》“颜子鬓先老”、《公无出门》“颜回廿九鬓毛斑”中两次慨叹颜回早衰当是实指。甚至,他似乎早已预知到自己的早逝。于是死亡成了李贺无法释怀的问题,洪为法先生云:“贺唯畏死,不同于众,时复道及死,不能去怀;然又厌苦人世,故复常作天上想。”[2](P521)所以,李贺好言鬼怪神仙,一半是出于对长生的渴望,一半是出于及时行乐的欲望。
在李贺诗集中,汉武帝除了作为英主之外,还有他追求长生及其同西王母间引人遐想的故事,这方面的题材主要来源于《汉武外传》、《汉武故事》等笔记小说,如“王母移桃献天子”(《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王母桃花千遍红”(《浩歌》)、“当时汉武帝,书报桃树春”(《仙人》)、“全胜汉武锦楼上,晓望晴寒饮花露”(《拂舞歌辞》)等。穆天子、楚襄王、秦始皇等的求仙遇仙故事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在此秦皇汉武等已不是历史人物而成了神界的一员,但李贺最终不相信神的存在,他感慨“神兮长在有无间,神喜神嗔师更言”(《神弦》),神仙总是缥缈的,其有无喜怒只能听从于巫师的鬼话。“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金铜仙人辞汉歌》),汉武帝——一个雄材大略的君主,既不能礼贤下士,又不能修仙得道,这便是人生的荒诞虚无。明明知道神仙是假的,却不惜用华丽细腻、离奇脱俗的语言将其描绘出来,如此惨淡经营恰恰体现了作者浪漫的情怀、凄美的心境和近于苛刻的艺术追求。
此外,对汉武帝与西王母、楚襄王与神女的描写还掺杂着李贺对两性情爱的渴求,集中对众多的女神、妃嫔的刻画也可说明此一问题。罗宗强甚至说:“他似乎不是在追求仙境的逸乐,而是在追求一种受到抑郁的、变态的热烈情爱。”[3](P99)李贺究竟有无妻室至今仍是一悬案,关于此事史无明载,主张有者多以《出城》“卿卿忍相问,镜中双泪姿”一联为据。其实李贺刻意塑造的诸多女神、女鬼和美人正好反映了他现实生活中的匮乏。这类诗歌基本是以杂史志怪为典实,借鉴屈原《九歌》、乐府、南朝民歌、宫体诗,再运用其丰富的想象力演绎而成的。
羲和御日的典故也多次出现,如《天上谣》“东指羲和能走马”《秦王饮酒》“东指羲和能走马”、《相劝酒》“羲和骋六辔”,等,同样表现了李贺对时间的焦虑,《苦昼短》便是其中的典型。该诗三、四、五、六、七言杂出,奇思异彩,一唱三叹,先以浪漫的笔调宣言要“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而结句“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又于理性中发出沉痛的感慨,凡此种种足见李贺内心的焦虑、斗争、希望与绝望的纠结。
二、用典手法与诗体的关系
李贺的诗歌不但用典繁密而且用典手法也很灵活多样,他往往能根据不同的内容和诗体而因地制宜。一般来说,李贺的五言诗偏于写实,用典少,其中赠别酬答诗,多写得质朴真切,饶有古风。又如《始为奉礼郎忆昌谷山居》(五排)一诗写其居京之寥落及思乡之愁苦,全诗仅“犬书曾去洛,鹤病悔游秦”一联用典,且用得甚为妥帖。《王濬墓下作》(五排)一首则述其途中所见,除起句“人间无阿童,犹唱水中龙”用典引起物是人非的感慨外,通篇纯用白描,把古墓的阴森荒凉写得如在眼前。而《送秦光禄北征》、《奉和二兄罢使遣马归延州》、《钓鱼诗》、《恼公》数首排律则用典极繁密,特别是长篇五排《恼公》,用典之多至于不可卒读,近于游戏之作,钱钟书先生谓其“繁简失当”,有“铺张之才”而乏“挈领之才”。[3](P150)
至于乐府歌行体则多写神仙鬼怪,用典多,用典手法也极独特、精彩。他喜欢把数个本不相干的事典连缀交融在一起从而营造出一种富丽梦幻的意境。如《天上谣》“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州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列仙传》载弄玉为秦穆公女,萧史“日教弄玉吹箫作凤鸣”,故言其窗前桐树上栖有青凤,而王子乔为周灵王太子“好吹笙,作凤凰鸣”,连类而及。《十洲记》载方丈洲有“仙家数十万,耕田种芝草”,李贺发为奇思,凤鸣之笙声竟能呼喊神龙耕烟而种瑶草,可谓“古今未尝经道者”。[4](P11)《十洲记》又载“长洲者一名青邱,又有仙草灵药,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天真仙女游于此地”,似乎天上的神仙甚为融洽相得。最后再用羲和御日与麻姑三见沧海桑田的神话来慨叹日光的飞逝,连神仙也无可奈何。即使咏史的《荣华曲》也是如此,此诗专咏梁冀,开篇“鸢肩公子二十余,齿编贝,唇激朱”真假掺半,《后汉书·梁冀传》“冀为人鸢肩豺目,洞精曭眄”状貌甚丑,后二典却出自《庄子·盗跖》“唇如激丹,齿如齐贝”和《汉书·东方朔传》“齿如编贝”。大致李贺欲极力刻画出贵公子的奢华逸乐,若其容貌丑陋似乎有伤意境。正如王琦在《苦篁调啸引》注用所言“以见于史传实有之事,而杂以虚无荒诞之词”。[4](P139)所以《秦王饮酒》、《李夫人》等作品究竟所咏何人历来素有争议,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古今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取其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4](P11)于是,读李贺这些诗重在欣赏其辞藻意象,没有必要过分去追寻其史实及寓意。
王琦言李贺诗“详言其状而隐晦其名,正长吉弄巧避熟处”,[4](P161)其实李贺不只用词如此,用典亦然。他或隐晦字词,或反用典故,所以有些诗句初看不觉其用典,即知之又不知所用何典。如《李凭箜篌引》“空山凝云颓不流”、《洛姝真珠》“玉喉窱窱排空光,牵云曳雪留陆郎”《申胡子觱篥歌》“天上驱云行”、《拂舞歌辞》“吴娥声绝天,空云间徘徊”皆本于《列子》秦青“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或言凝云,或言牵云,或反说为驱云,李维桢《昌谷诗解序》言李贺“极思苦吟,别无他嗜……是以只字片语,必新必奇。若古人所未尝经道者,而实皆有据案,有原委。”[4](P26)
三、用典取材与时代风气
前文已论述了李贺用典与其性情、遭遇及诗歌内容形式的关系,若从更大的视野——知识结构、时代风气来分析其用典的情况,这便涉及到当时书籍分类流传、科举考试、三教交融等殊难驾驭的问题,所以笔者只能作一大概的描述。
唐朝以科举取士,无疑对图书业的发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5](P417)韵书、类书等工具书极其发达。李贺在《五粒小松歌》序中言及“予以选书多事,不治取辞”,所选何书今已无法查明,后世目录亦不见著录。但从其用典情况来看确实可找到一些李贺引用类书的线索。如前引羲和诸典及《瑶华乐》“施红点翠照虞泉”、《日出行》“旸谷耳曾闻,若木眼不见”等原出自《山海经》、《南淮子》,俱见《艺文类聚》、《初学记》的“天部·日”,其他如麻姑沧海桑田、彭祖巫咸(《浩歌》“彭祖巫咸几回死”)、萧史、弄玉、王子乔等典故亦皆见于此二书。至若《古悠悠行》“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典出《三齐记》,《初学记》引)、《杨生青花紫石砚歌》“孔砚宽顽何足云”(《从征记》,《初学记》引)等僻书僻典如不得之类书恐怕很难闻见。所以武德七年(624年)编成的《艺文类聚》和玄宗年间官修的《初学记》两部类书应该是李贺诸多事典取材的渊薮。《昭明文选》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宝典,特别是显庆、开元年间的李善注和五臣注进一步丰富了该书的内容。而且《文选》在唐朝流传甚广,杜甫曾教导其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像李贺这样倾慕乐府和南朝民歌、宫体诗的诗人更不可能对其置之不理。如“曼倩诙谐取自容”(《南园十三首·其七》),东方朔事迹虽见于《史记·滑稽列传》、《汉书·东方朔传》,但此句明显是从夏侯湛《东方朔画赞》“诙谐以取容”一语而来,而该篇正见于《文选》卷47。又如《拂舞歌辞》“尊有乌程酒”中的“乌程酒”见于李善注所引的《荆州记》。
唐代因南北文化和民族的大融合,形成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儒学、道教、佛教三足鼎立给诗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从李贺用典来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可看出此一时代风气。

表1 用典出处统计表
由上表可见李贺用典多出子史而少出于经部,子部又集中在道家,这与唐代道教的兴盛、科举制度的沿革有着密切关系。袁守定言,“三教并称,始于宇文周之世,然道佛两家时行时禁,尚未与儒等也。唐始令释道讲论与麟德殿,贞元间又以儒生间之”。[6](P218)这从当时科举考试便可看出,“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 (明经、进士科)并加帖经。其后有加《老子》、《孝经》”(后来时有停废),“开元二十九年,是始于京师置崇玄馆,诸州置道学”,“习《老》、《庄》、《列》、《文》,谓之四子”。又言“(明经、进士)初只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开元二十五年制“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以上者,奏听进止”。[7](P354-356)经部因本身故事性、可读性较弱,所以占的比例小。但比例小到这种程度,当足见李贺对经学的轻视。
而佛教因唐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盛极一时,李贺诗中《亲王饮酒歌》“劫灰飞尽古今平”的“劫灰”一语,《浩歌》“彭祖巫咸几回死”体现的轮回说,及“世上英雄本无主”《送韦仁实兄弟入关》“野色浩无主”的“无主”都来自佛教。[2](P215)但必须说明李贺并非道教和佛教的信徒,尤其在思想上与之相去甚远。李贺诗中屡屡体现其对现实的执着、对物欲的追求、对死亡的恐惧都与道、佛两教的精神背道而驰,他只是借助其神话怪谈来增强诗歌的表现力而已。
至于神仙鬼怪等典故则多出于六朝以来的笔记小说、家传别传。单引用的次数来看,《史记》和《汉书》无疑是李贺最偏爱的典籍,但如果考虑到两书都有几十万字而各种笔记小说、别传家传往往只有数百上千字。若把各种笔记野史加起来,杂史、志怪在李贺用典中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这更多体现了他个人的偏好。
结语
陆放翁尝云:“贺词如百家锦衲,五色眩曜,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求其于用,无有也。予谓贺诗妙在兴。其次在韵逸。若但举其五色眩曜,是以儿童才藻目之。岂直无补已乎。”[4](P23)《臞翁诗评》:“李长吉如武帝食盘露,无补多欲。”[4](P24)可以说李贺诗歌的精华多在乐府歌行体,这些诗凭借繁密的典实来驰骋其丰富的想象力,再通过翻新出奇的语言营造成的诡谲绚烂的意境,从而宣泄满足其天真、压抑、多欲的心灵。正因用典繁复、用语新奇故如“百家锦衲”,正因耽于幻想、一任意欲,故“妙在兴,其次在韵逸”。
最后还须说明:李贺用典的繁密与宋人的“以学问为诗”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宋人“以学问为诗”,以至于“无一字无出处”(黄庭坚语),有时竟本末倒置,将作诗当作做学问。李贺则以奇思幽情融合众典,故能兴高而韵逸。
[1]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2]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李贺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陈允吉,吴海勇.李贺诗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王 琦,姚文燮,方扶南.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6]曹聚仁.国学十二讲[M].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3.
[7]杜 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