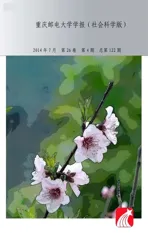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述评①
2014-06-28梁宏信
梁宏信
(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贵州贵阳550025)
仪式一直是人类学、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人类学、民俗学诞生之日起,对仪式的探讨就从未间断过,弗雷泽(James Frazer)、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范·热内普(Van Gennep)、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以及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西方学者对此研究乐此不疲,他们极力将“仪式”视为观察及诠释人类社会的经验性“社会文本”。诚然,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仪式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卷入人类的生活空间,依循一个有序的、传统的“我们的习俗”,即形式进行着[1]45,是人、神之间对话与合作成为可能的“中间桥梁”,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得各种社会关系在形形色色的仪式过程中得以建立与维系。
正因仪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备受关注。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Les Formes Ele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1912)一书中认为,宗教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把世界事物区分为“神圣的”与“世俗的”,即“世界被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包括所有的圣物,另一部分包括所有的俗物,这就是宗教思想的特征”[2]。人们通过宗教仪式来摆脱世俗以进入到神圣世界[3]。法国仪式研究者范·热内普提出的“过渡仪式”正是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一种通过仪式,他认为“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之间不存在兼容,以致一个体从一个世界过渡(passage)到另一世界时,非经过一个中间阶段不可”[4]4。“中间阶段”正是他“过渡仪式”理论的主旨,因为“在任何社会中,个体生活都是从一个年龄到另一个年龄、从一个职业到另一个职业的过渡”[4]5。所以这种过渡必然需要经历一个过渡性的中间阶段或是“地域”,“中间阶段或地域”自然客观地存在于仪式之中。他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动态的立体仪式“模型”,从而对仪式过程及仪式内部进行结构式的剖析,并将人的生命过程与社会化过程在仪式过程中很好地整合起来讨论。可以说,这一讨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尽管中国民俗学在上世纪80年代恢复学科重建的过程中,也引入了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思想,但并未对之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从中国目前可搜集到的学术文献资料来看,专门针对其理论讨论的文章或论著为数不多,或在论及维克多·特纳等学者及西方仪式研究时有所提及,大都并未细致考察。因此,本文立足于已有文献,采取评述的方式,条分缕析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及其继承与发展等相关论题。
一、范·热内普及其“过渡仪式”理论
范·热内普是欧洲民俗学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对法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民俗学贡献巨大。他1873年出生于前德国路德维斯堡(Ludweigsburg),由于父母未婚而跟随母姓,六岁时迁居法国里昂,在巴黎大学度过他的大学时代。大学里,范·热内普先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和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民族志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和东方语言等学科,且因接触宗教科学相关知识而逐步爱上民俗(folklore),“过渡仪式”无疑是其民俗学思想的精髓所在。自《过渡礼仪》(Les Rites De Passage)一书问世后,“过渡仪式”模式及该理论思想就一直主导着他的其他著作,并最终获得学界的认可,成为人类学、民俗学经典性理论之一。
在范·热内普看来,“每一个体总是共时性或历时性地被置于其社会的多个群体。为从一群体过渡到另一群体以便与其他个体结合,该个体必须从生至死,始终参与各种仪式”[4]188。尽管仪式形式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为了使仪式中的个体能够从一巫术-宗教或世俗群体到另一对立群体的过渡。那么,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从一个地位到另一个地位的过渡就自然而然地被视为现实存在的必然内涵,因此每个个体的一生均由具有相似开头与结尾的一系列阶段组成,即诞生、社会成熟期、结婚、为人之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职业专业化以及死亡等[4]5。其中每个事件都伴随着仪式,而这些仪式也都具有“巫术-宗教”的特性。
“巫术-宗教性”是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其用以说明仪式过渡中的神圣与世俗关系问题的。因而他认为,各种过渡仪式都是围绕“巫术圈”(cercles magiques)这个中枢而进行转动,每个个体经过人生不同阶段都会将过去视为世俗的部分,而把现在视为神圣(巫术-宗教性);反之亦然。但仪式过程并非简单地是一个从世俗到神圣的过渡与回归过程,它需要经过分离、过渡和融入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以及与各阶段特征相符合的象征性的仪式才能完成,这个过程暗含着一种生命状态的改变。他为了更清楚地解释过渡仪式理论,引入了更为形象的“地域过渡”话题。该话题包含着“中立区”和“过渡地域”两个具体的概念,它们是一个确定境地与另一个确定境地的交叉地带。当人们穿过这个地域去向另一个地域时,会感觉到从身体上到巫术-宗教意义上都处于一种“游动于两个世界之间”[4]21-22的境地,即在神圣与世俗间的游离状态。这种精神上和地域上的边缘会以不同程度和形式出现在这种从一个向另一个巫术-宗教性和社会性地位过渡的仪式之中。
可见,范·热内普在极力挣脱前人静态学的仪式研究走向,努力打造一种有关仪式的动态学理解体系。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过渡性”的含义,他将该动态仪式过程进一步分析成分隔礼仪(rites de separation)、边缘礼仪(rites de marge)聚合礼仪(rites d’agregation)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正是由于这三个部分的承继衔接才构成了一个动态的仪式过程,即“过渡礼仪”体系。从理论上看,过渡仪式总围绕着“阈限阶段”或“边缘阶段”展开,因而有从“阈限前礼仪”(rites preliminaries,即分隔礼仪)到“阈限礼仪”(rites liminaries,即边缘礼仪)再过渡到“阈限后礼仪”(rites postiliminaries,即聚合礼仪)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分隔-边缘-聚合”和“阈限前-阈限-阈限后”两套说法具有一致性。
在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里,“无论对个体或群体,生命本身意味着分隔与重合、改变形式与条件、死亡以及再生。其过程是发出动作、停止动作、等待、歇息、再重新以不同方式发出行动”[4]188。这样他对于仪式的解读极具说服力地使用了“过渡性”不断螺旋式前进的理解,使得社会状态、社会身份以及生命任务的转变在仪式之中获得其“合法化”,同时也更好地将人的生命过程与社会学家常常提到的“社会化”过程在仪式进程中很好地整合起来讨论。
二、仪式的过程:分隔-边缘-聚合
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是对仪式的动态学理解,强调仪式的进程,即仪式整体的发生顺序——过渡性。他通过考察世界各民族仪式举行的资料,洞察到仪式的动态进程其实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结构,即“过渡仪式模式”(le schema des rites de passge)。他认为,在这一仪式模式之下存在三个亚类型,即分隔礼仪(rites de separation,阈限前礼仪)、边缘礼仪(rites de marge,阈限礼仪)以及聚合礼仪(rites d’agregation,阈限后礼仪)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由于这三个部分的承继衔接从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仪式过程(见图1)。但范·热内普同时也声明,在社会生活中这三组礼仪并非始终同样重要或同样地被强调细节[4]14,三者无所偏重,在相应的仪式中各自呈现出自己的重要性所在;而且也不是每种过渡仪式都明显地根据这三个阶段进行,仪式过程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但其深层次的组合却始终如一。

图1 动态的仪式过程
范·热内普以其睿智察觉到“过渡”是一个包含着“分隔-边缘-聚合”的过程,这种划分不但具有时空意义,而且也包含了社会和心理上的过渡意义[5]。在过渡仪式进程中“分隔礼仪”具有重要地位,它是第一个阶段。通过分隔礼仪才能使仪式从正常的、平衡的、稳定的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才能突显仪式在时空中的特殊性,这也是仪式举行的必要性前提。这种“分隔”使仪式中的个体或群体离开原来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状态、生命状态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之中,范·热内普用极其形象的“地域过渡”(passage materiel)来表达这一礼仪的存在感——从一个年龄到另一个年龄、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的过渡常常礼仪性地以通过一种空间的改变来实现与之前生活的分离。正如一些民族的成人礼那样,受礼者首先得离开生活的村庄,住进深山中的小屋,在时空上实现与日常生活事物的分离,形成成人仪式的分隔礼仪。正是这种时空上的过渡,使仪式变得神秘、好奇而具有“巫术-宗教性”。
经历了分隔礼仪之后,受礼者与原来的生活状态分离,转而进入范·热内普认为的第二个阶段期,即边缘礼仪或阈限礼仪期,它是第一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阶段。范·热内普对此采用“边缘”的概念,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仪式中这一阶段与正常、平衡、稳定日常生活状态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主要表现为一种非正常的、不平衡的、动荡的状态,“受礼者进入了一种神圣的仪式时空,它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或象征性地被置于‘社会之外’,不同于过去和未来按照世俗生活准则构造起来的时空”[6]115。通过世俗行为规范被悬置或抹去的状态给受礼者的生活一次意外的“震惊”。正是这种震惊打破了个体或群体原有的稳定生活状态,使其处于一种模糊、混乱的状态之中,然后通过对这种混乱的整理以调适其适应新的生命状态。这正如“在某些部落,新员被视为已经死去,直至度过此阶段”,他们在这一阶段里,“包含对其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弱化,以使他失去之前的一切记忆,这样他可以遵行积极教导:学会遵守部落规定、目睹并学会图腾仪式、背诵神话等”[4]79。只有经历这种“破坏性的重塑”调适,才可以获得新的知识和力量。
受礼者不可能长期处于游离的“边缘”状态,他们需要通过“聚合礼仪”重新聚合或回归到日常的生活里。刚果伊肖戈人(Iohogo)在生了双胞胎过后,孩子和母亲所使用的餐具皆为禁忌,他们居住的茅屋门框上要挂上一块布,门槛边钉一小排涂成白色的木桩,将他们与村落中的其他人隔离开,要经历长达六年的边缘期。当孩子长到六岁时,为他们举行聚合礼仪:脸和腿被涂成白色的女巫和母亲从禁忌的茅屋门口,一个慢节奏击鼓、一个唱歌走向街头,当天晚上,还要邀请全村人聚集到一起唱歌、跳舞、喝酒。只有经历聚合礼仪之后,双胞胎才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到处跑动,与村里人一起生活[4]52。聚合礼仪是受礼者从边缘到世俗生活的必经阶段。
范·热内普将仪式的三个步骤归纳为“过渡仪式”模式,无所偏重的三个进程阶段构成了仪式的立体性模型。通过仪式进程的时空变化,个体或群体原本的社会状态、社会身份及生命任务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最终使生命体处于一种新的状态之中。但范·热内普并未花过多的心思对三个亚类型进行理论上的解释,而是将它们引入丰富的具体仪式案例当中,在仪式进程和仪式意义背景下揭示它们在整体仪式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这样的选择,遭致了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等学者的抱怨和批评,其实,这才是范·热内普对民俗学仪式研究的独到之处。
然而,过渡仪式却并非如此简单地按照“分隔-边缘-聚合”三阶段的线性次序进行,“为达到某种目的如何安排这些礼仪的相关顺序,在仪式过程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化,这取决于该场合是诞生或死亡、成人或结婚,但差异只存在于细节中,其深层组合始终如一”[4]190。在范·热内普看来,不论是个体的一生还是群体的生存发展,“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地位上都时时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特别是在两个精神世界(平凡或世俗与神圣或宗教)之间的过渡”[5]。因此“过渡仪式”理论始终围绕着“平凡或世俗与神圣或宗教”的二元世界观展开。在过渡进程中,受礼者与世俗世界的分隔即是向神圣世界的聚合,与神圣世界的分离也即是向世俗世界的回归。那么,在分隔与聚合的边缘必然面临着“边缘”的确指问题:边缘究竟是神圣状态抑或是既非神圣也非世俗的模糊状态?范·热内普察觉并承认分隔进行的同时也在聚合——“这些礼仪的目的是将新生儿与亡者世界分隔,同时与生者世界或特定群体聚合”[4]58,但他对此却并未用心。然而正是范·热内普的这种“未展开”的“留有余地”,为埃德蒙·利奇、玛丽·道格拉斯、维克多·特纳等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三、“过渡仪式”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范·热内普“过渡礼仪”模式是从时间的纵向和空间的横向上来建构该仪式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因此,过渡仪式既是时间上的“过渡”,又是空间上的“通过”。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这种“过渡”都涉及存在于神圣与非神圣、世俗与巫术-宗教之间的一个悬而未决的“边缘”状态,埃德蒙·利奇称之为“非正常”,所以他将从“正常生存方式”中经过分离仪式出来的个体或群体看成是“存在于非正常时间中的非正常人”[1]80。埃德蒙·利奇完整地接受了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的三阶段模式,且在过渡仪式的时空理解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时空都是相对而言的,仪式时间和空间是一种与正常时空相对的“非正常”状态,且这种非正常状态是一种“为神圣所传染”的、危险的、“脏”的状态,因此仪式中的人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聚合仪式才能使其“洁净”地回归到正常生活中(见图2)。由此不难看出,他试图将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和埃米尔·涂尔干的“神圣与世俗”二元观进行融会贯通。
埃德蒙·利奇将时空相对观念引入过渡仪式之中是对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的进一步解读。同时,他认为“由于社会时间的每一次间断都是一个时期的结束和另一个时间的开始,并且由于‘出生/死亡’是‘开始/结束’的不言而喻的‘自然的’表现,因而死亡和再生的象征适合于所有的过渡仪式”[1]82。那么,仪式整体的三阶段意味着象征性死亡、仪式性的与世隔绝时期和象征性再生,从而显现出生命的动态性。

图2 利奇的三阶段结构图
英国另一位学者玛丽·道格拉斯也同意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洞见,并将三阶段的仪式结构观导入自己的《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一书中。她认为处在边缘状态下的受礼者就如同在社会系统中没有获得自己的位置一样,是一种边缘的存在(marginal being),过渡状态正是这种“无位置”状态,它因而无法被定义。且这种无法被定义的边缘状态(或阈限状态)同时也是危险的状态,不仅是“从一个状态走向另一个状态的人本身处于危险之中,并且向他人发散危险”。但庆幸的是,“危险由仪式所控制,而仪式精确地将他同他过去的身份分开,将他暂时隔离,然后当众宣布他进入了新的身份”[7]121。她用很简洁的言语将仪式进程顺序及其社会功能描述得非常清楚。
然而玛丽·道格拉斯似乎更倾向于“分隔仪式”,她认为“处于阈限就是同危险相接触,就是处于力量的来源处。这与那些有形与无形的观点正相一致。它把那些从隔离状态出来的男孩看作充满力量,炙热,危险,需要绝缘,需要平静下来。污秽、猥亵和违法与隔离的仪式在象征意义上和其他对他们状态的仪式表达一样有意义”[7]122。因而,过渡仪式中的聚合意味着一种分隔或隔离,否则“他就将永远跟其他那些被定义为不可靠、不可教育以及所有对社会抱错误态度的人一起处于边缘”[7]123,而被永远地置于正常社会系统“外面”。分隔仪式自然而然地显现了其至关重要的一面。
无论是埃德蒙·利奇还是玛丽·道格拉斯都把三阶段的理论应用到对二元分类的研究上面,强调受礼的生命个体或群体在正常与非正常二元世界之间的过渡问题,且试图在边缘的模糊地带找到解决的答案,但更多的只是对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的一种应用和加强。他们虽然也涉及到了仪式与社会系统(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讨论,但远不及维克多·特纳对该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展。
维克多·特纳在仪式研究上所使用的概念基本上是袭用了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体系的原始意义。他首先对范·热内普仪式过程三段论的两种说法进行取舍,直接引用“阈限前”、“阈限”和“阈限后”等术语取代了范·热内普更为热衷的“分隔”、“边缘”与“聚合”三阶段说法。在他看来,范·热内普所称的“通过仪式”的“阈限阶段”,就已经展示了这一个主题的性质和特点。因此,他对第二个阶段,即阈限阶段的重视成为其仪式理论的一个特色,解决了范·热内普各类“边缘”未展开讨论的问题。
维克多·特纳在研究非洲恩丹布人的仪式中发现,仪式在阈限阶段表现出模糊不清的状态,阈限或阈限人的特征也受此影响而变得“模凌两可”(betwixt and between)。通过对各种实际仪式结构的解构与总结,他强调阈限阶段是仪式过程的核心部分。如果说我们的基本社会模式是位置结构模式的话,那么它即是处于“结构”的交界处,既不完全隶属前一个阶段,又不属于后一个阶段,是一种处于两个稳定“状态”之间的转换[6]314。这样既强调了“‘结构’与‘反结构’的共时性存在,同时也强调了‘结构-反结构-结构’的历史过程”[8]。因此,他对阈限的投入,跳出了范·热内普显得有些刻板的理解模式,使这套理论体系更加纯熟。
阈限阶段是一个模糊不定的、神圣的仪式时空,在这个时空及处于其中的人员会从“类别(即正常情况下,在文化空间里的状态和位置进行定位的类别)的网状结构中躲避或逃逸出去。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在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9],基本没有阈限前或阈限后的社会文化生活所具有的那些明显特征。因此,世俗社会生活中的种类和分类不复存在,各种行为准则在此被“暂停”,人们处于平等的、颠覆的“反结构”状态之中。由此,维克多·特纳提出了另一个处于阈限之中而不可忽视的存在状态——“交融”,它是一种“反结构”的社会安排,去除一切社会结构赋予的身份象征——语言、形体和性等,使受礼者交替体验结构与交融,最终协助实现结构的有效运行。阈限与交融由此而成为维克多·特纳仪式理论体系里不可分割的两个关键性概念。
维克多·特纳的研究并不仅限于此。他认为过渡仪式不只限于文化上规定的人生转折点上举行,还可用于部落出征、每一年的季节交替、政治职位的获得、秘密社团的加入等社会性活动当中,从理论高度对范·热内普杂乱无章的过渡仪式进行了总结。他还认为,仪式的阈限阶段可以是公开的、大众化的,也可以是隐秘的、与世隔绝的。他特别强调,这个阶段并非一种单纯的存在状态,而是一个过程。这一论说加强了人们对过渡仪式理论体系的动态学理解。
维克多·特纳注重将各种学科理论导入仪式分析之中,他既继承了范·热内普的仪式阈限理论,又借用了结构主义的框架和概念性工具。尽管“阈限”与“交融”的提出深受范·热内普的启发,但在结构与反结构之间转换的讨论加深并弥补了范·热内普仪式研究中较为单一、刻板的毛病,也直接影响了后来学者对于仪式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四、结 语
范·热内普用“过渡仪式”(或“通过仪式”)术语来表达仪式进程中的“过渡性”,即“改变状态或是地位,或为人或为季节,或为集体的或为个人的”[10]。正如“在一个社会中,人的社会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被赋予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些社会性的获取并不是当一个人达到某个年龄段就自然具备,而是需要‘通过’仪式来赋予”[11],过渡仪式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范·热内普在对丰富仪式资料的总结中洞察了仪式的“过渡性”机制,将其深化并形成具有深远意义的过渡仪式理论体系,从动态学的角度丰富了人类学、民俗学的仪式研究。尽管在仪式研究历史中,莫斯和俞波特(Hubert)在献祭的讨论中较早采用了“过渡性”的解释理念,但直到范·热内普才使“过渡性”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走进人们的视野。继他之后,马克斯·格拉克曼、玛丽·道格拉斯、埃德蒙·利奇、维克多·特纳以及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2]等后继者对该理论体系进行了批判、丰富与发展,使之成为一种经典,并影响现当代中外学者关于仪式研究的讨论。
无可否认,范氏的过渡仪式理论在人类学、民俗学及宗教学界的仪式研究中影响重大,但仍难免学界的各种“非难”,如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就曾直言该模式忽略了“女性”的存在,仅考虑社会中与男性相关的仪式进程[13]。无论怎样,该理论的出现首先使仪式不再作为功能性因子而被囫囵吞枣式地看待,人们开始重视仪式过程本身,将其作为社会过程的有机整体置于社会生活的实际场景之中加以关注;其次,让人们看到了过渡仪式并非简单的线性进程,“它与个人和群体之生活地位的改变有关”。因为在各个社会里,过渡仪式扮演着对此种与彼种平衡的调试角色,通过“分隔-边缘/阈限-聚合”的仪式进程,整体上使个体或群体从时间线上、空间广度上、文化制度上、社会机制上甚至在巫术-宗教性上实现“过渡”或“通过”,使社会和文化上的过渡及转变变得顺理成章,角色、地位、状态等获取“合法化”。
尽管过渡仪式理论体系在后继者们的努力中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仍可发现,在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体系中,“三段论”对“过渡仪式”及其过程的解释力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种完善不仅是看到在每个独立的进程中包含着相对独立的“三阶段”,而且可以根据“三阶段”的分割机制不断地进行再分割。这样的认识主要基于现实仪式当中总是包含着一些次级仪式,而每个次级仪式之中也都会包含完整的仪式过程:“分隔-边缘/阈限-聚合”。然而,建立在时间和空间基础之上的过渡仪式理论体系也给这种“完善”带来了难题。因为宽泛时空观上的过渡仪式既是时间上的“过渡”,同时也是空间上的“通过”,甚至还是文化、制度、经济等多个维度上的转变。因此,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体系应该是在多维的生活空间中,多向度、多层次、多维度的“过渡”或“通过”,而非简单的线性进程,也绝非一个简单的图式所能表达清楚。那么,这种三阶段的“分割机制”将要进一步延伸就存在其必然的难度,无法掌控其走向。尽管如此,在现代多元的时代背景下,从“多向度、多层次、多维度的过渡或通过与多层级的‘分割机制’”对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进行解读,正是对其《过渡礼仪》一书开篇提出的多维仪式分类的积极回应。
[1]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M].郭凡,邹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M].林宗锦,彭守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6.
[3]韦冬妮.维克多·特纳及其仪式理论[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11.
[4]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M].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张举文.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J].民间文化论坛,2006(3):27.
[6]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7]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剑波,卢忱,柳博赟,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8]张帆.特纳与仪式理论[J].西北民族研究,2007(3):108-112.
[9]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5.
[10]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M].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4.
[11]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86.
[12]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M].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
[13]LINCOLN B.Emerging from the Chrysalis:Rituals of Women’s Initiation[M].New York and Oxford:Oxfrod University Press,199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