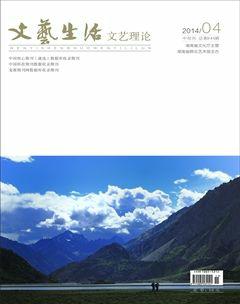论沈从文小说《生》中“笑”的艺术
2014-06-27陈鹏宇
陈鹏宇
(浙江传媒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论沈从文小说《生》中“笑”的艺术
陈鹏宇
(浙江传媒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沈从文的小说一向以冲淡平实的叙述来处理激烈的矛盾冲突,回味无穷。本文试图以沈从文的短篇小说《生》中对“笑”的描述上,通过分析五种“笑”的模式,发掘出沈从文笔下对悲剧那种以乐写悲的特殊处理。
笑;冲淡;以喜衬悲
生的滋味是什么?生时,别人在笑,你在哭,去时,你在笑,别人在哭。一哭一笑,就是生的全部。
这是一幅平常的“生”的图景。一个老艺人在表演傀儡戏,表演他死去的儿子和人斗殴的场景。一演便是十年,老人的“生”寄托在这场戏中,显得寂寞和无奈。
生的全部是“哭”和“笑”,《生》这部小说里没出现“哭”,但出现了十五个“笑”。正是这区区十五个字,便将当时整个社会环境,整个民众心态表露无遗。同时,文学是道德的,即是“本能冲动转化为文化形态的高级形式”,所以道德标准也就是衡量文学是否称其为文学的根本性。沈从文对时代的把握相当准确,他通过几个“笑”字,清晰地描绘了北京底层人民的生活,强烈地控诉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民的麻木,无奈,不能主宰自身命运的生存状况,对老艺人的同情,也寄托了作者对寂寞无言的“生”的叹息,一幅属于那个时代的图景跃然纸上。
首先,是社会民众木然的笑。
一样是写下层社会的日常人生,同时期老舍的眼光是批判的眼光,以一个改革者的眼光来看待人性,而沈从文则并不那么激烈,相反以温和的心境,尽量看取人性中的真与善。文章开头就交代了“有一圈没事可做的闲人”,或许这就是当时社会情况的的真实写照。《塘沽协定》签署后,国难当头,首当其冲的北平如此休闲。当然,我们不能确定沈从文描写的是1933年9月的北平,但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文学艺术必须是与现实条件相联的,脱离开现实生活则失去其生命力。”卢卡契也这样认为:“艺术作品是对现实的整体性批判”。可以说沈从文即使没有描写当时的社会情景,创作心境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制约作品的主旋律。“卖玩具人”笑咪咪地数钱,看客们百无聊赖地笑着,从“嘻嘻地笑着”到“场面上起了哄然的笑声”再到“众人又哄然大笑”,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人们颓废地欢乐着,他们每天生活就如同经历滑稽戏一般,麻木地,无生命地过着日子。他们认识不到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认识不到自己快要成为亡国奴,也认识不到做为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和职责。这群嘻笑派似乎和《孔乙己》里面短衣帮“快活”的笑一样,可怜可悲又可哀。
其次,是知识分子迷茫的笑。
鲁迅的小说中所描绘的知识分子的形象,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可悲性。例如《白光》中的陈士成,《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等,但是着眼点是否定和拒绝传统文明,强调和突出现代文明。与此相对,沈从文则是完全放弃了“五四”精神和灵魂,对即将到来的新社会持怀疑意见,所以笔下的知识分子往往是边缘化,模糊不清的。究其原因,这和沈从文的人生经历有关。
沈从文少年只身去北京求学,却不如意。但这些并没有造成他创作上的改变,他的人生的重大转折发生在上海租界的生活。
在李永东的《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里这样描述沈从文在租界的认识:“沈从文在个体生命的存在形态上,有感于都市人生的异化和堕落,崇尚乡村生命的自在自为,和谐健康”,“沈从文对都市文化的反思,不是在北平触发的,而是置身在上海的租界后才有的。”正是沈从文这样对现代文明的质疑,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大量描写乡村,文化底层人民,而对知识分子则做边缘处理。
“来了一个人,正在打量投水似的神气,把花条子衬衣下角长长的拖着,作成北京城大学生特有的丑样子,在脸上,也正同样有一派老去民族特有的憔悴颜色”。“打量投水”、“丑样子”、“憔悴颜色”,这样带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语言,可见沈从文对掌握未来文明的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好感。似乎当时的知识分子每天都在想如何救国,却不知从何下手,困惑、迷茫,却无能为力,只能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呆二”样,即使在笑的时候也是“忧郁”的。他们忙忙碌碌,脑子里思考的却是使人变傻的问题,而真正的、迫在眉睫的现实却又让他们手足无措。可以看出一个细节,就是《生》里面唯一几个泛贬义的词,都用在描写“大学生”身上,哪怕是剥削者巡警,也都被处理得“样子特别乐”,比较友善,作者的感情倾向显露无遗。
此外,是统治阶级嘲弄的笑。
全篇唯一的统治阶级就是巡警,在往常的人物塑造中,这样的剥削者无非是凶神恶煞一般,一副丑陋的嘴脸。但在《生》这部作品中,巡警没有像其他同类人物形象一样,猛地冲进去,把摊子掀翻或者拳打脚踢,而是非常和谐地观看老人的表演,直到一局表演结束,还是老人首先醒悟,如实交出地摊捐。巡警被塑造得相当友好,边走边回味老人表演的场景“王九王九”,甚至还笑咪咪地在人们作鸟兽散后唯一的观众留下来欣赏老人的下一场演出。那么他是在同情老人吗?并非如此。沈从文其实是在借巡警之“笑”,这种温柔冷暴力来反映社会的黑暗。这里认为虽然老人极力想掩饰他在表演自己儿子和赵四之间十年前的斗殴,但是巡警似乎已经知晓一切。他“轻轻说着王九王九”似乎是勾起了从前的回忆。这第一次笑或许只是被这出滑稽戏和被其中这个王九的名字逗乐。然而最后终于想起王九原来是十年前被打死的人,但这个老头子极力想表现王九把赵四打败,他这才笑咪咪地观看这个老人继续表演。巡警摇着头笑着走了,赵四五年前害黄疸病死了,说明杀人凶手出事之后依然逍遥法外,这里不得不引人深思,那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再者,是卖艺老人寂寞的笑。
卖艺老人不住地和他的傀儡,也就是精神上的儿子“王九”对话,即使“场中剩了七个人。”他也“微笑着,一句话不说”继续表演,“同傀儡一个样子坐在地下,计数身边的铜子,一面向白脸傀儡王九笑着,说着前后相同既在博取观者大笑,又在自作嘲笑的笑话。他把话说得那么亲昵,那么柔和。”实际上都反映了老人内心的的寂寞,也是作者一直渲染的情绪。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感受表达了多少生的无奈。儿子死了,作为父亲已经没有能力去挽回他的生命,甚至思念也无处倾述的时候,只能将全部的生命放在这场傀儡戏中。而他所能做的,也仅仅是“只让人眼见傀儡王九与傀儡赵四相殴相扑时,虽场面上王九常常不大顺手,上风皆由赵四占去,但每次最后的胜利,总仍然归那王九”。这场虚幻的胜利就是老人余下“生”的全部,让人想起契诃夫笔下对着老马诉说心事的车夫,那么悲哀,又如此寂寞。又恰如艾青的诗句:“寂寞得像老人的心。”这里对老人的描写,正体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关怀,当一个平凡的人,失去了现实的信仰,那么只能在幻想中得到安慰,构成活下去的理由。傀儡已经不是傀儡,而是王九的重生。人与傀儡同化了,不也正是反映了当时那些人民的傀儡人生吗?老人和傀儡王九就是当时人们内心的缩影,生在自欺的梦境中,活在被社会随意的操控里。
最后,是命运之神无情的笑。
这是文中没有出现的笑,但却是作者最终想要表达的。老人是否恨那个打死自己儿子的“赵四”,常理当然是恨得咬牙切齿,因为是“赵四”造成了自身的寂寞。但是文中最后一段:“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那个真的赵四,则五年前在保定府早就害黄疸病死掉了。”出人意料的结尾,升华了全文的主旨。这个年迈的老人,失去了爱的对象,也失去了恨的能力。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即使是那个打死王九的罪人,也抵不过人生命运的浮沉。使老人寂寞的,不是身边没有最爱的人陪伴,而是命运无情的嘲弄,它在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主宰着我们的“生”,这种没有爱,也恨不起来的空虚沉沉地压在每个读者的心中,显得老人这个形象更加凄凉,落寞。作者没有叙述王九和赵四打架的过程,就在于这一切都是不重要的,谁对谁错也无需计较,因为他们都在承受着自己的命运,预料之中或预料之外。与此同时,作品也饱含对社会的批判,对底层人民的怜悯和关怀,并以悲戚的眼光注视着在“生”的浪潮下起起落落的人们。《生》的艺术价值是不朽的,一如台湾作家白先勇所说:“如果要我选三篇‘五四’以来三十年间最杰出的短篇小说,我一定会选沈从文一篇,大概会选他那篇震撼人心的《生》。”
[1]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2]扬·克诺普夫.“问题的实质是现实主义”——关于布莱希特与卢卡契的论战[J].北京:外国文学评论.1990,(3).
[3]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4]艾青.冬天的池沼.选自艾青诗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5]白先勇.天天天蓝.选自白先勇文集·四[M].广东:花城出版社.2000.
I247
A
1005-5312(2014)11-0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