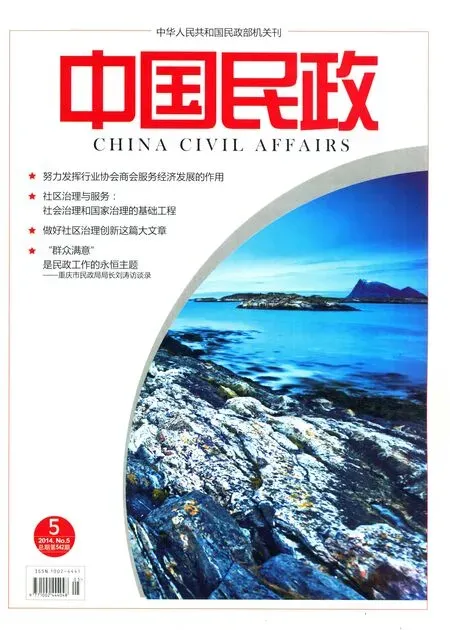媒体热点
2014-06-23
媒体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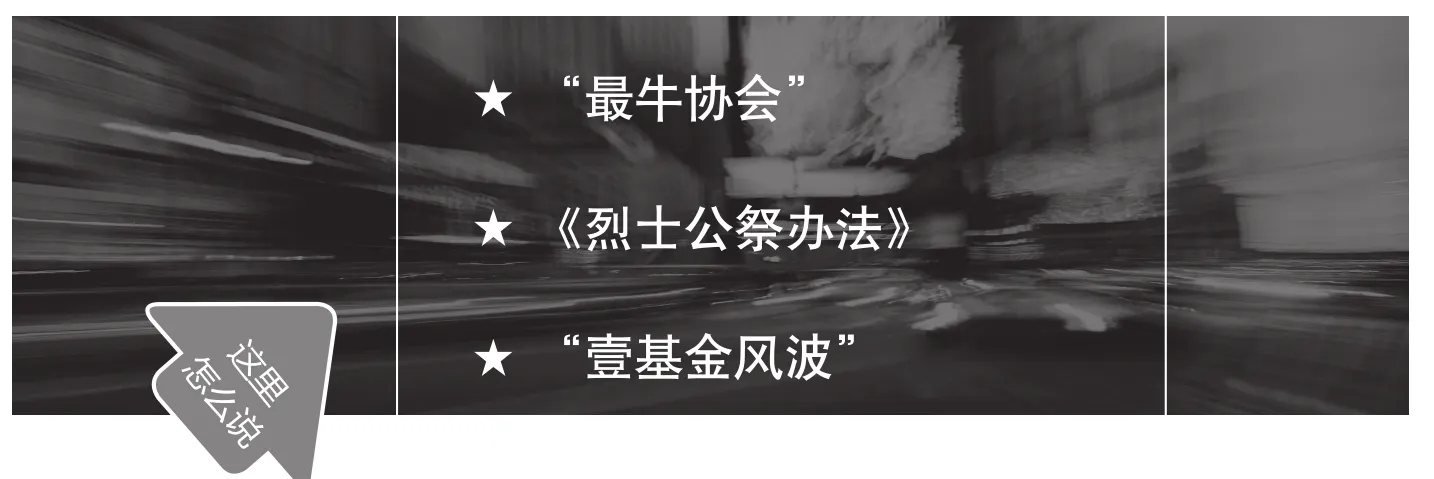
★ “最牛协会” 给行业协会的管理敲响了警钟
在百度中搜索“行业协会”词条,我们可以准确地了解它的定义:行业协会是指介于政府、企业之间,商品生产业与经营者之间,并为其服务、咨询、沟通、监督、公正、自律、协调的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是一种民间性组织,它不属于政府的管理机构系列,而是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属非营利性机构。4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南省长沙市建筑业协会某分会发公告要求企业交钱登记、评级,否则不允许承接经营业务的新闻。新闻立刻引发了媒体强烈关注,该协会也被戏称为“最牛协会”。
一位企业代表向新华网反映,协会公约有些完全没有可操作的执行标准,但实施细则上则说“本办法由长沙市建筑业协会建筑施工设备租赁分会负责解释”。可见协会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权利空间。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邵余良在新华网发表评论认为,行业协会履约保证金制度应该建立在自愿、协商原则上,而且操作一定要有严格的规范,要防止成为协会用来单方面对付会员单位的“紧箍咒”。作为行业协会,必须遵循政会分开、自主办会、民主办会的原则,警惕行业协会依托主管单位的权力,垄断经营,强制服务,强行收费,破坏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羊城晚报》则颇为调侃地评论道:协会的作用应该是企业间“抱团取暖”。遗憾的是,现在“抱团取暖”变成了“组团挨宰”,入会就得交钱,不交钱就做不了生意。该会和安监站联合发出公告,一下子就让协会的公告成了官方规定,有了强制力。说白了,人家玩了一招狐假虎威的把戏,企业不得不乖乖就范。当然,这“狐”可不是骗人的狐狸,而是退了休的真“老虎”。协会简直成了第二安监站。行业协会一旦成为行政机构的“下属单位”,那么很可能会站在企业的对立面,官方不方便办的事它可以办,官方不方便收的钱它可以收。而且,安监站的工作人员退休之后都有了去协会任职的后路,协会异化为安监站垄断的“买卖”。
《楚天都市报》从什么是真正的“最牛协会”,这个角度评论认为,协会存在是为了争取自身最大的利益,而不是成为某个附属品。但现实的尴尬却是,绝大多数的协会背后都隐现着官方的背景,市场需要的不是成为管理部门代言的 “最牛协会”,而是能够成为企业代言,敢于用市场的规律向不规则的管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牛协会”。

《法制晚报》从对政府公信力影响的角度评论认为,为进一步激励中小企业发挥自身活力,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已经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然而就在中央简政放权这一大背景下,长沙市建筑业协会建筑施工设备租赁分会却逆时代潮流而动,甚至还规定“企业不交钱就禁止营业”,简直令人愤怒。按照国家规定,有相关部门认可的经营资质和营业执照,企业就能开门营业。但按照该协会规定,在满足这些前提之外还必须登记、评级,由此看来这已经与国家规定产生抵触。换句话说,即便到协会去登记也应该是自愿行为,这种不登记、不评级就无法经营的荒唐规定,是在人为设置门槛。人为设置企业发展门槛,不仅会阻碍企业发展,甚至还会破坏政府公信力。
总之,“最牛协会”给行业协会的管理敲响了警钟,无论从企业的发展、管理的规范和杜绝权力寻租等多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研究案例。相信通过处理此案例的过程,今后对其他行业协会的管理可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将坏事变成好事、从教训中学到经验。
★ 《烈士公祭办法》 汲取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3月,我国首次大规模迁回境外烈士遗骸的国家公祭事件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专家曾建议以此次迎接遗骸回国为契机建国家公墓,并设立纪念日。4月1日,民政部网站就公布消息称:为推进烈士公祭活动规范化、法制化,通过烈士公祭活动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倡导奉献意识,民政部近日在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了《烈士公祭办法》。这次《烈士公祭办法》的出台,获得了一片赞誉。
新华网报道,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长期以来,各地高度重视烈士褒扬工作,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开展多种形式烈士纪念活动,社会反响良好,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但同时也存在开展烈士公祭活动差异明显,以及组织不得力、程序不规范、礼仪不庄重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烈士公祭活动的氛围和效果,亟待从法制层面予以规范。
《法制日报》发表评论,铭记先烈属于道德范畴,但离不开制度性平台作为保障。这其间,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个人应当履行什么义务,都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出台可以操作的具体措施。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开展公祭活动,除了缅怀先人,就是要用逝去的人教育现代人。官祭兴则民祭旺。“缅怀始祖,铭记先烈”必须发挥官方的带头作用,通过示范激活全民参与。仪式是精神表达的载体,只有公祭活动发挥了风向标的作用,民祭才会真正得到激活,并让祭奠这种道德表现创造出强大的精神力量。《烈士公祭办法》出台的重大意义在于能够为我们祭奠先祖、先人提供可以借鉴的样本。可以说,在缺少国家层面的清明礼俗和仪式架构的当下,这样的制度安排具有标志性意义。
法制网发表评论认为,公祭活动在生活中正走向两个极端,有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形式主义,在祭奠活动中讲排场,例如广受争议的公祭炎帝、公祭黄帝、公祭大禹等活动,这些活动通常由地方政府主导,其目的就是为招商引资,但往往公祭后商没有招来钱却花了一大把。与这些轰轰烈烈的祭拜神话里的祖先相比,真正为现代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民英烈却被冷落,一些地方的烈士陵园几乎荒芜,甚至出现烈士陵园要为开发商腾地的事件。在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宁愿祭奠莫须有的先祖,也不愿真心诚意地祭奠革命烈士,这是扭曲的政绩观与跑偏的历史观作祟。让公祭走向法制层面,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制定标准的程序,让公祭的质量不打折扣,一方面可以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让社会监督活动的开展符合办法要求。
《常州晚报》发表专题文章,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而不知景仰的民族,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英雄为他所处的时代作出巨大贡献,他们的精神穿越时空,值得我们学习、纪念。纪念先烈,缅怀英雄,以公祭来强化一个民族的精神骨骼,会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坚实。
我们相信,民政部门此次出台《办法》必将推进烈士公祭活动规范化、法制化,并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倡导奉献意识。人们将从中汲取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 “壹基金风波” 折射我国慈善基金发展之困
4月底至今,又一场“信任危机”在中国公益界发酵,矛头直指壹基金。事件起因是壹基金向社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据报告显示,该组织2013年共收到芦山地震定向捐款3.85亿元,截至今年3月31日,已发生捐赠支出约4907万元,捐款余额约3.36亿元。巨大的捐款和支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2日新浪微博“四月网”发出质疑,称尚未拨付的那3亿多元善款被“贪污”。一时间,中国的公益事业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金牛网发表评论认为,这些年,各类公益组织屡遭质疑,声誉不佳,而壹基金则因为管理规范、运作高效,成为人们眼中公益基金的标杆。因此,假如壹基金深陷丑闻,将意味着一个标杆的坍塌,这也是该事件引人关注的原因所在。在面对质疑时在第一时间自证清白,应当成为公益组织的一种惯例。
《法制晚报》评论认为,壹基金在慈善公益方面“受捐多,发钱拖”的情况是实情,这进一步显示我国慈善公益尤其是公益基金会生态链条尚不完善,相关法规与现实脱节。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说,从国际经验来看,基金会自我运作的效率普遍较慢,与专业的执行机构合作才是其应有的发展方向,国内现在是操作型组织太多,专门的资助型机构太少。

卓明地震援助信息小组负责人郝南则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认为赈灾是一个包含应急响应、紧急援助、过渡安置、灾后重建多个环节的复杂过程,而民间组织要做的是政府不做的或者做不过来的。花钱最快的是建设基础设施,但这主要是政府的职责。评价善款使用是否得当,不仅要看钱花的效率,更重要的是看钱花的效果。
齐鲁网则有网友持相反的见解:没有人主张把受捐款项立马花光,也没有人会赞成公益基金盲目投向,但是,募集善款时的急火火,支持赈灾时的慢吞吞,如此冰火两重天,效率低下表象的背后,显示出基金管理运筹者爱心、善心不足;一年多时间里才花出一成多,庞大的基金处于沉淀、闲置状态,自然难免让人怀疑。民间公益基金的使用避免与政府资源重复投放当然很有必要,但实践操作中与官方实现良性互动了没有?倘若政府投放相对充足,公益基金是不是就可以不出手、不作为了?钱花得精细、花在刀口上、花出最大的成效,无疑是应该着力追求的,不过显然不能成为花出少、行动慢的借口,灾区重建、群众生活最急切的时候,社会各方汇聚来的公益基金却在睡大觉,还有什么“精细”可言?
《中国青年报》则建言,“劝募许可”尽快立法。按照“劝募许可”制度的基本原则,公益组织只有在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救助方案,对项目救助对象、劝募金额、救助范围、实施方案都有明确规划,方能发起社会募捐。而社会公众在捐款的时候,也明确知晓自己的捐款将会用在哪些人身上,具体实施哪些帮助,这些帮助什么时候完成。这样的规定,对慈善公益组织透明化、建立社会公信力都会有极大的促进。“一事一募一账号”,即公益组织只能就一个具体的项目申请一次劝募,每次劝募必须单独在银行开设一个账号,劝募时间结束或者达到劝募金额,该账号就由金融机构自动关闭,不能再接收善款,以防止公益组织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公,有利于新生慈善公益组织的成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