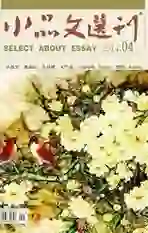感忆恩师
2014-06-10蒋建平
蒋建平
那一年,我6岁,刚进小学的学前班;她50岁,准备退休。
7岁以前,我一直呆在乡下的奶奶家。每天太阳快落下去的时候,奶奶便牵着我去割猪草,背着小背篓,一路上哼着没名儿的调调,在高低错落的田埂上蹦蹦跳跳,看见蒲公英鼓足腮帮子大力地吹落,扯下狗尾巴草求奶奶编小狗的模样。那时候以为村子就是整个世界,割猪草就是最大的快乐。这样的经历直接导致了我在上小学的第一天不得不被妈妈拿着火钳在后面赶着去学校,她在后面边走边骂,我在前面哭喊着“我要回家跟奶奶割猪草”。
她是我的学前班老师,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位语文老师。那时候学校安排班主任在门口接低年级的学生,我被她拉着走向教室。可能是在陌生人面前不敢哭闹,我倒是很乖地跟着她。我一边跟着走,一边不时抬头去看她,她总是笑着,剪个女士包头,黑发中夹杂着很多白发,阳光下白发显得很是耀眼,笑容也显得更加灿烂些,只是右边眼睛上长着一个瘤子,比较大了,多少遮住了眼睛,倒也不令我这个年纪的孩子害怕。“还看我呢,去上课吧,割猪草的小朋友。”她俯下身来看着我,依旧笑着。
上课并不是什么难事,我最愁的是下午放学前。老师总要求我们在下午最后一节课写当天的作业,写完给老师批阅过关了才能回家。长时间的“神游”加上7岁前并不像其他大部分同学那样接受了父母的早期教育,我似乎显得比其他同学要“晚发育”很多,每次放学我都是“雷打不动”地最后一个回家。很多时候因为写不出作业,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背着书包回家,我就会开始哭,越哭越大声。老师们大多在我一哭起来时就没了办法,只能催着我收书包回家,以免打扰其他同学写作业。但这对于她来说,又是一个例外,从第一次留下来写语文作业开始就是个例外。
那天,我照旧不会写作业,拼音字母歪歪扭扭地写得乱七八糟,擦了又擦,作业本纸都被擦破了。教室里的同学渐渐少了起来,我望了望讲台上的她,像前几次写其他作业那样,“哇哇”哭了起来。我抬头看了看她,她还是翻着手中的作业本,我顿了顿,鼓足气,哭得更加起劲起来。泪眼中她向我走了过来,我感觉自己的哭起了作用,心中开始窃喜。“不要哭了,你这招对我没有作用,前几次你写作业的事情其他老师都跟我说了。我不会因为怕你哭就让你回家,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想早点回家,你可以叫我教你。”我用手背抹了抹眼泪,小声抽泣着说“好”,心里却是一百个不愿意。她在旁边的座位坐了下来,拿过我的作业本,她叫我仔细看着,一边写一边跟我说着该如何起笔如何转弯如何结束。就这样她在每一行的第一个田字格里端端正正地写下五个元音字母,写完后推过来,“照着老师写的,你在老师写的拼音字母后面跟着写满一行,写完咱们就一起回家。”我接过她手中的笔,看着她在前面写的示范,又回忆她写时跟我说的过程,小心翼翼地写下了一个a,刚写下,就听见她说“好,很好”。我回头看看她,她正笑着看着我,一双眼睛仿佛闪着光,眼皮上的瘤随着她眨眼睛上下微微动着,倒是觉得很好玩。她总在我写下一个字母后表扬我,我就写得越来越快,下笔时候也不犹豫了,五行字母全部写完后,她几乎是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我听见了她的鼓掌声,虽然小声,却听得清楚,“你写得比老师还好,真棒!”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回应她,只是看着她笑,她捏了捏我的脸,用手背擦了擦未干的眼泪,“明天写作业不要哭啦,你看你明明就会做嘛,现在我们回家。”她用手背擦我脸时,我觉得有点疼,好像能感觉到了它手背上的细纹,却觉得暖暖的。长大后,才知道,那些细纹,因为总是接触粉笔的缘故,才会被刻画地那么深,那么糙。
后来,有大概半个学期的时间她都陪着我写作业,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学校给每个老师都配备一个火桶,早上起来在食堂借些火种燃起炭,晚上又用灰盖住保留火种。她总把自己带的火桶让给我坐,自己坐在冰冷的板凳上,看我写完。
大概一年级的时候,她离开了学校,我之后再也没见过她,只是偶尔听老师们聊天,说她跟着女儿到了北京去带外孙。她可能不知道,后来的语文老师都很喜欢我,每次考试我的语文成绩都是前几名,她可能也不知道,在其他同学还在為写作文看《作文大王》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已经叫我试着看《少年文艺》了,也开始鼓励我在县里的报纸上写些小作文。可是我知道,是因为她,因为喜欢她,我才喜欢上了语文这门课,也开始编织起自己的文学梦来。
选自《北京日报》2014年0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