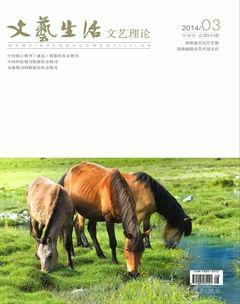《金瓶梅词话》中的多重宗教现象初探
2014-06-10胡晓莹
胡晓莹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4)
《金瓶梅词话》中的多重宗教现象初探
胡晓莹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4)
《金瓶梅词话》是一部以写实的描写劝诫世风日下中追逐财色欲望的世人的“世情书”的重要作品,其中存在着宗教的矛盾与异化,宗教已为人利用,成为谋生、谋权或招摇撞骗的保护衣。在《金瓶梅词话》多重宗教影响下,皈依宗教成为人生归属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作者再次向人们展现了自己的宗教观。
佛教;道教;多重宗教;人生归属
一、《金瓶梅词话》宗教的矛盾与异化
在《金瓶梅词话》中,宗教一方面继续发扬着宣扬善美摒弃丑恶的影响力,以教义戒律要求人们谨守伦理、不贪恋财色,一方面各种宗教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所需要,参与人们的生活,宗教自身继续着宣扬教义、发展信众,具有宗教独特的神秘性和庄重性,一方面又已明显地沦为了为人利用的工具,成为社会中特殊几类人群的谋生、谋权或招摇撞骗的保护衣。这并不是在《金瓶梅》所描述的时代与社会才出现的矛盾与异化现象,而是在一直以来的现实情境中早已有之,在元杂剧、宋元话本中也有部分体现,只是《金瓶梅》以其市井生活气息浓厚的特点和鸿篇巨制的规模将宗教传承、传播过程当中出现的普通民众因无知导致的对宗教的错误理解、盲目崇拜,宗教传播者因生活所迫或对资财权色的贪恋而对宗教擅自篡改和利用现象,结合了明朝社会的享乐、利己主义的盛行和资本主义萌芽刺激下对财色权势的过分欲求的社会大环境,似一面聚光镜将社会的百态特别是各种宗教整体性的异变呈现了出来。
(一)谋生、谋权或招摇撞骗的保护衣
在富户大家走动的尼姑便是这一类的代表。她们利用官家富户妻妾众多而关系到宠幸的多少、家业的继承等复杂而难以调和的这种矛盾,抓住了妻妾们的特殊心理和需求,便利用走家串户讲经宣卷的时机向妇女们兜售被渲染上了神异色彩的生子符药水,更有甚者,还利用施主家小孩生病的机会劝施主人家舍印陀罗经,本来印刷经书让更多人传颂无可厚非,但是两个尼姑为了争抢谁揽了这个事、谁拿了多少银子而争吵不休,作者明确写出她们是“六根未尽,本性欠明;戒行全无,廉耻已丧。假以慈悲为主,一味利欲是贪。不管堕业轮回,一味眼下快乐。哄了些小门闺怨女,念了些大户动情妻。前门接施主檀那(即布施),后门丢胎卵湿化(私生胎儿)”①。后文的泰山碧霞宫庙祝道士石伯才“专一藏奸蓄诈”,替殷太岁“赚诱妇女,到方丈任意奸淫”又印证了这一点。
(二)趋利拜金的崇拜心理的异化
和尚看见潘金莲后的一段描写“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维摩昏乱,诵经言岂顾高低。烧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烛头陀,误拿香盒……”只因为看见了“色”,画皮包裹下的一具粉骷髅,在为武大郎百日念经的和尚们个个意马心猿,作者对他们的描摹尤其是“宣盟表白,大宋国错称做大唐国;忏罪阇黎,武大郎几念武大娘。长老心忙,打鼓借拿徒弟手;沙弥情荡,罄槌敲破老僧头”一段,近乎荒唐的夸张,却能够把本应善守“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恶言”的戒律、不贪痴嗔慢,怀有慈悲之心解救众生脱离苦海,有宗教带来的智慧与道德标准的出家人在真正礼崩乐坏,商业文化与封建文化畸形的结合影响下的宗教异变表现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金瓶梅词话》中很大一部分标榜着宗教严格戒律与较高道德标准的宗教的崇奉者,并不是真正的虔心信仰求道,而是以染上铜臭的变形的生存方式寄生的世俗之人。
二、多重宗教影响下的人生归属选择
(一)及时行乐表象下肯定人性
在《金瓶梅》行文与多回回目下的回头、回末诗总是存在有一种固定模式,即前一部分是带有评论性的陈述故事情节或因果报应对人的规劝警告,最后两句往往是人生苦短、充满无常,应当及时行乐的观念,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但这正是作者的如椽巨笔,表面上的及时行乐如果不深切体味,就会如《金瓶梅词话》的《金瓶梅序》中所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其中后两者正是只看到享乐的奢靡光华,而非真正悟透此书真意。正如序中所举的少年观“霸王夜宴”而垂涎的例子,在书中,是存在有大量的“回头人”的描写的,所谓回头人,就是丧夫后的妇女可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选择再嫁,这与明代社会风气的开放和心学思潮的解放人性、肯定人性有关,加之道教讲求阴阳和气,肯定男女结合是阴阳交接之道的合理表现,体现的是一种与自然之理和谐相循的养生观和人与宇宙的同构相应。在书中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贞洁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又被运用得太过,不仅让传统礼教里的三纲五常荡然无存,而且让人为书中人物的违天理、人性泯灭为之扼腕。所以《金瓶梅》并非是以无限制渴求金钱权势、纵欲暴亡的悲剧来宣扬对人生的空幻、无欲无求和禁欲、绝欲,而是肯定符合情理的人生追求和正常的人性需求,避免七情六欲的过度放纵,达到人生在世精气神统一,身心和谐,对人生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的目的。“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正是作者写作意图最浅显明了的表达。
(二)宗教出世思想下的皈依宗教
佛教主张的修持佛法的三个基本原则“净业三福”里的第一福即为“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金瓶梅》的创作主旨在这一点上是遵循着这个原则的。为首的反面形象便是西门庆,而与之成为对立面的,敬修佛法用以镜鉴读者的则是与西门庆有夫妇关系的吴月娘。吴月娘的形象是一直作为一个对佛教有着虔诚的信仰、生平所行也大部分符合教义的形象来塑造,在她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妇女谨守三从四德的体现,尤其是
对于一生放荡淫乱的丈夫的从一而终,在妇德上对其他几房娘子的忍让与大度,对丈夫的劝诫等方面,吴月娘的作为是符合佛家修善业对修持者和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对妇女的要求的,当然在出嫁从夫的封建时代和人物自身性格缺陷的共同作用下,吴月娘眼见丈夫为所欲为只做劝说,并且不彻底,而且有些事情也间接参与,吴月娘的形象有其作为立体人物存在的缺点,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遵从宗教教义的人,但总体上来说,在这部作品里需要有这样的形象来表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的宗教观念。
西门庆在官哥病时恰逢道长老募修永福寺,月娘说道:“你日后那没来回没正经养婆娘、没搭煞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儿,却不儹下些阴功……”西门庆却说不了这样一段话:“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簿上注名……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从西门庆的狂言妄语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对佛法的因果报应与鬼神阴司的无知与无畏。
《金瓶梅词话》继承了传统文学形式当中的通俗文学的富有教育意义的特点,佛教经文的宣卷、元杂剧、三言二拍等作品当中的以因果劝诫和鬼神报应为教育目的。书中渗入大量宗教因素并不在于讨论皈依于哪一种宗教才是正途,作者的宗教意识是基于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在历史的传承、传播过程当中的相互吸纳、借鉴、渗透和影响。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在生命仪式中的参与可以体现在丧事当中念经超度亡灵、接引冥途,阴阳生推算凶吉邪崇、送殡,三者的共同参与表现出儒道会通、佛学玄化及诸家思想的大融合,道教的阴鸷说对于人的心性的要求建立在善恶的因果报应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为就是鬼神降予祸福的判断标准,道教的济度思想,受佛教轮回果报观念的影响,也关注在冥界的鬼魂的苦难。民间宗教在佛教道教的基础上构建完善自己宗教的体系。这些都是作者苦心的“世戒”。
陈经济的出家做道士更像是一场闹剧,全是因为家势颓败而自己又没有生存能力而被尚有仁慈之心的王杏庵介绍到晏公庙讨生活的。陈经济出家后在码头酒店的所作所为不惧清规戒律,而且还变本加厉,和岳父西门庆生前的淫荡所为相互映衬,也是一个可气可叹的玷污了宗教的神圣性的丑角。
吴月娘素常在家喜爱听姑子宣卷“说因果”,为了求子心愿吃了王姑子、薛姑子送来的求胎的药而坐了胎气,在怀孕时仍然听生死轮回之说,感得古佛日后出世度化受了佛法应召的胎儿,所以这个代替西门庆来悔过自新的孝哥的出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宗教出世思想的存在由来已久,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交融使得中国文人内心具有了生不逢时或壮志难酬时选择出世、向宗教里寻求精神寄托,当有施展机会时又积极入世的心态。而在书中,作者将各个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结合在一起,通过书中鲜活的人物形象来诠释出他的思想与祈愿,便形成了宗教出世思想下对宗教的敬仰观念,即人需在人生合理追求发展的进取与道的退守之间自如处之,又因为佛学的放下对人间权力、物质、欲望的“我执”,进而对众生怀有的慈悲之心,形成了既心怀天下忧乐荣辱,又情倾人间悲喜,既有此岸世界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善,又有关乎彼岸世界的通透到底的善的独特心理内涵。
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社会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已有了广泛的社会认可的基础,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当中,形成一种交融,在社会大环境下有共同的信仰氛围和认同感,《金瓶梅词话》中的多重宗教渗透进了上至帝王朝臣,下至平民百姓———社会所有成员的思维里面,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也就能够在社会生活当中被视为约定俗成。
随着时代的发展,宗教教义对无所畏惧、寻欢逐乐、追求无边无际的欲望满足的世人的警示还会发挥其劝诫功效吗?人生的怪诞、变形、异化,天道的长久不行,正体现着一种人间看不见的天崩地裂,而这种天崩地裂正动摇着社会的根基,腐坏着世道人心。究其根源,其实是社会秩序、道德伦理、真情真爱的严重破坏丧失。如何重建人间的正常秩序,重创清明顺正的人间正道,应该怎样对正常合理的物质需求、身心和谐和亲情爱情有正确的认知,摒弃贪婪罪恶的人生追求,寻求向善、有爱、讲求道德、伦常的世道人心,正是作者所探索的问题。
“世戒”非“世劝”,相较起来,“戒”比“劝”力度更大,程度更深,不再是老生常谈,容易使人反感的,以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和人物的失败与毁灭进行警示,让人们从文学人物身上找到与自己的共通之处,通常有类似经历与思想的描写就会自然而然地投射到读者身上,从而进行读者对人物形象、作品主旨的理解、加工和再创造。总体来说,这不是一本宣传宗教的文学作品,仍是为惩戒淫奔贪欲、草菅人命等不当行为进行更正,用以规诫世人立于世间多做善事少有恶行。通过阅读这一部作品,能于极端的奢华、迷乱的生活,对物质、享乐、财色、权势的盲目追求到突然间生命、权势、富贵的失去的幡然醒悟,自身思想修为达到一定高度,达到精神的独立自足而非空虚,道德上的趋善完满,保持人性最纯良的本质,谨守维护、恢复正常社会秩序与道德伦常的使命,使得社会恢复正常、人性归复淡泊和良善。
注释:
①引文据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下文所引例句,亦皆据此书,不另注。
[1]鲁迅,郑振铎等著.名家眼中的金瓶梅[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9.
[2]郑志明.道教生死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8.
[3]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4.
I206
A
1005-5312(2014)08-0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