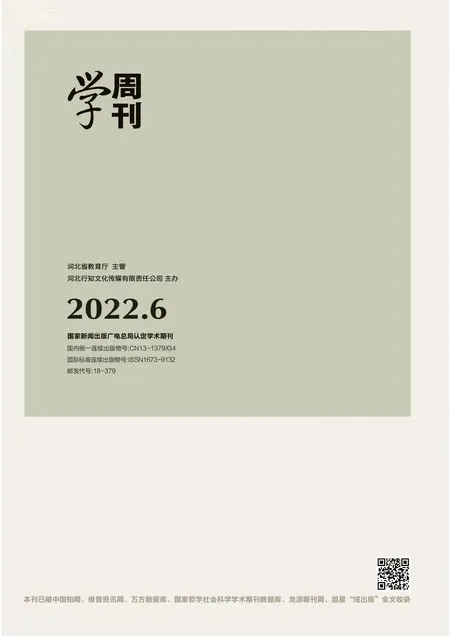从“穈”字的读音说开去
2014-05-30姜天智
姜天智
胡适的《我的母亲》(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册,简称“人教版”,下同)中有这样一句话:“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其中,“穈先生”的注释发生了两次变化。2002年12月第1版是:[穈(mén)先生]胡适小时候的名字叫“嗣穈”,爱称“穈儿”。后来,课本修订改为[穈(méi)先生]胡适小时候的名字叫“嗣穈”,昵称“穈儿”(2008年7月第3版)。这则注释有两个变化,其一是将“爱称”改为“昵称”。《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5版,下同)中“爱称”是“表示喜爱、亲昵的称呼”;“昵称”是“表示亲昵的称呼”,实在很难令人看出二者有什么区别。其二是注音的变化。《现代汉语词典》中“穈”字是作为“糜”的异体字,读作“méi”,没有“mén”的音。胡适的《我的母亲》节选自《四十自述》中的“九年的家乡教育之五”。在“九年的家乡教育之二”中有“(父亲)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天资聪明”的记述。作者自注“我的名字叫嗣穈,穈字音门(亚东版)”,这应该是课本最初注音为“mén”的主要依据。但为什么后来又改为了“méi”呢?可能是教科书的编者发现(或者有教师、学生发现,我也曾经就这个字的读音给人教社写过信)《现代汉语词典》“穈”字没有“门”的音,只有“méi”的音。为了避免纷争,教材编著者索性将注释的读音改为普通话读音。
“穈”的读音情况有点复杂。胡适的大哥名叫嗣稼,二哥叫嗣秬(jù),三哥叫嗣秠(pī),胡适小名叫嗣穈。兄弟几人的名字都取自《诗经·大雅·生民》。原句为“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康熙字典》中“穈,《集韵》谟奔切,音门,赤苗嘉谷。康成曰:‘穈,赤苗也,芑,白苗也;郭璞曰:‘穈,赤苗粟也,芑,白苗粟也。”《诗经注析》(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秬(jù巨),黑黍。秠(pī披),黍的一种,一个黍壳中含有两粒黍米。穈(mén门),谷子的一种,初生时叶纯赤,生三四叶后,赤青相间,生七八叶后色始纯青。”“汉和帝时,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实,实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则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别名之为秠。(《辞源》‘秠条转引自《十三经注疏》)”由此可见,秬、秠、穈都是粟(即谷类)中的嘉苗(好种),表达了胡适父亲对孩子的美好希冀,希望他们成为家族的好苗。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穈”就应该读为“mén(音门)”。注释中将注音改为“méi”是缺乏说服力的。课本的注释应该尊重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如果担心引起误会,可以一分为二,旧读为“mén(音门)”,现在普通话读做“méi”,是“糜”的异体字。在不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将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字音直接改掉,这是不尊重历史和文化的。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中,关于“朱文公”的注释,课文注为“朱文公是朱熹的谥号”。翻检《宋史·朱熹列传》有“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文”,也就是说“文”是朱熹的谥号,而“朱文公”是后世对朱熹的尊称。“朱”是姓,“文”是谥,“公”是爵位。将“朱文公”注为朱熹的谥号,容易给学生造成误会。
《邓稼先》(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一文中引用了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其中“亭长”的注释值得商榷。“亭长”秦汉时十里一亭,亭长掌管捕盗。唐代为管理治安的小官。《大唐六典》卷一“三师三公尚书都省”中有“亭长六人”的官员设置。“亭长”的记载是“亭长六人(汉因秦制,每十里一亭,亭有长。高祖为泗上亭长。隋文帝始采古亭长之名以为流外之号,皇朝因之。主守省门,通传禁约。)”“流外”指九品以外,俗称为“未入流”。唐代亭长的主要职责是看守省门,通禀报事,似乎并无管理治安的职责。“战国时始在国与国之间的邻接地方设亭,置亭长,以防御敌人的侵扰。至秦、汉时每十里设一亭,置亭长一人。掌治安、诉讼等事,并监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多以服兵役期满的人充任。《史记·高祖纪》:‘为泗水亭长。《正义》:‘亭长,主亭之吏……盖今里长也。汉高祖刘邦即曾为泗水亭长之职。此外,城内和城厢的‘都亭,城门的‘门亭,也设亭长,职责同上。隋、唐采用古亭长之名,作为流外的称号。在尚书省各部衙门设置,负责省門开关和通传等事务,其职务与秦、汉时的亭长不同。(《简明古代职官辞典》孙永都,孟昭星编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综上所述,唐代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都事、主事(从九品)之下设亭长,掌管省部的门户开关和通报传禀事务,是中央官署中最低级事务员,而无管理治安的职责。唐代的亭长与秦汉亭长职责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一点在注释中是应该强调的。
注释应该以晓畅明白为要,给读者以清晰的理解为宜。尊重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应该成为注释的要义之一,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
(责编 张翼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