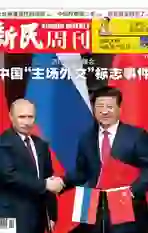走进十里店
2014-05-29高初王烁
高初+王烁
大卫·柯鲁克1910年出生于伦敦,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曾参加西班牙内战。1938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授课,后前往成都,并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伊莎白。
1947年底,在二战期间曾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并在东南亚度过了大部分战时岁月的大卫和妻子一起,离开英国,乘船经由香港、天津,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十里店村。在随后的八个月中,他们以英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人类学家的双重身份,在这个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小村庄进行考察,为《十里店: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两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前一本书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共土改问题的必备参考资料。
在此期间,大卫·柯鲁克拍摄了近1000张照片。这些图像不但记录了作为历史事件的土改和整党,而且通过训练有素的人类学观察,完整地再现了村庄的日常生活,节庆、祭祖、婚礼、葬礼等仪式性活动,及其背后的传统华北乡村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系统。
1949年之后,柯鲁克夫妇留在中国,为中国培训外语人才。他们的三个孩子也是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柯鲁克家的长子柯鲁先生(Carl Crook)和我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10月24日。柯鲁先生和我父亲认识在先,他或许因此而得知我过往的工作:整理老照片,做口述史。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友谊而产生的信任,柯鲁先生邀请我协助整理他父亲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在中国拍摄的底片。而关于他父亲的生涯以及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他的母亲,当时已95岁的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将会是一个很好的讲述人。
在过去的3年多时间里,我们一点点发掘、整理和探究这些照片,并通过阅读《十里店》两书,对认识1940年代的华北农村做知识上与情感上的双重准备。
从2010年10月左右开始,读这两册书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刚刚开始读的时候,还在忙着一天四场的口述史访谈。口述史的访谈最忌讳迟到,提前到采访对象家的楼底下等候的那段时间,就可以拿出书读上十几页。印象颇深的是有一次早上5点才熬完一个稿子,7点半要和摄像团队开会碰进度,准备一个8点的采访。在天蒙蒙亮时,我到了采访对象楼下街心花园的石凳上,秋露渐重,裹着衣服斜靠在石凳上睡觉,被冻醒过来,索性拿出《十里店》,读了几十页。在这段时间断断续续地读了一遍《十里店》,这书和书里的人成为这段过于劳累的工作期间不多的陪伴,因而也寄托了些别的情绪。
那时候我已经完成了对1949年前“解放区”摄影师拍摄的近4万张图像的考证和整理。这些照片大多是关于战争的。战争以外的生活是怎样的?正在此时,遭遇到大卫·柯鲁克的近千张照片,与那些关于战争的照片形成强烈对照,由此受到的冲击和兴奋可想而知。
从2011年10月15日起,我和我的夫人王烁每周二和周四会和伊莎白见面,通常是上午10点到11点,一天里伊莎白精神最好的时候。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们请伊莎白看大卫当年拍摄的照片并回忆当时情景,讲述他们在十里店村的经历和感受,并就我们自己观看照片的想法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进行交流。这一工作持续到2013年5月30日。之后,我们对革命、革命文学、乡村和十里店的现状仍有着断断续续不定期的讨论。
2011年对伊莎白的访谈开始时,伊莎白96岁,我和王烁26岁。年龄的差距、经历的迥异以及知识结构的差别使我们对一些问题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对此我们彼此直言不讳。思想的交锋令每次谈话富有成果,即使到最后没能说服对方,我们在争论结束道别之时都觉得互相促进了思考,充实而愉快。
最近,我们策划了一次展览,展出对大卫·柯鲁克在十里店及附近村庄所拍摄照片的整理成果。展览思路来自大卫·柯鲁克的照片,来自伊莎白·柯鲁克的近100次口述访谈,也来自事隔六十多年后我们对这个变迁中的村庄的再次田野考察。相差七十多岁的两代人所完成的资料整理和学术对话,蕴含着对于中国问题的思索与热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