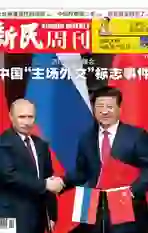城与事
2014-05-29



一鱼三吃
阿 布(上海,编辑)
单位附近有家老字号川菜馆,从外观看,很像80年代的高档国营饭馆,玻璃橱窗里透出白色布帘,胜在清丽。据说早年是董竹君开的,陈毅神马的都来吃过。又据说服务员直到现在都是一水的上海本地老阿姨,态度不咸不淡,即使服务行业也带着一份历史上传下来的矜持。
考虑到菜色有传统,价钱也不贵,某天看话剧之前,就和同道一起去那里吃个晚饭,感受一下上世纪的经典。
没想到,真正经典的来了。
点的菜里有一份水煮鱼,服务员老阿姨端上来一看,裹着面粉炸过的一坨一坨金黄色鱼肉,好像应该是炸鱼块嘛,这不对吧?把意见跟服务员一说,要求退换,对方先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烧的……”无奈这解释理由实在太过牵强,于是过了一会儿炸鱼块被端下去了。
十分钟后,水煮鱼又来了,这一回炸鱼块变成了炒炸鱼块——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厨新加了几根鸡毛菜,炒巴炒巴,再上一点酱油色勾了芡的混汁。我们当即有点无语,连申辩维权都懒得干,就朝厨房方向指了指,示意再度退货。服务员大概也知道这么做太侮辱顾客的智商,倒也没怎么再费劲解释,端起盘子又退回了厨房。
又过了十分钟,正当我们在想象炸鱼块还能以什么样的包装变身回来时,服务员又出现了,手里端着一盘虽然看起来仍然不像水煮鱼,但起码和之前两盘炸鱼块有所区别的东西——目测是炒鱼片,浇上了红红的辣椒油。想到那句“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烧的”,再想想都已经退了两次,再维权下去连话剧都要赶不上,也就挥挥手,凑合吃吧。
然后,一口咬下去,这鱼片怎么能这么硬?再仔细一看,鱼片边上还残留着一点点零星的碎面糊残渣,那熟悉的金黄色,时隔二十分钟,再度回到眼前——原来这还是那份炸鱼块,被厨子剥去外面那层面粉壳,混到辣椒油里再炒上一炒,度尽劫波地回来了……
从前只知道北京烤鸭有一鸭三吃,今天可算领教了什么叫作一鱼三吃。
不几日,川菜馆装修,原本素净的80年代造型换得艳红,一上午的敲锣打鼓,但不知那经典的一鱼三吃,可有登上新的招牌菜单?
安阳到杭州的距离
刘连振(杭州,研究生)
早上从梦中惊醒,看看手机,才六点半。梦里娘晕倒了,紧张得我喊着喊着就醒了。随着年龄增长,娘在我心里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恐惧莫名地增长。一个在浙江杭州城区,一个在河南安阳的农村,这不只是南宋到商的距离。
虽然生活在杭州,但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娃,而且是成功逃过计划生育的“黑娃”。1988年冬天,我来到这个世界,当时娘39岁,和我年龄最近的二哥比我大7岁,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小学没念完,大哥和大姐都结婚了。
2008年考到杭州读大学,当时娘已经59岁了。第一次来杭州报到的时候不需要人送我,因为哥哥姐姐都忙,让爹或者娘送我,我还怕他们回不了家,他们都不识字。第一次坐汽车到郑州,第一次从郑州站出发,在火车上站了19个小时,经过1200公里行程来到了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杭州,内心除了紧张不安,还有激动难耐。
跌跌撞撞地随着人流走动,紧张地看着指示牌确定方向,内心多半是惶恐。看到火车站写有浙传的牌子,我不安的心慢慢静了下来。当学校迎新的车开过来,车上三分之一是学生,剩下的全是家长。还记得在树荫下等车的时候,一个叔叔看了我很久,突然问道:“你一个人吗?”“嗯。”“你老家哪里?”“河南安阳。”“市里的?”“不是,农村的。”“哦。”看到他走回去和家人嘀咕着,心里莫名地紧张。他旁边的男孩一手扶着吉他,一手吃着冰激凌,微胖的体型在阳光下发着汗,不过还好有一个女人在旁边扇风,我想那应该是她的妈妈。
入学之后,回家只有寒暑假,不仅因为距离遥远,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时段学生火车票打折。清明、五一、十一……总有同学会问:“你回家吗?”我的答案永远是:“太远了。”吃过晚饭,打个电话回家,来个“城乡”沟通,孤单的感觉总会减半,但孤单总会有一点。
从本科到读研,六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把户口迁过来,不是不想成为杭州人,而是知道现在自己还不能成为杭州人。在老家,在存放我户口的地方,有爱我的爹娘,那里是我的家。
我想说假期在哪里过不重要,因为有爱你的人在,可我知道,这是骗自己,因为时间冲淡着生活的味道,清晰终究会成为模糊,这让我害怕,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娘做的槐花包子了。
浣熊的故事
翁 俊(芝加哥,创业者)
开车上班,又看到一只倒卧在路中央的浣熊,黑褐色的小身体,肚子滚圆,旁边有一些血迹。一年里,这种揪心的场面,要看到十数次,尤其是冬天。美国每年殒命于车祸的浣熊数量,几倍于人,属于交通事故死亡率最高的族群。这高发的车祸,既源于浣熊数量之多,也因为它们太调皮。
一天晚饭后,我去散步。寂静的路上,只有脚步踩着落叶发出的沙沙声。二十米外,一只胖乎乎的家伙,正穿越马路,走到路中间,还警惕地停一下。浣熊昼伏夜出,这小家伙是出来觅食了。我蹑手蹑脚摸过去。但浣熊胆很小,警惕性很高,马上就发现了我,哧溜一下钻入了对面路沿下的下水道。我很好奇,这肉墩墩、圆滚滚的肚子,是怎么挤进狭小的下水道口的。于是我挨过去看,不想就听见“扑通”一声。原来那小家伙并没有钻进下水道,而是用尖锐的爪子,勾住了下水道口,悬在那里。我一过去,它见没法躲了,只能爪子一松,投水了。我这个内疚啊,想着它会不会游泳;即使会,这么脏的水,也够它受的。本来它好好出来觅食的,结果掉阴沟里了。后来我才知道,浣熊不怕水,而且这些城市“居民”,早已习惯钻阴沟了。
几年前,公司为产品营销拍宣传片,我被选中当录音师。一行人利用周末,赶到一个湖边的露营地拍外景。野外露营,晚饭就是烤香肠、烤鸡翅、烤牛肉饼等。野炊的香味,飘散开去,吸引来好几只饥肠辘辘的小家伙。天色已黑。黑暗中,小家伙们眼睛发着亮光,在我们周围游荡,不敢靠近。同行一个胆大的女孩,把一块面包放在手心,招呼小家伙们来拿。一只胆子大的开始慢慢靠近,停一停,观察一下,见我们没有动,又继续靠近,两只眼睛看着我们,又看看食物,来到近前,伸出右前爪,从女孩手里抓了面包,调头就跑。那只小爪,像新生儿的小手,小巧灵活。得了一次好处,小家伙明显胆子大了,又折回来,从女孩手里抓吃的。女孩调皮,趁小家伙不注意,反手摸了它的爪子,把小家伙吓得掉头就跑,再也不敢回来了。endprint
不久前,网上报了个趣闻,一只浣熊趁夜跑入居民家厨房找吃的,把女主人吓醒,以为闯入了盗贼。这倒是个可爱的“盗贼”,一场误会之后也最终得以被“释放”,相信它们也希望能与人类和谐共存。
当一个手艺人
舒 畅(贵阳,文字工作者)
过年的时候旋子送我一件土布做的棉衣,立领,盘扣。她自己身上这种土布做的复古式样的衣服很多,布料都是她从乡下收来的,裁缝有时候就是她自己。那天聚会其他人也都收到了她的礼物,是一小袋西红柿种子。送植物种子是旋子的一大爱好,行走村寨时,她教村民们种植原生物种;回到城市,她把方便种植的农作物种子送给朋友分享。
棉衣上身,好评如潮,我请旋子吃饭表达谢意,这才知道她吃素,点菜时让我很头疼。同时对我这样吃香喝辣惯了的人来说,和她吃饭压力也很大。她总是在你夹起任何一筷子菜的时候说:这个吃多了要得病;那个的种子你知不知道是裹了农药才种下去的……后来我干脆就叫她神仙姐姐,因为心灵手巧和不食人间烟火至此,我在凡间还找不到合适的身份来和她对应。
春天的时候,旋子又约我到一个需大肆折腾方能抵达的苗寨去“评花”,也就是陪她去给苗寨里的刺绣比赛当裁判。一路行车颠簸4小时,再在江上行船近3小时,下船后又在几乎没有路的泥泞中手脚并用爬山1小时——旋子利用募得的社会资金,帮助苗族妇女恢复传统手工记忆的展留村,就藏在山腰上刚刚长出新叶的枫香树背后,苗族古老的锡绣工艺在这里安然保存。
村里的妇女全都聚拢来了,评花活动从傍晚持续到天黑。夜色里的展留,周遭黑漆漆一片,只有评花这一张露天大桌四周围满了人。电灯泡被系在长棍上,有人一直用手高高挑起。多年来走乡串寨,潜心研究少数民族刺绣工艺的旋子,将99张锡绣细细比较,全村的妇女都在黑暗中静静等待她宣布结果,获得前三名的将获得分别为700、500和300元的奖金,这对深山里的她们来说是笔奢侈的收入。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身边有了很多旋子这样的朋友,朴素坚定,对村寨生活方式和手工技艺充满感情并付诸行动。有趣的是,大多都是女孩子,她们坚持很多年,在贵州的大山间行走村寨,探寻技艺,甚至自己动手,兴致勃勃学习当一个手艺人。
旋子说苗族手工艺有些很神奇的规定,比如某些技艺,不管已经多么烂熟于心,不到一定的年纪也不能去做——这个让人学会等待;还比如苗家对女红高手的要求,是必须在不经意间留点缺漏,不管你手艺多好,意为凡事不可十全十美。——“评花”时遇见不尽如人意的作品,这就成为旋子为她们找到的借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