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镜像中的精神溯源与重构
——评深耕的诗《三才胡同》(外六首)
2014-05-21崔国发
崔国发
深耕是天津诗坛上一个有历史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的诗人之一。从《三才胡同》文本上看,深耕的诗歌打下了明显的历史文化的戳记,基于历史语境和时空经验与身心经历的变迁,他的诗歌于个人记忆与时代记忆的双重规约中,承载了复杂而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精神履历,已自觉潜入到文化本位和人性的、民俗的、伦理的、情感的内核,并在不断地追溯、缅怀与反思中,找到了与心理结构和心灵秩序对接的支点,让诗歌在更深的层面上回到人类存在的本身,在审美流变与价值标向上求得意蕴的重构。
毫无疑问,三才胡同是诗人深耕灵魂的居所与精神根据地,是一个能动的自为的存在,是诗人在自我内心的深化中从繁复的生活进入艺术与诗歌的入口。“三才胡同,天地人,映对日月星,是哪个先人/志存高远,用如此好的口彩,为你命名?”作为一个浑然融入艺术血液的符号形式,三才胡同脉动于诗人深耕心灵的长河,浸润着诗人深邃的历史意志和艺术生命的理想价值。无论在情感上、心理上、情绪上,还是在理性上、文化上、人伦上,都是以一种现代精神溯源的姿态,要么在“日月星”历时性结构中呈现出现代审美镜像,要么在“天地人”共时性结构中产生一种紧张的文化拉力。寻根的意向,使深耕的叙事赋予诗文本以“此在”的“他性”,以及对于生命的一种深刻体验。诗人走故地寻旧,“烧开一壶隔日水,老旧心绪,开始冒泡/焖上一杯乌龙茶,陈年往事,渐泡渐浓”、“丢弃的日子,像羊,边走边拉的粪蛋/ 五十年后捡回来,颗颗,变成金豆子。”
走进三才胡同,便走进了一个不可深测的精神结构。世事沧桑巨变,带给诗人多少存储在生命中的珍贵的记忆,这些记忆本身便是诗人的精神存在,一种对“陈年往事”与“丢弃的日子”的眷恋与热忱,一种人生无论在何时何地也无法割裂的牵连,这条扯不断的精神丝缕,注定了诗人所皈依的精神旨归具有心灵史的意义,诚如渐泡渐浓的“乌龙茶”,在让我们口舌生香的同时,还会令人产生一种异样的亲切感,之所以对一条“胡同”的执著守护,是因为它能带给诗歌以隐喻的深度、思想的深度、生命的深度。为此,诗人使词语在“三才胡同”中穿越或逡巡,那里是他生命的本源,只有在不断地激活记忆、还原生活、进入人类共同生活的历史和经验之中,才能触到“此在”之根,才使一个诗人真正体验到那温暖与感动中的巨大力量。
可是,置身于消费时代的人们,在面对文学寻根、传统文化时,在面对历史与个体关系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仅不接受记忆的邀约,反而采取淡漠、粗暴、鄙弃的态度,进而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三才胡同,说是发炎阑尾/一刀,被激进医生从版图上割去//三才胡同的后生们,太阳般鲜活,只有我/还把多余一段盲肠,紧紧揣在怀里”、“绕遗地三匝,高邻犹在,不报大名,互不相识:/三条石,已被打磨成光亮拐杖,历史真实,还需后人探认。”是啊,尤其是在这快餐化、时尚化、现场化盛行的当下,人们表现出的历史失忆、精神浮躁、不堪回首的情形,使历史与文化的绵延出现了障碍,即便是像“三才胡同”这样的历史人文景观,亦被太阳般鲜活的“后生们”所遗忘,甚至于连“三才胡同”的存在也似乎成了问题,它仿佛一截“发炎的阑尾”,被偏激的医生“从版图上割去”,只有“我”还把那“一段盲肠,紧紧揣在怀里”,“三条石,已被打磨成光亮拐杖”——字里行间渗透着诗人痛彻肺腑的感知,一些所谓的“后现代”,对于传统文化的疏离与审美的畸变,使那些刻骨铭心的历史经验与生活记忆蓦然断裂与破碎,诗人在扼腕叹息的同时,发出了“历史真实,还需后人探认”的深切呐喊。
深耕就是这样在他的诗歌《三才胡同》中,揭开尘封的往事,让胡同中的那些人(老母、“熬死你”、姜老五、糖房老主人、小小顽童、马来雨等)、那些事、那些物、那些风景画与风俗画,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通过各种丰富而独特的人物图谱来展示诗人的审美理想,通过对胡同文化的深入发掘,唤发人们一种似曾相识的情绪体验,从而在“人性关注”、“道德关切”、“生命关爱”、“兴味关怀”中,为现代人迷失的心灵,建构出了一个理想的安妥之所和栖息地。为此,深耕在诗的结尾这样写道:“回忆是枚甜甜果糖,稍稍夸饰,是果糖美丽衣裳/我把果糖含在嘴里,再把衣裳,轻轻叠放。”深挚的个人回忆总是一个起点,它引向历史、现实和哲理的深度,而不啻是甜美的回忆。这个扎根于个人记忆的书写者,再耕在他的《三才胡同》里,于外在化的叙事支点上,撬开人性化的精神内核,进而向我们昭示:往事不再遥远,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在《四十年前桃花堤》一诗中,也有着内心的那种自我反思。这首诗把我们带到四十年前——诗人青少年时代所历经的痛苦、迷茫、忧郁、不安的记忆之中——“刺眼红袖章/胡乱揣进衣兜/看浅湾搬罾,舟子拍桨,鱼鹰捕鱼”、“一本偷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夹进四月花信/撩荡邻桌女孩/桃树下伴我读书/花影怯怯/羞在“冬妮娅”脸上/俏俏的/一朵两朵。”那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诗人个人成长在政治伦理沦丧中的无序、懵懂、彷徨和虚妄状态,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文化专制主义所导致的精神空虚也暴露无遗。其时没有多少好书可读,邻桌女孩对自己偷来的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竟是那样的“垂涎欲滴”,渴望而难求。诗人通过这个细节传达出自己对于阶级论、文革风的尖锐批判与深刻反思。那真是一段不可磨灭的严酷而沉痛的记忆啊!深耕的这首诗,短短十数行,可谓尺幅千里,它指向历史,诘问历史,席卷历史的风云,通过诗歌与那个时代的投射与“对位”,在一个布满苦难的记忆里,揭示出一种共性性的本质关联,显示了一种历史的觉醒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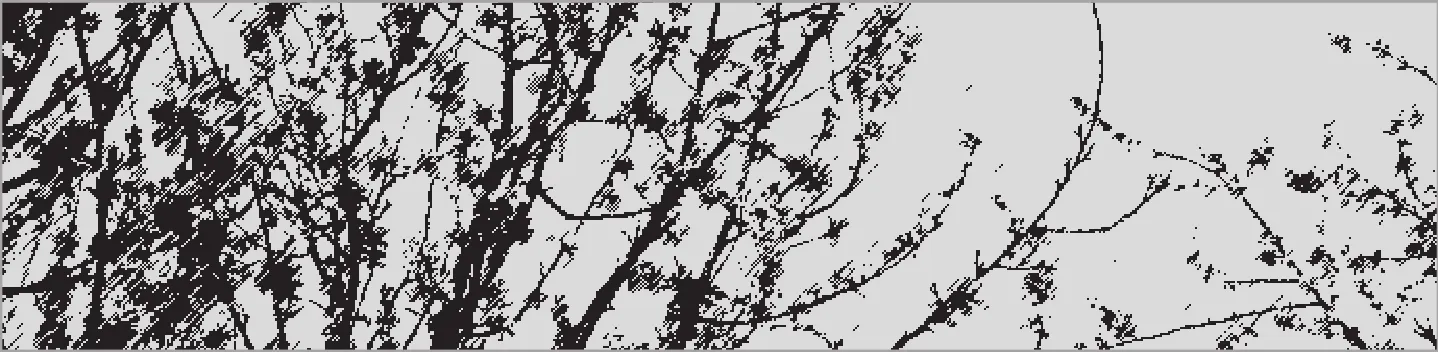
深耕是一个用记忆和心灵进行双重写作的诗人。无论是窗台上古旧首饰和水仙花,还是晾晒新物旧件甚至是灵魂的绳子,他都在历史与现实的缠绕中吐故纳新——抚今追昔,他所要表现的“往昔”,往往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往昔”。即使赶着勒勒车奔向大草原时,也不忘唱一曲苍古的长调。一代人寻求历史文化的深刻性,一旦个人记忆在追本溯原中获得了精神指南,便会坚卓扎实地、不屈不挠地投身于深度域和价值域的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