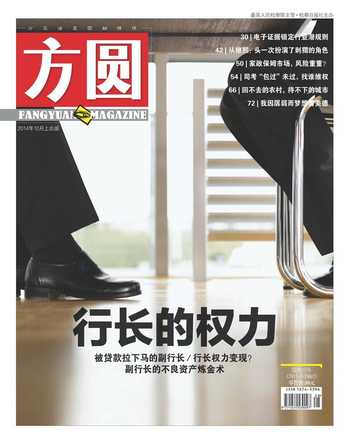在路上的毁灭
2014-04-29
他们和社会的格格不入,他们的人性深度、魅力、复杂性和混乱不堪的私生活都成为了过去式。唯有作品,这些天才手笔,像遗落人间的珍珠,上帝召唤回了他们的肉身,却带走不了灵魂
“五十年前埋下的一颗灵魂,五十年后屹立出一种姿态。”这句话来评价“在路上”的鼻祖凯鲁亚克再合适不过。作为“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之父,凯鲁亚克他们当年驱车沿着66号公路一路狂奔的时候,不会意识到,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会影响接下来的好几代文青。现在动辄将骑行挂嘴边的人,大多都看过《在路上》,对凯鲁亚克、金斯堡们奉若神明。
这些不安分守己,试图做出一番事业的人,都拥有一颗拒绝循规蹈矩的心。作为反主流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全世界文青的超级偶像,切·格瓦拉更是一位血液中永远燃烧着不安分因子的人。青年时代,他曾和友人一起骑车环南美大陆旅行。电影《摩托车日记》,讲述的就是切·格瓦拉青年时代的这段旅行故事。这段旅行对他的人生起到了重大的影响,正因为深入了南美大陆的肌理,他才透彻了解到了革命的迫切与重要性。这使得他放弃了当医生的体面工作,决绝地踏上了革命之路。革命取得一定成功之后,又毅然放弃在古巴拥有的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务,选择重返丛林打游击,誓将革命进行到底,最后战死于玻利维亚的丛林中。关于后点,我由衷折服。这是一位真正的战士,他拥有一颗时刻在路上的心。
1982年6月10日,一个壮硕显得有些肥胖的男人疲倦地躺在床上,嘴里依然叼着那根永不熄灭的香烟。然而,他已经死了。时间再往前推十天,他刚度过37周岁的生日。这个人就是法斯宾德,一个恶棍、瘾君子、虐待狂、双性恋的天才导演。天才总是喜欢自毁。长期毫无节制地工作、暴饮暴食以及食用毒品、麻醉药和大量吸烟毁掉了他的健康。或许童年时的缺爱让他从小就在内心深埋了一颗悲剧的种子。他的确也曾因自己擁有一个比别人更为健硕的身躯而自吹自擂过,在与戴特·席多尔的专访中他不无得意地说,“要是原子弹大战爆发的话,人们将会紧紧地跟随在我身边,因为即使有炸弹掉下来,它也无法毁灭我,我拥有比炸弹更强的力量。”这种过度的自信最终要了他的命,在他生命的末期,他平均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一天喝两瓶威士忌。甚至直接在拍摄场地吸食大麻和麻醉药。
这类人大概只有接近死亡时才能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向死而生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而在活着的每个日子里,局促不安是他们在俗世中必须要面对的生活。我能理解凯鲁亚克、金斯堡他们的疯狂嚎叫,也理解法斯宾德的歇斯底里。法斯宾德只需花几天时间就可以拍出一部故事片来。所有的演员与工作组的人员每天被这个手舞皮鞭的施虐狂狂轰滥炸着,他喜怒无常,有时可以花上几个小时耐心地给演员详细讲解,有时得到的是一顿咆哮和怒骂。总之他无须任何的理由。每个演员都战战兢兢地臣服于他的脚下,并任由这个疯子式的天才调教着。他像一台高速超负荷运转发动机,永无停歇地工作着,狂欢着。很难以相信,这个英年早逝的人在他短短37岁的生涯中,自他24岁那年开拍的第一部电影长片起,14年间竟然拍摄了25部故事片和14部电视剧以及两部纪录片。
任何天才的英年早逝,对后人来说都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惋惜。后人再也感受不到这些天才曾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的痛苦体验。他们和社会的格格不入,他们的人性深度、魅力、复杂性和混乱不堪的私生活都成为了过去式。唯有作品,这些天才手笔,像遗落人间的珍珠,上帝召唤回了他们的肉身,却带走不了灵魂。所以很多年后,我捧着一杯热茶,在夜里重温《在路上》,这些强烈到要将作者的狂想注入自己生命中的作品,就像一杯浓烈的威士忌。
“游荡在颓废中的肉身应接不暇,沉潜于探索里的灵魂欲罢不能”,这是他们最好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