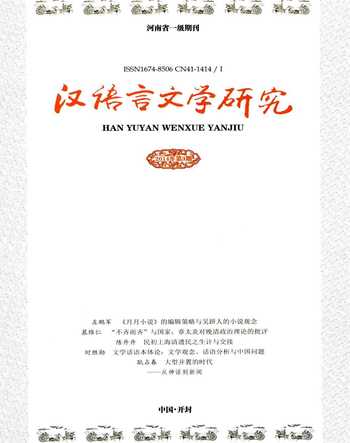大型并置的时代
2014-04-29耿占春
耿占春
网络风景。这是戏剧舞台与生活场景的合一,新闻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重叠。或者相反,这是舞台与社会场景的错位,新闻叙事与历史叙事的视野偏离。你能够目睹的是错位产生的缝隙,是视野偏离产生的可见性。
如同思想之眼有两双眼睛,一个是历史之眼,一个是新闻之眼;一只盯着永恒,一只盯着现在。
神话、传说;历史、新闻。这是两种不同历史阶段的叙事。它们不同,前者是虚构,后者强调真实或事实;它们相似,都包含着对人类生活的叙述。我在激烈的无意识中写下这些类似于题目的临时措辞。在新闻的层面上,每个日历都布满各种偶然性的事件、冲突;事实上,这些事件都已成为制度设置与经验秩序的一部分。对于新闻之眼,这些事件都是具体的、个别的;对于历史之眼,这些事件发生在更具普遍性的层面上,发生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过程中,但寻求什么样的更普遍性的话语对其进行表述?这一历史过程、加入真的是一种历史过程的话,将显现出什么样的意义?“意义的显现”是历史过程的一种驱力还是目标,抑或是历史或文学叙述所产生的一种“表现主义”的结果?即一种符号化行为而非原始事件所携带的东西?
人们置身其中的事件及其过程,既不是混乱无序的表象,又不可能纳入一种由符号化完成或终结了的象征秩序。每天发生的事件是偶然的、具体的、个别的,又处在并不明晰的某种历史过程之中。我们凭借着什么才能觉察到每天的生活事件同时也发生在历史的层面上?或许这一切,压根儿就没有历史性的维度呢?或许历史性本身越来越像是一种希望、起源、终结之类的叙事幻觉呢?或许历史性意识本身就是宗教神话、叙事文学的价值剩余物呢?就像生活的意义感或许仅仅是从圣言到诗歌话语的剩余物呢?
我们在观看、了解、觉察这些事件时,除了短视而善于重复并遗忘的新闻叙事外,既不知道这个细节或情节构成了怎样的历史叙事,也不知道这个细节或情节是不是无关紧要的琐事或与之相反,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叙事的“结尾”,因为新闻叙事与信息话语,没有结尾,它只有无数的开头。新闻叙事确实不过是呈现了人类生活中无数个短暂的瞬间里的更加短暂而微弱的含义。或许比之神话、史诗、文学来,没有连续性的新闻话语、没有故事预设结构的新闻叙事才第一次符合了人类生活的虚无性,尤其是个人生活的瞬时性?
近代文学叙事与艺术的发展如同近代历史世界的结构:文学、诗歌、戏剧、绘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象征主义逐渐让位于现实主义的历史过程。现实主体的人一点一滴地替代象征主义的人物,从宗教戏剧中的面具、传统戏剧中脸谱的广泛使用,到现代话剧中的人,象征性的人物才变成实在的、日常性的、生机勃勃的活人,他们才抛开了自身象征主义的外壳或面具,露出自己的面孔,以血肉之躯迈出走向生活世界的步履。
在艺术领域,象征主义的人开始获得个性。一些活生生的人,却被围困在过时的象征主义的概念框架里,他们在新闻话语中,说着过气的和死去的象征性人物的语言。犹如一些幽灵,游荡在现实与象征世界之间的灰色地带。一些非人类的、反人性的东西,依然戴着高贵的神话面具与宗教面具,参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对活人的恐吓。
在一个利益觉醒、社会生活世俗化的世界上,象征性的人物,类似于假神与政治流氓的混合体,被架上台面的装腔作势者,他们的残忍行为对于受害者之外的旁观群体来说,已不会带来任何神圣感,徒增喜剧效果,小丑的统治的国家像一个马戏团。一种象征主义的历史剧受到现实主义动机的打扰。
戏剧中的人物等级,与历史中的人物等级相似:最高的人物与宇宙、神灵建立了联系;最低的人物诸如贩夫走卒之类,则与世俗性、物质利益建立了生活性的关联。前者的世界总是企图通过象征主义获得崇高性,而后者则是现实主义的。一般而言,在古典式的社会里,后者总是一些悲惨的或微不足道的小配角,而现在,后者登上了舞台,以群体的优势让前者充当道具。
当暴力提升为暴力之神,当诱惑戴着诱惑女神的面具,当仇恨戴上复仇之神的面具时,暴力、诱惑、仇恨并没有消失,只是这些日常生活的现实力量,戴上了超自然的面具,并加剧了那种力量的非自然属性。
在概念的崇高化技术中,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其组织及领袖人物,均戴上了神圣化的面具。
一个袭击者,一个由家庭成员构成的袭击者,他没有个性,没有历史,没有环境,没有社会联系,对这一切我们一无所知,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突然进入了这段新闻故事。就好象是在一个表现神秘命运的戏剧中,一句台词就固定了他的类型:一个恐怖主义者。甚至连最简单的心理主义的描述也没有,不要说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事实上,不仅这个无名的人物这样出现,连著名于世的人物也常常如此出现在“新闻话语”中:他要为许多事件的发生负责,而受众对他一无所知,受众仅仅知道介绍他“被迫出场”时的一句台词:他是一个分裂分子。同样,他的历史、他的个性、他的真实形象,他的话语,完全被“新闻”报道隐去了,连最低限度的新闻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也没有被了解的可能。
他的性格呢,行为逻辑呢,动机呢?缘由呢?一个事件、一个被曝光的事件事实上彻底隐匿了,消失了,人们能够看到的,仅仅是因为图像的透明性而不得不出现的事件的残骸。我们必须在一场新闻话语的空难之后屈从于事实的残骸吗?
小说的叙事逻辑,新闻的叙事逻辑,历史的叙事逻辑。我们已经从小说、电影等最通俗的形式中获得了人的心理学,获得了叙述逻辑,以及认知的结构。然而,受控的新闻话语似乎颠覆了这一切。如今,不仅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受到精神分裂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干扰的,主要是新闻话语。意识形态干预新闻的叙事话语,甚至干预新闻事件的发生或不发生,干扰事件的披露时间、方式、属性。它扰乱了我们从小说、戏剧、历史中掌握到的心理学,干扰了我们已经明了的叙事逻辑与结构。也干扰了外部世界与我们的内心世界的认知关系与道德联系。
于是,饱受现实主义叙事——小说、电影——熏陶的受众,在新闻受众的角色中受到了新的心理受辱,人物的台词呢,性格、心理、行为的逻辑呢?
我们必须听任我们经由伟大的经典所培育的现实主义叙事所馈赠的理解力受辱?还是我们决意要把残缺之外的叙事结构都视为一种虚构?
无关联事物之间的同时性存在,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敏感性还是麻木、漠然?对于多数人而言,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同时性带来了无助感、无力感,没有联系的事物的同时并存带来了世界的荒谬感。如果一个网民一边浏览一个富翁如何炫耀式挥霍消费的网页,同一个页面上有同时有孩子冬天穿不上暖和的衣服,上学的路上要爬过危险的吊桥,如果一个网民只能听任这一切“无关”地并存,就像听任网页上的战争图景与商业广告同时并存:这就是幸存者的感受,这就是他的伦理感知的困难。这就是感知的遇难:一边是正常的生活和现代社会,人们睡觉、喝咖啡、读报纸,同时一边存在着死亡集中营,存在着绝望的嘶喊和无声的垂死挣扎。难道一切事物、一切事件的同时性或并置系列于无意识中培育着一种冷漠的文明,既不像启蒙理性那样追求可理解性,也不像浪漫主义诗学那样寻求可感知、可分享的意义?在面对一切悖谬经验的时刻既不陷入理解力的困境,也不感受到伦理想象力的折磨?
而问题还在于,即使同时存在着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关联,这些关联与关联意识也会被太多难解的同时性存在所麻痹。
通过新闻时刻,我们越来越能够适应一个万事都只有开头而无结尾的世界。这是古老的民间故事、戏剧和现代小说叙事都不能接受的世界。一个轰动一时的案子判决之后,对于当事人的生活而言这是一个开头,然而,不论他曾经多么牛,对于公众而言他就是最终一次成为新闻时刻中的新闻人物,这意味着对于公众而言,一个人一件事失去了新闻时刻这就是突然来临的结束。一个故事只有到了结尾才会出现教益,新闻不需要提供教益,新闻只需提供每天的惊讶或瞬间的引人注目。接着而来的就是遗忘。或者说,是新闻时刻的覆盖,如果一个人出乎意外地关心一周之内的新闻的话,那就是无数开头的集合。当然,没有结尾的开头并不构成一个故事。在此意义上,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给小说读者开了一个新闻式的玩笑。
最重要的精神体验转向了新闻时刻?留在人们心中最重要的精神经验是一首诗、一部小说或电影吗?对我而言,新闻时刻无疑构成了最重要的震撼性经验:“75”事件、“512”汶川地震、“89”事件……,一些毁灭性或无言的创痛体验也是一些语焉不详的新闻时刻所带来的,如钱云会疑案、文建刚灭门疑案……当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件经由媒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构成了对内心感受与世界感知的震动时,新闻时刻替代文学叙事变成了最重要的精神体验。如若现代性审美经验是一种本雅明所说的“震惊体验”或“震惊效果”的话,很难说新闻时刻带来的是美学经验,新闻时刻带来的是一种超负荷的伦理学体验或伦理情感体验,然而,伴随着的伦理认知却极其暧昧,尤其当新闻叙事陷入欲言又止的时刻。
新闻、信息的涌流,同文学与历史叙述一样,都关乎意义的生成。不同的是,历史和文学叙述已经为阅读提供了话语结构-意义结构,而处在当前混杂不清的信息和认知语境里,需要像收拾杂物间或收拾震后的家园一样努力给予秩序,如果不想陷入一种精神分裂式的心理灾难的话。每日面对新闻时刻,远没有阅读经典那样享有美学愉悦,尤其是想起每日里消失的新闻,消失的声音与信息,想起一些本该被认为视为时代楷模却被当作嫌犯的名字,想起一些半透明的新闻事件的深深匿名性,新闻时刻带来的是日常生活与罪感的隐秘联系。
新闻时刻并不是一个单一瞬间,尽管新闻事件时常被表述为一种偶然的单一瞬间,但新闻时刻往往是来自不同方向力量与障碍的一次不幸的交集,就像一场车祸发生时那样。或许,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力量正在被视为一种不幸的偶然性,被叙述为一种失去历史方向的单一瞬间。
新闻时刻的诗学或符号学解析:从将军府中搜出成吨的黄金,成吨重的黄金制作的毛像。黄金铸成的毛像是文革的观念剩余物还是官僚经济的剩余价值?黄金自身作为储备物和财富中介,它的价值不仅源于自然或物质现象,至今人们并不知道,比起工业上应用广泛的各种金属,黄金的实际使用价值是什么,然而,黄金确实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采集自阴间的凝固之光”的符号源。“革命”扬弃了货币,却把金色的比喻扩展至从权力的宫殿到人们的无意识,在数十年间空气中都飘荡着闪烁着金色思想的光芒,“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涵盖了多少对金色的赞颂啊,那是太阳的颜色,赤金也是赤子的比喻,黄金般的辉煌、金子般的纯洁、珍贵或稀有、黄金似的光芒、金子般的心灵,将军囤积或储备的是一个古老而又被革命翻新了的比喻?这些财富中介或货币储备物不过是成吨的符号与象征?至少,将军是多么地热爱着视觉隐喻的金色与辉煌啊,因为实在没有金子般的贪婪、黄金般的肮脏,没有金子般的权力暴发户、黄金般傲慢的权贵这样的符号学表达。然而,黄金毛像不是光芒、辉煌、高贵、珍稀、纯洁概念的死魂灵吗?黄金毛像是双重概念的符号学死亡。转眼间被曝光的黄金毛像成为政治生命的死亡符号,金子没有证明符号的永恒却沦为腐败的证据。
新闻媒介所展现的时间是线性的又是重复的,无数的花边新闻像日常消费品一样构成了一个琐碎的日常时间的散文。但在线性的重复的新闻时间或散文之中,突然一些戏剧性的时间穿插进来。一些事件发生了,标志着一种力量与另一种力量之间的戏剧性较量,或者标志着一种自我分裂的力量开始了一种由事物的分裂所发生的运动,尽管方向并不明朗。当观众由浏览网页转向戏剧性的时刻,剧情又隐晦起来了,戏剧冲突又消失在不可见之中了。观众被晾在舞台下面,真实的戏剧发生在幕后,投射到网络透明空间的情节不是幕后故事本身的呈现,而是故事的诸种表征。每一个名字下面都有一个别的更隐晦的名字,每一个名称下面都有一个隐去的名称。观众在新闻与戏剧之间、瞬间当下与情节剧时段之间,猜测一幕戏中戏中出场的人物与未出场的幕后人物,在侧击、旁白、幕后一角以及最终演练好的落幕大戏中锻炼理解新闻时事的心智。
在社会新闻与宫廷戏剧之间,“真实事件”消失了。觉醒了的社会意识焦急地期待着剧情和整部戏剧的进展,然而,戏剧似乎无疾而终,剧情从社会新闻视野消失在宫廷剧的幕后了。意识的焦虑在于它的期待一再落空,社会意识期待从社会新闻的角度看到包括政治的一切事物渐渐透明起来,而过气的宫廷剧却一再地将戏剧冲突的意义限制在权力内部,以至于不再具有真实的社会意义。社会意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对抗表现在,社会意识的认知期望一再地失望,它无法参与、无法推动剧情,无法塑造出一种真实的社会进程。
电影发明了蒙太奇,报纸和互联网重新发明了与蒙太奇作用相似的诗歌的并置。并置在诗学中是一种想象力和灵感的体现,但在互联网中是最无需想象力的方法。并置让无数的新闻时刻重叠,使无关的事物、事件之间交相污染,无解、庞大、混乱、神经质、强烈。
报纸的同时性叙述在互联网上更为强化了:互不相干的事件被并置着,像一幅社会精神分裂的面孔,像一个小丑的面孔,每块肌肉、每种表情之间都不协调,它们怪异地组合在一起。自报纸时代诞生以来,自互联网以来,人们接受互不相关的事件的能力提高了,人们接受互不相干或又相互干扰的声音的能力提高了,精神分裂变成了常态。在关于现实的小说叙事、一种历史著述中,我们接受的是一种时间上连续性的叙事,我们在所有的事件中寻求的是相关性,是事件的逻辑与可理解性;在互联网的页面上,这一切都不见了,没有事件与人物的连续性叙事,没有事件之间的相关性,所有并置在一起的事件之间没有逻辑层面上的可理解性,自然,也没有结束、结尾或终结。没有最终一幕。同时性是唯一的逻辑,一切事物与事件的同时存在是唯一的依据。
文学、戏剧、历史,还有它们古老的前驱神话、传说、史诗等等,提供给我们的是时间性、历史性,也是关于时间性与历时性的叙事模式;新闻、信息,即报纸与互联网所提供的是关于空间性的经验、同时性的叙述模式。这种经验模式已经占据传播的主导地位。连主流的宣传话语也不得不陷入这一同时性的噪声叙述模式。同意而不是消除背景噪声意味着一种民主化的叙述伦理?
没有联系的各种声音的同时性最终结果是噪音;没有联系的事件并置是事件的无意义。然而,前者可以突然被聆听为多声部,后者即事物、事件的无理并置突然间被感受为一种诗歌。同时性替代了历时性,空间性取代了时间性,并置代替了逻辑,无理链接或无理剪辑替代了合理化或可理解性。
新闻信息或互联网上的每一件事孤立地看都是经过合理编排或可以理性地加以认知的,但所有事件的并置是一种同时性的无理剪辑。互联网呈现的是一种社会无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犹如诗歌是个人无意识的呈现。
或许不能恰当地称为“新闻小说”,确实存在着“新闻叙事”。在摆脱了神秘主义语境之后,确实会产生新闻诗学、社会诗学、历史诗学、人类学诗学诸种……理性话语诗学。
比起结构严谨的小说叙事,报纸、尤其互联网更接近人的无意识活动,我走在冬日暖和的阳光下,去蒙古羔羊店的路上,在人群中又一次想起从这里离开的和已故的友人,是的,就是这一瞬间我接近认知互联网的信息并置(在理想状态下)非常接近无意识活动,互联网如同社会的神经系统,或许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历史叙事、小说叙事和口头讲述更倾向于产生认知功能和价值判断的意识活动,事实上后者是从那一繁杂纷乱的神经系统中辩认出意义的一种有限的努力。
小说没有消失,历史著述没有消失,但它们属于小众;一种历时性的记忆、一种理解力的连续性属于少数的心智?然而,是否一种新的理解力、即一种由于并置事件所产生的“诗性”的理解力与感受力?将一切事物感知为同时性存在而产生的意义?
新闻类似于一种新的原始文化。这是现代社会里新出现的原始文化。新闻多半是历史故事的重复,或历史事件的变形记,然而,有时也会有一些新的、源始的东西。这些真正新的东西预示着一种以原始样貌出现的创始性文化要素。人们多半既没有意识到新闻是历史故事的重复,也没有意识到新闻事件与新闻叙事中的原始属性,即那些真正或许是初始性的因素。新闻之新不是突发事件意义上的新异,新闻之新是叙事形式、叙事话语之新。
从神话到新闻。经验这一概念穿越了神话、史诗、历史、戏剧、小说、新闻,叙述也同样贯彻了这些不同历史阶段支配性的经验表达形式。经验背后的各种冲突着的力量、意志、观念,控制着经验现场的秩序、制度与结构,也渗透到从神话叙事到新闻叙述。象征形式或叙事话语自身的建构与变化也参与了从神话到新闻的经验与秩序的构成。从神话到小说,叙事话语都隐含着一种叙述结构或意义框架,新闻叙事则没有预设意义结构或叙事框架。新闻叙事将一切事件还原到叙述的可见性、可理解性。在此意义上,新闻叙事最接近的是历史叙述。探索人与事的可见性与可理解性意味着为社会世界清理出一个根基。而神话、史诗与小说则都喜欢将可见性、可理解性置于神秘的语境之中。这意味着,神话、史诗与小说是魔幻现实,历史与新闻叙事是对现实性的追寻。
神话、史诗经验背后的秩序是神圣的,处处彰显出神圣的意志或总体意志,神的意志或族群意志的对抗;历史叙述后面的经验秩序则转向其世俗性;在小说的经验秩序中则主要是个体自由意志的显现。社会新闻与国际新闻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无序、失序或对新的经验秩序的质询。新闻回到了或呈现了社会世界的某种初始状态。秩序与规则在解构过程中,同时亦在生成过程中。在秩序的增长中,秩序与规则处在困难的辩认并开始获得出自理性与自由意志的尊重。但噪音与混乱始终伴随着生成状态的秩序、规则与意义,如同噪声与躁动始终伴随着新闻话语。
从神话与史诗,到历史叙事与经典现实主义小说,都预设了一个近乎全知的视角,一个整体的视野和历史主义的巨大视域,新闻叙事则没有这样一种整体性视角,没有预设一种整体视野或历史主义的视域。新闻叙述是碎片的,零散的,非全知的。任何企图用统一用稿或权威发言人辖制新闻的多重立场、多重角度的分散叙事的行为,都有违新闻叙事的属性,即有违当代社会事件的属性。没有人是一个新闻事件的全部知情人与当事人。
尽管新闻事件看起来如此喧哗嘈杂,事实上新闻所面临的叙述禁忌一点也不比历史书写少。一些历史事件与细节因为当时的新闻禁忌在社会记忆中消失了,在历史话语中消失或模糊不清了;当下新闻叙述禁忌又导致未来历史细节叙述的语焉不详。
昆明事件似乎在新闻管制下变成了无解的悬疑小说。一旦新闻叙事被管辖,真实的新闻就消失在统一口径的宣教话语中了。新闻媒介在一个恐怖事件之后保持缄默变得比恐怖事件本身更恐怖。一个无解的事件被禁止探究将直接伤害社会理性及其理解力,将社会世界驱入更深的暴力属性的裹挟之中。
马航事件的新闻叙述正在变成跨国悬疑小说,暴力恐怖小说,政治黑幕小说,时空穿越小说。多个国家的众多媒体每天都会力图重新开始一个叙事,然而每个叙事都只是一个不同故事的开头,每个叙事的开头都没有了下文。马航事件成了现实版的《寒冬夜行人》。
如果说昆明事件在新闻叙事的禁忌中销声匿迹了,变成了新闻叙事的悬案,马航事件则貌似是在新闻自由的叙事中、在新闻眼的众目睽睽下逐日逐夜陷入了不可见性与不可理解性,变成了新闻叙事的反面,沦为悬疑小说,沦为只有无数个开头而无结尾的悬疑叙事。与《寒冬夜行人》不同的是,这不是作家独具匠心的想象力,而是变得不可见、变得不可理解的现实性。
新闻疲惫。就新闻的属性而言,一个旷日持久的新闻就不再是新闻,即使每天都有一些捕风捉影的爆料,一则新闻也在变成旧闻。事件变得陈旧的速度很快。遗忘也很快。新闻的疲惫也加速了。每天点开网页的人们开始寻求“新闻”。人们对在新闻中理解力受挫的感受不会塑造成一个问题。在不间断的新闻所释放出的新的刺激中,理解力陷入了疲惫。感受力也陷于疲惫。这是新闻疲惫。
无论是一个新闻事件近乎自然地无解,还是在新闻叙事的禁忌下被突然冻结了,只要间隔一些日子,就不会引人瞩目了,因为事件已经陈旧,新闻叙事已经疲惫,感受力与理解力更加疲惫。然而,疲惫的感受力或被遏制的社会伦理情感会释放出一个遗忘的磁场。如果记忆和理解力没有发生社会功能,遗忘就会替代它产生相反的功能。
神话与史诗对世界的叙事是通过一套语言表意系统,不可能忽略神话史诗的语义系统的符号性与象征性,一般而言,这一表意过程或叙事方式深深依赖一种象征图式。因此可以说,在神话与史诗的叙事后面,存在着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抽象的语义系统,人类社会的经验世界只有在经过了这一象征图式或语义符号系统的抽象程序之后才能得以表现。
而新闻话语则如同图像这一观念所显示的,图像是人类社会未经符号转换的经验自身,图像被感知为经验世界自身。如果说神话史诗乃至小说戏剧拥有文体、修辞、象征、风格等符号性的转换与“表现”,新闻则似乎体现了一种“摄影的认识论”,除了一种机械的和光学的过程之外,摄影是“没有符码的信息”(巴特:《明室》),新闻如同图像一样是没有转换的认知,是没有符号的现实自身的显现。但这不是一种错觉吗?神话、史诗、小说提醒我们象征图式和符号系统的存在,而新闻话语与图像让我们对此保持着无知觉,或将之视为世界自身的影像。
意义源自于世界本身还是来自于象征符号对意义的表达,意义是生活世界的属性还是表现世界的符号属性?自不待言,生活世界与象征符号的交互作用似乎更符合对意义的认知。
神话与史诗叙述总是比新闻话语给予世界更丰富的意义。不过人类社会也为此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新闻话语分析。就词与物的关系而言,新闻话语是词与物之间的高度吻合,词与物之间没有距离、没有脱节、没有不及物的语用学,新闻话语的词与物之间也不需要有文学性修辞,没有隐喻、比喻、象征等等造成的歧义与多义现象,新闻话语是没有词与物、言与义张力的话语。新闻话语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词就是物。这是新闻话语的认识伦理要求。文学性的话语修辞出现在新闻话语中是不道德的行为,是对作为“事实”或信息的认知态度的干扰。文学性修辞在新闻话语中属于噪音系统。有时意识形态话语及修辞就是出现在新闻话语中的噪音系统。诗歌话语是新闻话语的反面景观。诗歌话语醉心于词与物之间的张力,游艺于词与物之间无法消除的间距。对于诗歌来说,词与物之间的间距就是意义瞬间生成的空间。一个飘浮的意义空间。
就像古老的经文一样,诗歌话语并不消除词与物之间的间距,不仅因为消除词与物的间距是不可能的,它甚至加大或制造这一间距,保持着言与道之间的反思性启迪。
新闻话语是及物的话语,是能指与所指的重合,词与物的一致,就其经验的参照而言是高度饱和的,然而这种经验性的或事实性的话语其意义却付诸阙如。经验上高度饱和的话语其意义却是匮乏的。简言之,新闻话语的经验参照是清楚的,而新闻话语的意义参照是模糊不清的。诸如“反腐”新闻是民主话语?是权力话语?是民主叙事还是权力叙事?
从宗教神话到诗歌,这一话语传统完成了词与物的分离,即完成了可说物与可见物的分离,哲学以它的概念系统诸如理念与感性等也参与了这一漫长的分离过程,而新闻话语再次让我们听到可说物与可见物混合在一起的原始喧嚣。
过往社会是一个以史为鉴的教化型社会,如果考虑到传统社会文化中的“六经皆史”这一文化史实,经的教化作用是通过对史的认知来完成的,对历史的认知不仅通过个别和个人事件也通过社会整体发生道德教化作用。近代的历史观及其历史叙述则继承了基督教的救赎观念,发展了一种世俗的救世观和解放的历史观念及其历史话语。新闻话语则与之相悖,新闻话语似乎不过是一些意义并不充分的无限的单数形式发生的现在史或“临时的历史”,它只关心当下性而不企图把社会理解为一个整体,或者把社会当作一个历史整体向一个通往自由的道路演进,它不承诺拯救与解放,不关心福音,不关心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仅仅关注瞬间的“灾难”或“灾变”,而且往往是局部的、偶然的、单数的、个别的事件。
历史话语与新闻话语之间的一个链接点是“事件”。如果说历史叙述企图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寻求一种通鉴,新闻叙述中的事件往往是“贬义”的,是一些负面经验,新闻话语只关心所发生的事件,而不关心教化目的。
历史话语或历史叙述意在建立各种事件之间的语义连接,或逻辑关系;新闻话语的关注力是分散的,事件表现出偶然的、孤立的和分散的特性,新闻叙述并不寻求把单个分散发生的事件整合进连续性叙述的企图,因为这样做冒着丧失真实性而进入主观性意图的风险。后者是历史叙述所要寻求的语义连接。
麦克卢汉曾用马拉美的话说,报纸是一首隐形的象征主义的诗歌。这意味着报纸将表面的、互不相干的、异质的现象,将之充满撞击力的组织在一起,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一种组织或秩序,而是如同诗歌意象一样采用了强行并置。诡异的事情或许在于,没有共同属性的事物在无理并置状态中分享了重新生成的属性,没有共同尺度的现象通过无理剪辑生成了各种尺度可以分享其尺度的场域。比之报纸,网络空间漫无边际的无限扩展了这一并置能力,并产生一种指向不明的撞击,也在从辩证的剪辑、辩证的并置、辩证的组合转向隐秘的象征主义的剪辑或象征主义的并置,从而生成一种象征主义的世界秩序,一种万事万物同时在场、共同出场的世界?或许如郎西埃所说,断裂之物的撞击生成了连续性,异质之物的并置生成了一个同质层?辩证的、断裂的、非连续性的、异质性的世界在无限度的并置或无理剪辑中最重新生成一种象征的、联系的、连续性的、同质性的世界?“从前保证辩证法撞击的异质的连续程序,现在产生了正好相反的结果:神秘的巨大同质层,其中所有昨天的撞击都走向了反面,成为融合式共同在场的表现”。{1}
或许,非同质性是一种现实,同质性是一种迷恋;辩证的是一种现实,象征的是一种诱惑;不在场是一种现实,共同在场是一种想象的秩序。
象征主义是一种诱惑,来自不可见物的诱惑;表现主义是一种迷恋,来自可见物的迷恋。一个象征主义与构成主义之间的时代?一个表现主义与纪实主义之间的时代?象征的,古典的,浪漫的,还有现实主义的,并不只是一种艺术风格或美学类型,存在着一种象征主义的或表现主义的人类社会,同样也存在着一种象征主义的或表现主义的人生。
一种观念通常并不一直停留在它最初看起来所在的地方。有时人们能够在不同的领域将它辨认出来。这个现象本身就是象征主义的。
维利里奥的一个看法是,“无边的艺术”会导致直接感觉的远离,旧的利益群体让位于“一个瞬间情绪的群体”,一个公共情绪的社会替代了公共利益的社会,一种“情绪的假民主化”遮盖了公共舆论的民主化,并有利于舆论的转移。伴随着民众主义的兴起,“大众个人主义”也会取代集权制度的集体主义。
替代了艺术的可见性的是一个与“媒体瞬间性的实时产生直接共鸣的当下”,一个大众个人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有限世界的果实,处在“瞬间当下”自我中心轴上。
关于艺术的失明,或可见性的丧失,凝视的逐渐消失,在维利里奥看来是当代艺术的灾难,“它预言了一种公共亵渎的重大风险,这种亵渎从此威胁着任何的再现,而在短期内则威胁着任何的‘文明”。如果艺术意味着可见性之前的“预见”,新闻则是可见性之后残留下来的不可预见,“在可见之前,已有先可见的世俗特点,然而在可见之后,残留下来的就只有不可预见、意外和对认识意外的揭示”。{2}(维利里奥)新闻图像的可见性在爆炸,新闻图像或被维利里奥称为远程客观性的东西在大量并置、叠印,新闻图像的可见性替代了艺术的可见性,新闻的明察替代了艺术的失明。然而新闻可见性的特性是突然出现的风险,突然出现的意外,新闻呈现的可见性恰恰是不可见性,是不可预见性。新闻是“无边的艺术”的残留物?
这一时代或许否定性地达到了尼采的酒神精神的世界,即维利里奥所说的进入了一个追求自我陶醉的“感觉文化”的领域,其表征就是大众式的个人对音乐的痴迷。在某种意义上,对音乐的痴迷摹仿了身体交流的沉醉,并且损害了日神精神及其造型艺术,即损害了艺术的可见性,于是出现了维利里奥所说的以大众个人主义的盲目的“情绪民主”取代了具有可预见性的“舆论民主”。情绪民主是虚假的,受控于某种本能和条件反射,而舆论民主本可以以思考、预见、可见性来抵制受控的条件反射。
媒体从“舆论民主”的场所滑向了“情绪民主”的场域。意识形态不容易操控舆论民主,却相当容易操纵情绪民主。反贪反腐或反美反日,以及它们背后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能够在最短暂的时间完成一种“情绪民主”的瞬间聚集,都能够从社会意识不成熟、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从舆论民主蜕化为情绪民主。而一个惯于情绪用事而非理性思考的幼稚社会也能够有效地自欺,将盲目的、短暂的、又常常携带着破坏性的情绪民主误认为建构性的舆论民主。
郎西埃注意到“图像句子和大型并列”现象。他说在福楼拜的时代,大型并列可以是“感觉和行动等所有理性体系的倒塌,从而扩大原子的无区别混合的随机性。……通过将它们的理性等同于事物理性的巨大缺席而创造爱情”。同样是这样一种事物-世界理性的巨大缺席也能够“创造”出恐怖、荒谬、厌恶、无意义感自身。在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或罗贝尔·昂泰尔姆的集中营经历的描述中,对事物与环境的一系列细微感知与大量并列句法,感性事物的过度在场带来的理性缺席,导向的不是物的自在或采用事物的立场所感受到的那种古老的圆满,而是不幸、惶然、无意义。
新闻比其他艺术形式都更为迅速和彻底地实践了“图像句子和大型并列”,这是一种新的福音还是噩梦?“这是一个所有故事都被分解成句子的世界,句子本身又被分解成词汇,可以与线条、笔触或‘活力进行交换,任何绘画主题都可以分解在这些素中;也可以与声音的强度进行交换,其中旋律的音符与轮船的汽笛、汽车的噪音和机枪的连射声融为一体”,{1}这是诗人们的并置句法被普遍化的时间,是诗人们分解句子并使更细小的元素如词汇并置方式的普惠化。一种制造出非诗的诗意的简化方式。就像巴列霍常常采用的趋向于高度简化的词汇的并置。
分解和并置。非连续性和并置。非同质性和并置。碎片化和并置。繁杂表象和简单并置。不想人工化的进行结构,不想非自然地建构逻辑,就有了人工化的并置结构,非自然地并置逻辑。万物一体。分解成碎片的万物一体。弥散各处、互无关联的事物之间的混合。
分解成为唯一的理性原则。并置成为唯一的知识综合形式。这不是真实的认知性综合,这是并置、邻近性所生成的“物质性的混合”。分解的理性与并置的逻辑,创造了一个一切存在物都是其他存在物的转喻形式的世界。
分离的艺术、分解的世界之后,经由并置、经由大型并置产生了一种新的共同尺度,这就是“节奏”的共同尺度,原子化的细微物质与细微感知的并置逻辑。艺术的新尺度是一种悖谬的尺度,又从分散、分解的成分大型并置中所生成的巨大混沌力量中获得滋养。
混乱的共性与深层的今天,或者混乱的共性与大型并置的定律,它们之间有着难以觉察的界限吗。就像在福楼拜笔下可以创造出爱情的氛围的东西,却在博罗夫斯基的笔下重现了恐怖。一边是幸福,一边是剧痛;一边是安慰,一边是绝望;一边是融合,一边是深渊;一边是生,一边是死。“一边是精神分裂的巨大爆发,句子崩塌在叫喊中,意义崩塌在物质状况的节奏中;另一边是等同于商品及其复体的并列的巨大共性,或是等同于空洞句子的不断重复,或是等同于受操纵的强度的狂热,等同于有节奏地前行的物体。精神分裂或普遍赞同”。{2}一方面是对整个时代体验发出质疑时爆发的巨大笑声,另一方面是一种普遍赞同,“或对共性的陶醉躯体的巨大操纵的赞同”。这一表述暗示着一种音乐经验:对共性的陶醉躯体的巨大操纵的赞同。
然而,狂热与赞同都可能重蹈愚蠢与麻木。
【责任编辑 付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