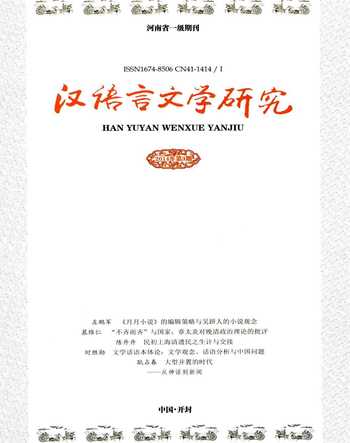从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谈“国学”视野下的“戏曲”研究
2014-04-29游富凯
游富凯
摘 要:胡适因应清华学校学生之邀,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1923年3月4日),以供清华学生在出国留学前,能够了解增进国学知识的方法与管道。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所开列的书目中,出现若干戏曲书目,如《元曲选一百种》、《六十种曲》、《笠翁十二种曲》、《缀白裘》等。本文从此现象出发,主要讨论重点有三:第一,在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风气盛行的学术氛围下,戏曲是如何被纳入“国学书目”之内,其中是否可反映出胡适自身之学术主张与文学思想;第二,胡适所开列之戏曲书目,又与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所列之戏曲书目有何不同,其中如何展现各自的特色与主张;第三,戏曲自晚清以来,多依附为小说之属,当“国故运动”展开之后,戏曲便得以凸显自身的发展脉络与价值,其中胡适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胡适;国学;国故运动;梁启超;戏曲
一、前言
1923年3月4日,胡适于《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7期上刊登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1}(以下简称《最低限度国学书目》),此书目是应清华学校学生之邀,提供该校学生在出国留学前,能够了解增进国学知识的方法与管道。然而,看似一篇青年学子向北京大学教授请益的文章,却引发后续诸多学者对于国学书目的论争。如将这篇文章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学术环境来看,即可发现,此书目不仅仅是身为师长的胡适给予学生的建议,更多是蕴含了胡适个人之学术思想与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份书目中,竟出现若干戏曲书目,如《元曲选一百种》、《六十种曲》、《笠翁十二种曲》、《缀白裘》等,其中含括了金元诸宫调、元杂剧、明清传奇、清代花部戏曲与戏曲史专著。从中可以看出,胡适是有意识和系统地依据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脉络来构思书目安排。如从“国学书目”的立场来看,胡适放入多达13种的戏曲书目,可谓前所未有。换句话说,此份书目是否代表着戏曲正式进入“国学”概念之下?而这究竟是胡适个人之见解,抑或是当时整体的学术氛围所造成?其背后之动机与影响究竟为何?以上,为本文所关注的焦点。
目前,学界对于胡适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已有诸多探讨,所关注之重点,多集中将胡适《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与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2}(以下简称《国学入门书要目》)相比较,以及后续所引发之“国学书目”论争议题。如傅正《略评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③、罗志田《留学生读什么书: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讨论》{1}、董德福《简评二十年代的两份“国学书目”》{2}等文章,都是以梁、胡二人所列之国学书目为讨论对象,探讨二人书目之差异与学术主张之异同。
徐雁平《20世纪20年代国学书目推荐及其文化解读》③、张越《“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4}、王存奎《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国学必读书目”之争》{5}等文章,则是将二人之书目,置于当时学界对于“国学”、“国故”等概念的论述脉络下进行探讨,并将论述场域延伸至后续国学书目之论争,以及1925年由《京报副刊》所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十部”,以此作为整体的论述背景与脉络。
如从胡适与戏剧(曲)之关系来看,目前,多数学者仍将讨论重点集中在胡适与《新青年》派学者集体抨击传统戏曲的激进五四时期,部分学者则针对胡适与戏曲之关系进行探讨,如刘恒《胡适与戏曲》⑥、黄艾仁《风风雨雨真情在——胡适与梅兰芳的交谊始末》{7},以及蒋星煜《胡适与元杂剧、明清传奇》、《胡适与京剧》{8}等文章。这些论文多以胡适出国留学前的观戏日记为基础,辅以其为戏曲类书籍所撰之序,以及与梅兰芳、齐如山等民国时期剧人之往来书信,作为主要研究依据。
综观上述,如谈到胡适《最低限度国学书目》时,学者普遍将重点放置在国学、国故运动、历史观与文化史观的论述脉络下进行探讨,并将其与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进行比较,评价此二书目之孰是孰非。目前仍然少有学者针对戏曲书目出现在《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中这一现象本身进行探讨。此外,在谈到胡适与戏曲相关议题时,亦多是在胡适反对旧剧的主流论述下,尝试开辟不同的论述场域,或是只为“一个空白的填补”。{9}
本文期望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胡适、《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国故运动”和戏曲研究等相关议题,进行关联性思考,并尝试进一步探讨胡适是如何在《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中,透露出其文学思想与戏曲主张;胡适与梁启超所列之书目有何不同?将戏曲纳入国学范畴之内,又是基于何种立场;对20世纪初的戏曲研究而言,“国故运动”和胡适的戏曲观,彼此是否产生影响?以上,即是本文所讨论之重点。在进入讨论之前,将先针对当时“国故运动”之发展背景进行概述。
二、胡适与“国故运动”
当谈论到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学术风气,最引人瞩目的即是其时盛行的“国故运动”。“国故运动”的开始,并非是一个经过缜密构思和计划性推行的运动,而是由毛子水、傅斯年等人在杂志上发表有关“国学”、“国故”的文章后,进而引发其他学者加入讨论,最终在知识界与学术圈中形成风潮;以至于1922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设立国学门、1923年北大创办《国学季刊》、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国学院,并邀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执教,人称国学院“四大导师”。这一连串的文化事件,皆可视为“国故运动”的影响与持续。
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发表《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一文,其认为国故代表“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并认为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因此,要用“科学的精神”去重新研究国故学。{1}毛子水的文章发表后,以张煊为主的《国故月刊》则出现另一种声音,并发表《驳〈新潮——国故与科学的精神篇〉》{2}一文,对于毛氏之说法多有批判。而后毛子水又于《新潮》第2卷第1号刊登《〈驳《新潮——国故与科学的精神篇》〉之订误》③,加以回应。
其间,胡适亦曾写信给毛子水,发表他对该文的看法。他认为,“张君的大病是不懂国故学”;同时也提到,“况且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4}基本上,胡适是赞同毛子水对于研究国故之看法,在同年11月所撰《“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便提出四个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将“整理国故”正式纳入新思潮的概念里,认为要用一种“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5}然而,胡适的“国故”究竟指的是什么?
1921年10月,胡适将其在南京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暑期学校的演讲稿,刊登于《东方杂志》第18卷16号,名为《“研究国故”的方法》。在文中,胡适说道:
“国故”底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底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
在此,胡适认为,相较于“国粹”一词,指称“国故”更为恰当,其所涵盖之意义更为广泛。由于国故是“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胡适因此提出四种研究国故的方法,包括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和整理,并强调研究国故“非但为学识起见,并为诸君起见,更为诸君底兄弟姊妹起见”。⑥由此可知,胡适在讨论研究国故时,是以历史文化的传承为主,而这样的想法亦延续到了1923年。
1923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创办《国学季刊》,编辑委员包括沈兼士、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李大钊等人,胡适担任编委会主任,并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在该文中说: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
此处胡适对“国学”与“国故学”的关系有明白的定义,认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又包含了“国粹”与“国渣”。笔者认为,此段话重要之处在于,胡适将国学的领域扩充到包含“国粹”与“国渣”的概念,甚至认为两者同等重要。他说道:
近来颇有人注意戏曲和小说了;但他们的注意仍不能脱离古董家的习气。他们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说,而不知道在历史的眼光里,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传》和一部精刻的残本《五代史平话》有同样的价值……
胡适在这里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并明确指出国学研究的范围:“过去种种,上至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1}
由此不难看出胡适对于整理和研究国故的看法,除了延续1919年毛子水提出的基本思路外,更在其基础上不断扩充与修正,而最终将国故的概念扩及上至学术思想之大,下至一支山歌之细。如从胡适的思想脉络来看,便不难理解,何以在1923年开列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中,会将戏曲类书目纳入国学书目之内。尽管其背后有一贯之思想脉络与主张酝酿,然而在当时,似乎也容易被视为惹人争议之举。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1923年二三月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胡敦元等四人之邀,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专门提供“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之用。胡适拟写书目时,特别声明两点:第一,此份书目“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第二,胡适将此份书目看作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叫作“历史的国学研究法”,主张“用历史的线索作我们天然的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2}
胡适在《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内,罗列共计185种书目,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一)工具之部:《书目举要》、《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14种;(二)思想史之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四书》、《墨子间诂》等93种;(三)文学史之部:《诗经集传》、《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78种。其中,有关戏曲类书目被归入“文学史之部”,共计13种,如下:
《董解元弦索西厢》(董解元)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元曲选一百种》(臧晋叔编)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商务印书馆本。
《六十种曲》(毛晋编刻)汲古阁本。此书善本已不易得。
《盛明杂剧》(沈泰编)董康刻本。
《暖红室汇刻传奇》(刘世珩编刻)原刻本。
《笠翁十二种曲》(李渔)原刻巾箱本。
《九种曲》(蒋士铨)原刻本。
《桃花扇》(孔尚任)通行本。
《长生殿》(洪升)通行本。清代戏曲多不胜举;故举李蒋两集,孔洪两种历史戏,作几个例而已。
《曲苑》(上海古书流通处(?)编印本)此书汇集关于戏曲的书十四种,中如焦循《剧说》,如梁辰鱼《江东白苎》,皆不易得。石印本价亦廉,故存之。
《缀白裘》这是一部传奇选本,虽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戏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戏曲总集中,这也是一部重要书了。通行本。
《曲录》(王国维)晨风阁丛书本。③
从所拟之戏曲书目,可看出胡适是经过思考,且有系统地按照戏曲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罗列书目,上至《董解元弦索西厢》的金元诸宫调,下至《缀白裘》的清代花部戏曲,可见胡适确实用着“历史的眼光”作为判断的依据。然而,不察此点的人,则会对于胡适所列之书目感到不解。
此份书目发表之后,胡适便收到清华学生的复信,信中提及学生们对于书目之看法:“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先生在文中并未下国学的定义,但由先生所拟的书目推测起来,似乎只指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而言。思想史与文学史便足代表国学么?”{4}如从胡目来看,的确文中只有三类书目:工具部、思想史部和文学史部,这与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提到理想中之国学研究,有不小落差:
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中国文化史:1.民族史;2.语言文字史;3.经济史;4.政治史;5.国际交通史;6.思想学术史;7.宗教史;8.文艺史;9.风俗史;10.制度史。{1}
此处所罗列的国学研究十个范畴,如今在《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中却只剩下思想史和文学史两部,胡适对此解释说,“我暂认思想与文学两部为国学最低限度,其馀民族史、经济史等等,此时更无从下手,连这样一个门径书目都无法可拟”。{2}
在清华学生的信中,还提及胡目的另一个问题,即书目太深、太多。由于清华学校当时作为留美预备学校,从中等科一年,到大学一年止,总共八年的求学时间,除了必读的西文课程之外,还要应付自身之课业,似乎再难有时间阅读如此大量的书籍;同时,作为留美预备生,是否有必要将佛经、戏曲、小说作为国学必读书目之一,因此,清华学生们质疑:“而且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③对此,胡适则以曾身为留学生的过来人经验作说明:
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这个书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班留学生或候补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4}
可以看出,两方所持的观点及立场都有所不同,胡适希望学生们既身为预备留学生,就应该多认识他所认知的“国学书”,包括佛经、小说、戏曲等;对学生而言,这些书目的出现,似乎难与以往“国学”的概念相契合,且基于上述种种问题,学生们因而希望胡适再拟一份“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足以“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5}胡适在稍后的回信中,果然又拟了一份“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书目总计39种⑥,其中仍保留3种戏曲类书目:《元曲选一百种》、《宋元戏曲史》及《缀白裘》。
在整理国故的风潮之下,胡适打开国学大门,迎接戏曲入内,除了是受时代学术氛围影响外,其个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思想的主张,亦存在由“破坏”到“建设”的内在思想转化过程。{7}可见在当时特殊的社会风气与学术思想环境下,不能用片面或狭隘的视角去评判、看待一个人的言行。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口号的同时,他也正代表着《新青年》攻击“旧剧”一派的领导人物之一,而这看似冲突与矛盾的立场,实际正凸显当时学术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关于胡适的文学观与戏曲观,本文将在后文继续探讨。下面将先针对同时期另一位重要人物——梁启超所开列之国学书目进行讨论,并将之与胡适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进行对话与比较。
四、20年代的两份国学书目
在中国20世纪初的学术思想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位代表性人物——梁启超与胡适,分别对“国学”拟出书目,这一文化事件自然在当时的学术界与文化界造成轰动效应,并引发后续“国学书目”论争的风潮。由于梁启超的书目拟于胡适之后,明显可以看出梁启超在拟此份书目时,其主要对话的对象就是胡适,梁启超甚至另外撰写《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针对胡适书目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批判。
胡适开列《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之后约两个月,1923年4月下旬,梁启超也应《清华周刊》记者之邀,拟了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该篇“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1}开出了139种国学书目,共分五个类别: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丙、韵文书类;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戊、随意涉览书类。
如拿《国学入门书要目》和《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做比较可以发现,前者不仅是一份国学书目,也是一份书目提要。梁启超在每本书之后,都会附上对该书的撮要和点评;如讲到《老子》时说:“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讲到《世说新语》时说:“将晋人谈玄语分类纂录,语多隽妙,课余暑暇之良伴侣。”{2}事实上,对于梁启超而言,开拟书目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早在1896年,梁启超便刊行过《西学书目表》③;东渡日本后,在1902年的《新民丛报》上,亦发表过《东籍月旦》{4}。
从梁目来看,其书目涵盖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经、史、子、集各部,并额外添置“随意涉览书类”。此类的增设,明显是因梁启超个人之读书方法与喜好所致。其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后,另附上《治国学杂话》一文,其中提及:“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涉览的。”{5}梁启超非常重视读书的趣味,在此亦与青年学子分享自己的读书经验与方法。
如以“最低限度”之国学书目来看,梁启超认为,胡适这篇书目最大的问题即在于“文不对题”,一方面“挂漏太多”,另一方面又“博而寡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第二,“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而梁启超最在意之处,则是胡适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中,并没有包含史类书籍:
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
梁启超对于胡适将史部书一并弃绝,而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等白话小说纳入国学书目之举,感到相当不解。他认为,“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之部分”,如今在胡适的书目中竟完全不见,难怪梁启超的话越说越重:
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彀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⑥
梁启超在此处所指出的问题,正如同清华学生质疑胡适将《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和《元曲选一百种》等书纳入“最低限度书目”的做法,所表达的疑虑如出一辙。如从“最低限度”的角度看,胡适在构思该份书目时,的确有偏颇之嫌,而这也说明为何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梁目更具实用性,也更适合青年学子参考。{7}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如先搁置书目之实用性或是否“名符其实”,胡适将戏曲书目纳入国学书范畴,其中包括李渔《笠翁十二种曲》和花部戏曲《缀白裘》等以往较不受重视之戏曲书籍,这是戏曲在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思想上之地位的一大突破。而将胡目与梁目中相关戏曲类书籍作比较,即可说明此点。
在梁启超的书目中,戏曲书目主要在“(丙)韵文书类”和“(戊)随意涉览书类”两部份。笔者将二人书目中相关戏曲书目进行整理,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此表可以看出,在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中出现的戏曲书目,皆已单独列于或含括在胡适《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中,而胡适所列之戏曲书目以总集{1}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所列戏曲书目自身即呈现了中国戏曲发展的进程,也就是由金元诸宫调、元杂剧、明清杂剧、传奇到清代花部戏曲的发展过程。胡适将戏曲置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下来看,所要凸出的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2}的观念,将每个阶段的中国戏曲发展,回归至其自身所属的时代。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说道:“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③正是这样的历史眼光,才能将以往不被重视之戏曲论著和文本,纳入国学书目内。
不同于胡适,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中,除了强调国学的知识外,更重要的是为学的“常识”。{4}在《治国学杂话》里,梁启超就强调“课外学问”和“养成读书趣味”的重要性,而《国学入门书要目》中另设“随意涉览书类”,便可说明梁启超的书目是要让清华学子们兼顾国学研究的“学识”与“常识”,并非像胡适所开列之书目,仅因自己“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借的资料”。{5}如果从此角度来看两人所开列之戏曲书目,便可以明了何以出现如此差异。⑥必须说明的是,笔者无意在此展开胡、梁二人之戏曲书目和戏曲观的比较,此议题之庞杂,亦非笔者现阶段学识能力所能完成。本文在此想要强调的是,何以胡适与梁启超所列之戏曲书目有如此之差异,甚至因各自出发点不同,而引发后续论争,并期望能在众多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之外,另辟一新的论述场域与视角。以下,将从20世纪初的戏曲研究环境,探讨胡适《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在其中所显示的意义与价值,并进一步探讨胡适戏曲观念的立场与态度转变。
五、“活文学”下的“戏曲观”
自晚清以来,以梁启超、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中国面临“救亡图存”之际,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1}“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2}等主张,开启了晚清戏曲改良运动的高潮,而戏曲也在中国文化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面临西学冲击的晚清时期,也正是中国传统文类重构的时期,即使戏曲在当时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但仍主要被视为“开民智”的工具之一,附属于小说的范畴之下,更无法与“国学”一词相提并论。
自1908年起,王国维陆续完成了《曲录》(1908年)、《戏曲考原》(1909年)、《录鬼簿校注》(1909年)、《优语录》(1909年)、《唐宋大曲考》(1909年)、《录曲余谈》(1909年)、《古剧脚色考》(1911年)等著作后,终于在1913年,《宋元戏曲考》的问世③奠定了近代戏曲学研究之典范与模式,就连刚返国的胡适都认为,“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4}与此同时,另一位曲学大家吴梅,则曾在1917-1922年,作为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亦在最高学府讲授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曲学”,进而引起很大争议。{5}王国维和吴梅都被视为近代戏曲学研究的奠基者。钱基博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称:
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列;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为大师云。⑥
在前辈学者的奠基与开拓下,随后的1920、1930年代,即可看到戏曲学的研究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如出现了吴梅《中国戏曲概论》(1926年)、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1933年、1936年)、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1934年、续编1937年)、卢前《中国戏剧概论》(1934年)与《明清戏曲史》(1935年)、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略》(1936年)与《中国剧场史》(1936年)、徐慕云《中国戏剧史》(1936年)、王芷章《清代伶官传》(1936年)与《清升平署志略》(1937年)等著作。{7}如果说,中国二十世纪初戏曲研究得以展开,除了王国维与吴梅在开始便已打下良好的研究基础外,另一个必须关注的重点,即在于胡适和当时盛行的“整理国故”风潮。
自20年代“整理国故”在学界兴起后,“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的文学观念已被打破,代之以新的文学观——‘托体稍卑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亦成为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8}传统文学观念的重构,足以让戏曲在文学中凸显其自身的特色,并跳脱以往附属于其他文类概念下的事实;抑或是在“充分肯定和凸显了戏曲社会教育功能,但又恰恰过分强调甚至夸大了戏曲的这一功能”的情况下,回归到戏曲自身的发展脉络。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其最具有代表性且能够说明此点的,即是胡适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
上文曾提及,在《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中,戏曲类总计有13种;到了《实在最低国学书目》中,仍包含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元曲选一百种》和《缀白裘》3种。{9}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在当时戏曲研究界之重要性与地位,被列入书目内可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将《元曲选一百种》和《缀白裘》也一并保留到最后,则凸显了胡适一贯以白话文为“活的文学”的主张。而此观点的坚持,从胡适留学时期便可看出端倪。
在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前,早在1914年1月25日《今日吾国急需之三术》的笔记中,胡适便提出:
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1}
显然,此处所说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正是胡适日后返回中国时所一再强调、坚持的主张与口号。而在1916年4月5日的《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一则日记中,胡适就透过上述的观点清理出“文学革命”的历史进程: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
胡适透过历史的眼光,发现中国文学的发展自身就是一种进化,而最后归纳出:“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2}这里提出以俚语创作的文学,才是第一流之文学,而“活文学”的观点,亦延续到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
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③
胡适在此不但强化了早期的观点,更认为元代是接近“言文合一”的时代,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而其中又以小说、戏曲的成就最大。至此,胡适对于戏曲的相关论述都是建立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与脉络中,并坚持元代的小说、戏曲最接近“活文学”的主张。
而在1918年发表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则是将文学进化观与戏曲作整体性的结合论述,并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基础上,概述了“中国戏剧进化小史”的发展模式。胡适指出,就体裁而言,从元杂剧四折形式到传奇体制,使得“体裁更自由了,故写生、写物、言情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而从传奇到“俗剧”{4}的发展,“也可算得是一种进步”。
此外,胡适亦针对“旧戏”之“遗形物”加以批判,如“现今新式舞台上有了布景,本可以免去种种开门、关门、跨门槛的做作了,但这些做作依旧存在;甚至于在一个布置完好的祖先堂里‘上马加鞭”。{5}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对旧戏台上的“遗形物”加以批判,正如同他在强调创造“国语的文学”时,主张“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胡适强调的是“今日”的客观性与现实性。如用同样的眼光审视中国戏台上的旧戏,就不难理解,何以胡适会将拥有新式(或西方)剧场的中国戏曲表演,视为“今日”的“遗形物”,而元代以来发展极为兴盛的“活文学”(旧剧),也应被以“中国将来新文学用的白话”、“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⑥为主的话剧(新剧)所取代。
尽管如此,此篇文章之重要性仍在于,胡适此时虽仍是以文学的进化观来评判旧戏,但其论述和关注之焦点,已拓展至戏曲的剧本体制、角色人物性格的塑造、舞台艺术、戏曲语言等问题,甚至在用一种理性和科学的眼光,提出了“文学的经济方法”的概念(即时间的经济、人力的经济、设备的经济、事实的经济)。且不论以今人眼光视之,其论述是否有偏颇或“急功近利”{1}之嫌,但这样的论述,更多是建立在“评判的态度”之上。
将近20年后的1937年,胡适曾为《缀白裘》一书作序,从序言中可以看出,胡适对于戏曲的发展观念,仍延续其早期的论述,甚至仍有许多过当之处{2},但从胡适在文末所说,“读《缀白裘》的人们不可不知道这些打诨的俗戏都是中国近世戏曲史上的重要史料”,③便可证明其在思想观点上的转变。笔者甚至认为,其早期对于戏曲言论之偏激或激进,更多是因“特定时代之需要”,而策略性地建构新的论述场域,就如同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引用尼采的话,认为“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4}如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更可以理解,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何以在反传统文化的氛围下,提倡“整理国故”的运动,何以在旧剧面临《新青年》一派猛烈抨击的同时,又将旧剧纳入“国学书目”之内。
六、结语
以往前辈学者在讨论胡适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时,多是关注到胡适与梁启超之间“国学书目”的差异,以及后续“国学书目”的论争,很少有学者将焦点放在二人的戏曲书目上。如从戏剧研究的角度来看,不论是晚清的戏曲改良,还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甚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起的新、旧剧论争等议题,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似乎少有学者从“整理国故”的角度,去审视20世纪初至20年代戏曲研究所受到的影响。{5}本文因而选择从胡适《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出发,试图去开启另一论述面向。
综上所述,当胡适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时,便将以往不被视为“国学”的小说、戏曲,纳入其“整理国故”的整体概念之下。而戏曲在历经自晚清以来的“文类重构”之后,又一次因中国传统文学、文化面对科学精神的重新审视,得以凸显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与地位。胡适在当时能重视《笠翁十二种曲》、《缀白裘》等作品,如以现今的眼光审视,仍然十分具有前瞻性与价值。其个人对于戏曲的相关论述与研究,虽然始终局限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但也明显关注到戏曲演出的其他面向。即使仍在文学进化论的语境下展开论述,然而,以胡适在当时文化界的影响力来看,其真正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许是要用科学的精神、评判的态度,去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与文化,引入新的文学观、历史观,进而在“人为的破坏”之后,有意在新开辟的论域中展开建设。
【责任编辑 穆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