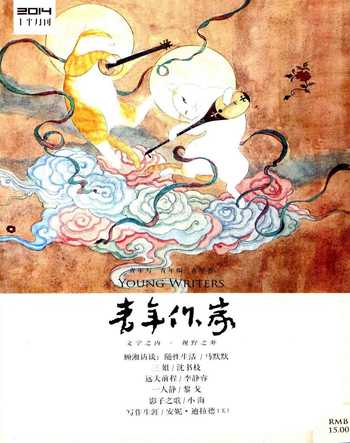盛筵难再,空谷余音:汇文堂
2014-04-29苏枕书
苏枕书
【一】
数年前的冬日黄昏,天色阴沉,突然下起雪。黄昏雪停,忽而起意到汇文堂看看。这间旧书店开业于明治四十年(1907),旧址在丸太町南、御灵神社前,初代主人大岛友直曾就职于东京的中国文史专门书店文求堂,不久回京都独立门户,这与当时京大建校(1897年)也不无关系。大岛友直本人对中国文化极感兴趣,汇文堂也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史类书籍、论文集,因此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方文化研究所、人文研究所、京都学派诸贤交谊极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汇文堂深受森鸥外、西园寺公望、富冈铁斋等人的喜爱。“汇文堂书庄”的匾额即为内藤湖南所题,至今仍悬于店前。
1990年,汇文堂迁到今天的地方,在御所东南角、丸太町通北侧、御灵神社以北,距旧址不远。人事几经代谢,而纵然登门买书的人越来越少,特地到门前瞻仰湖南先生手泽的人依然许多。国内有至京都访书者,亦必造访此地。如辛德勇先生在《未亥斋读书记》中就提起过,说店家老太太怀念昔日学风之盛,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懂读书。故时常不愿与人说话,有些不近人情。
我也是与大岛夫人接触后才知,她并非不近人情,只是常觉寂寞而已。
平时在柜台里看店的是她年轻的儿子。店内靠墙两大排书架,中间一排,尽为文吏书籍。间有少量文艺小说类。书架外侧堆满文库本,皆为古典文学、东洋史一类。柜台后方垂帘右侧有一张堆满线装古籍的书架,断简零缣,卷帙蒙尘。书架之间零零散散堆满书籍,有很多并非二手书,而是当年存下来的老版本,内地、港台及日韩出版者,凡与中国文史相关者,均有所涉。只是久未整理,随手抽出一册,就要落一阵灰。
那天梭巡间发现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的影印本《王国维遗书》,标价一万两千日元。检点发现缺第一册。问店家可否低价出售。此书并非很难得,但市上售价也不低。我在国内一直想收,犹豫未买。当时并没有抱着非买不可的心情,因此问得很随意。年轻的店家到柜台内电话请示他的母亲,说客人想折价买一套书,您过来瞧瞧。
俄而内间帘内走出一位瘦削的夫人,打过招呼后,先道:“怎么会呢,怎么会少一册呢?记忆中明明是全的。”又在架上仔细翻找,仍无所得。便问:“实在抱歉得很。如果你想要。五千可以么?”
她清瘦美丽,披一件大袖交领棉袍,系一条丝巾,也不着急等我的答案,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我便与她多聊了几句,她始终不坐在柜台里,而是极谦虚地立在书架旁,缓缓与我讲了许多旧话。说汇文堂最鼎盛的年代在初代主人大岛友直经营时期。那是她的叔父,刚从东京文求堂回来,广交名士,意气风发。出版了许多书籍,如青木正儿《金冬心之艺术》,内藤湖南、铃木虎雄等人谈梅兰芳京剧的《品梅记》。店内定期刊行的书目《册府》,卷首曾有诸多知名学者供稿,一时风行盛极。1920年,小岛祜马、本田茂之、青木正儿等人创刊《支那学》,最初亦由汇文堂出版,后来才转由京都的弘文堂书房出版。青木正儿回忆创刊往事:“《支那学》发刊的导火线虽说是我和汇文堂点着的,但经营全赖小岛兄的尽力,编辑主要由本田兄负责。我仅列三人鼎坐的编辑会议,纯粹是为了等待会议之后的宴饮。宴饮的盛况——不,其轻狂,属于机密,不可泄露。”
夫人说:“自己生得晚,并没有见过内藤那一辈的老先生。不过家父与他有往来,这匾额——先生题后不久即驾鹤西去。据说编《支那学》时,青木与本田二位先生在我们这里的二楼组稿……”她指指楼上,微微笑道,“他们喝许多酒,畅谈终宵。那会儿来店里的老师很多,吉川幸次郎先生也常来敝处。自己当时年纪轻,什么都不知道,只晓得是位了不起的先生。可惜如今,也都不在了。”
她随手拿了一期《册府》给我瞧,说封面‘册府”二字似为铃木虎雄所题。“那时候每一期都会请不同的老师题字,如今都已不再有了。”翻了翻目录,那期刚好有青木正儿、滨田耕作等人的文章。到此,我己大致决心将那缺一册的套书买下,随口问能不能再稍稍便宜些。京都默认的规矩,不管在哪里买东西,都不可议价,尤其是传统旧书店。早些年,旧书店门口还会贴出“非诚勿扰”的招牌,意思是一口价,要不起就别来打扰店家。我一问出口就觉抱歉,知道自己坏了规矩。
但她想了想,非常爽快,道:“四千吧。”我一愣,忙说十分感谢。
她将十五册书逐一确认,为我找了只大纸袋装好,在手里试了试,不放心,又命儿子找了只纸袋套好,轻声道:“王国维先生在京都待过三四年,叔父还是祖父与他有一张合影……我应该看到过,去给你找找。”遂去房内翻检。过了会儿出来抱歉道:“一时不知道放在哪里。如果找得着,下次给你留着。”谈兴正浓,与我讲湖南先生晚年栖隐在瓶原村读书,即今日木津川市内,距关西大学某校区不远。湖南先生哲嗣乾吉先生亦有著述,可谓家学渊源。
天色已晚,不好意思过多打扰,遂躬身告辞。出门将书放在车篮内,正要离开。那位青年忽而拉门出来,手里有一小包豆政家的果子:“家母说送给你。”声音很小,不待我道谢,又迅速回去了。
豆政是京都百余年历史的老店,经营以黑豆、黄豆、红豆、蚕豆等为原料的豆类小点心,京都人很爱当零食。日本各地都有特色点心,譬如较早接受西洋文化的九州与神户多奶油、黄油类洋果子,靠海的东京、名古屋等地多有虾片、烤鱼片,像京都、奈良这样的古都,人们在饮食方面的趣味也很怀旧,葛粉、麻花、红豆饼、落雁、金平糖。传统点心大多原材料简单,技术朴素,只为恪守传统之味,或许已难满足被牛油、蛋黄、奶油、香精等丰富用料惯坏的味蕾。因本地人的推荐与好意,我也学老派人,逐渐亲近这些古朴的旧味。
那以后,凡有空暇,都会到店里看看。
未必能挑出什么书——架上地下堆满的,实在凌乱极了。有些当年不错的版本,但翻开纸页窸窣,残损得厉害,也没什么买的必要。标价都不低,有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定价。问那位青年,他又只道不知,总要打电话叫母亲下楼。每次都这样打扰,很让我不好意思。2011年冬天到2012年二月末,忙乱困顿,未有余暇,亦难有闲心逛书店,蹉跎到三月初,又回北京度春假,到三月底才回京都。春寒料峭,到熟悉的几家书肆转了圈,未见有什么好的。又到汇文堂,仍是老样子,很冷清。买了两册《皇朝经世文编》,敷了很厚的灰。那位青年讷讷的,在逼仄柜台内四下翻找,寻不到合适的书袋。我忙说不要了,直接放到书包里。
【二】
新学期选了一门中国古代史料学的课,老师是从龙谷大学请来的木田知生先生。木田先生出身京大文学部,在宋史、文献研究、佛教文化方面很有名。上世纪八十年代留学北京大学,在邓广铭先生门下。历任龙谷大学文学部教授、龙谷大学图书馆馆长、龙谷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汉语讲得很好,与中国学术界交往颇密。先生精于版本目录学,对日本旧书店极为熟悉。课上课后听他提起不少书林逸话,极受教益。因常向他请教,他赠我一册影印《京都古书店巡礼》,2000年京都府古书籍商业协同工会出版。内有京都诸家旧书店的照片、简介、地址等。看目录,有不少旧书店今己不存,也有不少这十年间新开的旧书店未录入,世运升降盛衰,令人感慨。木田先生道,现在逛旧书店的心思已经淡了,因为可逛的太少。好容易碰到本好的,又漫天要价,贵得离奇。故而利用日本旧书店网站就好。他为我们整理过日本的中国书籍专门书店,东京有亚东书店、内山书店、光儒堂、海风书店、上海学术书店、书虫、中华书店、东方书店、山本书店、兰花堂、燎原书店、琳琅阁书店、六一书房。大阪有东方书店关西支店、上海新天地中文书店。神户有和平书店。京都有中文出版社、高畑书店(此二者已无实体店,仅余仓库,非熟客不知也)、汇文堂、朋友书店。名古屋有亚东书店、昆仑书房、燎原书店。九州有北九州中国书店和中国书店。冲绳有乐平书店。他说,常用的大部头书就从这些店里挑选、网购,很便利。偶尔也会在孔夫子买书。
“京都的旧书店比起东京,还是逊色许多。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过往事还是很让人留恋。”我曾问他,“老师您对京都哪家书店印象好些?”他笑答“高畑书店、东方书店、朋友书店都很好。不过高畑书店店面已经没有了。东方书店也倒闭了好些年,只有东京的还在。朋友书店好书是不少,第二代主人在生意方面也挺上心。却不重视网络经营,没有主页,在网上也查不到书目,实在很不方便。”
木田先生对图书资料电子化很重视,他善用电子书,精通网络。提起国学网、四库全书、古籍检索系统等电子化资料,常慨叹此于保存文献、便利研究、提高效率功莫大焉。他讲起原京都大学校长、国立国会图书馆第十四任馆长长尾真先生,也极佩服。长尾真毕业于京大工学部电子工学科,专业是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画像处理、模式识别。1980年代前期确立日语形态分析法,完成科学技术论文的日英、英日双语翻译系统,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处理研究专家。1997年到2003年担任京大校长,2007年担任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长,致力于开发电子图书馆。向政府申请得一百亿日元资金,将海量馆藏文献资料电子化,不管是为普通读者还是专门研究者,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箴言是“真理给予我们自由”,长尾真又添了句“知识令我们丰富”。2012年3月末,长尾真辞去馆长之职,引起不小的话题,大多都是感谢他为图书电子化作的贡献。现在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资料库大约公开了古籍资料室七万余种资料,如江户时代以前的和书、清代以前的汉籍。近代电子化资料更庞大,有几十万种。此外,还有大量电子化杂志、报纸、音像资料、官报、博士论文。每回使用,都不免在心中感谢此种功德。
又说了大篇题外话。我虽不担心纸本书的消亡,也不得不承认纸本电子化为势之所趋。相似道理,旧书店的网络化也不可缺。木田先生提起汇文堂,颇为惋惜,认为其风华不再。他评价初代主人大岛友直和三代主人大岛五郎都很有经营的头脑,也有文人风骨。“如果他们还在,大概也会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
不惟木田先生这样说,与其他老师提起来,也均叹惋汇文堂今不如昔。我一得空仍到店里看看,希望能碰到些有用的,但收获寥寥。后只买过京大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森时彦《中国近代棉业史研究》与朋友书店出版的竹内实著《现代中国论争年表》。也未见大岛夫人在店内,那位青年人十分沉默,问他什么,几乎都答“不知”。
【三】
四五月间,好几回过汇文堂,皆闭门不营业。汇文堂定休日在礼拜天,不知为何平时也歇业。与同门提及,大家都觉蹊跷。莫非和福田屋一样迁址?而湖南先生的匾额仍好好挂着,无此道理。想起此前所见店内的冷清,心里总有些不安。一直到六月初,仍没有遇到开门的日子。课后问木田先生可知此况。先生略语数言,大约家道艰难云云。
又一日到寺町通买纸墨,阴雨梅天,市街清寂。循例往汇文堂瞧一眼。远看门前摆着特价书摊,心头大喜,暗道总算赶着一回开门。巧的是大岛夫人也在家,这一天谈了不少。她说,前些日子不在,是因家里有病人。数月不见,她似憔悴不少。仍立在柜台边,并不坐下。知道我想听些旧话,反复称自己记忆力太坏,知道的东西太少。“我只是觉得很疲倦,勉强维持而己。”我口拙,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她道:“我们店已没什么值得提的。父亲过世后,就再也不复从前。”
她说,汇文堂创始者大岛友直是她的叔父,却在盛年遽然病逝。她的祖父大岛友爱维持过一阵,将店传给她的父亲大岛五郎。五郎先生六十岁过世,店传到她手中,衰势已呈,无力挽回。她说,还记得很早的时候,大约是1955年前后,她还很小。父亲和几位相交甚密的老师同聚中国菜馆喝酒谈天,往昔盛会,极可追怀。然而想起来也徒有伤感而己。
她从架上找出大正十一年(1922)再版的《增订平安名家墓所一览》,说这是叔父当年出版的书,店里几无所剩。我说在学校图书馆还见过一些。她面上露出一丝笑意:“是么?那倒真是想不到。”此书一函两册,橘红棉纸封面,收录京都著名的墓地所在。访墓扫苔之类的事,我也做过。初到京都就去法然院前墓地探访内藤湖南、谷崎润一郎、河上肇、九鬼周造等人之墓,又往金戒光明寺寻找竹内栖风之墓。此书所录墓所年代较早,翻阅下来,大半人名不识,非熟悉京都历史掌故而不能读也。勉强看到几个认识的,如“伊藤若冲墓,名汝钧,字景和,宽政十二年九月十日。八十五。深草石峰寺。碑在相国寺中慈云庵。”“上田秋成墓,号无肠,一号鹑乃屋。文化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七十七。南禅寺西西福寺。”“浦上玉堂墓,姓纪名弼,字君辅。文政三年九月四日。七十六。寺町御池南本能寺。碑在嵯峨法轮寺侧。”问她如今汇文堂可还出版图书。她摇头道:“早就不了。父亲过世后就没有了。叔父当年做的那些书,虽有知名的老师抬爱,却受众甚窄,很难出售。凭自己的热情做了些,却卖不动,到底也不长久。父亲当年和中国的一些书商也有往来,关系很不错。父亲一去,也都断了。”
她指着壁上一幅富冈铁斋的书法:“过去铁斋先生常来店里,送了好些书画。父亲死后,亲朋好友常上门来瞧。有伸手要的,我也不知珍惜,东送西送,竟全散了。如今所剩寥寥。”
她四望书架,又歉然道:“店里的书,真的没有什么了。还是常有人到店前看湖南先生的字。我却总有一种感觉,这家店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关门。说出这样的话,很难过。但也没什么办法。”她说前些日从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一封仁井田性书信。信里说看店里的书目有某某书,希店主留下,待自己来京都时亲到店头来取。
仁井田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大家,出身东大法学专业,是东京学派的重要学者。所著《唐令拾遗》《中国的农村家族》《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研究》(全四卷)《中国的法律、社会与历史》均为法制史经典之作。我问她,后来先生来店里了么?她仍是抱歉道:“我不清楚这些掌故,家里只有父亲知道……”
说话间从柜台内的书架上翻了很久,找出两册《册府》,赠我道:“这个给你,如果对你有一点用处的话。”
是复刊后的第十九号(1964年正月)与第二十一号(1965年正月)两种。《册府》创刊于大正五年(1916)十月五日,当时决定一年发行六期。创刊号卷首云“鄙堂经营中国新书并和刻本各书,经验尚浅,多蒙江湖诸贤荫庇。”“中国书籍系直接进口,有各省出版者,私家刻版者”等语。创刊号目录有祁承煺《澹生堂藏书约》(第一),罗福苌《勒柯克氏高昌访古行程小记》,黑风白雨楼主人《嫩窝笔抄》,野狐禅侣《筑山精舍读书记》(一)。附录为中国新刊书目介绍与汇文堂发售书目。第四号、第五号有缪荃荪《清朝经师经义》。友直先生谢世后,《册府》一度停刊。到五郎先生时又出过几期,内容己简略不少。京大图书馆仅有创刊前八期《册府》,关西大学、佛教大学也有零星收藏,此外就只有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得稍微多些,或可一观。
谈话间店里电话响过一回。青年接了,似乎是家事,低声征询夫人意见。我忙告辞。夫人却说不忙,命先挂了电话,仍要和我说几句。自不便久留,复道珍重。她笑着,说恐怕还会有临时停业的时候,未免走空,来之前可以给个电话。以后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资料,也会告诉我。
离开时外面雨己很大,东山烟云飘渺。过丸太町桥,北面群山也云山雾罩。桥下流水湍急,有白鹭与野鸭淡然处之。忽想起清人曹溶《流通古书约》有“古人竭一生心力,辛苦成书,大不易事。渺渺千百岁,崎岖兵攘劫夺之余,仅而获免,可称至幸。又幸而遇赏音耆,知蓄之珍之,谓当绣梓通行,否亦广诸好事。何计不出此,使单行之本,寄箧笥为命,稍不致慎,形踪乖绝,只以空名挂目录中,自非与古人深仇重怨,不应若尔”之语,又觉感慨。
【四】
回校后特往图书馆找出馆藏汇文堂出版的书籍,多少想记录些什么。很难说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一点纪念。那册出版于1919年的《品梅记》很可留意,此书早己进入不少中国研究者的视野,据说译文会收入近年出版的《京剧艺术大典》,不过至今未见面世。原书做得很可爱,小三十二开本,梅红函套,书封正背面有两幅版画,正红底色。绘梅兰芳天女散花‘离却了众香国,遍历大干诸世界”。有“迷”字钤印,疑为青木正儿所作。馆藏乃铃木虎雄所赠。内附戏单六页,梅兰芳同好会印。置于内页手制纸袋内,可能是随书附赠,也可能为铃木虎雄自留。
梅兰芳一生三度赴日演出,每一回都引起相当的轰动。1919年4月是第一次,在东京、大阪、神户演出共十七场。在大阪演出的两天,第一日戏单为《思凡》《空城计》《御碑亭》。第二日戏单详见于此新闻之后,第一,《琴挑》,梅兰芳饰陈妙常,姜妙香饰潘必正。第二,《乌龙院》。第三,《天女散花》。
卷首有人作《观梅兰芳来浪华演御碑亭曲》。次为汇文堂主大岛友直作小引:“江南无此花,傲霜偏幽燕。偶飞入东瀛,墨堤无颜色。既己西下,难波津畔此花绽,因缘亦匪浅。幽赏未央,东风一去。呜呼,余馨满衣,忆君下西洲。如今品花有何人,当代菅原道真也。屈指几何,十三先生并鄙人。”日韩人作汉文,难免生硬堆砌。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倾慕中国文人酬唱之风的他们总绕不开汉文写作这件风雅事。书商能作这样冶丽的文章,已属难得,也难怪汇文堂曾吸引了那么多学者文人,成为京都中国学的俱乐部了。
后录供稿的十三位学者姓名,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小川琢治、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人,共收文章十四篇,有不少标注的是雅号,如小川琢治为如舟,铃木虎雄为豹轩陈人,神田喜一郎为神田鬯庵,内藤湖南为不痴不慧生。文前有梅兰芳生活照一幅、戏装照十二页,风神俊秀,不染凡尘。后附《思凡》《御碑亭》《天女散花》戏词。
当时青木正儿恰在病中,未能去剧院看戏,写了一篇《梅郎与昆曲》。1924年梅兰芳再度访日,青木终于得见,并作画记之。八十余年后的我,在京都思文阁美术馆某次展览中,见到了这幅设色清淡、笔致飘逸的画。
铃木虎雄《观梅杂记》一篇盛赞《葬花》《天女散花》《琴挑》。认为日本的歌舞伎亟待改良。唱腔方面也有必要师法中国戏曲。他说,妙常着道服,抱琴缓步而来,风姿优雅。与生隔案操琴,疑在广寒宫。赞梅兰芳的陈妙常“幽愁暗含娇态,此等妙技恐无人能及”。
神田喜一郎云平生对日本戏剧毫无兴趣,此前对中国戏曲亦一无所知。后听湖南先生提起梅郎,趁此番梅郎东渡,得汇文堂主人热心相助,初次接触京剧。孰料大为震撼。认为梅兰芳的象征主义艺术为最卓越之处。
江户以来,日本学者文人服膺儒教,对中国的学问、文章、诗词、绘画、音乐都很感兴趣,多有潜心研习者。到清末,庞大帝国衰颓受辱,日本也陷入深重危机,但两国民间往来仍密,双方互派留学生,不乏好意。甲午海战之后,日本野心膨胀,纵然此时,中国还有人抱着“学东邻以强国”的心态,日本也有人试图两国联合,共拒西洋。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兴盛,正出于这样渊源与背景。不过,纵是再博学的学者,也会受到政治局势与国家关系的影响,他们研究中国的欲望,并非全出于喜爱与倾慕,还有冰冷剖析与淡漠嘲讽。因此,像青木正儿这样醉心文化、不问政治的学者,在我看来,尤其可亲。他与大岛友直关系很好,1920年编辑《支那学》的同时,还在汇文堂出版了个人专著《金冬心之艺术》。序文写得真诚亲切,忍不住翻译出来:
“从出町一站下来,大约坐一里的人力车,汇文堂主人就叩开我在河畔的土屋。晨光清凉,乃心情甚佳之时。其时此稿恰将收笔,再有一两项补足就告完成。两人一壁眺望前山,一壁交谈。他来是为我在《品梅记》中那篇稿子校正的事。此书是他五月被梅兰芳的京剧迷倒后,在狂热与好奇中,决心出版的。再就是为我送两三册之前预订的书。
他与我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单纯的书商与客人,不如说更像是朋友的交情。他从东京回京都开店,与我是极熟的旧相识。他也是冬心党之一人。要模仿那种两端破圆为方的笔法,必须将笔端剪平。这个纯真的男人很擅长此事。我开始迷上冬心时,他也一起帮我搜集其著作。故而我关于冬心的所有资料都从他的店里得来。
因此当他知道我在整理冬心的资料,看到桌上的草稿时,就怂恿说一定要刊行。我笑了。其内容实在单薄,我实在没法厚颜出版面世。说登在杂志上也就罢了。他说,我不知道。不管怎样,秘置箧底的书稿,已在杂志发表,如果编辑成册,刊行于世,也是一个道理。总想着如何做出不同寻常的书,并不怎么考虑是否好卖,这样不按常理行事的做派是他的癖好。湖南先生曾戏语,将他比作汲古阁的毛晋。
我校正《品梅记》时,他去三宅八幡宫拜谒。校正毕,他又来了一趟。随后即决定着手冬心一稿的出版,高高兴兴回去了。但是我就没那么兴奋。怎么想怎么看都有无耻之嫌。我虽极嗜中国艺术,但提到研究,也不过是在文学研究之余略有涉及而己,是实实在在的门外汉。我在本专业中国文学方面都乳臭未干,若凭副业问世,真是非常寂寞的感觉。由之去罢!毕竞我的事业也都为业余爱好,同以业余爱好出版此稿,本身也是一种业余爱好。就与汇文堂的业余爱好共鸣罢。
乃可准备单行本之题材。且为方便读者,添加书画等插绘。空山蓊郁,必也有两株枯木,两株杂草以作附录。其中一篇《诗画一致》,根据大正三年(1914)秋在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学会公开演讲会上试讲的稿本略作修改而成。另一篇《古拙论》及两篇汉文久于箧底蒙尘。这些是南画主要理论的一部分,冬心艺术的基础特在此中。想起来时,也是更加无益的蛇足罢?”
出町即今天的出町柳,在高野川与贺茂川汇合为鸭川之处,是京阪线与叡山线的起点,旁边有家临川书店,也以出售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籍闻名,据说店名还是初代店主在东京文求堂做学徒时,文求堂主人与郭沫若先生一同拟定。青木正儿对金农是真爱,他到过中国三次,第一次是1922年,游历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扬州、镇江等地,归来即作随笔集《江南春》,文字清雅,极富温隋。其中《湖畔夜行》一文就记载了他在西湖逛夜市时,邂逅金农《梅花图》拓本的兴奋往事。
《金冬心之艺术》后收入春秋社1969年版《青木正儿全集》(全十卷)第六卷,而单行本的面世却全出于青木正儿与大岛友直彼此的信赖与欣赏。作者对书商如此信任,可交付原意尘封箱箧的书稿。书商对作者亦如此知心,可仅凭兴趣全力以赴,而不计销售之难。青木先生也自道此书不被世人理解,无人购买。想起大岛夫人说叔父做的书受众甚窄,难以出售,可为互证。或许大岛友直文人气过重,并不适合做商人。
青木曾将《品梅记》《金冬心之艺术》二书寄赠胡适。胡适有两通回信,予以很高评价,认为《金冬心之艺术》是很有价值的研究。附录的“诗画一致”“古拙论”都是“很有独见”的文章。并指出几处引文句读的错误。且在信中说:“周作人先生读《品梅记》,最赞成浜田先生的一篇的一论,我以为周先生的见解很不错。”
之后的一天,来到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申请阅览《册府》。馆内共藏;大正六年(1917)十月第七号,大正七年(1918)第三、第四号。大正八年(1919)第一、二、六号。大正九年(1920)第一至六号。并复刊后第三号(1955年11月)、第四号(1956年5月)、第十二号(1960年6月)、第十三号(1960年12月)、第十四号(1961年7月)、第二十号(1964年6月),共十八册。原刊为小三十二开本,每期最少二十页、最多四十页不等,发行者大岛友直。复刊为三十二开本,发行者已是大岛五郎。
复刊第四号收入京大中文研究室六位研究者的文章,有清水茂、清水雄二郎、都留春雄、村上哲见、荒井健、高桥和巳。本期附有汇文堂旧址的照片,为二层木楼,临街有两间,并立两面招牌,左侧为内藤湖南的匾额,右首为“中国书专门”的字样。
复刊每期都有大岛五郎简短的跋文感谢供稿人。此外常常提到某日自己身体状况糟糕,导致本期延迟发刊等语。第二十号有一则简短告示,说最近旧书业经营十分困难。汇文堂会尽可能给出收购的高价。请诸君参考本书所附图书目录,对自己想出手的藏书估价。若想出手,必登门收购云云。目录大概分经、史、子、集部、甲骨、金石、书画、印谱、丛书、新刊本几类。也有少量港台书籍。可惜我对目录版本一无所知,只能略翻而过,无甚所得。
大岛夫人未见过她那位叔父,只从父亲那里听到点滴片语,而今也渐随记忆模糊销蚀。她反复说,汇文堂是过去的事,今日之况羞于提及,觉得辜负了逝去的故人,也辜负还记得这个名字的人们。我听了不知作何言语,惘然并惋惜。
那位青年,有一天突然对我说:“汇文堂之类,每次听客人说起来,都无言以对。过去的经营方式,店家与客人的交流方式,我全然不知。那是彻底不再有的事。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其实完全不想这么做。可我到底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听了默然无语。
【五】
光阴荏苒,转眼就到了2013年的春季旧书即卖会。京都一年有三大祭,五月葵祭,七月祗园祭,十月时代祭。日文中的“祭”,是盛大的节日。有意思的是,京都古书研究会每年也会举办三大祭,时间与前述三大祭大略接近:五月初于劝业馆的春之古本即卖会,八月初于下鸭神社古森林的夏之纳凉古本祭,十月末于百万遍知恩寺的秋之古本祭。春季书市在平安神宫附近的劝业馆举行,相对其他两场设于室外的书市,要稍冷清些,或许是因为室内封闭的环境,“祭”的气氛不够浓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