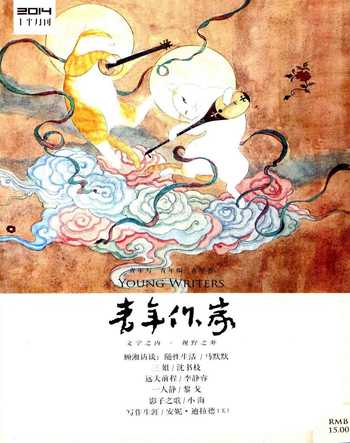老挝,神的游戏
2014-04-29叶舒婧
叶舒婧
【一】
当我们谈论一个国家的时候,脑海里会潜意识跳出那个地方的关键词,比如巴西和热情、日本和精致、英国和绅士、不丹和虔诚等等。然而,在去老挝之前,我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连一个意义明确的形容词都蹦不出来,甚至完全没有它与柬埔寨、缅甸等邻国的差别概念。这个置身于我们西南方的小邻国,一直保持着那种不输于不丹的低调和神秘。正是这样,我选择了一种最不观光客的进入方式,搭车到云南勐腊县的磨憨口岸,从陆上穿越边境,用这种渐进的方式,开始对神之国度——老挝的初探索。
跨国的巴士上,我遇到了一个去老挝琅南塔省教书的女孩,瞥到她护照上也是和我一样的30天旅游签证,不禁好奇地问,“你去大学教书不是工作签证么?”女孩倒是很不以为然地回答,“没事儿,只要进去了就行,过期就滞留着,到时候会有人派车把我们偷偷送出来。”刚聊完,就在简易棚似的入境处遇到了预期中的海关索贿。一起过境的大多是来往老挝做生意的云南人,大家早己熟悉了这套规则,交了钱迅速过关了事。出于那么点不想逆来顺受的心理,我假装不明状况,在窗口和工作人员僵持着,似乎在比谁能坚持更久。最后,无奈的海关人员只好给我的护照盖上章,放我这名“不明事理”的观光客入境消费。
我这才意识到,面目模糊的老挝,正在我脑海里一点一点建构着属于它的关键词,尽管开始并不那么美好,但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它的美丽与哀愁。
【二】
从边境坐车前往老挝的古都琅勃拉邦,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却用了将近十个小时,我被挤在一辆严重超负荷的巴士里不得动弹。车顶绑满摩托车,车里的过道堆满了米袋,同时听了十个小时不间断的老挝语神曲,同车的另一位外国人是意大利人安迪,他是我在这一段漫长的折磨之旅中唯一可以交流的对象,每当两首歌中间出现短暂安静的间隙,让我们以为可以稍微睡一下时,紧接着更如雷贯耳的音乐瞬间打消了这种美梦。安迪垂头丧气地对我说“你听,又来了,我的上帝啊。”我只好开个玩笑安慰他,“在这里你还是求求佛祖大人,或许更有效。”
就在即将对我的忍耐能力丧失信心时,巴士停在了琅勃拉邦不那么撩人的夜色重。我们饥肠辘辘、筋疲力尽地下车,背起那个快把我压垮的大背包,走向古城最著名的洋人街。对,这个太不老挝的街名,显示出一种它对全世界背包客的开放姿态。我和安迪在身心俱疲中坚持着穷游的原则,艰难地穿梭在夜市的人群中,一家一家地寻找便宜又干净的小旅馆。我隐约感觉到经过了无数座安然藏于夜色的寺庙,在世俗的喧哗中感受到一些不可思议的注视,看着洋人街上这一派西贡范五老街、金边河岸区、曼谷考山路似的情景,会差一点忘了这是个不太一样的国度,神的游戏每天在此上演。
【三】
琅勃拉邦失去首都的身份,仅仅40年不到。在1975年君主制被推翻前,它还是这个国家的王都,毕竟“琅勃拉邦”这个名字就来自老挝的国宝金佛“勃拉邦”,自从澜沧王国时期起,它已是这个神奇国度的中心之中心。
古城恰处于南康河和湄公河的交汇处,洋人街是贯穿这片区域的主要干道,从地形上看,这一小块河州,像是大拇指和与手相连接的虎口,而琅勃拉邦的新区,可以说是这只手的其他部分。对游客来说,我们每天的观光路线就是在这根大拇指上来回地走,假如你还渴望一点奇遇,大可以抱着刻意去迷路的心情,走入左右两边岔开的小道,但多数的结果是,晚上你会发现一间又一间流光溢彩的酒吧和餐厅,白天则会闯入一座又一座安宁的寺庙。
洋人街上最著名的景点非香通寺莫属,它是我心里唯一能和吴哥窟巴戎寺并驾齐驱的寺庙。一个美得灿烂炫目,一个美得神秘深沉。寺庙这种博大精深的美,从来就不是相机这种现代文明的产物能摄入的。多数东南亚寺庙的美,都是具有叙事性的美,柬埔寨的小吴哥、印尼的婆罗浮屠、曼谷郑王庙的浮雕,包括香通寺墙上镶嵌的彩色镜面拼贴,都在讲述着佛教中的传说故事。香通寺除了镶有生命之树图案的黑金漆大殿外,后边有两座粉色打底的小佛堂,四面墙都贴满了六色镜面组合的壁画,阳光下反射出的光芒虽然华丽,但单纯的色彩组合,却让整个基调看起来很质朴动人,可惜才疏学浅,对于墙上那些典故只能看懂大概,剩下的就是纯粹欣赏工艺之美了。
但说起来老挝最爱的,不是这华美无比的香通寺,也不是首都万象的玉佛寺和塔銮,反倒是琅勃拉邦一间不起眼的小寺庙——春孔寺。寺如其名,就是一种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感觉。
很奇怪,虽然也是典型的琅勃拉邦式寺庙建筑风格,春孔寺却有种日式花园的纯朴自然感。粉白色的三角梅作前景,后边是青苔剥落一半的石头小佛塔,还有脚下飘满一地落英缤纷的木质殿堂,两条曲折度恰到好处的小径从旁擦身而过,路两侧摆满了一盆盆带刺的热带花卉。没有游客,偶尔会在花丛中蹿出一名着橘色袈裟的小和尚,或者只得我一人。特别安静的时候,仿佛能听到掉在地上那些三角梅和蚂蚁讲话的声音。
那时候我有点明白春孔寺为何美得如此不可方物了,它不经意间在人工美和天性美之中找到了最恰当的一个度,所以美,能美得浑然天成,美得呼吸顺畅。此时老挝已经在我脑海中增加了一些关键词,比如“遁世之寺”。
【三】
在本可以懒洋洋宅着的琅勃拉邦,还有一项“神秘”的活动风雨无阻地进行着。为了看这著名的清晨布施,调了早上5点的闹钟,来不及洗漱就冲出旅舍门。寺庙遍布的洋人街边早已站满守株待兔的游客,个个手持长枪短炮。这情景是那么的似曾相识,喀纳斯禾木的日出,又或是小吴哥的日落,哪一处美景不是如此呢?
只是没想到,作为僧侣日常功课的布施活动,因为游客的围攻,居然完全沦为一场“秀”了。旅游大巴载来专为体验布施的泰国游客,这些信徒跪在席子上,身披同样的绿格子绶带,头戴旅行社发的帽子,面前的竹篓里放着统一分配的米饭和零食。旁边一对上海小夫妻已把相机调到了录像模式,突然一个跑到前头侦查情况的杭州老头,拿着三脚架飞奔回来。大喊道“来了来了!”无数相机举起,闪光灯蓄势待发,颇有奥斯卡明星走红地毯的气势。
只见远处一大片橙色缓缓飘过来,连绵不绝的僧侣们排队挎着锡钵,一个接一个从信徒面前走过,接受布施的米饭、零食,甚至还有钞票塞进来。扮演信徒的游客身后还有一支强大的摄影大军,负责给她们抓拍布施的一刹那,待僧侣走过后,信徒们纷纷起身摆出v形手势合影留念。哪知道后边又一片橙色飘来,措手不及之下慌忙坐下,有几位太着急还一屁股摔倒在席子上。而僧侣们的锡钵经这么一路不停地施予,往往被塞得要溢出来,这就无法满足前边信徒的布施需求了。怎么办?不怕,早有人贴心地在路边摆上垃圾篓,我就眼看着一位僧侣边走边偷偷把锡钵里的米饭和旺旺仙贝拿出来倒掉,好把钵空出来。
这样的布施非但不神圣,反而让人感觉出一份搞笑意味,大家都无奈,但恁得也要把这戏演下去。然而,假如你离开洋人街走到旁边的小岔路上,倒是能看到当地人虔诚地跪在自家门口,双手合十,闭上眼睛,把清晨煮的第一勺饭菜布施给僧人。
僧人接受完布施便纷纷隐入修习的寺庙,游人这才心满意足地一哄而散,信徒们钻进旅游大巴被一车车拉走,街道终恢复宁静,仿佛清晨的那一阵骚动全然没有发生过。天仍未亮得彻底,被沁入鼻孔的丝丝鸡蛋花清香所迷惑,我打消了回旅舍睡回笼觉的念头,漫无目的地在六点的洋人街上乱逛。我走入一家西式早餐店,选了面朝街道的位置,藤制桌椅和餐具盒古朴可亲,穿着白衬衣的侍者端上现磨咖啡、吐司和煎鸡蛋卷。一个古城正在慢慢醒来,这是一种你可以感受得到变化的缓慢,街角昏睡的猫咪伸了伸懒腰,似乎在抱怨美梦被打搅的不满;两层高的复古西洋建筑一间间睁开眼,
一缕阳光打到寺庙白色的低矮围墙上,光影攒动。
若此时步入路边一座不起眼的小寺,看到小和尚在三角梅花架下打扫、学习的背影,作秀归作秀,他们的生活倒是从未改变。
【四】
琅勃拉邦的晚上,似乎就是在等夜市开场和等夜市结束中度过的。即使没有清迈周末夜市那样眼花缭乱、充满艺术气息,但作为东南亚旅行中的保留节目,老挝也绝不会缺席。傍晚,则是世俗世界与神祗国度的分界线。
正对大皇宫的普西山是座只有328个台阶的小山坡,但它有一种神的视角,站在山顶能俯瞰整个古城的美景。日落时分,我在半山腰找了个座位,看着下边洋人街上红色的帐篷支起来,一顶顶像水面上浮起来的莲花,盘着髻的苗族老太太拎着蛇皮袋跳下大卡车,开始铺出传统筒裙、木雕、手绘纸灯笼、民族饰品等物件。来往的嬉皮男女都穿着地摊上淘的花裤子和麻布衣,踩着破破的拖鞋,努力把皮肤晒得又黑又糙,显得很异域风情又很融入当地生活的样子。不远处的街角,一位刚刚抵达的金发姑娘跳下突突车,从车顶取下比人还高的大背包,带着那种明显初来乍到者的好奇眼光,开始寻找她的落脚地。和三天前的我一样,疲惫又义无反顾地扎入眼前这个崭新的世界。
她也穿着同样的东南亚风情衣裳,或许是穿越泰国或柬埔寨而来。对于长期在路上的背包客来说,首先我们就可以从服装上去尽可能地接近当地,这是把自己丢出游客身份最快捷的方法。然而,两者之间总有种轻而易举就能看到的隔膜。这种隔膜,如同何伟写《江城》时的距离,正因为他能够随时抽离涪陵这个小城市,才能够以那么客观冷静的眼光观望,才能够不带任何情绪地诚实书写。我们每一个到此晃荡的背包客也都一样,无论我们多想摆脱自己的不同,但终究和那些下半生被浇铸这片水泥地里无法移动的人们不一样,一旦我们不喜欢了,厌倦了,就可以立刻买一张车票,换到下一个新的城市,再借此来释放对困于原本人生局限性里的不甘。
第一天晚上,我和意大利小伙子安迪忍不住在每个摊前停留,尝试着糯米饭、老挝米粉、生菜春卷、肉末色拉、椰奶饼等小吃,为那些绣着大象图案、画着橙色僧侣背影的小玩意着迷。到了第三天晚上,我们渐渐发现,每天在这来回的夜市摊上,总是在和同一些旅人相遇,人们不厌其烦地走着同一条路,试图在这色彩缤纷之中淘到一些属于自己的特别的东西。或许我们最后都失败了,仅仅买了一件柬埔寨市场也有的灯笼裤,一条做工粗糙的编织手链,或者几枚无一例外有僧人出场的明信片。
回到旅舍,发现房间里又住进来两个在北京工作的亚美尼亚人,大家打招呼的方式无一例外,“嗨,你去夜市了吗?”“嗨,你从夜市买了什么回来?”逛完了夜市,意味着你在琅勃拉邦的一天可以名正言顺地结束了。当然,假如你想去爵士酒吧再喝一杯的话,也一定会有人愿意奉陪的。
【五】
和每一个饱受殖民之苦的国家一样,老挝在被邻国暹罗和越南入侵过之后,十九世纪末期又沦为法国殖民地。最明显的痕迹便是皇宫博物馆里的旧皇室生活的居所,除了那些金碧辉煌的佛像、传统器具之外,还有最后一代国王西萨旺穿过的西装和王后的高级法国洋装,而皇室接待厅里的壁画,也是由一名法国画家在1930年绘制而成。
这种殖民经历显然造成了老挝某种程度上文化的分裂。整个老挝境内没有一间KFC之类的全球连锁快餐店,却有不少口味正宗的西餐厅、烘焙坊和法棍摊。比如洋人街路口一家叫“Joma Bakery”的咖啡厅,格调雅致,三两木质小圆桌,乍一看是像带有异域风情的星巴克。点了一杯拿铁、一小块烟熏三文鱼培根披萨,坐在二楼的百叶窗前,吹着头顶四页的铜质电扇,边享用悠闲的下午餐,你可以想象,一百多年前,穿着华丽洋装、跟着丈夫从欧洲远道而来的大使夫人们,就这样打发着每日时光。的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老挝抵挡住了全球化的冲击,它没有被卷入那种模式化的现代文明漩涡。古城的街道更不会像国内大多数二三线城市的步行街那样,开满麦当劳必胜客;也不会像小清新胜地厦门丽江那样,被食物难吃却只剩下文艺的咖啡店攻占。更重要的是,人们依旧生活在这里,不是表演,也并非交易,仅仅是那样地生活着,在自己的信仰里。
然而当我爬上普西山时,恰好一间寺庙学校下课。一个个穿着鲜橙色袈裟的小光头从身边窜出来,打着赤脚,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学生一样,嬉戏打闹着。在山顶的小亭子里,我遇到了一名叫Kun的小和尚,他有着健康的肤色,从袈裟里露出一只黝黑光洁的胳膊,眼睛明亮,睫毛浓密,用一口流利的英文跟我聊起来。
“你有Facebook吗?可以告诉我吗?”Kun开门见山地说。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呢。Facebook在老挝很流行吗?你一般都上去玩什么?”我支吾着回答。
Kun眉飞色舞地说起来,“上面有好多好玩的呢,还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儿。”
“可是,你不是在当和尚么?”我感到有些不能理解。
“不要紧不要紧,在老挝,几乎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当过和尚,去庙里念书。再过几年就可以选择还俗还是继续当。”说着,Kun给我看他的英文课本,“厉害吧!我要把英文学好,也许以后能找个外国女朋友。”我一边笑着鼓励他,一边为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和谐给自己造成的冲击而困惑。
再把镜头转到万象,最大的市场里卖着稀奇古怪的山寨电子产品、封面诡异的唱片、闪着过度耀眼光芒的首饰、款式浮夸的服装,很多商品在我看来都散发着一种自然的复古气息。不像柬埔寨满大街放着张学友陈奕迅的翻唱歌曲,老挝的Ⅱ昌片大多是自己本土的民族歌手,也有一些泰国的流行歌,印刷质量看上去很差,歌手的人影是重的,但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在琅勃拉邦去万象的大巴上,车里的老挝乘客全程兴致高昂地看着车载MTV,毕竟没有比流行音乐更容易让年轻人感到欢乐的东西了,即使是在一个信仰小乘佛教的国家。
我租了一辆自行车,穿梭在这个奇妙的首都,骑着骑着,后面居然追上来一个男人,用蹩脚的英语跟我搭话,聊了没几句便笑着问,“可以跟你合个影吗?”尽管不好意思拒绝这么诚恳的请求,还是觉得有些唐突,作为一个走在街上很扎眼的外国人,万象的节奏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就在那天下午,我在湄公河边逛着逛着,又遇到了之前那个男人,他邀请我进去吃饭,说河边这家餐厅是他开的。半信半疑地接受了好意,才发现我的疑心真是对这种热情的亵渎。
不得不承认,从踏入老挝的国土开始,心里预设的“落后”“传统”等先入为主的观念仍旧在那里。在老挝历史上第一部故事片《早安,琅勃拉邦》里面,带有一半老挝血统的摄影师回到故乡取材,爱上了当地的女导游舜。两人从巴色到万象再到琅勃拉邦,经历了被船夫放鸽子、订了票的车却提前开走等等意外,同时也被当地的农家热情款待。在老挝,尽管也会遇到这些东南亚式的匪夷所思,至少你不用像印度那样时刻提防陷阱和骗子,你仍旧可以保持对纯真的想象和期待。这也许是我们大多数人去老挝旅行时想要找回的东西。
【六】
本来打算在老挝呆足半个月,每天过着低消费却闲适到把旅行变成生活的日子,好像也不错。然而琅勃拉邦虽有让人欢喜的寺庙,有干净平和的花园式街道,有随处可见的咖啡馆西餐厅,但每每促成我尽快离开一个地方的理由就是——没有吸引人的本土美食,在几次失败的尝试后,也终于失去了对老挝菜的再次探索。
决定从万象坐巴士出境,这个首都就位于边境,隔着一条薄薄的湄公河,对面就是泰国廊开。世界上把首都设在边境的国家屈指可数,和朋友聊起这一点的时候,对方不以为然地说:“那是破罐破摔吧。”
这略带讽刺的回答让人莫名有点心酸,归根到底,也是历史对一个民族不怀好意的玩弄的结果。想起在老挝的最后一个夜晚,暮色降临,我穿着在夜市买的民族服装,趿拉着人字拖,在湄公河边散步。广场上立着阿努王的雕像,以一种面向泰国廊开的耐人寻味的姿态。要知道,这位国王在1827年领导了反抗暹罗国的起义,可以算是老挝的传奇民族英雄之一。我在河堤席地而坐,任由傍晚的凉风灌满我的棉布灯笼裤,身后是这位争取民族独立的阿努王,眼前是以泰国廊开作背景的金色落日,一前一后的强烈对比,足以让人体会到老挝和它的邻国之间纠缠不清的历史过节,这个国家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苦难,现在它如此的平静自然,罕见地在全球化的热潮中走着自己的步调。也许可以将其归为信仰的力量,然而免不了担心,下回再来的时候,洋人街上是否真的会开起麦当劳之类的洋快餐?在消除信息不对等的同时是否也消除了难能可贵的保守和传统?
对有一些城市的喜欢,可能要等到离开之后才会发现,而且是在某种怀念中渐渐升华的。琅勃拉邦就是其中之一。让我离开后还时时想起的,是洋人街迈佛寺路口那个夜夜座无虚席的自助摊,老板面前摆着十几种菜,有通心粉、蔬菜杂煮、炒南瓜、炒米饭等等,付八块钱人民币,可以在一个盘子里任意装,接着老板把这一盘倒进锅里,像大杂烩似的一炒,买一瓶老挝啤酒放旁边,琅勃拉邦路边派对就这么开始了。
简陋的一排小桌子前,有个讲单口相声似的法国妖娆大妈天天坐镇,炒热气氛;对面是一对韩国老夫妻,旁边是几个德国背包客,还有来自日本京都的小伙子岸渊。大家用英文间歇性转换母语的频率聊天,你能听到法语、日语、韩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单词在头顶上面的空气中爆炸。来自不同的远方的我们,各自在老挝找到了某些期待中的东西,或许只是一个抽象的旅行的意义。
夜摊散后,我和日本小伙岸渊君绕着洋人街散步,走到河边某个转角,棕榈树下凉风习习,湄公河的流水轻声呜咽。岸渊君突然抬头指向天空说,看,北斗七星。果然,漆黑的夜空中满天繁星,有一把勺子的形状在静静闪烁。习惯了大城市被光污染后永恒的橘红色夜空,我居然都没有想过再抬头看一看这里的天,原来是多么不一样的夜空。
满天的星光啊,还有黑暗中静默以待、包围着我的大大小小的佛像。在这里每天都可以做着神的游戏,众人如神寂寞,众神如人般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