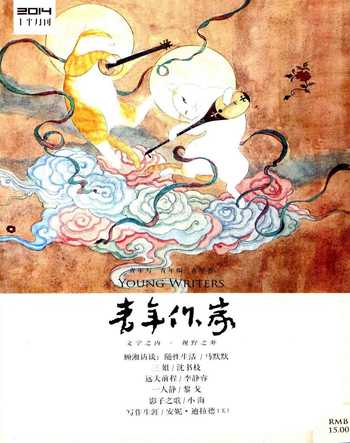远大前程
2014-04-29李静睿
李静睿
时间只用稍微倒回一点点,大三的最后几天,我在图书馆里和范语有第一次对话,内容如下:
范语走过来问我:“同学,能不能看看你正在翻的这本《金瓶梅》?”
过了十分钟,范语又走过来问我:“同学,能不能把你撕的插图给我复印一下?”
因为这次对话,我觉得范语是个流氓。我回去给宿舍的人就是这么讲的:“范语是个流氓。”宿舍的人表示了谨慎的赞同。
同样的话,我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陆续给好几个人说过,包括我当时的男朋友、物理系的林小飞。事实上,那些人和林小飞都根本不认识范语。时间过去三年,林小飞从北京飞来广州看我,我们在北京路上的一家小店喝粥,天气很热,林小飞一边不停擦汗,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范语是个流氓。”
时间只用稍微倒回一点点,我和范语有第一次对话那天,南京的天空蓝得发晕,一团团云厚实得像我刚晒在阳台上的被子。我从宿舍慢慢走到图书馆,途中经过奶亭,我用牛奶卡换了一瓶像海藻一样的绿色酸奶,一口气喝完后觉得很满足。我刚过21岁生日,穿一件前面印着鱼骨头的蓝色T恤,不穿内衣,头发乱蓬蓬地梳成一条很粗的辫子,两天以前刚和林小飞去过学校旁边的北郊宾馆开房。林小飞问我,为什么做爱的时候我总是有点漫不经心,喜欢把双手枕在脑后?这个问题我想了想,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我天生冷淡二是我喜欢思考,任何时候都不乐意闲着。两种可能我都觉得会伤了林小飞的心,所以我选择了什么都不说,但是我并没有什么都不做。
那一天,我从宿舍慢慢走到图书馆,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拿了一本插图本的《金瓶梅》,开始小心翼翼地撕里面的插图。
范语走过来向我要插图复印的时候,我刚好撕完最后一张。不用仔细想我也记得,那时候的范语个子很高,一脸不耐烦,穿一件很皱的灰色衬衫。即使他不向我借插图,我还是要说:“范语是个流氓。”
时间回到现在,范语说他当时就注意到我胸部很平,而且没有穿内衣。但是范语也注意到我睫毛很长,后颈上文了一个小小的加菲猫。
时间回到现在,范语在和我做爱的时候最喜欢吻的地方,一是我的睫毛,二是那只加菲猫,尤其是加菲猫的肚子。
时间回到现在,我和范语做爱的时候极其认真,双手喜欢紧紧抓住他的肩膀,高潮来的时候,经常把范语抓伤而自己浑然不知。这说明我一不是个性冷淡,二也没有那么爱思考。我对范语说,“林小飞知道这些肯定会伤心。”
不用说你也知道,在知道范语和我一样喜欢《金瓶梅》之前,我事实上已经认识他,而且对他很是注意。范语大我一届,读的是法律。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多次在学校的各种讲座上和各种演讲人吵架,而且每次都吵得很凶。在听过一两次之后,我去听各类讲座的目的悄然变成去看范语吵架,而且再也不喜欢林小飞陪我去。
范语吵架时说过的那些话,有一些我至今记得。比如他说,一听到所有人都装作这场演讲这些人这个世界不是那样把有趣糟蹋成无趣,他就气得发疯,忍不住要和所有人为敌;再比如他说,明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你们还要他妈的若无其事装作这件事不存在,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范语吵架的时候同样是一脸不耐烦,拿烟的手微微发抖。和范语有了性关系之后,我发现他的手总是微微发抖,抽烟的时候烟灰总是往下掉,经常烫坏自己的裤子,所以范语的裤子上均有尺寸不一的小洞。但在和范语有关系之前,我不可能注意到他的裤子。我只注意到,范语和人吵架的时候拿不稳烟,而且满脸痛苦,头发乱得不可收拾。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暗下决心,终有一天,我要在范语抽烟的时候握住他的手,让他好好把烟抽完,除此之外,我还想把范语乱蓬蓬的头抱在胸前,然后吻他的耳垂。
然而事实是,我一直还是没有实现那些心愿。所幸时间还很长,我对范语说,“这种事情就像扳手腕,总有一个人会先手酸。”
范语不相信生命就是一个手酸的历程,不相信自己手酸了,然后就放开拳头。范语说,一定还有别的出路,他一定可以一直紧紧攥住自己的手。就为了范语这句话,我觉得自己可以爱他,必然爱他。
在我四处说“范语是流氓”之后不久,范语毕业离开学校。辗转多人后我打听到,他去了广州。因为司法考试只考了两百多分,拿不到律师执照,他在一家都市报里做记者。知道这些后没多久,我和林小飞在学校南门外的一家小饭馆里分手。
和林小飞分手那天南京刚降温,风从各个方向灌进饭馆,为了保暖,两个人一杯一杯地喝茶,直喝到那壶劣质龙井淡如口水。按照我们的习惯,点的四个菜是红烧排骨、大煮干丝、酸菜鱼和韭菜炒螺丝。因为觉得是分手饭,后来又加了一个小盘鸡,下面皮的时候我觉得林小飞哭了,但我装作没有看见。就像我装作没有注意到,酸菜鱼还没有吃到鱼头,我也哭了。那顿饭吃了三个小时,我和林小飞把所有的菜吃得精光,包括那些零零落落的鸡皮。付账的时候一人出了三十块,然后他回三舍,我回四舍。就这样一直到毕业,我再也没见过林小飞。
这件事情说起来理直气壮,实际上我却觉得颇为诡异。分手之前,我和林小飞的宿舍窗口对窗口,每天中午我只要对着三舍叫一声:“林小飞,吃饭啦!”五分钟之后,穿戴整齐的林小飞就会拿着饭盒在食堂门口等我,塑料饭盒上有一只嫩黄色的小鸭子,因为那是我在教育超市给他买的。如果你要说有一天我会和林小飞老死不相往来,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时间稍微倒回多一点点,林小飞是我的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高中同学,两个人的家相隔一百米,我妈在阳台上对着他家叫一声:“林小飞,阿姨今天做蒜苗回锅肉啦!里面放了锅盔!”无肉不欢以及酷爱锅盔的林小飞“噌”地就会来敲我家的门。
然而忽然之间,林小飞消失无踪,仅仅是因为我们不再每天用各种匪夷所思肉麻话填充彼此耳朵,以及每个月存钱去宾馆开一次房间。仅仅因为这些我从来不在意的联系,我和林小飞就此断了所有联系。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荒谬之极。
时间回到大一,我和林小飞在珠江路的宾馆里第一次做爱,由于低估了这件事的难度,我们折腾了大半夜都没有成功,两个人都有强烈的挫败感。林小飞想开灯找找位置,被我严词拒绝。说他“耍流氓也不能不要脸”。
时间过去没多久,比开灯找位置更不要脸的事情我也让林小飞做了不少,因为我觉得我和他熟,既然大家都那么熟,要不要脸就没那么重要。
我还觉得,既然做了这么多又耍流氓又不要脸的事情,我和林小飞这辈子就更不可能脱了干系。我经常给林小飞说,“因为我们熟,比世界上大多数和大多数之间都熟,所以我们应该永远保持联系,而且不是偶尔打个电话问‘你好吗这种联系,这和我们是否接吻上床一点关系都没有。”林小飞对此表示了谨慎赞同。
可惜学物理的悟性毕竟有限,吃过分手饭之后,林小飞就把这些忘得干干净净,这让我觉得他做人太不地道。我一直想冲到林小飞面前给他一巴掌,但是因为始终没再见到他,所以未能如愿。
时间过去两年,林小飞最终悔悟,决定从北京来广州看我,我陪他在广州的街头走了两天,始终想给他那一巴掌,但最终还是没有,因为我还是觉得我和他熟,既然熟,就不能太过计较。
时间回到现在,我从日常生活到性生活都渐渐走上正轨。每周末从我住的地方开始转两次公交车,用掉四块钱的羊城通,下车之后在7-11里买两瓶矿泉水、一包棒棒娃牛肉干,然后过天桥,走一条长长的路,路旁种满了细叶榕,长长的须垂到地上。我在东张西望后闪进范语的宿舍,范语从不锁门,一般是光着上身坐在床上抽烟、看电视,他转头看看我,又把头转了回去。
有件事情多少有些难以启齿,不知为何,我一看见范语的身体就会邪念顿生,总忍不住动手动脚一番。范语对此深为不满,认为我总是试图玩弄他。我只好告诉范语说,我认为他万分性感,一见之下总是难以自持,冒犯之处,请多包涵。
事实上,范语虽然个子很高,却也甚是粗壮,比一般意义上的粗壮还要粗壮那么一点。如果哪一天凑巧吃得太多,范语告诉我说,那他低头系鞋带就会多少有点障碍。有一次我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抽烟,范语看我一眼,又看我一眼,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嫉妒我,因为大腿太粗,他很久没能跷起过二郎腿。除此之外,范语毛发很重,随便哪里摸上去,都是毛茸茸的一片。因为毛发太重,范语还很容易出汗,即使刚用威露士洗过澡,身上还是有淡淡的汗味。因为这些,范语不甚自信,因此说,我愚弄他。
事实上,我所说一切皆出自真心,我敢发誓,甚至敢用那些并不拥有的永恒发誓,虽然细想之下难免理亏,但我就是觉得范语万分性感,一见之下也的确总是难以自持。我相信这句话经得起很多考验,虽然考验的时刻还尚未到来。
我告诉范语,沈从文追张兆和的时候对她说:“我爱你的灵魂,也爱你的肉体。”现在我也要对他说同样的话,虽然抄别人的情书有点小家子气,可是这句话是对的,是真理,我们就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我们不要与真理为敌。
我还对范语说,等他和我一样把这句话烂熟于心,并且付诸实践,那即使是谈恋爱这么摇摇欲坠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战战兢兢地表一表决心,现在谈这些还为时过早。
我没有对范语说的是,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们谈什么是正当其时。做完爱后范语倒头就睡,我却时常在半夜醒来,翻身起床,从窗头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手电简,再顺便看看里面是不是还有范语和王仪的合影,放在一个小小的木质相框里。由于相框始终在那里,我也就常常穿好衣服后出门。有时候就在宿舍大院里走走,有时候会走得很远。
某一个晚上,大概是在2004年的12月,广州已经数月没有下雨,空气中充满灰尘,即使是深夜里也是如此。那一个晚上,我从沿江路走到二沙岛,再走完整条东风路,途中抽完整整一包紫南京。空气是如此之差,以至于我一边抽烟,一边几乎窒息。由于走得太累,抽最后一支烟的时候,燃尽的烟头把我的手指烧出一个小小的水疱。
回到床上的时候已经是清晨,我悄悄脱光衣服躺到范语旁边,他下意识地一把把我抱住,几乎是片刻之间我就睡着了。清晨醒来后我们做了一次爱,我在迷迷糊糊中吻遍了范语满是汗水的身体。
阳光透过被我贴满报纸的窗户一点点地照在范语毛茸茸的身体上,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居然让我猛然惊醒,好像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正当其时。我尽可能紧密地抱住他,直到自己也喘不过气。
范语对这些浑然不知,范语睡着的时候对一切都浑然不知。我有时候会想,幸亏这一切都浑然不知,要不我就害羞脸红掩面而逃了,你也知道,爱情总是一件害羞的事情,我们都还没有习惯它。
和林小飞分手三年之后,我和范语在一起的第一天晚上就上了床。比起和林小飞的艰难历程,我和范语都显得轻车熟路。两人均在黑暗中沉默不语,没有舌吻,几乎没有抚摸,整个过程不超过十五分钟。因为没有准备,也没有用安全套。范语睡着后我就起身凹家,一觉醒来之后,我一边刷牙一边费劲地想:昨天晚上到底是不是在做梦?但如果真是…场春梦,它又是不是过于潦草过于不尽兴了一点?
由于做爱的时候并没有第三者在场,我想来想去,要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做梦还是真的满身汗地和范语有了一夜情,唯一的办法是直接向当事人范语求证。但这件事显得太过荒谬,加上怕范语全身发抖地和我吵架,我一直没有将其付诸实践。
在拿不准是不是和范语上过床的那段时间里,我想到了几个和范语有关的问题,一是我认识他这四年,范语过得到底怎样,以及在我不认识他的超过二十年里,范语到底过得怎样;二是范语是否记得沉默着和他做爱的这个女生,总是在大学的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与他不期而遇,她眼睫毛很长,后颈上文着加菲猫,以及她总是在所有的场合里,看着你。后来我们渐渐成了熟人,不管是床上还是床卜,我却从来没有问过他这两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既然我们已经是熟人,这些问题不再重要,一切都不再重要。
我后来给范语说,之前的事我看不到,之后的事我也看不到,但是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开始,他的生活巨细,就统统和我相关,因为我们建立了联系。建立联系,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不管以后我们跟谁满身大汗地接吻上床,这种联系都不可能凭空就此消失。这件事情说来荒谬,其实却是真理,我再说一遍,你不要与真理为敌。
我还给范语说,我相信他前程远大,和人上床这种事情,他以后还会经历许多。比起我们的沉默不语,在他的远大前程里,一定会有更美妙的爱,但是因为我和他建立了联系,并且在他察觉之前许多年,这联系实质上就已经存在,他就不能粗暴地把我甩出他的生活。
范语说,由于尚无经验,他对我说的这些不甚了解,但因为听上去颇为吸引人,他也愿意斗胆试一试。何况从我的话来看,即使试验失败,他也想不出能有什么后果,反正这件事情我一个人也能完成,从我的话来说,我根本不需要他帮手。我说,“不是的,我不喜欢一个人做爱,范语,这件事需要你。”我暂时还难以启齿的是:范语,我需要你。
在两年杳无音信之后,我再见到范语是在他们报社的电梯间,我抱着一个硕大的鱼缸,一条鲜红的孔雀鱼忽然毫无征兆地英勇一跃,成功把水溅在了站我旁边的范语身上。我一转头,还没看见范语的脸,已经准确无误地认出了那件皱巴巴的灰色衬衫,袖口高高挽起,露出毛茸茸的手臂。由于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范语活色生香的肉体,我稍微有点紧张。即使这样,我还是注意到范语手臂很粗,比我总是想象的还要粗一点,手腕那里有一个淡红色的疤,在手毛与手毛之间若隐若现,我一时激动,几乎拿不稳手里的鱼缸。
时间来到两年之后,范语长高不少,两年之前我大概还可以勉强把头放在他肩膀上,现在却是的确不行,25岁的范语居然还在长个子,我觉得这总说明了一点什么;除此之外,范语无甚变化,依然是满脸不耐烦,衣服皱巴巴,头发如乱草东倒西歪。透过鱼缸,我看到范语摇摇晃晃走出电梯,斜挎着一个很大的包,因为摇摇晃晃,那个包总在范语的屁股周围晃荡,也因为摇摇晃晃,我从鱼缸里看到的范语有一点兴高采烈的味道。范语会兴高采烈地走出电梯,从我的鱼缸里慢慢消失,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范语说,电梯里抱着鱼缸的那个女孩子和他无甚关系,他没有注意到她细细的手臂大概只有自己的一半粗,也没有注意到她头发长得那样长,因为水土不服,皮肤过敏得厉害。电梯里那个女孩子,对范语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
但是范语还说,两年之前那个睫毛很长的女孩子,对他来说则不是陌生人。因为这句话,我在重逢范语后不久,紧紧抱住了他。
我跟林小飞分手的那个下午,他一边啃鸡骨头一边给我下了几个结论,鉴于我跟林小飞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的交情,我听得还算认真。
林小飞说,“想想,你这辈子都不能有太大出息,因为你太不认真太容易走神。你看,你连跟我做爱的时候都漫不经心,何况别的呢?”
林小飞说,“想想,你总以为自己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远大前程,但是这件事不会发生,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件事真的不会发生。”
林小飞说,“想想,我还爱你,但是我不想爱你了,爱你这件事太麻烦了,我想一定会有不那么麻烦的人生。”
我听完这些话的时候就想,看来林小飞默默地恨了我很多年,一时半会儿这种深仇大恨是排解不了的了。事实证明,林小飞果然在三年之后才愿意犹犹豫豫飞到广州来找我,而且始终没给我一个好脸。对此我的理解是,既然春风得意的林小飞很快要去美国读书,好歹我跟他做了许多许多夜的夫妻,耍过多种类型的流氓,分别在即,大家又这么熟,我就不能再跟他计较。
林小飞表现得非常矜持,没有过问我任何层面的生活细节,反而是我非常关心他这三年的性生活质量,有甚说甚,我倒是衷心希望他能享受到专心致志不走神不放空的性爱。但林小飞对此很不屑,似乎数年之前省吃俭用要去开房的是我而不是他。
林小飞只关心了一个问题。在吃完一份浅绿色的西米露后,他若有所思地问,“想想,我们谈的那次恋爱,你说,算不算真的恋爱。”
“当然”我回答。
“那以后呢?”
“以后的事情我看不到,但按照我的推理,以后就是再来一次,然后,再来一次,依次类推,不断重复,也许能停下来,也许停不下来。”
林小飞大惊失色地看看我,然后下结论说,“白想想,三年不见,你还是那个神经病。”
神经病简明扼要地给林小飞讲了讲和范语的种种,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讲,林小飞大概不甘心承认范语在实质上是个跟我很般配的神经病,林小飞只是说,范语是个流氓。
我后来想了想,大家说范语是流氓,无非是因为他有点不一样,仅仅因为一个人不一样,就说他流氓,这样的事情我多少有点做不出。我对范语说,如果走在路上不会彼此扯胳膊扯腿,我倒是很有兴致和他一起走一段。
“然后呢?”
“然后就是再来一次,然后,再来一次,还能怎样?”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生的种种可能,足我始终感兴趣的神秘领域。如果本着一种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我的人生经历非常贫瘠。时间回到二十五年前,我爸跟我妈也曾和著名的王二与陈清扬一样,在农村的玉米地里乱搞一气。由于我妈不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所以拿不到免费的安全套,只能丝毫没有科技含量地乱搞,并且理所当然地怀了孕,打胎花了我爸一分一分存下来准备买《鲁迅全集》的30块钱,为了给我妈补身体,他还冒着几乎是生命危险偷了好几只鸡——除此之外,我妈还当过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团支书,我爸被抄过家,不管是我爸还是我妈,都曾经挨过饿,半年没吃过一点肉,诸如此类,把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成了一部超过五百页的回忆录,但时间回到二十五年后,我的人生只能写满一张作业本纸,当中只有范语的名字,仔细看会发现是加粗而且黑体。
我跟范语在一个几乎谁都不认识谁的校友会上再次见面,聚会非常沉闷,基本没有人说了什么话,等到终于入席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范语坐在我旁边,他看我一下,又看我一下,若有所思地想了很久,然后说:“我见过你,我记得你,眼睫毛很长的那个小姑娘。”
我说,“是啊,我是长睫毛的白想想,你得把这三个字好好记住,范语。”
就是同一个晚上,我跟着范语回了家,范语走路很快,以至于我不得不紧紧抓住他的衣袖,范语转回头看了我几次,带着某种“这不可能发生这他妈的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眼神。在离开他家门的时候,我迷糊之中听到范语似乎叫了我一下,我略为犹豫,并未回头。
第一次上床后大概一个月,某一天我下班的时候看见范语坐在公司门口的台阶上抽烟,手微微发抖,烟灰一截截地往下掉,掉在卡其色的长裤上。我远远地看着范语,看着他满脸不耐烦地看着广州蓝灰色的天空,好像下一分钟就会破口大骂的样子,我忽然涌出某种指向不明的柔情,确认我和范语就此会有再也割裂不了的关系,发生这些的时候,是在接近十月的广州。
范语看见我,微微点点头,羞涩地没有说出一句话。就这样,我跟范语谈起了恋爱,比起和林小飞的十年磨剑而且开始一直磨不成功,我跟范语几乎是轻率地就从肉体关系进展到了精神关系,但奇怪的是,我们都没有吃惊。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范语家,这一次我牢牢看清了范语皱巴巴的蓝色床单和床上乱七八糟扔的杂志,在范语洗澡的时候,我把杂志收好,从衣橱里又拿了一个枕头,然后倒在床上沉沉睡去。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范语不在身边,我透过满是灰尘的窗玻璃看看外面,虽然下着小小的雨,但天空亮得惊人。
范语在洗手问里放上了新的牙刷和毛巾,我把自己收拾好后出门,白色阳光刺得我流了一点点眼泪,我跟范语的故事,就这样开了头。
我最常对林小飞说的一句话是“林小飞,你这个笨蛋。”从小学开始就以精英人士自居的林小飞对此嗤之以鼻,几乎不屑申辩,因为人人都知道物理系的林小飞每年都是拿一等奖学金,我和他第一次挫败重重的开房资金就来自于此。
那天退房出来的情景是林小飞怒气冲冲地结了账,然后在公交车上一直和我怒目相向,想来是彼此都觉得吃了大亏。我认认真真地看了看林小飞,看见他穿了一件不大合身的蓝色衬衫,米色的长裤微微有点发皱,林小飞五官端正,根据我刚刚得来的经验,身上没有一点点赘肉,一笑起来就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我忽然看得笑起来,喜滋滋地说“林小飞,你这个笨蛋。”
下车后林小飞钻进一家小药店,然后拿了一盒杜蕾斯出来,非常得意地说,“草莓昧的,想想你最喜欢吃草莓。”我狠狠看他一眼,说:“林小飞,你这个笨蛋,我不会吃这种草莓。”后来的后来,我们当然用了很多的草莓味,以及柠檬,以及橘子,我,总结性地对林小飞说,“还是草莓比较好。”有了肉体关系以后,林小飞整天整天地要和我待在一起,就算去实验室,也要我在旁边的化学系实验室里待着,偶尔与他在长长的实验桌上用一个杜蕾斯,我渐渐很有感触地对林小飞说,“乱搞这件事情,真是勤能补拙。”多年以后回忆起来,我跟林小飞,就是在这样亲密的肉体关系里渐渐地分了手。
在那个看上去可以制造科学怪人的实验室里,我用酒精灯熬了不少鸡汤和红枣银耳,陆陆续续看完了被林小飞称为“毫无用处”的一堆杂书,林小飞每一个小时就过来看看我,某一次看到我试图用酒精灯炸爆米花吃,林小飞跳起来说,“白想想,你这个笨蛋,你迟早会把自己给杀了。”笨蛋林小飞忽然变成了笨蛋白想想,这一点,我始终没能释怀。按照林小飞的说法,白想想懒惰得好像没有心,看上去一脸分分钟就会睡过去的茫然。林小飞说,“白想想你不能过这样的人生,这是错的,没有一点点出路。”
我说,“我不要出路,我要一条路走到黑,走到尽头,林小飞,你这个笨蛋。”
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林小飞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交流,在去之前,他替我报了一个GRF的补习班,交了两千块钱,换了一个小小的听课证。林小飞说,你好歹得“考个GRF成绩,不然怎么跟我一起出国?我几乎是跳起来骂,“林小飞你这个笨蛋,你不把两千块吐出来,我就阉了你。”
林小飞“嗖”地逃到香港去,一去就是三个月,没钱打电话,只能每天发邮件,痛心疾首地催我去听课。我暴跳如雷却阉无可阉,只得挂着听课证去学校,试图把两干块听够本。我第一次去教室的那个晚上,南京下了一场空前的台风雨,闪电照得天空亮如白昼,全身湿透的白想想拎着球鞋垂头丧气地走进教室,小腿被雨水泡得苍白发皱,每一个地方都在往下滴水。
就是在那个教室里,我把我头发上的水全甩到了徐文的IBM笔记本上。我后来想到,如果不是当时徐文毫不客气地要我赔钱,这后面的一切也许就不会发生,按照著名的蝴蝶效应,我也不会在多年之后,为范语落下泪来。
我非常固执地想,如果把所有的过去都和范语联系起来,那样我们就不会分开,那样我就不用找到出路,我就可以一条路走到黑。
到底会不会和范语分开,是我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如果说一半是出于与身俱来的好奇心,那另一半,我愿意归结为是出于某种对远大前程的期望,对我来说,这期望清新诱人,是初学会走路的小男孩赤足踏上草坪的那一刻。“小男孩的草坪”是范语的比喻,范语说,“白想想,跟你在一起,就像小男孩踏上草坪。”范语说下这句话的时候,白云山上风雨大作,每一下闪电都像就要劈到我,过于喧闹的雷声让我和范语几乎听不到对方在说些什么,就是在雷声和雷声之间,我永远地记住了范语关于小男孩和草坪的比喻。也就是在那一个晚上,范语和我牵着手走下白云山,两个人的手心都很湿,我的头发长到腰际,范语背了一个硕大的包。骤雨过去,天空快速飘过一片片白得耀眼的云彩,范语从我的衬衫里抓出一只活蹦乱跳的金龟子和数片紫荆叶子,然后在出租车后座上和我接吻,我紧紧抓住范语的衣服下摆,等到我松开的时候,那件棉质的衬衫居然破了一个小小的洞,范语一言未发,在我家楼下把我推下出租车。如果认真回想起来,就是在那一个晚上,我开始使用“远大前程”来描述我和范语的关系,我对范语说,除了感情关系,我不相信有任何关系能够得上使用这样隆重的词语。
“远大前程”这个词最初来自徐文。我认识徐文的时候,他刚刚离婚,房子和存款被前妻一并席卷而去,一个人在学校旁边租了个小房子,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台IBM的笔记本,就是靠这个笔记本,徐文偶尔写点小程序,赚很少的钱,然后他才能保证一日三餐吃饱以及每天抽两包烟,某一个程序卖得比较好,徐文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张GRE班的听课证。我第一次看到徐文的时候,只觉得他全身上下都是烟味,衣服像腌咸菜一样皱在身上,皮肤非常不好,个子很高,长腿和长胳膊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多少有一点点愁眉苦脸。就是这个愁眉苦脸的徐文,毫不客气地让我赔了他一千块以排掉他笔记本键盘里所有的水。
就这样,徐文和我以金钱关系为纽带,迅速混得烂熟,至于为什么没有从金钱关系顺理成章地过渡到肉体关系,我总结为大家都对此没有太大兴趣,但绝非毫无兴趣。按照徐文的说法,要对一个人产生一点点兴趣是如此轻易,轻易到完全不值一提。但是徐文说,“我们一生之中,都得做那么一两件专心致志的事情,专心致志的意思是,你得准备好为这件事受尽折磨,贫穷、疾病、火烧、水浸、竹签扎进手指里,长头发被人扯住不松手,等等等等,统统不在话下。”徐文说,“首先有了这样的前期准备,然后你才可能拥有远大前程,所有的前程都建立在你愿意为之承担的苦难之上。”
在告诉我这些话后不久,徐文考到美国一个小学校的奖学金,迅速飞走,就此全无音讯。因为一直牢牢记住了徐文的话,我终于和十佳青年林小飞分了手,然后上了范语的床,并且不知羞耻地试图和他拥有远大前程。我对范语说,“现在我走在这条路上,除了我们的关系,我蔑视一切,一切都是虚妄,一切都与我不甚相关。如果我走到了尽头,那是理所应当;如果我只走了一段,你也永远不能否认,我曾为此,做好所有准备,我曾心甘情愿地为我们的远大前程,承担一切苦难。”
关于王仪和范语的事情,我一直不甚知道,就是这件不甚知道的事情,让我数次在深夜的东风路上落下泪来,这说起来很是荒谬,但细想之下,却也并不出奇。关于王仪与范语,大概是谁爱过谁,谁没有爱上谁,谁后来又爱上了谁,但谁和谁总之没能在一起,之类的故事。事实上,所有的故事,想来只是不过如此。在我数次走完整条东风路,然后带着一身烟味回到范语床上的时候,我终于对任何谁谁都失去了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范语醒来后,是否会在迷糊中毫无意识地吻上我的睫毛。
范语和王仪的那张照片背景是学校办公楼,在满墙满墙的爬山虎下面,我看见王仪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把手放进范语的臂弯里,笑眯眯地看着镜头,范语既没有怒容满面,也没有愁眉苦脸,我的范语微微侧过脸去看王仪,微微在笑。这样的笑容,在白云山那个晚上,我也曾在范语脸上找到过。这样的笑容,对我而言有诸多意义,这样的笑容,是我们远大前程中的必经之地。
关于王仪,关于那些爬山虎,范语绝口不提,我绝口不问。但是关于林小飞,关于徐文,范语却全全知晓。我对范语说,“因为你习惯了小心翼翼地生活,我同意你仅仅把今天交给我,我同意你心存怀疑,因为人人都心存怀疑。”但这不是白想想,白想想会犯愚蠢的错误,而且是一个接一个的错误,在这些错误里面,白想想毫无顾忌,在远大前程的路上,白想想穿着高跟鞋昂首挺胸前行,你准备好认识她了吗?
时间回到现在,范语正儿八经地和我谈起了恋爱,每周约会三次,一本正经地看电影吃法国菜然后做爱,以及在做完爱后一个人吃二十个速冻饺子,一人捧一个大海碗,都爱吃韭菜馅,吃完了都打嗝。恋爱多闷啊,闷到我们什么也不做的时候,只好裸体坐在床上玩跑得快。但我还是这么高兴,习惯于喜滋滋地自言自语说,我的范语,并且在过马路的时候紧紧拽住范语的衣角。
至于范语,偶尔和我谈谈未来,大部分的时候却并不,在更偶尔的时候,范语也会说,“我们的远大前程。”我对范语说,“虽然我早就知道远大前程意味着承担一切苦难,但是途中的所有苦难,我却愿与你一一错过,这与诸多崇高的情操无关,仅仅与我的爱情相关。你别转过头去啊,我也知道,爱情总是一件害羞的事情,但我们得慢慢习惯它。”
有一天,正是半夜,吃完饺子打完跑得快,我和范语打算从东风路走到珠江边上,两个人都抽着烟,穿着“踢踢哒哒”的拖鞋,他有时候搂住我的腰,有时候只是自顾自往前走。那时候正是三月,木棉开出火红火红的大花,空气中有不确定的香味。
我对范语说,“你看到没有,前面这条路,看起来多长多黑啊,我们把它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