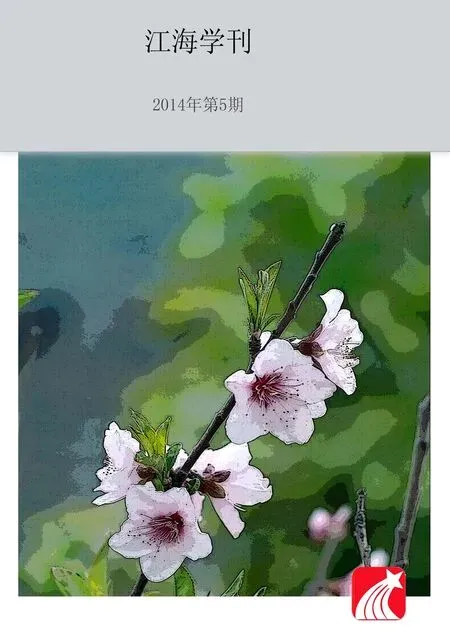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的涌起*
2014-04-23王荣国
周 棉 王荣国
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但是,对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之间的关系,还缺少专门的研究。据此,本文力求拾遗补缺,略抒己见,以就教于同行专家。
近代中国的留日运动,始于甲午战后的1896年①。甲午之战,中华帝国败给蕞尔小国日本的惨痛事实,激发了国人向日本学习的热情,希望借鉴明治维新的经验而复兴强国。这一年,清政府同意驻日公使裕庚的建议,派出13人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1898年张之洞《劝学篇》的刊行不啻为向日本学习的宣言书。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系统地论述了留日的益处:“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②此种观点为清廷所接受并推广指导学生留学。
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的关系
1.留学日本是新政解决人才缺乏的重要途径
清末新政,清政府遇到的突出问题,是旧式教育体制无法满足“新政”对新式人才的需要。因此,清政府在新政伊始,便大力开展新式教育。一方面,废除科举制度,颁布新学制,创立新式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留学教育,逐步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和奖励政策,促成了清末留日大潮的涌起。
随着新政的实施,奖励游学被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联名呈递了《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进一步阐发了留日的思想:留日“传习易,经费省,回华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③。同年9月17日,清帝“广派游学谕”颁布:官派生“学成领有凭照回华,即由该督抚、学政按其所学,分门考验。如果学有成效,即行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部复加考验,据实奏请奖励。其游学经费,着各直省妥筹发给,准其作正开销。如有各备旅资出洋游学者,着各该省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如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厚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④。在此影响下,一些偏远的省份也开始重视游学。如1902年《前云贵总督魏奏陈资遣学生出洋游历折》称,已遴选“心术端正文理明达”⑤之士10人即将派出。1903~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端方、直隶总督袁世凯,先后奏请用考试的办法奖励本省回国留学生。其中1903年10月张之洞所呈《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对留学生的奖励尤其是对留日归国学生的奖励更加具体化,建议分别给予在日本普通学校、高等学堂、大学学堂学习并取得优等文凭的留学毕业生拔贡、举人和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并主张若在日本大学堂和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得有学识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若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文凭者,“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⑥。
清政府接受了这些建议,于1904年12月制定出台了《验证出洋毕业生章程》,规定对回国留学生进行考试,合格者给予奖励。据此,1905年清政府对归国留学生进行了第一次考试。同年,学部成立后,这一奖励方式得以进一步完善并固定下来。光绪帝于同年9月批准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至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传统知识分子的进仕之路被摧毁,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则成为踏上仕途的新路。为表示鼓励,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也与公派学生同等对待。1906年10月,学部又奏定《考验出洋游学毕业生章程》,明确规定留学毕业生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并要在出身前加某学科字样。⑦1908年,学部会同宪政编查馆奏定《酌拟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给予通过学部考试而获得进士、举人出身的留学毕业生以参加廷试的机会,分别等第,授予官职⑧。此外,清政府还对早年毕业归国的留学生予以奖励。1907年4月,清政府采纳了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建议,对回国10年以上且业绩突出的詹天佑、吴仰曾等4人给予进士出身。后经学部奏准,这一建议被推广至全国。学部饬令各省督抚广加查访,“凡专门学成归国在十年以外,学力素优,复有经验者”,均可“胪举实际,或征其著述”,咨送学部。核定后,“其著述卓然成家,成绩确然共见者”,请旨赐予出身,以奖励后进。⑨
2.为了在华的长期利益,日本政府希望中国学生留日学习,但也确有少数有识之士,真诚地欢迎中国留学生
甲午战后,日本国力还不能独霸中国,所以,既不希望中国被西方瓜分,也不希望中国强大,而是力图有效控制。为此,日本对中国实行“两面开弓”⑩的战略,一方面在军事上派出宇都宫、尾川重太郎和福岛安正等军官,游说张之洞等清廷重臣,鼓吹“联英联日,以抗俄、德而图自保”⑪;另一方面,通过有影响的日本各界人士传播和散布相关的观点。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日本有很大市场,例如农商大臣大石正已在1898年5月5日《太阳》杂志上发表评论《东洋的形势及将来》中称:
如果希望彻底地实现此方针(以保护我在华既得的权益),首先必须防止清国分割的危机而确保其平和,诱促其进步,增长其资产及实力。这样,在我帝国与列强的对立中,才能维持东洋的均势。⑫
当时也有一些人考虑到中日友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希望以接受中国留学生来报答中国昔日对日本的帮助(也确实有主张日中友好的明智之士),如美国学者任达认为,在1898年6月底至11月初的第一届大隈“短命内阁”期间,大隈重信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就反映了这种心理,“日本长期从中国文化中获益良多,是负债者,现在该是日本报恩,帮助中国改革与自强的时候了”⑬。此外,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等也持类似的看法。还需指出的是,在日本民间,确有一些有识之士,希望日中友好。他们多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中国不抱偏见的日本人,其中多为教育工作者,真诚地欢迎和对待中国留学生,例如鲁迅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创办东亚预备学校的松本龟次郎等。
但是,持这种观点并能在行动上真正对中国友好、热情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日本人仅为少数,更多人则是口是心非、两面三刀。例如,教育家、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外山正一,在1898年4月20日出版的《太阳》上杂志发表的《支那帝国之命运与日本国民之任务》一文中指出:“我的观念是,支那的存亡对所有日本国民自家的安危有切实的关系。”⑭但实际上此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分子。1890年他参观北洋舰队的旗舰后声称:“中国和我们就像长兄幼弟,我们应确认中国不会成为我们的敌人。”但在四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时,他又得意地声称自己写了最早的第一首战歌《Battista》(《拔剑队》)。他在后来的战歌《Yuke Nihondanji》中,更竭力煽动反华情绪,称中国人是“恶魔”、“窃贼”、“狼群”,“我们母亲的敌人,我们妻子的敌人,我们姐妹和女儿的敌人”,狂妄地叫嚣“神圣土地的纯洁血液,不能被敌国野兽玷污”。⑮美国学者指出,外山自相矛盾的言论,“是在明治中期不少日本人的普遍表现”⑯。
明白道出日本接受中国留学生“天机”的是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1898年5月14日,他在致外相西德二郎的密件中说: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军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段。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10倍,且无可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⑰
西方有学者据此写道:“就这样,从1898年年初开始,为了与西方帝国主义直接相关的原因,为了民族利益,杰出的日本人大声疾呼与中国合作,突然成为政治时髦。这是意义深远的新开端,中国从新的途径进入日本的民众意识。”⑱也就是说,在甲午战争以后,包藏祸心又掌握日本政局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了日本在华的长期利益,套上了各种面具,拉拢、诱使中国亲善日本,其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乃是其惯用的伎俩之一。
概言之,清末留日大潮的出现,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清政府派遣和奖励游学政策的颁布和实施,科举制的废除,直接促进了清末留日大潮的涌现;而日本出于自身的需要,也鼓励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又兼日本路近费省等原因,成为读书人留学的首选,晚清中国留日的序幕由此开启!到1905年、1906年达到高潮。当时,早稻田大学教务主任青柳笃恒这样描述中国留学生蜂拥赴日的情景:
惟舍此途而外,何能跃登龙门,一身荣誉何处而求,又如何能讲挽回国运之策?于是,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至于东京各校学期或学年进度实况,则不暇计也,即被拒以中途入学之理由,亦不暇顾也。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⑲
这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称,清末的留学运动最终汇成了“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⑳。
1901 ~1911年留日学生人数辨析
由于清末留日人众,渠道多,形式多,当时就缺少官方的统计,因此,对1901~1911年留日学生的人数,在统计上常有分歧。下面根据三种说法予以分析。

表1 实藤惠秀、李喜所、李华兴和陈祖林统计的数据
为了便于比较,特对表上没有列出的数字,用这三组中同一时间的数字补充,其中实藤惠秀和李喜所的表上缺少1910、1911年两年的数字,分别补上李华兴、陈祖林表两年数字之和7307(3979+3328);李喜所表又缺少1908年数字,补上实藤惠秀和李华兴、陈祖林表同年数字的平均值4608[(4000+5216)÷2]。这样,1901~1911年留日学生人数,实藤惠秀为34080+7307=41387;李喜所为 37553+7307+4608=49468,李华兴、陈祖林为44667。其中李喜所的数字与实藤惠秀的数字差别最大,差额为8081,与李华兴、陈祖林的数字差额为4801,与实藤惠秀和李华兴、陈祖林的差额的平均值为6801。原因何在呢?
应该说,李先生引用的数据来源并没有错,而且他在这篇专论《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的文章也没有计算总量。笔者认为,这并非他的疏忽,而是出于一个严肃作者的谨慎。为了考证清末留日学生的人数,在此对数据的理解和统计方法上还可作新的解释。如1906年的数字12000余人,就可重新计算。因为其根据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版的《学部官报》第8期有一张留日学生人数统计表……该表最后汇合的总数为5418人”,同时加了一个按语说:“联队及振武学校六百余人,其有未到使署报名及不用介绍之学堂各均未列入表内学生。”照此看来,如果加上这些未列入表内的学生,总数应稍大一些。这个表只是1906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同一期官报上还刊有1906年6月19日至9月17日的留日学生人数。表后附一按语说:“此外尚有入东京及东京外各校者253人,共计送学6883人。”将两表人数相加,约12000人。
问题在于,上面引用的材料并没有说明同期官报上第二个表,即1906年6月19日至9月17日统计的人数没有与上半年的人数重复。而根据通常的统计学生的方法来看,除去毕业离校等原因外,用简单相加的方法统计的结果,同一年的大部分学生肯定是重复的。其主要佐证材料《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丁编)一书中记载,1906年留日生为“一万二千余人”,也存在类似的误区;至于吴玉章的《辛亥革命》记载:“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组织虽然活动起来了,但要领导无数学校、一万多学生的罢课,并组织他们分批回国,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从其话语来看,仅仅是一种估计。对此,我们还可从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分析中得到证实:
有人以为1906年数目比1905年为高,我不敢苟同……以当时留学教育大本营的弘文学院而论,该校1902年在东京牛込西五轩町创校,1903年在大冢设分校。1904年增设麹町分校、真岛分校、猿乐分校及巢鸭分校。但在1905年末,由于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不少留学生归国,使麹町、真岛、猿乐町三所分校关闭。到了1906年,归国学生大部分重返日本留学,新来的留学生人数也有增加。倘使新来的留学生较1905年为多,由于新来者大多不能立即进入大学,所以非入专为留学生而设的学校不可,但在这类学校中最具信誉的弘文学院却不能恢复上一年关闭的三所学校,只能在牛込区开设白银分校。纵使白银分校收容人数较多,但亦不可能超过三所分校。特别是专为留日学生而设的学校……最后的一所是1905年设立的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1906年并无同类学校开设。由此观之,1906年的留日学生人数比以前为多,是不可能的事。故此,我同意青柳笃恒在《中国留学生与列国》一文所说,“据最近确实统计,文武男女学生共约八千人。亦即1905年及1906年都约有八千人”。㉑
至于1907年的10000人左右,也有理解上的歧义。其根据是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学部奏定日本官立高等学堂收容中国学生名额折》所记载:
比年以来臣等详查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㉒
歧义的焦点是对“比年”的理解不同。查“比年”的解释有二:“近年或每年。”㉓根据“比年”在语句中的位置和语境,它并不是确指当年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而是指“近年以来”,所谓“臣等详查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是指最近几年日本留学人数的总数,而不是指1907年当年。
因此,增补后李先生的这组数字与其他两人数字的差额具体表现在1906年和1907年。但是,其他两人统计的数字也并不能确认无误。因为,其中留学生中不乏一人兼具数校学籍的,难免重复统计。对于这种现象,1907年4月,青柳笃恒在《中国留学生与列国》一文中说:
有谓中国留学生留学日本者,其数达一万三四千之巨,此乃一人同时兼具数校学籍,而以校别统计计算所致也。查最近确实统计,文武男女学生共约八千人,包括文武官费生约二千八百人。
同年8月,青柳笃恒在《每日电报》的《清国留学生之减少》一文中又说:“据本年年初之统计,居留我邦之清国留学生竟达一万三千之多。然而,彼等中有为得多种毕业证书而一身拥有几种学籍者。实际人数应为八千左右耳……”而且当时的留日学生虽然速成的居多,有的半年就毕业,但是相当一部分又并不是当年去当年回的;有的甚至在日本学习了几年,如鲁迅、郭沫若等。也就是说,每年非正规的统计又难免重复,有的甚至重复多次。因此,较普遍的说法是从1896年官派留日生开始,到辛亥革命为止,留日学生总数在万人以上。按照上面所说,除去部分速成时间为半年左右的不大会重复统计外,还有至少35%左右应该是重复统计的。因此,根据上面三组数字,1901~1911年留日学生的实际人数,应该是他们三人总数的平均值减去重复的35%,即:
[实藤惠秀41387+李华兴、陈祖林44667+(增补后李喜所49468-差额6801)]÷3=42904,42904×35%=27888。
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数字(实际上也无法精确,只能尽可能接近真实),1901~1911年的留日学生大约是20000人左右。笔者曾在1995年推算当时的留日学生总数应在22000人以上㉔,但是当时的算法与现在的方法不尽相同,如果取这两种方法计算结果的平均值应为24944人。这个数字与美国学者伍达的观点不谋而合。㉕因此,现在看来,21000人以上应该是比较接近实际的。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个数字也是令人惊讶的。从根本上说,留日人数如此之多,是清末新政直接推动的结果。
留日学生的构成分析
当时的留日学生使命感强,绝大多数是抱着“寻医求药”、振兴中华的目的东渡日本的,“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㉖。但是,对具体人而言,又不尽相同。对数以万计的留日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对他们的特征有一种概括:
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此类以学自然科学者为多),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此类以学社会科学者为多),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其原来之资格年龄,亦甚参差。有年已四十、五十以上者,有才六七岁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来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进身之捷径者。㉗
1.留日学生的地域与出身
留日学生数量众多,改变了早期留学生限于东南沿海各省的格局,来源于全国许多省份。据《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统计,除留学人数向来较多的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直隶、山东、四川、福建外,还有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广西、河南、奉天、山西、陕西等,另有旗人留学生。只有甘肃等极少数省份没有人出国留日。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对留学日本都一路绿灯,加上官费、自费多渠道赴日留学,且无年龄限制,因此,在这些人中既有富家公子、王公贵族,也有贫家子弟,还有兄妹夫妻。廖仲恺就是依靠妻子何香凝变卖陪嫁的珠宝首饰得以留学日本。而自费的秋瑾,在日本出门行路从未坐过人力车。广东顺德人李昂新已82岁,但向学之志至老不衰,尚欲前赴东瀛学习工业,后由学务处批准嘉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前清朝王公贵族对留学不屑一顾,但到新政时期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宗室良弼、张之洞之孙张厚琨等都在日本留学;1900年赴日本学习军事的贵胄铁良,则成为中国首批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学生。从1898年至清朝灭亡,贵胄出国的人数大约为100人左右㉘。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新政开始以后,留日女学生逐渐增多,很多省份开始官费派遣女留学生。如1905年湖南派20名女青年赴日攻读速成师范科。同年,奉天农工商务局总办熊希龄与日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约定,每年派遣女生15名至该校学习师范,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一次就派了21名学生到该校攻读速成师范科。
2.留日学生的主要学校和类别
在日期间,留日学生初期主要集中在弘文学院、成城学校、振武学校、经纬学堂等几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学校,少量的升入专门学校或大学深造。从学生类别来看,留日生大体分为普通生、速成生和特约生等。所谓普通生,指在日本受中小学补习教育的学生,年龄较小,先入日本小学补习语言文字和基础知识,然后再入中学、大学。这类人数较少。所谓速成生,指赴日后入某一专门学校学习某一专科,主要是学习师范、法政专业,学习年限可长可短,长则两年,短则几个月,但其效果不好的流弊也很明显。为此,1906年学部通令各省,无论官费、自费、师范、政法,一律停派速成生。特约生,是指进入日本所指定的高等学校学习的高级留日生,相对于大批的速成生而言,这部分人还是比较少的。
3.留日学生的主要专业
从专业上看,留日学生所学科目和专业非常广泛,如理科、工科、外语、师范、史地、法政、军事、制造等等。其中法政、师范科为热门,这是清政府鼓励的结果。1903年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主持编订的《学务纲要》要求:“各省城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若无师范学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员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㉙此后,国内开始有组织地选派学生赴日学习速成师范。当时清政府提倡新式教育,准备立宪,师资和宪政人才严重缺乏,速成教育可在短期内培养新政所急需的人才,一般青年学生也希望尽早学成归国。因此,速成教育大受欢迎,赴日习速成科者与日俱增。当时仅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博士在1904年至1908年所办的5期法政速成科,中国学生就达2117名㉚。至于师范生,除官方派遣外,许多自费留学生也纷纷选学师范。速成师范虽然学习效果不明显,但对当时严重的师资紧缺状况而言,还是起到了救急的作用。
另外是军事留学生,主要是陆军留学生。自1898年起清政府派陆军留日,以后随着各地武备学堂的设立,留日习陆军军事的人数增长迅速。1902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上奏清廷,建议选派学生赴日学习军事:“日本同洲之国,其陆军学校,于训练之法,备极周详。臣部武备右军学堂诸生,现已三届毕业之期,虽规模颇有可观,而谙练犹有未至,自应及时派往东洋肄习,庶学成返国,堪备干城御侮之资。似变法图强,无有要于此者。”㉛1904年,出使日本大臣杨枢也表达了与袁世凯同样的观点。同年5月,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规定凡志愿出洋学习军事的学生,须先由各省督抚咨送练兵处,再经练兵处考选及格者,始能派遣。赴日学习军事的学生起初要进入成城学校接受预备教育,1903年振武学校成立,原在成城学校肄业的中国武备学生一律移至振武学校,毕业后入士官学校正式学习。据笔者统计,自1900年至1911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共9届,总计647人。这批人后来对民国社会有很大影响,如蒋介石、何应钦、蔡锷、唐继尧、吴禄贞、汤恩伯等。陆军士官学校以培养下级军官为主要目的,而高级的军事教育在户山、炮工、陆军大学等各校讲授。但日本政府鉴于各校所讲授军事学难免涉及国家机密,故拒收外国学生。后来经过交涉,只有极少数中国学生如蒋百里、杨杰等进入高级军校学习。
综上所述,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的关系极为密切,留学日本是清政府解决人才缺乏的重要途径,而日本政府为了其在华的长远利益,也试图利用中国从上而下的留日愿望以实现培养亲日分子的阴谋,少量日本有识之士则希望接纳中国留学生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清末留日学生人数众多,达20000人以上,达到了当时人类有史以来留学人数的最高峰。其主流后来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试图通过吸纳中国留学生,培养亲日派,从而控制中国的图谋并没有得逞,而对华友好的日本人士维护中日传统友谊的良好愿望,也在一个多世纪复杂的中日关系中继续坚持。
①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据此首先认为,这一年为中国官派学生留日的时间,此论并为中国台湾和大陆学者所广泛认可。但20世纪90年代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否认此说,认为这批学生的所谓“留学日本”,不过是在延续原来使馆东文学堂的基础上略加变通,即将以前专属于使馆的东文学堂改为同时还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负责部分教务,所学课程则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负责,从专攻日文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学堂也由使馆迁到高等师范附近的一座宿舍。但是,这些并未改变东文学堂的性质。因此,“清末留日学生的正式开端定于1897年底或1898年更为恰当。尽管清廷将派遣权限下放到各省,各地首批留日学生东渡时间相去甚远,但并不影响事情的基本性质”(详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此论有据,更准确,但1896年说也无大偏颇。
②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游学第二》,《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③《张文襄公全集》(一),奏议五十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917页。
④朱寿明编:《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720页。
⑤《光绪壬寅政艺丛书》上编(一),《政书通辑》卷八,1907年。
⑥⑪《张文襄公全集》(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9、348页。
⑦《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学部奏咨辑要》卷二,学部总务司案牍科编,宣统元年(1909年)。
⑧《会奏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折》,《学部奏咨辑要》卷三,学部总务司案牍科编,宣统元年(1909年)。
⑨《学部官报》,第24期,1907年。
⑩⑬此为美国学者任达的观点,详参氏著《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⑫⑭转引自细野浩二《清末中国之“东文学堂”及其环境:明治末期日本夺取中国教育权的伦理概略》,载阿部洋编《日中教育交流与冲突:战前日本在华的教育事业》,(东京)第一书房1983 年版,第72、72 页。
⑮Donald Keene,“This Sino - Japanese War of 1894 - 95 and Its Cultural Effects in japan”,in Donald H.Shively,ed.,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JapaneseCultural,Princeton,1971,pp.121 ~175.
⑯⑱㉕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40、34、105 页。
⑰[日]矢野文雄:《清国留学生招职策》,云述译,《近代史资料》(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96页。
⑲㉑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7、39页。
⑳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㉒《大清宣统新法令》,第15册,《补遗》。
㉓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7页。
㉔周棉主编:《留学生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一),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㉖《江苏同乡会创始记》,《江苏》1903年第2期。
㉗《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第4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3页。
㉘王秀丽:《晚清贵胄留学初探》,载李喜所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㉙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㉚王敏:《关于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与辛亥志士的考察》,《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1期。
㉛《奏遣派游学生赴日本肄业片》,陈学恂、田正平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