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蟠虺者,醒龙也
2014-04-23刘莉娜
文/本刊记者 刘莉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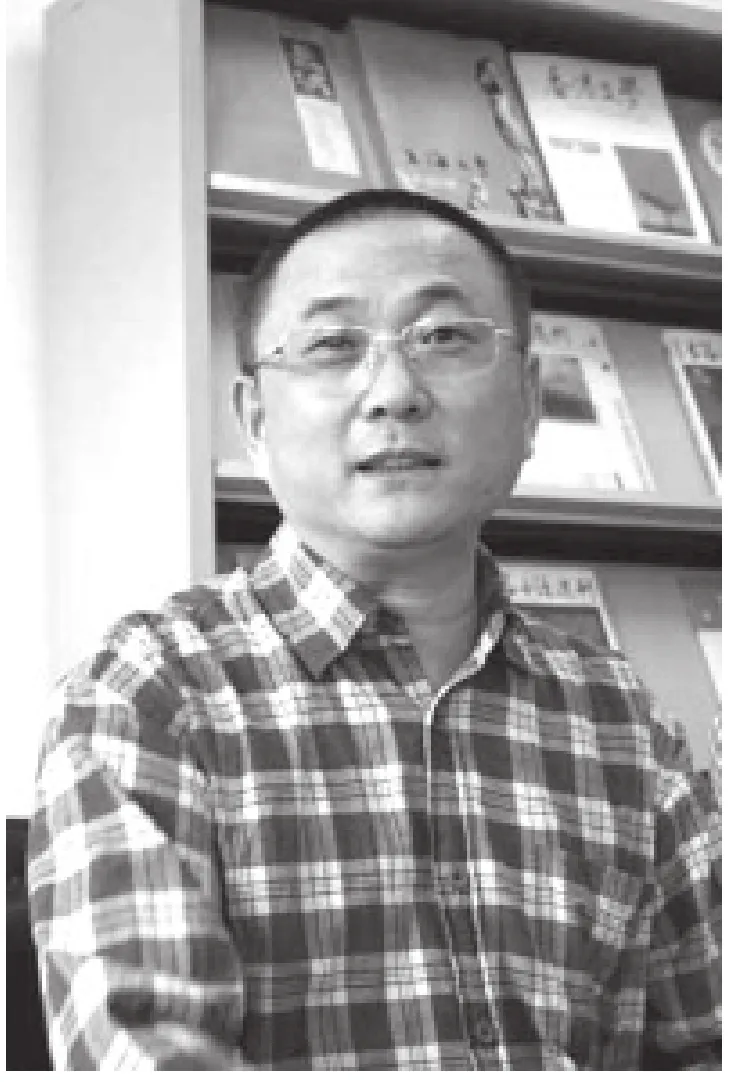
身为首届鲁迅文学奖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一向被视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领军人物,早期成名和得奖的系列作品更是让他一度成为“乡村教师”代言人。所以,虽然他这一次在上海书展上拿出的新长篇《蟠虺》被宣传为“都市实景”加“盗墓元素”加“中国版《达·芬奇密码》”的华丽合体,但有了先入为主的强烈暗示,当我在巨鹿路上见到留着清爽寸发、一身休闲搭配简约又不失儒雅的作家本尊时,心里完全有一种“以为要见莫言却见到了苏童”的惊喜——广大文艺女青年们,个中微妙你们懂的。
当然,形象永远不是一个作家的名片,作品才是他们的脸面——然而对于刘醒龙这一次重磅捧出的新作《蟠虺》,我必须汗颜地承认,如果不翻字典我简直无法顺溜地读出它的名字;但同时我也乐观地相信,读者中的大部分会和我一样需要扫盲——所以贴心如刘醒龙,直接就在书名的旁边标注好了拼音:Pan Hui。即使如此,在写手们为搏畅销恨不得把书名取成华丽歌词的当下,这种取两字书名并且其中一字还是冷僻字的做法真的好么?
对此疑问,本书的策划、同时亦是刘醒龙好友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魏心宏作为资深出版人有自己另辟蹊径的见解:“我们不要小看了读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有时候当他们发现一本自己读不出名字的书时,他也许会更想翻开这本书而不是放下。”魏总编的出发点立足于市场调研与心理分析,但刘醒龙给出的段子却更加简单直接——《蟠虺》在上海书展上立了一张宣传海报,根据站台的工作人员和刘醒龙自己的观察来看,布展3天里的每一天的每隔一两个小时,总会有一对年轻的情侣被书名吸引,玩起了猜字游戏。“一般都是小姑娘跳上台一把遮住海报上的拼音,然后问男伴,哎,你认识这两个字怎么读么?”刘醒龙笑嘻嘻地学起小姑娘的娇俏口吻,说得活灵活现:“大多数男孩子是读不出的,于是两个人就一起乐着拼读;然而但凡有一两个男生读出来了,那女孩子看男生的眼光绝对是立刻就带上欣赏崇拜了呀。”“所以说你的这本小说还有促进情侣感情的功能咯?”我这么打趣他,没想到刘大作家对“红线工程”非常热衷:“姑娘们,遇到能读出‘蟠虺’的男生就嫁了吧。”
玩笑归玩笑,但能一口读出书名这两个字的年轻人却真的不简单,“其实很多学者也不一定能马上读出‘虺’这个字,”刘醒龙坦言:“但我还是在小说里用了大量我们现代人不用的字——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直不用就废弃了。虽然人的认知有惯性,但我们这些文化人必须有意打破惯性,这也是文化的意义和文人的宿命。”事实上,在刘醒龙看来,《蟠虺》这部作品的写成在最开始就充满了宿命感。
蟠虺,是青铜器纹饰之一,以蟠屈的小蛇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起源于商代,是珍贵文物曾侯乙尊盘的主要纹饰。“曾侯乙尊盘是那种真正国宝中的国宝级别的文物,在我们湖北省博物馆里至少摆了二十几年,看过的人、了解过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但为何从来没有人想过把这件古老而又神秘的青铜器写成一部作品?”而刘醒龙的家就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旁边,他之前去过博物馆无数次,自己去看,带朋友去看,却也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件重器。“我之前经常去看的是一套编钟,有一次我带一个美国的朋友去,一进门就碰到一位工作人员,她迎上来说你是刘醒龙吗?你们是不是想看编钟?但今天我想带你去看一个更好的东西。”就这样,如同宿命一般,这名神奇出现的工作人员就这么把刘醒龙引到了曾侯乙尊盘的面前,向他介绍了这尊独一无二的文物——那套编钟至今已经被复制了四套,由于工艺被破解,复制品与真品并无区别;但这尊曾侯乙尊盘却至今都没有人能破解其制造工艺,以至于它至今都无法被复制。“就是这一句话打动了我,”刘醒龙年轻时曾做过车工,所以他非常惊叹于曾侯乙尊盘如此复杂的工艺,“天衣无缝、百无破绽,真是鬼斧神工,让我每看一次都会感慨。”就这么感慨着,感慨着,突然有一天,他觉得这可以写成一部小说。
“我个人很喜欢悬疑小说,当然写这样一个故事,我也没办法用其他形式。曾侯乙尊盘是怎么制造的,它的工艺是怎样的,至今还是谜,在学术上争论不休。何人拥有,何人制造,随国和曾国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悬疑,都没有定论。所以在我看来,只能用悬疑方式来写一个关于曾侯乙尊盘的故事。也只有这样,才让小说不至于太枯燥。”在《蟠虺》里,刘醒龙用悬疑小说的手法写了关于曾侯乙尊盘失而复得的虚构故事,以及围绕着曾侯乙尊盘展开的政治权力博弈。而在悬疑的框架下,刘醒龙也融入并介绍了大量关于青铜器和甲骨文的知识。
在写这本小说前,刘醒龙说自己关于青铜器和甲骨文,“不能说零知识,100分有5分吧。伴随写作而来的是大量关于青铜器、古文字的阅读,真的很枯燥,阅读中经常发现,很多字我都不认识。”刘醒龙也知道自己的这部小说有一定的阅读门槛:比如书名的读法;比如书里小学生楚楚用来刁难成人的那三十个与青铜重器相关的汉字;还有贯穿全书的一大争议,即曾侯乙尊盘究竟是用“失蜡法”还是“范铸法”制作,没有金属铸造知识的人也不太好理解……但他并不担心因此失去读者,相反,作为一位乐观的作家,刘醒龙笃信在写作时千万不要低估读书人的求知欲和向上的渴望:“一个正常的读书人,遇到难题的时候,一定会选择去认知、了解。不认识的字就去查字典,当书名都不认识的时候,会极其挑战人的自尊心的。如果说,文学是文化的边疆,那汉字就是文化边疆上的界碑。”结果他是对的,虽然新书取了个“扫盲型”书名,但在上海书展的每一天里都会有“无畏”的读者直奔展台,直接表明“我要买刘醒龙那本两个字的书”——而书展结束后根据举办方的最后统计,《蟠虺》的销量排列全部小说类书籍第一名,并获评书展十佳新书。
“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的相遇是真正的宿命,就像我和《蟠虺》。”对于刘醒龙来说,《蟠虺》的写作过程从开始到最后都充满了宿命——除了最开始和曾侯乙尊盘的邂逅充满了偶然与机缘,这本书写完出版以后还出现了更为宿命的巧合。刘醒龙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曾侯丙”,然而当2014年小说出版、6月在湖北省博物馆开新闻发布会时,博物馆馆长反复追问,这个书确切的出版时间是何时。“得知是2014年4月出版的,馆长惊呼‘太巧了’,原来就在4月他们刚刚在曾侯乙墓附近发现一座楚墓,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正好有‘曾侯丙’。”而当刘醒龙带着新书来上海宣传并向读者解释何为蟠虺的时候,一位现场的记者朋友马上就给他发了条信息,“原来‘蟠虺’就是‘醒龙’的意思嘛”。“我一下子就很有感怀,我的名字和我的书的名字,竟然时空交错一样,通过宿命这双无形的手交织起来,当时我就会心一笑。”刘醒龙说,“一部至关重要的作品的出现,一定不是无缘无故的,它的出现会让你觉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记者: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让人看了之后“念念不忘”,很有阅读欲。其实在欧美的小说写作中也非常讲究所谓“黄金第一句”,比如《洛丽塔》《百年孤独》《双城记》等的开头如今都是经典,你是不是也有这个“野心”?
刘醒龙:野心倒不至于,但《蟠虺》的这个开头确实曾经让我纠结了很长时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很平常的话,接下来就不常见了——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是小说的灵魂,写这一句话时,在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下社会太多俊杰们识时务的实践,而少见圣贤者不识时务的标准。所以,这句话一写出来,我马上就找到了这本小说的基调与节奏感,对这个小说充满了信心。
另外我也认为,一个心智健全的读者,包括我们自己读书,总想从书里找到某种值得我们敬仰的、留恋的、讲给后代听的东西,甚至是把它变成某种家教,在自己的血脉当中往下传承的东西——我觉得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可以承载这些。
记者:不止是第一句,这本小说被宣传为中国版的《达·芬奇密码》,的确在结构上也设计得很精彩,悬念迭出,写这样的小说有提纲么?
刘醒龙:我写小说从来不要提纲,比如我的100万字的那部小说,也没有提纲。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状态和最可靠的设计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产生的。实际上像《蟠虺》这个小说,好多细节,都是在写作的过程中,神来之笔也好,上天的恩赐也好,都是在写作的时候突然冒出来的。比如夜里11点要下电脑突然冒出东西来,电脑关不成了,赶紧写完了。还有睡觉的时候,突然想起来的东西,赶紧写一下,不然明天忘了。我比较喜欢自在一些,我如果什么都想好了去做,确实不会累,但有点直奔主题的感觉。写作过程突然冒出来的一些东西,是非常美妙的一种享受。感觉我还可以,奇思妙想还可以,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记者:说得那么轻松,可我听说你写小说的时候可是闭关到朋友们都联系不上你啊。
刘醒龙:对,所以他们说我笨说我矫情还说我装,哈哈。我人可能不太笨,但是用了一个笨办法——黄冈人都有一个毛病,就一根筋。我去年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手机关一个星期,从星期一开始一直到星期六、星期天,中途就不打开。那是非常没有办法,因为手机只要一开,短信就来了,现在高科技都有“接受回执”什么的,对方就知道你收到了。收到你不回人家,那还活不活在朋友圈里啊?要被骂死了——特别是2011年拿了茅盾文学奖之后,朋友找你的时候特别热情,你真不理人家,人家肯定要有想法了。
记者:说到茅盾文学奖,最近话题很盛呢,你也谈一谈吧。
刘醒龙:别人的事儿我就不说了,说说我自己的感想——其实这话我当初得奖时就说过了——对我来说,写作就是过日子,得奖就是过年;没年过的时候日子也得一天天好好过下去,但有了年过,这日子就过得更加开心有滋味了。
记者:之前魏总编说,你的这部小说打破了“文学大奖得主5年内无法写出力作”的魔咒,非常难得,有没有趁势计划下一步作品?
刘醒龙:下一部肯定也是个长篇。按照我的想法肯定要写35万字以上。但是魏总编对我说一定不能超过30万字,超过就不好卖——但是实际上我还是超了。好卖不好卖,实话说我在写作的时候是不会考虑的,包括所谓“读者是上帝”,那些都是对资本而言,是对出版社而言的。如果写作者真的把读者当上帝,写作是完蛋的——好的读者确实是上帝,但有些很糟糕的读者,分明是魔头,你却把他当上帝,是不是自取其辱?一味讨好别人的写作,就像一味阿谀奉承的人。我们可以不信任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信任内心。我们的写作不是为别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内心,只有这种写作才是最可靠的,才有可能成为经典。连对自己都说假话的作品,绝对是垃圾。
记者:刚才进门就听见你在谈书法,好像很多作家都对书法很有研究,你也是?
刘醒龙:我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写毛笔字的。但写书法时我发现,现在很多书法家的作品只有法,没有书,把写字纯粹当做笔墨纸的技巧——那么只要将“厚德载物,天道酬勤”八个字照着字帖写上千万遍,一般人都能写得像模像样了。然而在我看来,写书法绝不是个技术,我把苏轼和王羲之的字帖摆在面前,怎么看还是喜欢苏轼的。如果一个字一个字比较,王羲之的每一个字都比苏轼写得好。但是,苏轼的《赤壁赋》文气逼人,任谁也挡不住——那里面有种旷世才情在感染人!所以在我这里文学和书法是相通的,书法是一个书家的气节,文学是一个时代的气节。
记者:最后聊聊上海吧——既然我们在这里相见。
刘醒龙:上海在我童年时是那种梦想中的城市,距离遥远,却也是后来与我的文学生涯产生最多联系的城市。我写作时间不算短,1984年处女作发表,1993年就在当年第四期《上海文学》头条发了一个中篇小说。那个时候因为《上海文学》在全国的文学界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我作为一个作家从区域性走向广泛性的标志就是从《上海文学》和上海开始的。
十年之后,我和好朋友魏心宏在安徽亳州见了面,聊起来,他约我写下一部长篇,就又给了他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是这部《蟠虺》。当我写《蟠虺》的时候,我感觉心理成熟了很多,尽管这个小说比我前面那部小说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但是整个书的出版已经很顺利了。所以作为刘醒龙这么一个作家,我的成熟期和上海是密切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