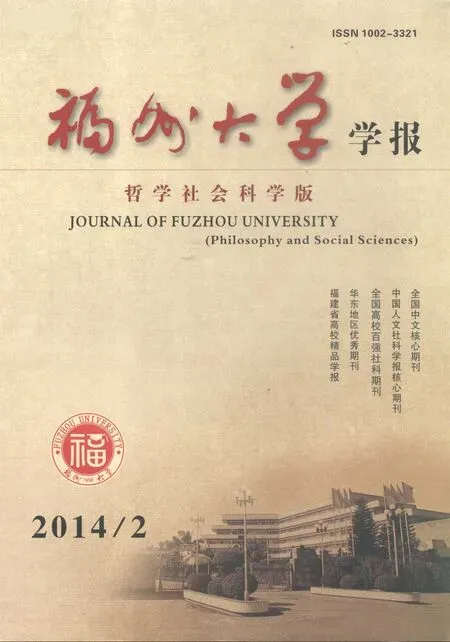文学翻译的英文句简汉文句繁现象
2014-04-18丁志聪
丁志聪
(泉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引言
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该诗常见有以下三种英译文:(1)Before my bed I see a silvery light,I think the ground is covered with hoar frost.Raising my head,I find the full moon bright.And bowing down,in thoughts of home I’m host.(2)Abed,I see a silver light.I wonder if I’s frost aground.Looking up,I find the moon bright.Bowing,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3)Moonlight before my bed.Could it be frost instead?Head up,I watch the moon.Head down,I think of home.无论是哪种译文,相比之下都显汉文句简英文句繁。因此人们常常说文学翻译“汉简英繁”。其实文学作品也不乏英文句简汉文句繁的例子。笔者以为,英文句简汉文句繁是由文学特质所决定的。一般说来,文学文本(尤其小说)的文学特质有六:
一、迁移性冗余在源语信息中的被压缩与被解压
文本解读的前提是透过语言迷雾把握作家的生命创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每一个文本都是作家用独特情感营构的语言艺术大厦。一个文本所传递的信息总是由诸多信息单元组成,从信息论的角度看,为保证主信道畅通,有时要对源语信息进行压缩,避免迁移性冗余在源语信息中出现。为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能顺利理解原文作者的真正含义,有时则要对源语中被压缩的信息进行解压,解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英文句简汉文句繁现象。[1]
如:Jane Austen:Pride and Prejudice有句:Unfeeling,selfish girl!好一个没心没肺、自私自利的小丫头!
又如 100 World’s Great Letters有句:It lies between you and Katherine,nowhere else.这是你和凯瑟琳之间的事,别人拿不了主意。
为确保主信道畅通,上述二句源语信息分别被压缩成Unfeeling,nowhere else,这完全是为了避免迁移性的冗余。为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能顺利理解原文作者的真正含义,源语信息分别被解压成“好一个没心没肺”,“别人拿不了主意”。解压过程完全可能出现英文句简汉文句繁的现象。这是一种不完全性压缩和解压的关系。完全性压缩和解压见于完整句子,典型例子有:
Charles Dickens:Old Curiosity Shop有句:All happiness had an end.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Bernard Shaw:Saint Joan有句:Dressing up don’t fill empty noddle.打扮尽管打扮,笨蛋还是笨蛋。
二、潜势系统功能的发挥与原作美学效果的再现
文学语言是假定的、蕴藉的、不确定的,充满了空白点和可能性,才能激活读者的想象力和审美创造,获得阅读的互动、快乐和共鸣。不同于单义的透明的科学语言,文学的语言是多义的、不透明的,容易被激活。要使译文读者产生类似于原文读者的审美感受,“对于艺术性较高、语言抗阻性较强和文化负载高的文学文本,应尽量减少语义冗余度,尽可能发挥意义的潜势系统功能,侧重再现原作的美学效果”[2],于是英译汉时原文句简译文句繁现象出现了。如:
100 Myths of Greece and Rome有句:Procne was chattering unintelligibly.普洛克涅正在唠叨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语。
Charles Dickens:David Copperfield有句:I detest this mongrel time,neither day nor night.我恨死了这种不阴不阳、朦胧暧昧的时候啦,昼也不是,夜也不是。
John Steinbeck: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有句:The quick jump never fails to startle me.像这样突如其来地转变话题,老是弄得我不知所措。
对于艺术性显著、语言抗阻性较强和文化负载较高的,如 unintelligibly,mongrel,jump等词组成的文学文本,再现原作的美学效果必须尽可能发挥意义的潜势系统功能。意义的潜势系统功能的发挥,才能使读者想象力和审美创造被充分激活,充分激活的结果完全可能是英文句简汉文句繁。又如:
Jack London:The Iron Heel有句:In short,a sudden colossal,stunning blow was to be struck.一句话,我们志在来一下迅雷不及掩耳的全面打击,把对方打得不省人事。
三、运用独特的审美“三力”去把握作家的价值取向
文本解读必须透过迷人的语言表层,运用独特的审美想象力、理解力和创造力去把握作家的价值取向。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应忠实于原作,即准确理解原作的真正意思,把握其精神、体会其特色,领悟言外之意,发掘深层结构,以求最大限度再现原作的“意境”。[3]文本主受纳,读者主运化。文本为作家耕耘之仓库。作者试图传达给读者以什么“意境”,读者能否达到原作的“意境”,从忠于原作到再现原作的“意境”,这一以文本为媒介受纳运化的文本解读过程中,产生英文句简汉文句繁现象。如:
Graham Greene:The Heart of the Matter有句:The absurdity of the phrase took Scobie off his guard.斯考比怔住了,他没有想到对方居然说出这样荒谬的话。
Jack London:Martin Eden有句:Back came a cool letter from the editor that at least elicited Martin’s admiration.编辑回了一封冷冰冰的信,马丁看了,不禁佩服对方真有一手。
Harriet Beecher Stowe:Uncle Tom’s Cabin有句:The man said that he was going to break him in,once for all.那个人说,他得狠狠治一治他,叫他以后再也不敢这样了。
Agatha Christie:Death on the Nile有句:Signor Richetti had insisted on making an excursion of his own to a remote spot called Semna.Everything had been done to discourage this example of individuality,but with no avail.里克蒂先生坚持要独个儿到一个偏僻遥远的叫赛姆纳的地方去游玩,为了不使他一个人单独行动以免他人跟着效仿,各种方法都用尽了,但毫无结果。
四、日常语言转化为艺术语言,再现文学美学价值
语词是文学的唯一表达手段,因此文学形象的建构首先要寻找最贴切最具有个性化的语词符号来物化蕴涵着写作者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构思。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不同,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准确、鲜明、简练的,更注重形象生动、具体可感、充满个性和情感特征,甚至为了情感表达的需要,语斟词酌地将日常语言转化为艺术语言。翻译过程中,是积极的消解还是保留原作的“文学性”,二者通常令译者难以抉择。在此情形下,译者应在敏锐识别作者语言意识和原作意图的同时,融入自己的“审美阅读”和“文学性”语言,凭借丰富的审美想象,运用创造性的语言,最大限度再现蕴含其中的文学美学价值,实现日常语言向艺术语言的完美转化。[4]如:
Walter Scott:Woodstock of the Cavalier有句:An amour was with him a matter of amusement.在他看来,一件风流韵事只不过是一种消遣。
Saul Bellow:Herzog有句:God’s veil over things makes them all riddles.上帝的纱缦覆盖着万物,使它们变得扑朔迷离。
Olive Goldsmith:The Vicar of Wakefield有句:Poor Deborah,instead of reasoning better,talked louder and was quite outdone.可怜的黛博拉并不想以理服人,只想用声势取胜,只落个理屈词穷。
George Eliot:Adam Bede有句:He outshone them as the planet Jupiter outshines the Milky Way.他们在他面前相形见绌,正如银河在木星前黯然失色一样。
要是将amour用日常语言“偷情”来表达,显然达不到文学性效果,若将日常语言转为艺术语言“风流韵事”,文学效果不言而喻。riddles,outdone,outshine用文学语言“扑朔迷离”,“理屈词穷”,“相形见绌”或“黯然失色”比日常语言“谜语”,“战胜”,“胜过”更加形象生动、具体可感、充满个性和情感特征,日常语言向艺术语言的转换完全可能出现英文句简汉文句繁的现象。
五、变形和“陌生化”使文艺新颖别致、避陈去俗、翻新出奇
文学语言,就是一种情感化的语言,它是最忌讳没有个性的日常语言的。要使人们感受艺术的新颖别致,体验着文艺的避陈去俗、翻新出奇的创造过程,就必须对其进行变形和“陌生化”处理。这意味着要避免将文本归化成译入语读者所熟知或显而易见的内容,而是将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作适当的保留即异域化,将陌生化的手段保留或将源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与平行文本的诗学特征杂合即杂合化,使主体和受众之间不断有新的发现。[5]也是一个使本来已经熟悉到丧失感觉的词语突然发出陌生的光彩,让读者尽可能延长和强化审美感知的过程,重新去审视和解读原来的事物,在接受过程中感受到文学形象的新颖别致,得到审美的愉悦。如:
Irwin Shaw:The Young Lions有句:Her German was halting.她的德语很不到家。
如果说“她德语讲得结结巴巴”,这显然是文学语言所忌讳的,因为它毫无个性。要使“结结巴巴”这个人们已经熟悉到丧失感觉的词语焕发出陌生的光彩,取而代之的是“很不到家”。
Ernest Hemingway:A Farewell to Arms有句:The leave started Oct 4th.Three weeks was 21 days.That made Oct 25th.假期从十月四日开始,共三个星期,二十一天,这就到了十月廿五日。
同理,表达 make用没有个性的日常语言“等于”,比用陌生化的“就到了”逊色。
Irving Wallace:The Miracle有句:Mrs.Moore is quite a lady.摩尔太太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女人。
Saul Bellow:Herzog有句:The new legislation is highly discriminatory.新的方案有许多地方厚此薄彼。
用日常语言“出众的”和“不公平”表达quite和discriminatory,没有个性。对其变形处理后即成了“不可多得的”和“厚此薄彼”。经过变形和“陌生化”处理后,明显出现英文句简汉文句繁现象。
六、通过细读法最终达到读者与作家的心灵沟通
文学作品的复杂含意远远超过它的字面意思,它是隐蔽的,深藏于作品的有机结构之中,因此必须采用细读法对作品进行仔细推敲分析,从语言和结构中寻找意思的痕迹和线索。“细读法”激发读者去关注和理解的积极性,在努力理解的这一过程本身就带给读者无穷的审美魅力。迷人而精炼的语言在启人思绪的同时,也给读者以更广阔的联想空间,在读者探寻作者深层含义的过程中,“细读”作品的语言和结构要素,分析解读文本主题,最终达到和作家的心灵沟通。[6]如此一来,也会造成英文句简汉文句繁的现象。如:
Richard Wright:Native Son有句:A bed spring creaked.弹簧床叽叽嘎嘎一阵作响。
Reader’s Digest:Bilingual Selections有句:I had the usual high-school and college ups and downs.我在中学大学读书,像一般人一样,有得意的事,也有失意的事。
creak“叽嘎”,up and down“上下”是它们的词典义,通过细读法对作品仔细推敲,它们深藏于作品的有机结构之中涵义分别是“叽叽嘎嘎一阵作响”,“有得意的事,也有失意的事”。细读法也完全可能出现英文句简汉文句繁的现象。
Edward Dolnick:Why Women Live Longer than Men有句:He had had his girls,and his familiar places where were lights and delightful songs,and dancing betimes.他也玩过女人,有过他经常光临的去所,那儿酒绿灯红,不时能听到悦耳的音乐,看到蹁跹的舞蹈。
Katherine Anne Porter:Noon Wine有句:Arthur and Herbert,grubby from thatched head to toes,from skin to shirt,came stamping in yelling for supper.阿瑟和赫伯特这两个小鬼,从乱蓬蓬的头发直到脚跟,身上也好,衣服上也好,无处不是烂泥,他们踩着重重的脚步走进屋来,嚷着要吃晚饭。
dancing和 grubby词典义分别为“舞蹈”和“邋遢的”,从语言和结构中寻找意思的痕迹和线索,读者不难联想到实际义“蹁跹的舞蹈”和“无处不是烂泥”。
七、结语
本文结合经典名著英译汉译文,通过运用文本解读方法,分别从读者与作家两个不同角度,剖析英译汉时英文句简汉文句繁现象的成因。文本解读的价值在于实现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作家与读者相表里,开窍于文本。对读者来说,这是一个透过语言迷雾把握作家的生命创造,更进一步透过语言表层,把握作家的价值取向,达到和作家的心灵沟通的过程。对作家来说,为了实现情感表达的目的,需要将日常语言转化为艺术语言,需要对语言进行变形和“陌生化”处理。当然,文学作品的复杂深沉的含意,激发读者运用细读法对作品进行仔细推敲研究,这一调动读者积极性的过程正凸显文本解读的无穷魅力。
注释:
[1]盛俐:《汉译英过程中信息的压缩与解压》,《绥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肖娴:《从符号美学看语义冗余和等效原则的悖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朱三毛:《“意境”难求——《夜雨寄北》英译之对比分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潘莹、熊丽君:《文学视域中的歧义与翻译策略》,《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5]陈琳、张春柏:《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性》,《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6]彭书雄:《“文本细读”与中国古典诗歌解读方法研究》,《语文学刊》(高教版)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