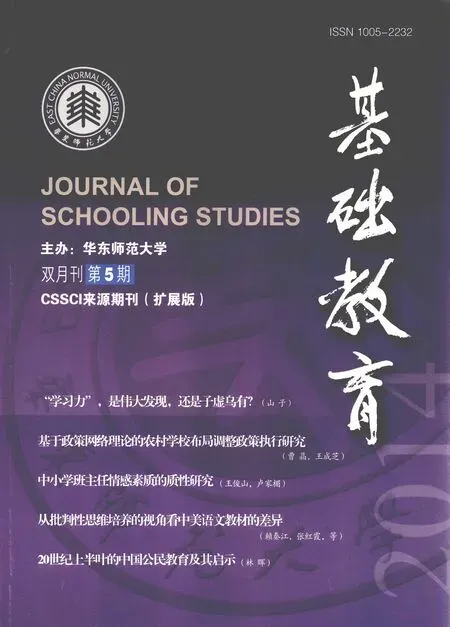教学的道德尺度失衡:病理性德育的归因追寻
2014-04-17毛红芳
毛红芳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教学的道德尺度失衡:病理性德育的归因追寻
毛红芳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病理性德育在归因争论上呈现出责任泛化的尴尬现实,对病理本体之教育进行原点审视,有助于打破这种尴尬找到症结所在。人们在过分强调知识传承的同时,往往将教学缩水为纯粹的知识和技能的教与学,遗忘了教学本身所承载的道德承诺——善和美的教学。回归教学的道德使命是善的必然诉求,维护个体的主体性、相互付出努力和回归本真是教学道德性得到确证的前提和基础。
病理性;德育;教学;道德性
道德伦理难题及学校德育困境历来是备受关注和持续论证的热点话题。无论是现实舆论还是理论逻辑,往往在讨论道德伦理难题的同时,把矛头指向学校德育的低效或无效。这种低效或无效最一致的结果呈现就是“学生知道应该怎么做,却仍然不这样做”的矛盾。学校德育似乎变成了“一种存储行为,学生是保管人,教师是储户”[1],学生只会机械地接受、输入并存储道德知识,而无法有道德情感体验和道德行为体现。事实上,道德要教,更要育。教只能教人以知识及其应用方式,却不能教人情感,因为,人的情感需要经过体验形成的。从影响程度来说,道德首先是情感,然后才是知识和能力。然而,情感态度本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使德育实践多停留在道德知识的教学,这种“知性德育”或德育“智育化”对于学生来说,也多像是一个道德知识的保管者。这样的德育两难和现实境遇不得不使人思考以下问题:专门设立的德育课程是否能包揽道德教育的使命,德育与普遍意义的教学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德育在教学过程中独立,还是教学脱离了德育,抑或是我们从根本上已经遗忘了教学的基础、责任与属性。
一、病理性德育及归因争议
(一)病理性德育
“病理”是指“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和原理”。[2]也就是疾病发生的原因、发病原理和疾病过程中发生的结构、功能和代谢等方面的改变及其规律。目前,这一概念已经走出医学领域,被社会和教育领域所接受、借鉴并予以自省。所谓教育病理是指“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偏移和失调状态,是教育内部和外部的异常条件使教育功能的实现受到严重阻碍,使教育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发生异常变化的过程”。[3]它在一些情况下与教育疾病、病理性教育、病态的教育行为等意思基本一致。病理性德育或德育疾病是教育病理的内容之一,其病理性表现为德育任务模糊化、德育的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相距太远、德育实效性低、德育的情感态度障碍、德育功利化倾向明显、学生道德缺失现象严重、德育的控制性说服处理以及网络德育的潜病理等等。例如,德育异化为分数的教育,用分数来考查学生的道德水平;教师在说服学生尊重他人的同时,却频频体罚学生;再如一个小学生描写五星红旗耷拉在旗杆上被斥责为不爱国的表现等,这些事例都是病理化的具体症状表现。
(二)病理性德育的归因争议
探讨“病理”,就需要明确疾病的发生原因及其发展的过程、机制和原理。对于病理性德育的疾病归因有诸多争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1)德育课程虚设,学科教育渗透空泛。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长期以来,学校和教师习惯性地认为德育是一项专门课程或活动,认为通过德育课程化、活动化和长效化就可以达成德育目标,认为这些课程或活动担负着学生道德的培养的使命。由于德育课程“单打独斗”及“育人”的复杂性,最终使德育的情感态度被自觉不自觉地回避、忽视或病理性控制。另一方面,尽管人们普遍认同学科教学要渗透德育,但这种渗透往往被误解为德育作为外在附加因素的“渗透”,或将德育因素的存在仅仅局限在教学内容上,把教学内容看作是德育渗透的依据,把“添材加料”看作是德育渗透的途径。(2)知性德育模式仍是主流。这种模式主张德育“智力化”,德育被看作是施加规范、制度及道德影响的过程。德育的目标和任务被模糊处理为让学生在某些观点、某些概念上具备知识,而他们首先需要拥有某种情感态度和立场信仰往往被忽视了。德育的过程重在强调无坚实认知基础的理论灌输,过多运用病理性说服教育。[4](3)德育“外铄取向”与“个体取向”的转型与冲突。由于我国在社会转型期同时经历着“从强调社会秩序的传统伦理观到强调个人自由的现代道德观的变迁”[5]。变迁过程中,德育外在价值和本体价值的两种取向在争论中开始彼此分离,出现过分强调外在的社会公众价值,忽视育人的本体价值,使得德育的价值取向和本质特征越来越模糊。(4)外在多种因素的影响。德育病理化主要受社会伦理层面尤其是社会道德危机、价值判断缺位、教育者及学生自身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复杂性和难控性导致德育的实效性不高。(5)功利主义教育的陷阱。在社会泛起唯经济主义、唯科学主义等浪潮,学校教育丧失了它应有的批判和反思功能,反而在相与同流、推波助澜中,与社会其他方面共同酿成了当前的道德危机。[6](6)道德教育理解偏差。现实中,人们把“培养人、处理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善恶好坏的行为规范”的道德教育完全等同为“培养现实公民的活动”的公民教育。如此,道德教育演变为一系列“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的公民教育。实际上,尽管二者在包含内容上有交叉,但教育重点却不能相互混用或套用。[7]
综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必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从上述德育病理归因的梳理来看,无论是价值层面、社会层面、伦理层面还是教育自身的原因,已经流露出了病理性德育责任泛化的尴尬现实。社会对学校德育的质问、学校对社会道德危机的无奈,使得道德教育默认了“既必要却又不可能”的境遇。反观病理性德育的形成,尽管我们不能机械地将“病理”归因为某一层面的影响,也不能简单地将“病理”泛化到任何“患病”的可能性,但对道德教育疾病机理的研究还需要从剖析本体入手。
二、教学的属性与责任
如前所述,当德育被作为专门活动或课程来探讨的时候,教学与德育之间就开始越来越疏离,教学缩水为强调“技术和策略”的实践活动,德育在管教分离的体制下背负着“育人”和“育德”的使命。当这样的“细化”分工被认为是“应然”取向时,教学的“去道德化”现象也就越来越凸显,教学全过程及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所承载的道德承诺也越来越被遗忘。
(一)重申教育与教学的内涵
在审思病理教育本体的同时,有必要重申教育既然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所必然包含的两层含义:一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致力于人的完善,其根本价值在于增进人的幸福;二是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指向于人的生存和生活实践,而不是运用原理、规则生产某种对象的过程。那么,教学作为实现教育的最基本途径,理应有教育的全部内涵。教学的对象是人,指向人的整体生成,致力于人的智力与道德等多方面的完善。
尽管人们对教学具有道德性早有认识,比如赫尔巴特的“教育性教学”原则已经被普遍认可,但实际上这种认可仅仅停留在教学伴随功能的认知层面,并没有建立在对“教学”全部内涵认识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将“教育性”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这是因为我国的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相对更关注“如何教”,而忽视“教养”的传统。这里的“教养”既是一种状态或目的,也是一种过程和手段。作为目的的教养,主要是指人的整体性和自主思考的达成。作为过程的教养,是指通过与文化和世界的交往,实现完整人格培养的过程。[8]换言之,“教养”的本真价值在于教学本身具有道德性,即是善和美的教学。相反,现实中教学的成功与否往往指向认知层面,忽视、遗忘了教学本身所承载的道德承诺。这种遗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将学科教学与德育课程相互分离,将教学缩水为纯粹的知识与技能的教与学。这既是教学的异化,也是德育的异化。
教学是动态变化的实践活动,不是静态不变的文本。教学过程并不是线性的预设目的和结果的统一,教学目的和内容的道德性未必能保证过程和结果的道德性,同样也不能保证教学行为和手段的道德性。课堂教学中,不乏有这样的事例存在:教师采取条件反射的方式(诸如教师时不时喊出“一二三”,学生要回应“闭上嘴”)来控制纪律以表示课堂教学过程中对教师的尊重;教师在批判强制灌输的同时,也在强调答案统一,而这种强制着理解统一的做法实质上是对精神思想自由的一种背叛。
(二)教学专业化之道德特殊性
如果说学校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教会学生知识和技能,那么在这个层面上,学校是可替代的,因为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化社会,能够完成传授知识任务的机构和设备非常之多。所以,近年来,“学校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已逐渐成为焦点问题。进而,人们在教师专业化和教学专业化论证过程中,力求说明学校的必要性及教师的职业属性,寻求专业的特殊性以认同其不可替代性。在“教学专业化”文献资料中,相关的论述大多都旨在说明教学所需要的专门化的知识和技能基础,以及教师获取这些知识和技能的途径,或是讨论教学能否实现专业化发展之路。对于教学的道德本质、教学工作的道德属性的论述很少。这里,我们要明确的是,专业知识和技能基础的扩大,的确让现代学校教育中的教师可以熟练地进行教学。但是,具备专业知识是由于现代学校教育的复杂程度加深,而不是为了对教学的内涵进行根本性地修正,因此它并没有改变教学的终极诉求。
试想抛开教学工作的道德属性,教师的职业属性该如何界定?这就如同医疗和法律行业,如果剥离了道德责任,其价值和用途将难以确定。同样地,教学需要知识和技能基础,但如果教学脱离了其根本的道德目标就会陷入“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需要说明的是,学校教学区别于医疗和法律行业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相互付出努力。如果学校教学以医疗行业和法律行业的成功转型为榜样,那么教学将会具有知识神秘化、保持社会距离的特点。因为这种专业化会加大教师与学生的距离,会对学生隐瞒所需的知识,会让学生成为技术性教学的接收器。[9]相反,教学之所以具有特殊性,正是因为师生在相互付出努力的过程中蕴含着道德承诺。
(三)教学是一种道德活动
美国教育学者内尔·诺丁斯指出:“道德教育不仅是指任何一种旨在培养一种有道德的人的特殊教育形式,它也可以指任何一种在目的、政策和方法上合乎道德的教育形式。”[10]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性地将道德教育与特殊和特定的活动形式绑定,忽视了任何教育形式都可以成为德育实施的一种活动形式。在德育实施的多种形式中,教学应是最基本的形式。此外,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那么作为一种人为的及为人的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体间教学,教学的确是一种具有高度道德责任感的事业,尽管我们也知道道德教育存在于普遍教学之中,然而现实教学实践也清楚地显示出教学的道德尺度总是被忽视,抑或是被遗忘。[11]可以肯定的是,教学之所以成为一种道德活动正是因为它是要为其他人负责的人类活动。它经常要面对诸如什么是公平、权力、正义和美德等问题。教师的行为随时随地都是关乎道德的表现。仅从这个原因出发,就可以说教学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活动。所以说,常见的把教学定义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把教学过程看作是特殊的认识过程,这种界定本身就是对教学的误解和误读,掩盖了教学的道德本质。
所谓“师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12],每一个师既是道德行为者,又是道德传授者。教师以身作则的行为表现对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行为更能有效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那些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教师,往往是源于他们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的影响,而不是通过灌输和说教的影响。教师这种通过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所产生的作用普遍存在于任何教学中,存在于教学的方方面面,且具有不可替代性和责任意识。现实中过度关注教学的知识尺度,而忽视教学的道德尺度,也是在某种意义上忽视了教学高尚内涵的根本所在。
三、教学道德尺度的失衡现实
我国学校教育有“德育首位”论的传统。将道德教学看得很重,思想品德课、政治课、班级班会活动等都被看作是道德教学的重要途径。遗憾的是,高涨的德育热情和众多的道德教学实践,未能收到应有的道德效果。这是因为人们长期对道德教育理解的偏差,将德育“公民教育化”,看作是外在附加因素,同时陷入德育只能通过专门课程或专项活动等途径来完成的固着模式,使得人们已经遗忘了普通教学的普遍属性和责任——教学道德性的普遍存在,忽略了教学才是德育长效化和真正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主阵地。当然,这里并不是在强调非此即彼,只是要再现教学道德尺度的失衡现实。
(一)教学:迷失了情感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性地将教学实践的属性限定在知识和信息的传递,就连“专修”式的德育课程教学也多是进行道德知识的传授。至于学生心理、情感和态度在课堂上是否会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教师的教学行为及知识传递过程是否渗透了道德性往往是被忽视的。与此同时,我们普遍认可一个教师、一门课程或是一个学校对一个学生所产生的重要人生影响。例如,学生会崇拜自己所喜爱的教师,那么,学生记住的是他们所讲授的具体知识,还是被教师对教学的钻研和坚持不懈、对学生全心全意的关爱或是某种精神所感染。不得不承认,这种感染和影响往往不是通过“专修”的德育所产生的,而是在日常教学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的。通常来说,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关键和重点在于其行为与心理变化,而要想让学生保持这种持久、牢固的变化,就必然是学生自觉自愿所发生的变化,否则,当个人的主体性和情感体验不得不屈服于课堂中的权威、规范等“物”的因素时,课堂教学也就流失了心灵的吸引和感召的魅力。当学生的变化被强迫时,它就是非道德的,也是难以持久的。即使是在“专修”的德育课程中,以病理性说服来进行教育也是违背道德规律的。正如柯尔伯格所指出的,“这既不算道德的教育,也不符合教育的道德”。
(二)教学:忽视了主体
反观学生主体地位在教学实践中的表现,主要集中在强调师生平等交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等方面。师生间的伦理关系往往被工作关系或规范规则所代替或淹没。学生必须遵从教师的权威,质疑和反驳经常被看作是不礼貌的行为,把分数与光荣或羞耻相等同,因分数和学习努力程度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的事例屡见不鲜。课堂教学中,很多学生都曾被拒绝回答“为什么”,他们往往被告知“只需要背记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识的情感成分被冷冰冰的抹去,代替的只是机械的信息和思维逻辑的训练。控制性的说服常常被认为是教师权威的体现和运用,教学目的已经从理论上“为人”异化为实践中是否完成信息传递。如果信息被传递和掌握了就会认为是教学目的达成了,反之则不然。从本质上说,这种控制性的说服教学,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三)教学:疏离了生活
教学回归生活的话题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命题了,但统一的课程、标准化知识、客观化考试的复制俨然使教学从一种生活状态异化为标准化的生产过程。随着人们把学习的需要强化为谋生之道和功利性竞争生存的时候,制度化教育和专门化教学也就开始成为了思维、语言、知识、行动都模式化的训练活动,“其工具价值(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价值)逐步得到强化,道德教育也越来越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演变成封闭的制度体系。”[13]在这种体系中,反复灌输、强化作业、外在奖惩成了教学最有效的手段。柯尔伯格指出:灌输既不是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道德的教授方法。[14]只强调理性知识,而忽视真实情感体验过程,就会使教学与生活的“真实”和“意义”越来越疏离,教学的神圣感和信任感就会受到怀疑。也正是因为教学对生活的这种疏离,学生对生活的体验匮乏,才存在作文中大量的编造、抄袭、雷同和虚假的现状。因为,知识和技能可以与生活相隔离集中学习,道德却不能与社会生活隔离开来。教师在教学生活中的情感疏离、对儿童生活的疏离,简单地将教学与智育等同、将德性发展与智性发展等同,违背了伦理的、道德的逻辑构建原则,使得教学的“去道德化”状态愈演愈烈。所以,将教学缩水为纯粹知识和技能传授,就是教学异化的表现。从教育教学本身的品性来看,道德性是其天然的内在品性要求,如果将这一成分从教学中剔除,教学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
四、回归教学的道德使命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对于教学而言,这种善的目的就是教学的最高品格和终极诉求。因此,判断教学“有效性”,不应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策略、方法等技术层面,而应从更深层的教学道德性的问题出发,即教学本身所承载的道德承诺。
(一)维护主体性
教育领域中,人们似乎已经习惯将师生称作为主体而不是教师身份和学生身份来讨论。而实际教学中,“主体”却又往往被理解为身份的固化与互换。例如,学生被理解为只能是“学生”,抑或被理解为可以在一定情境中承担教师的角色。这里,有必要先对主体和身份的内涵进行厘清。对于师生来说,一方面他们都有各自身份的自我“本质”,另一方面,这种身份又是可塑的且形式多变。这就说明了身份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随时可以被更改的。那么,“主体”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我们在强调主体的同时,往往也会强调权力。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认为,权力不只是一个消极的控制机制,而且也是自我的生产。“权力赋予主体以个性”。那么,何为主体性,在福柯看来:“主体性是话语产物。也就是说,话语(作为说话/实践的规定方式)建立了说话者的主体位置”。“主体的地位是通过某种观点或规定的话语意义,使话语产生意义”。[15]主体性内含了师生如何成为主体以及他们如何体验自己。
课堂教学中,如果我们把师生身份固化或物化,就会使教师只能是“教师”,学生只能是“学生”,也就很难突破传统“教师教、学生学”的课堂文化定势,也就会使师生身份和主体变成“规训”的产物,使主体也就更像是“产品”。在这个层面上,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及主体性更多的像是在身份的固化表层所涂抹的色彩,而不是基于权力和话语的自我“生产者”。那么,要改变这种定势,就需要我们从主体存在的前提、主体的本真意义来关注师生,从身份的可塑性和多元性来审思师生身份,从身份与主体性的转变特征来关注师生作为主体的形成方式,即师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把握是避免单纯追随教师权威和口头宣扬“主体性”的前提,是注重师生个体精神自由、推进主体自主与主体间相互理解的基础,是理解和回归教学“道德性”的先决因素。
(二)相互付出努力
诚如前述,医疗行业、法律行业和学校教学最重要的区别是知识神秘化、保持社会距离和相互付出努力。相互付出努力蕴含并承载着教学的道德性,是教学作为一种道德活动的特征表现。如果师生之间只是简单服从于某种“应该”的规则,而忽视“善”和“正当”的前提,那么,彼此间再如何付出努力,也不过是控制性规范的表征。相互付出努力,关键在于“相互”,重点在于“用心”,表现为师生之间关怀和被关怀的关系,这是教学道德性得以发挥的前提。对于教师而言,教学是一项道德事业,教师不能将“教书育人”这个统一过程人为剥离开。因而,教师付出努力就不仅仅局限在建立和谐师生关系上,更体现在教学的方方面面。因为,教学的道德性往往“隐匿”于教学组织、教学氛围、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行为及师生交往等教学的各个方面,教师在其中对人的情感投入、对物的处理态度和方式都在潜移默化地感染、影响着学生。对于学生而言,教学活动不是教师单方面的行为,而是师生共同的活动。学生付出努力也不仅仅是完成作业,而是要对教师所付出的各种努力做出尊重和信任的回应,在互动交流与相互努力的过程中,彼此真诚地沟通、关怀和理解。这个过程是人性关怀和学生道德成长的过程,是“育人”和“育德”的过程,也是我们把促进人的发展界定为教学的最高目标的达成过程,因为促进人的发展的教学的过程本身也是德育的过程。
(三)回归本真
道德最根本的一个因素就是真实。剥离了这一因素的教学本身就不能称为是道德的。教学“真”与其“善”的品格是相统一的。其中,“真”是起点、前提,“善”是终点、目标。从教学的“真”走向教学的“善”的过程则是教学的“美”。如此,教学的道德性也就蕴含了三者的统一,体现了增进人幸福的本真价值。
回归本真的教学,并不是在否定教学真实性的存在,也不是否定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知识和技能真实性的存在,而是强调教学的道德性要贴近生活的“真实性”。因为促进人的发展,不是仅仅通过特殊的认识活动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将教学还原为特殊而真实的生活过程,让学生作为完整的人参与其中。这也是为什么多年来教育领域所倡导和呼吁的教学回归生活,让课堂教学焕发生命活力的宗旨所在。此外,人的存在与增进人的幸福是内在统一的,如果教学所追寻的道德目的和理想的幸福不能在生活中践行,就不是“真”的教学。例如,那些要求学生写下环境保护倡议书寄给市长,最后又不了了之就是“伪真”教学的表现。因此,回归本真的教学有助于教学道德性找到美和善的落脚点,体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推动人的德性实现内在人格形式和外在行为确证的自我同一。当然,教学回归本真,并不是主张教学要回归生活的自然状态,而是对教学本身具有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重申。
[1]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顾建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5.
[2]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9.
[3]石鸥.教学病理学基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9.
[4]石鸥.教育困惑中的理性追求[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8-32.
[5]郑富兴.责任与对话——学校道德教育的现代性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3.
[6]鲁洁.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55.
[7]张笑涛.为“道德教育、公民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正名[J].现代教育管理,2012(9):88-93.
[8]王飞,丁邦平.苏联教学论与美国课程论:在中国的误读与误解[J].比较教育研究,2013(1):47-51.
[9]古德莱德,索德,斯罗特尼克.提升教师的教育境界:教学的道德尺度[M].汪菊,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116-117.
[10]内尔·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M].于天龙, 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4.
[11]Huge.T.Sockett.Further Comment:Has Shulman Got the Strategy Right?[J]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1987,57(2):208-219.
[12]荀子·儒效.
[13]高德胜.知性德育及其超越——现代德育困境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26-127.
[14]谢登斌.德育新观念:将单向灌输转变为参与式道德实践[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31-35.
[15]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M].孔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19.
Imbalance in the Moral Dimension of Teaching : Attribution of Pathological Moral Education
MAO Hong-fang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nxi, 710062)
There is an embarrassing condition that the debates on attribution of pathological moral education move towards a general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It is helpful to break the embarrassment and find the crucial reason through inspecting the origin of pathological moral education. As teaching has been shrunk to transmission of pure knowledge and skills along with knowledge inheritance being overemphasized, the moral commitment has been forgotten that teaching itself conveys goodness and beauty. Accordingly reverting to the moral mission is an appeal of goodness. Ultimately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teaching morality lie on the maintenance of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mutual efforts and recurrence of true reality.
pathological; moral education; teaching; morality
G40-012.9
A
10.3969/j.issn.1005-2232.2014.05.010
(责任编辑:李家成,姚琳)
(责任校对:朱振环,姚琳)
2014-7-27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SGH13331);咸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12XSYK096)。
毛红芳,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咸阳师范学院讲师。E-mail: mhf200066@163.com